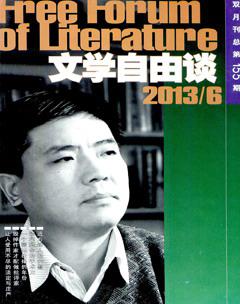大時代呼喚大國文學
傅書華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大時代。所謂大時代,有四層含義:
其一,中國社會結構正面臨著千古變革:鴉片戰爭之前的老中國,學界公認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這一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在經歷過了作何種選擇的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之后;在經歷過了以農耕經濟為主要經濟方式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終于形成的秦帝國及將這一社會結構其生機活力發展到頂峰的盛唐時代之后;在經歷過了新的商業經濟初步形成的北宋時代及一度中興的明代,但終于因為兩次異族入侵導致這商業經濟滯后于西方,導致農耕經濟山窮水盡之后;終于因為自身律動的需求,而以與西方沖突為表面征兆為契機,轟然崩潰,從而告別老中國,步入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西方社會結構作用于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途徑有三:一是資本經濟模式。在歷經洋務運動的技術革命、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五四”運動的思想革命之后,西方資本經濟終于于1920年代末在中國初具規模,但伴隨1920年代末全球性資本經濟危機的發生及自身內在矛盾內在危機的激化,資本經濟模式終于在1949年在中國大陸全面崩潰。二是以蘇俄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模式,這一模式在1930年代全球性的紅色革命中誕生,在1949年的中國大陸取得了全面勝利,之后在1980年代調整自身內在矛盾內在危機中,迎來了對這一模式的重新認知與實踐。三是日本影響。日本的社會結構深受中國盛唐影響,但在明治維新之后,脫亞入歐,形成一種東西方融合體,并從官方民間,從武力侵略的極端方式到政治交流等多種途徑影響中國。中日關系的微妙性、敏感性遠遠大于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關系,其因概出于這種歷史的近緣性。
在中西各種社會結構完成了各自對中國的影響之后,中國的社會結構可謂正面臨著千古性變革,所謂中國大陸目前的現代自由主義、威權主義、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等各種思潮之爭,正是在如何應對這種變革中而發生。
其二,中西方歷時性演化過程中所體現的價值形態精神形態在當今中國,以共時性平面性得以全面呈現。諸如,西方希臘神話中的欲望天性,中世紀神喻用天理對欲望的束縛,人文復興對神喻天理虛偽性的嘲諷及對世俗欲望的價值認可,古典主義對建立滿足人的欲望的社會規范的努力與想往,浪漫主義對個體感性生命的張揚,批判現實主義科學性實證性的對社會的批判,現代主義對認知人與外部世界雙重絕望后的孤獨感、絕望感、荒誕感,后現代主義放棄永恒追求的瞬間快樂,大眾文化消費性的精神快餐等等,無不在當下中國可以找到與其相對應的價值形態精神特征。諸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互補,天理人欲之辨,修齊治平的理想人格,魏晉風度,明代世風等等,單單一個對《論語》的多重解讀,也可見出其與當下中國的血脈相連。諸如民國時代的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等等,單單一個“民國范兒”也就足以讓我們看到其在當下的“在場性”存在。
其三,當下中國每個國人的個體生存方式存在形態、價值選擇都面臨著根本性結構性的動蕩。中西之爭,古今之爭,傳統現代之爭,國家個人之爭等等,都不再僅僅是發生在文化思想層面,政治變革層面,少數精英層面,而是切切實實地發生在每個國人的具體的生存方式存在形態價值選擇之中。這是為中國社會結構正面臨千古變革所決定。而每個國人在如何選擇個人生存方式價值取向中的各各不同,亦或各各困惑,也是當今中國重要的社會特征。然也正因此,構成了當今中國空前未有的社會變革精神演化的深度與廣度。
其四,由于東西方各種社會結構價值形態在當今中國的登場的豐富性,也構成了中國在應對過程中所發出的“中國聲音”在全球話語場中的“對話”分量與“對話”價值。
大時代呼喚大國文學。大國文學不是經濟大國的必然產物,而是一個時代全球性的前沿性的精神焦點都凝聚在某個國度并對此作了充分揭示的產物。在東西方曾相互疏隔的時代,大國文學曾經以地域性標高的形式出現,諸如人文復興時代的莎士比亞,工業革命時代的巴爾扎克,西方東漸過程中的俄國文學,作為中國傳統社會頂峰時代的精神標志的唐詩,作為中國從農耕經濟到商業經濟根本性社會轉型初期精神標志的宋詞等等。由于諸如此類的原因,文學大國正在呼喚著當今的中國文學。
當今的中國文學,或許應該從下面五個方面回應時代對中國文學大國文學的呼喚:
其一,寫出當今國人五光十色的豐富人生或者人生亂象:老板階層的崛起,白領階層的形成,知識分子的蛻變,官員的焦灼,平民百姓的甜酸苦辣,代際之間的文化沖突,底層群體的辛酸無奈,金錢的光芒與炫耀,肉體的覺醒與沉淪,人生無從選擇的困惑與迷茫,如此等等等等。不用觀察與體驗,這些通過各種社會事件、大路小道新聞、網絡媒體、甚至你的直接人生,幾乎無時無刻地就發生在你的面前,響在你的耳邊,刺激著你的神經。只是要寫出這其中的來龍去脈,歷史原由,現實成因,情感的深處,心靈的內在,生命的肌質,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但惟其如此,才能滋潤當下心靈溝通的荒蕪,滿足現在情感共鳴的迫切。
其二,雖然中國現當代文學曾經一度成為了演繹先驗理念的形象的社會歷史教科書,但這絕不能因此而遮蔽了文學概括、揭示社會形態演化、歷史變遷的功能。作為大國文學的中國文學,要通過對各種人生形態的描寫,讓讀者看到中國社會結構在千古變革時的時代風貌、歷史性過程,看到社會矛盾、沖突的錯綜復雜,給讀者以認識外部世界認識歷史的價值。
其三,如前所述,中西方歷時性演化過程中所體現的價值形態精神形態在當今中國,以共時性平面性得以全面呈現,諸如,政治說教的無力,欲望的張揚與泛濫,對理想社會道德人格的追求,對社會不公進行批判的呼喊,放棄精神只要養生的文化潮流等等等等。作為大國文學的中國文學,應該對此給予生動有力的揭示與展現。如此,方能構成大國文學的價值分量精神含量。
其四,大國文學氣象。大國文學可以對人生百態給予高度概括,對社會歷史變遷給予深刻揭示,對精神形態演化給予全面描述,但所有這些,固然可以給后人條分縷析的可能,但其自身,卻不是如此地自我展示的,而是作為一種氣象流淌于字里行間。讀俄羅斯文學,無論是寫苦難,還是寫幸福,你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博大的人道情懷;讀盛唐詩,無論是寫人生窮途,還是寫希望之旅,你都能感受到那其中的大氣、健康,謂之盛唐之音。當今中國文學,若成為大國文學,亦應該自有大國氣象生成于其間。
其五,亦如前所述,由于中西方種種社會結構形態、價值形態、精神形態在中國的“在場性”使中國在應對中所發出的“中國聲音”在全球話語場中,具有了“對話性”。中國文學作為大國文學在全球話語場中,不是孔子學院的變種,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代言人,由于歷史的際遇,中國的肉身上,烙下了中西方各種創傷的印痕,它所發出的痛苦呻吟,生命吶喊,就有可能獲得他國民族的關注與共鳴。
當下中國文學,作好了回應對自身成為大國文學的歷史性呼喚的準備了么?
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力,從價值形態來說,主要由三種力量構成:一種是1930年代生人,一種是1950年代生人,一種是1980年代生人。
1930年代生人的作家學者,如王蒙、錢理群等人,他們的文學創作在當今中國文學格局中,不再發生重大影響,但他們的思想資源,卻在實際中,仍然影響著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他們的優勢與局限都在于,無論是懷念還是反思,他們與毛澤東時代有著血肉相連的生命性維系,所以,在中國由毛澤東時代向后毛澤東時代作整體性轉型中,他們對新的時代的提問與對應,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的豐富性與真切性,他們對自身生命歷程的反思程度,直接影響著后幾代人對當今時代認識的深刻程度。
1950年代生人的作家,是中國當今文學界的實際領導者,1960年代的作家,在價值形態上,基本上不出其右,所以,盡管創作甚豐,實力頗強,但也可以歸納于這一代作家的版圖之內。這一代作家,生命經歷最為豐富,1930年代生人的作家,曾經作為他們的父兄輩引領他們,但與“五四”一代作家的對接,與西方現代作家的對接,他們自身的生命成長,終于使他們成為獨立的一支,且較1930年代生人的作家,有了更為寬廣的價值視野與更為豐富的人生經驗,更少了些生命經驗性束縛所帶來的價值性束縛。這一代人是中國目下最具實力最有希望的一代作家。但他們在當今歷史的斷裂處,較之“五四”一代作家,沒有西方的實際的人生經驗;較之1980年代生人的作家,他們對新的社會形態人生形態,少了親緣性,多了歷史的因襲的沉重。
1980年代生人的作家,是中國當今文學創作界最為活躍的一代人。他們的生命經驗、人生歷程、價值觀念,與中國的市場經濟同步生成,他們最容易生成中國文學的新的氣象。但在當今歷史的斷裂處,較之“五四”一代,他們沒有歷史的縱深感,他們也沒有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豐富性,這不由得使人疑慮于他們創作的厚重性、深刻性。
司馬遷的《史記》一向被視為歷史書、文學書,也因其中蘊含人生哲學,被視為哲學書。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出現了一批對應當下現實價值缺失的現實意義極強的字里行間充溢著深刻的思想性的以回憶、記寫一度被遮蔽、遺忘的歷史中的人、事的散文作品,因其遠追《史記》品格,我們可以姑且將之名為史記散文。此類史記散文,近些年成為了中國文學領域里的一個標高。或許,它們是中國文學回應中國文學成為大國文學歷史呼喚的尖兵部隊?魯迅曾云:“五四”時代的文學,小品文的成功,是在小說、詩歌之上的。但“五四”文學的輝煌,畢竟是由小說、詩歌、小品文共同完成的,作為大國文學的中國文學,也將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