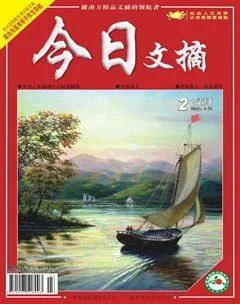在美國想念喧鬧的廣州菜市場
來美國的日子久了,不免懷念起國內的生活,特別是中學上自習課的情景。
那時候我們的教學樓離校門很近,門口對過去便是一間小賣部,地方雖小卻五臟俱全。下午,面對那些漫長而沉悶的自習課,不時有同學偷偷溜去那小賣部帶些零食回來,于是,教室里一陣熱鬧之后,瓜分完食物的眾人又開始埋頭做題。
后來,學校設了門禁,便有人隔著墻高聲喊小賣部的老板,老板將東西包好后拋過來,我們將錢拋出去,如此一來二往許多次,我們與小賣部的老板和伙計建立了深厚友誼。畢業那天,一伙人聚在店門口依依不舍,老板請每個人吃雪糕,叮囑以后有空回來看看。
到美國留學后,在圖書館坐久了或是課間休息,拎著錢包想買些零食,發現只有自動售貨機,反復看了好幾遍總提不起興趣,只好作罷。
除了想念學校旁那間小賣部外,我還想念離家不遠的菜市場。還未進去,便先看見街道上一些菜農擺了新鮮的瓜果蔬菜和人討價還價。走進市場,中間是生肉區,左邊賣熟食,右邊賣河鮮,里面是干貨,沒有明顯的招牌,卻一目了然。
在廣州十幾年,習慣了菜市場這種充斥著吆喝、討價還價、刀切砧板和禽類聒噪的景象,在美國,面對貨倉一般的超市時,我感受到的除了茫然還是茫然。
美國的大型超市隨處可見,沃爾瑪自不必提,好市多是相當有名的本土品牌,其余的還有商人喬、天然食品等等。這些超市往往占據整一層或幾層空間,龐大的貨物架上整整齊齊擺放了各種商品,分類細致,單是罐頭沙拉就有十幾種。一旁的冷凍區碼著各式牌子的香腸、火腿,隔著玻璃的肉類林林總總,一走近便覺得寒氣逼人。面對繁多得讓人眼花的品種,最后只會胡亂地指一塊稱好接過便匆匆離開。
美國人平時忙,周末便拉著大大的購物車在超市海量采購,分量之多令人咋舌,因此有些地方的收銀臺還分了類:少于十件商品的站左邊,多于十件的站右邊,以提高收款效率。
而與美國超市的大規模一般,美國商品的規格也遠大于國內,往往一盒餅干能吃上幾個星期。我曾買過一包最小規格的鹽,吃了將近一年。
有一次,我在當代美術館看到一個現代藝術家的作品,他將自己一整年吃住行所有購買的商品包裝保留下來,分類整理,展開排列在一起,占了滿滿一面墻,放眼望去,面積驚人。我真正領悟到什么叫做“消費主義文化”了。
在美國,有那么幾個詞總是很難翻譯準確的。“菜市場”便是其中一個。習慣了干凈、整潔、安靜、高效購買環境的美國人,也許永遠不能理解這么一個表面上混亂無序實則自成一體的購物場所。我對他們解釋說這是和超市不一樣卻同樣是買菜的地方,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是鄉村集市!”“不不不,跟這又有些不一樣。”怎么也說不清,到最后只好大眼瞪小眼。
雜貨店和小賣部,美國這邊也是有的,譯作“食品雜貨店”。同樣常見于街角,店面也不大,然而,與我印象中的國內雜貨店和小賣部總有那么一些區別。它們都很光鮮,都隔著厚厚一層玻璃門墻,窄窄一扇門在一邊,得用力推才能走進去。
我在美國居住地的附近,就有這樣一家小商店,我經過無數次,卻從未進去過,更不要提認識里面的老板了。
每當經過,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學生時代常常光顧的廣州小店鋪。每天一大早,老板將報紙書刊放在外面搭好的桌子上,把零食車拉出來,擺上一罐罐糖果,又從屋里搬出一臺小電視機,放在收銀臺不遠處的柜子上,然后坐在一旁抽上一根煙看報紙電視,偶爾瞟一眼街上,看見認識的人便打聲招呼。
放學時,那里總是最熱鬧的,有些家長路過買一份晚報,聊幾句頭條,而最常見的是一群打完球,滿身大汗的男生站在門口一邊喝冰飲一邊討論當天的球賽,間歇爆發出一陣大笑。
到了晚上,路上的行人少了,老板沓好報紙收起桌子,鐵門一拉,結束一天的生意。
若說美國沒有這樣的地方是不公平的——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作者簡·雅各布斯便不止一次提到過這樣的小店鋪,說它們既給周圍的居民提供了便利,也充當了街道看護者的角色:“表面上,老城市看來缺乏秩序,其實在其背后有一種神奇的秩序,在維持著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處。其中,帶來一個又一個駐足的目光的小店鋪,就是維系這種秩序的重要環節之一。”
然而它們畢竟是越來越少了。在上世紀60年代,雅各布斯就強力抨擊了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只要我們擁有足夠的金錢,那么我們就能在10年內消除所有的老城區,但帶來的卻是空曠的、毫無生氣的灰色地帶,這不是對城市的改建,這是對城市的洗劫。”因此今日我所見到的紐約,有著遠勝于昔日的繁華,卻顯得如此冷漠和無味。
如今,國內的許多城市規劃似乎在走這些美國大都市的老路,幾十年前為人稱贊的街道文化似乎正迅速流失,同樣流失的,還有那種隨性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