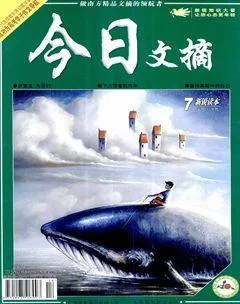65年未能寄達的家書
仿佛戀人在懷,“有著一種說不出的甜蜜蜜和軟綿綿的感覺,頓時我便想入非非”,他請求“您別生氣,且當是閨中戲謔吧。醒來余香猶在,窗外雨聲淅瀝,更添惆悵”——寫信人用略帶羞澀的語氣談到昨夜一場“春夢了無痕”。
這封浪漫多情的書信,來自1948年被解放軍包圍中的孤城長春。
信中柔情蜜意,現實卻是窘迫不堪。信的落款之日,正是節節勝利的解放軍攻占長春機場之時。解放軍切斷了城里國民黨守軍和外界的聯系,最后在一架倉皇駕駛的飛機上截獲大量信件。
這批家書先后被長春公安局和吉林省檔案館接管,在半個多世紀里成為沉睡的歷史。
兩年前一個偶然的場合,記者見到這封信的作者梁振奮,落筆時年方24的青年,前年已是87歲的老人,生命如同鬢發般染盡風霜。
那之前,記者從他的朋友處聽到信的故事,趁他夫人離席,便半開玩笑地問:現在說起來不怕太太吃醋嗎?
他微笑著搖頭,但顯然也不愿再就這個話題深入。
事實上,如果不是2008年吉林省解密的出版物里包含了這封信的原文,又恰好被他朋友看到,恐怕他后半生都不會主動言及。他的忘年之交告訴記者,他們相交數年,無話不談,除了長春那段經歷。
1948年長春解放,國民黨守軍被俘,無從得知梁振奮在那時遭遇了什么。從戰俘營回到廣州后,不愿連累女友的他選擇了分手,此后飽受各種政治運動折磨,50多歲才成婚,畢生無子女,信中的初戀女友則嫁了他人,再無聯系。
長春的記憶,成了這位前新一軍偵察兵的禁區。惟有這封信,在那段他諱莫如深的歲月里,留存了惟一的甜美和明媚。
2008年是長春解放60周年,吉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首次披露了圍城時沒能寄出的國軍信件,這些一手資料以個體記憶呈現了那段真實歷史。
65年前的長春,憑借當時號稱“堅冠全國”的工事,國民黨10萬留守部隊與城外進攻的解放軍對峙了5個月。
圍困中悲觀的情緒彌漫全城。國民黨守軍在信里頻繁抱怨糧煤短缺、物價飛漲。
士兵季平寫道:“市民有的吃樹葉、樹皮,有的吃豆渣,高粱米成為上等餐了,一斤四萬余元。市內天天聽到炮聲,射程居然打到了省政府門口,長市變成了一個孤市。”
百姓餓殍成群,“軍人雖糧食尚能維持,然而亦陷入最困苦狀態”,士兵玉軒這樣回復家中寄錢的要求:“恐怕你不會相信我的話,我哪里有錢寄到家里?一瓶黑人牙膏合法幣千余萬元,此地豬肉每斤一千五百萬法幣,我們月余未吃過。”
生存危機中發生了一些荒誕事。一名新七軍士兵記錄道:“在兵荒馬亂的東北,只要有高粱米吃,結婚是特別容易,尤其學校的女學生,你可以任意選擇,她們則無從選擇,條件只是問你每月的收入和高粱米而已。”兵團部政訓處一個快60歲的楊處長,娶了17歲的少女。
比物資匱乏更讓人煎熬的是精神恐慌,季平提到“居民一天內總有千百人攜老小(壯丁不準通過)離城經共區向關內走”。
而據當時的統計,3個月內國軍逃亡人數超1.5萬人,最多時每天300人。未逃走的,只能幻想“湊足川資回家”,烽火連三月,寄出的家書沒有回音,更令人心惶惶。
那一年的孤城長春,春天來得很晚。如今隔著65年光陰,在字里行間,仍然能夠感受圍城中人們深重的恐懼和絕望。
即便如此,在這些沉重的記錄里,也不乏如梁振奮那樣甜蜜美好的情信。在窘境中,親情愛情成為最牢固的寄托,那些不能停止的思念和期待,猶如絕境中的花朵,尤其令人心折。
1948年6月28日這一天,60軍的尹輔臣在燈下給妻子芬妹寫信:“相片我已收到,云峰長大了,好像很瘦,云霞好像很乖,我心真歡喜極了。”讓他心疼的是,芬妹的樣子苦惱而蒼老,他鄭重保存收到的黑發,寄語“您是我永遠的發妻”。
在相近的日期,士兵培軍向妻子張氏寫道:“我們在這生途上,都是一朵美艷的花蕾,在極寶貴的時代,一刻也不肯把它輕易放過。但現在關山相阻,家鄉千里只是望而興嘆。”
雖然“想嬌妻而痛泣夢中”,這位丈夫仍寬慰愛人:“現今別離之苦正是奠定我們永久的甜蜜,我期待相聚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信件都是單獨一封,但其中一份,因為女方事先把之前往來的信件都存在男方這里,而男方預見到長春可能被攻破,又把它們打包寄出。從這些連續的文字中,可以拼出一段相對完整的故事。
這個士兵叫符祝憲,他的意中人叫劉維廉。“當你用纖指拆開這封突如其來的信,你一定會忙于看末尾的署名,陌生的名字使你費思索嗎?我還沒有過和你傾談的機會,不過我卻已是最仰慕你的人”,第一封信,男人單方面陷入愛情;
可女子似乎無動于衷,第二封信,心急的男人繼續表白:“我胸頭小鹿一刻沒安靜過,你是否在諒解我抑或嗔怒?”
第三封信,女子大概接受了他的示愛,因為他對她的稱呼從“維廉小姐”變成了更親密的“廉”;而第四封信里,他已經開始討論婚禮細節了。
隨著城內彈盡糧絕,城外攻勢加劇,日愈絕望的國民黨守軍紛紛將照片、婚書、任職令等重要資料寄出。一個叫胡長庚的少尉就把300多篇日記夾在了信里。
這個年輕的少尉頗為有趣。兵臨城下,21歲的他仍牽掛著4月4日是中華民國兒童節,這天的日記,他寫道“今天過了我的第21個節”。
他帶著童真記錄瑣事,“今天見到了久仰的東北歌手miss王,原來是這樣一個女人,失望”“英國人說話時要輕快,要溫柔,K、T、E、Z音均不發得太明顯”。
他也記錄國民黨高官腐敗:“燈紅酒綠、舞影婆娑與難胞乞討鮮明對照!”
4月15日這天,他寫了一件小事:副連長因發軍餉時被克扣1萬元發脾氣,“狂呼要當八路去,說著哭了起來”!
3年前偷偷從家里跑出來從軍的胡長庚開始思考“我也希望八路來嗎”?他想通了:哈,少將,我才不稀罕當呢,還是回家去吧,做媽媽的好孩子。
終于,他決定“物色我的收音機、腳踏車的買主,賣掉它們換成金子做路費”“只要能回家,就死了我也滿足了”。
7月25日抽到一支問出行大吉的上上簽,3天之后他去郵局寄信,日記到這里戛然而止。
胡長庚是否能走上回家的路?符祝憲和劉維廉是否終成眷屬?而培軍和他的張氏,尹輔臣和他的妻兒,在那年深秋長春解放之后,有沒有團聚?
盡管后來吉林省檔案館幾經尋找這批信件的主人,但都未能如愿。這一個個塵封60多年的昨日故事,寫下了開頭,卻沒有人能補上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