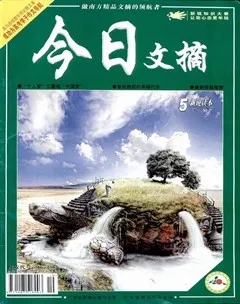尼泊爾同學的中國夢
第一次見到古馬爾是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旅行時,一位中國驢友的生日派對上。這個清瘦的尼泊爾年輕人一口流利的中文讓我不禁咂舌。更讓我驚訝的是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理解。一番攀談,我了解到古馬爾只有22歲,90后,正在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Tribhuvan University,尼泊爾排名第一的大學,設于加德滿都),讀碩士一年級,但是,他已有五年的高山向導經驗。一年前,他因為身體原因離開雪山,現在一邊讀研一邊經營一家旅行公司。
我對古馬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想聽一聽他的故事。凌晨5點的泰米爾區尚未恢復白天的喧囂,我與古馬爾會面。他整潔的西裝外面套了一件橙色的沖鋒衣,以抵御冬季清晨的寒冷——這是出團時的標準裝束。
穿過泰米爾區迷宮一般曲折的幽暗小巷,古馬爾的“中國尼泊爾國際旅行公司”標志掩映在紛繁的各式標牌之中。這次業務是一個來自中國重慶的攝影團,他們操著帶有重慶口音的普通話向古馬爾問好,其間夾雜著對食宿等一些瑣碎的抱怨,比如,熱水供應。古馬爾以純熟的中文應對自如。
穿校服的高山向導
尼泊爾被譽為“徒步者的天堂”,這個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國度坐落著全球14座8000米雪山中的8座,其間散布著世界上最多、最壯美、最完善的徒步路線。數不盡的背包客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為當地人提供了絕好的工作機會。
古馬爾的兼職高山向導生涯從15歲那年開始。
古馬爾出生在距離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約80公里的一座小鎮,在15歲之前從未走出過加德滿都山谷。雖然從小學到高中都享受著免費教育,家境普通的古馬爾像眾多尼泊爾少年一樣,早早開始為未來做打算,籌備大學階段需要的學費。選擇高山向導這個行業,一部分是因為相對豐厚的收入(15~20美金/天),一部分是出于對冰雪巔峰的向往。
成為一名高山向導并不容易,在空氣稀薄的喜馬拉雅山區,天氣以及路線變幻莫測,而徒步者的身體與心理狀況也千差萬別。古馬爾說向導必須是冷靜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需要在各種重要的時刻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獨立帶隊進山之前,古馬爾經歷了漫長的實習期,從幫廚和隊醫助理開始,一點一滴積攢這個行業所需要的經驗與膽識。
17歲那年,他獲得了尼泊爾旅游管理局的向導資格。
每逢學校假期,徒步旺季,年輕的古馬爾就帶領來自世界各地的徒步者,奔波在世界屋脊的峰巒之間。在兼職高山向導的5年時間里,他的足跡遍布了尼泊爾和印度北部幾乎所有知名的徒步路線,看遍8000米雪山的雄奇,也涉足過穆斯塘秘境探尋失落王朝的遺跡。后來,他終于不滿足于在雪山腳下仰望,作為一支登山隊的協作,登頂了印度境內一座6000米級的雪山Stok Kangri,他形容登臨巔峰的快意:“就仿佛自己是一只雪豹!”
五年間,古馬爾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徒步者,不同的語言,千差萬別的文化背景,懷著各自的動機與抱負——
最多的是來自歐美的年輕人,每個毛孔都蒸騰著冒險的沖動;
古馬爾曾經和一群來自澳大利亞的年輕人在冰封的高山湖泊游泳,比拼誰能夠在水下支撐更久;
也曾遇見過80歲高齡的老者,雖然步伐緩慢,卻具有非同常人的耐力和隱忍,最終走完整個珠峰環線,讓他肅然起敬;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位來自英國的徒步者,徒步開始時他的體重重達140多公斤,臃腫到每邁一步都會搖晃,不得不靠登山杖勉強支撐,在十多天行走中,他不僅完成了自我設定的目標,還減去了30多公斤體重。
喜馬拉雅山區入夜之后徹骨寒冷,客棧的火塘周圍就仿佛一個人生秀場,來自不同角落的背包客們依次分享自己的故事,那些野心、夢想、與自我的角力,抑或是逃避與落寞。古馬爾特別享受這樣的時刻,他也喜歡聽抵達珠峰大本營,或者徒步終點時,徒步者們擊掌歡呼,那是夢想實現的聲音——這個在雪山腳下長大的年輕人覺得整個世界都向自己敞開了。每一次十多天漫步雪山荒野結下的友誼,不會輕易消逝,有很多徒步者至今依舊與古馬爾保持著聯系。
有些時候,這樣的情誼是生死與共的。
在2009年一次環安娜普納徒步途中,一名年輕的徒步者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高原反應,使用抗高反藥物也不見好轉,并逐漸出現肺水腫的體征。古馬爾決定立刻帶他下山,一方面迅速降低海拔,一方面盡快就醫。其時是深夜,天氣極端惡劣,大雨傾盆,這名徒步者已虛弱到不能行走,古馬爾背起他,咬牙沖進雨里。雨下了一夜,古馬爾在泥濘的山路上一直走到天明。“回頭想想,真的記不起一路是怎么走過來的,大腦好像麻木了,一片空白。”到達山下的醫院時,古馬爾感覺全身的力量被抽空了,癱坐在地上,很久很久沒法站起來,那年他剛剛19歲。經過兩周的治療,徒步者最終康復出院。“這就是山,一念之差,可能就是生與死的差別。”
五年間,古馬爾被尼泊爾名校特里布文大學經濟學系錄取,并憑著高山向導這份職業賺了大學期間的全部學費。順利完成本科學位之后,他選擇在經濟系繼續碩士的學習,主攻旅游經濟學。
今兒不懂中文就out了
古馬爾學習中文已經有三年時間了。“我爺爺那輩,不懂梵文不行;我爸爸那輩,不懂英文不行;到了我這一輩,不懂中文就out了。”
古馬爾說,五年的高山向導生涯告訴他,只精通英語和尼語是遠遠不夠的,他將目光瞄準了新興的中文學習熱。特里布文大學的中文學校每天早晨七點至八點上課,以錯開學生們兼職與專業學習的時間。
這樣早起學習中文的生活,古馬爾堅持了三年。
除了去中文學校修讀課程,古馬爾最感興趣的是結交中國朋友,用中文向他們介紹尼泊爾的歷史和文化。“古馬爾和很多尼泊爾年輕人不一樣,走在泰米爾街頭,時刻會有人用蹩腳的中文搭訕,但是你知道這大多數是出于某些目的,比如兜售商品或是要求做收費導游。可是他交朋友就是為了交朋友,很純粹很有誠意的人。”古馬爾的一個中國朋友如是說。
古馬爾不時會用qq和遠在中國的朋友聊天,空間的中文日志也經常更新。在最近一篇描寫巴德崗的日志下面,有網友批注:“古馬爾,你的中文又進步了!”
2011年,古馬爾沒有想到,他會在高山向導這份做得輕車熟路的工作上遭遇挫折。那天,他帶隊徒步至之前曾無數次到訪的安娜普納大本營,突然感到無法抵御的疲憊與虛弱,隨隊的醫生測量血壓嚇了一大跳:“75/40!”“我不斷地告訴自己不能睡著,一旦睡過去就無法醒來了。”后來,古馬爾僥幸脫險,但是,醫生說,他在很長一段時間不適合再去高海拔地區工作。這就是喜馬拉雅山區,神秘中掩藏著危險,你永遠想不到下一秒會發生什么。
離開雪山的古馬爾有些低落,他頻頻出現在泰米爾區的青年旅社做義工,與天南海北的背包客交流,把陌生人變成朋友總能使他開心起來。古馬爾擅長講故事,周圍總是吸引了眾多的中國朋友。他能夠用易于中國人接受的表達方式,將尼泊爾陌生的宗教與歷史,融合在一個個有意思的故事里。比如,他堅持稱印度教中的婆羅門祭司為“老師”,因為他很清楚師長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與新結識的朋友無意閑談中,新的機會不期而至。
在泰米爾街頭,古馬爾辨認出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中國旅行者正逐漸成為尼泊爾旅游市場的主力。“之前,尼泊爾旅游業的支柱是來自于歐美的徒步者。現在,中國旅行者增長得特別快,幾乎超過了歐美背包客。”與尋求驚險刺激的歐美背包客不同,中國旅行者往往被尼泊爾獨特的宗教文化與喜馬拉雅風光吸引,但是,語言往往成了他們體驗雪山之國文化的障礙。
一次偶然的機會,古馬爾向一位中國朋友聊起自己創業的想法。他想創立一家全中文服務的旅行公司,向中國旅行者提供十天左右的尼泊爾攝影之旅。這位在中國從事旅游行業的朋友與他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