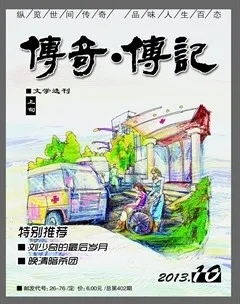晚清暗殺團
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裝力量里,既有經過正統訓練的新軍、民軍;也有作戰團隊如敢死隊、暗殺團、飛機團、商團;更不乏秘密的會黨組織如洪門、哥老會、鐵血會等。在這些作戰組織的帶領下,反清之士前赴后繼,舍生取義。無論是民間組織還是正統的軍隊,都紛紛變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
“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是1910年一位名叫汪兆銘的人在謀炸攝政王載灃失敗后留下的豪言,如今,世人記住的則是他另外一個名字——汪精衛。
歷史功過任評說,多少烈士前仆后繼。
從史堅如刺德壽開始,到吳樾刺五大臣,徐錫麟刺恩銘,再到彭家珍炸良弼,在清王朝最后的十年里,在北京、天津,在上海、廣州,這種近乎“獻身成仁”的作戰風潮,無疑是夾在眾多失敗的武裝起義中,最令人熱血沸騰的革命手段了。
他們,擁有共同的名字——刺客,短短十年間實行了50次暗殺行動。
他們,依靠共同的團體——暗殺團。由革命黨人籌組的暗殺團前后就達16個之多。
炸彈、匕首、子彈,如驚雷貫耳,驚醒沉睡國人。
暗殺,最省錢的革命方式
1911年4月27日,廣州城內刀光劍影,這場事后被稱為“碧血黃花”的起義最后以失敗告終,革命軍傷亡慘重。幸存黨人逃亡蟄伏在河南(現海珠一帶)郊區,除了養傷,革命者在等待一個機會,等待反撲復仇。這在一個月后胡漢民致孫中山信中可見一斑,“現時克強傷大愈,憤恨張、李二賊,欲以個人對待之”(胡漢民致孫中山、馮自由函《1911年5月31日》)。信中所講“克強”便是革命敢死隊首領黃興,而“個人對待之”所指便是暗殺。
從革命“經濟”考慮,暗殺是最省儉的一種方式,只需一兩條人命和炸彈,便可收獲廣泛的社會效應,但也體現革命消極的一面。有人統計過,作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中鼓吹暗殺的內容,占了全部圖文20%以上。一聲巨響,暗殺團風起云涌,在辛亥年間,“欲以個人對待之”不在少數。在眾多有組織的暗殺團中,擁有徐錫麟、秋瑾等的光復會最為后人所知,而在廣東,則活躍著令兩廣高官聞風喪膽的“支那暗殺團”。
作為“支那暗殺團”締造者,劉思復1905年加入同盟會,在留學東京時從一名沙俄無政府主義者那里學到了自制炸彈的技術。第二年春天,帶著絕活的劉思復在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自制炸彈,準備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不料事泄被捕囚禁,但因此也名噪一時。1909年出獄后,劉思復便在香港組織“支那暗殺團”,目標鎖定廣東高級官吏,而暗殺團的副團長,便是大名鼎鼎的嶺南畫派先驅高劍父。成員中還包括有日后炮轟總統府的陳炯明,1910年2月新軍失敗后,陳炯明潛回海豐家中,途經香港時秘密加入暗殺團。
制“毒彈”炸死廣州將軍
在廣州海珠區寶崗路的西邊,在一片綠蔭下,一個叫“龍導尾”的地方顯得格外幽靜。關于“龍導尾”,當地流傳著一個有趣的說法:廣州城龍頭位于越秀山,龍身自北逶迤而南,到了現寶崗大道西一帶便是龍尾,故該處也稱“龍導尾”。此說看起來似乎有穿鑿附會之嫌。但這個現在看來有些市井味的地方,一百年前卻聚集過一群熱血青年,他們曾如龍尾般攪動過當年的歷史。這幫熱血青年,便是“支那暗殺團”成員。
龍導尾七間直街9號老宅外觀看起來和普通民宅無兩異,但在廣州彩瓷歷史上同樣有特殊地位,為“河南彩”的發源地,老宅主人則是廣彩大師劉群興,他另外一個身份便是“支那暗殺團”的成員。劉群興與高劍父、高其峰自小便是親密無間的朋友,原本只悶聲搞藝術的他,在高劍父回國擔任廣州同盟會分會會長后,加入到革命起義的隊伍中。
離劉群興所住的七間直街9號不遠處,便是“廣東博物商會”彩瓷工場,如今舊址雖已淹沒在一片建筑中無跡可尋,但據劉群興之子劉致祥介紹,當年在這個工場內,劉群興白天主持彩瓷工作,晚上則在外面望風放哨,高劍父等人則在其中制作炸彈。“常常是睡在工地,床底下就藏著炸彈。”
1911年8月13日,“支那暗殺團”團員林冠慈在雙門底(現北京路北段)炸傷李準。僅僅兩個月后,暗殺團成員李沛基在南關倉前直街位置炸死新任廣州將軍鳳山,一時名聲大震。據記載,由于在暗殺李準中僅僅是炸傷對方,所以暗殺團在對付鳳山的炸藥上進行了“加工”,改用更重的七磅毒藥炸彈,血一見藥便自動凝結。為試驗炸彈效果,高劍父在制造炸藥的龍洞婆髻嶺炸傷一頭小牛和兩只小狗,結果“小狗即死,小牛雖只腿上傷二小孔,但因藥性發作,掙扎半個鐘頭,也即死去”。
作為活動聯絡和會議之用,支那暗殺團在廣州河南(即廣州珠江以南地區,現為海珠區一帶)設立了三個據點,其一為南華西鰲洲內街的裱畫店“守真閣”,其二為位于河南尾的“源利木店”,其三則為河南金華廟“信安顏料店”。其中“守真閣”為同盟會廣東分會舊址,以開設何鉅裱畫店為名,在二樓設立通訊社。
入團須練膽 先看骷髏頭
在廣州海珠區昌崗中路懷德大街3號,一座典型的嶺南建筑特別引人矚目,滿洲窗、長廊相繞,花草叢生,這便是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十香園,也是高劍父早年學畫的地方。日前,在十香園舉辦的《嶺南畫派與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書畫展》中,展館中央一幅《骷髏頭骨圖》引來許多人的關注。該畫主題為三個滾在青草地上的骷髏,用濃墨表現出來后,雖形態各異卻陰森撼人,據十香園紀念館館長劉志輝介紹,這幅高劍父真跡畫為首次公開展出,畫中內容反映的正是“支那暗殺團”神秘的入會儀式。
作為一名刺客,必須具備充分的膽識和面對恐怖氣氛時的絕對淡定,所以“支那暗殺團”一般會選擇在夜晚舉行入會儀式,大廳四周用黑布圍蔽起來,正中則擺著一張鋪著白布的圓桌,桌子上放著一個骷髏頭,旁邊點起一支白蠟燭。這些擺設,多半是從俄國虛無黨那里模仿過來的。等到燈熄滅后,在搖曳的燭光中,主盟人走到會場中間,舉起右手宣讀暗殺團宗旨和方略,一次儀式下來已令人毛骨悚然,入會新人終生難忘。“《骷髏頭骨圖》正是高劍父根據當時的情形所繪制。
入會人員經歷了儀式后,還要進行其他的技能訓練,其中便包括進入暗室,由訓練者扔人體骸骨或其他物件進行持續適應,反復鍛煉暗殺團員膽量。而訓練出來的隊員主要包括兩大類,一類為執行員,負責執行最后暗殺任務,一類則是補助員,負責后勤供給和聯絡掩護等,暗殺團用“同心同德”四字為團的小章。
據介紹,“支那暗殺團”的歷史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建立后,團員才“初志已遂,議決自行解散,且恥于求名,遂將團章盟書與年來會議函札等文件,悉皆燒毀”。
暗殺女杰宋銘黃
制炸彈,埋伏炸官吏,不成功便成仁。在許多人看來,這種鐵血而近乎悲壯的行為應屬革命年代的男人所為。其實不然,辛亥革命前后,一批女性革命者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宋銘黃的歷史,你們應該好好寫一寫,關于她革命的資料太少了。”作為廣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的曾應楓,最早接觸宋銘黃這個名字,還僅僅了解其為西關刺繡名手,但當她細讀這段歷史,才驚訝地發現宋不僅是民間工藝大師,還是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先行者。
據曾應楓介紹,宋銘黃早年由父母做主嫁給了西關一富家公子為妻,婚后因感情不和而離異,這在當時已算是件轟動的事情。由于她從小喜歡女紅,所繡的花鳥蟲魚都栩栩如生、形神兼備,在當地小有名頭。
光緒末年,宋銘黃被聘為廣州潔芳女校刺繡教師,結識了同在該校擔任圖畫教員的高劍父和潘達微。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她與高劍父擦出愛情火花,倆人同結連理。在高劍父擔任“支那暗殺團”副團長的日子里,作為妻子的宋銘黃用其女性身份為暗殺行動做掩護。那時內地很難買到炸藥,所以暗殺團在香港購買了炸藥和軍火后,便由宋銘黃組織承擔運輸任務。宋銘黃有時化裝為香港的豪門貴婦,將軍火藏在貴重行李中帶回廣州“省親”;有時又假扮是醫生、護士,帶著醫療器械護送病人來廣州求醫,而瓶瓶罐罐的醫療器械中便暗藏情報和炸藥引線等。
孫中山“姐妹保鏢”深諳武當派絕學
在辛亥年間的暗殺行動中,最讓人記住的女性無疑是“鑒湖女俠”秋瑾。但在革命年代中,還有一對姐妹花也格外引人注目,她們便是曾任孫中山貼身保鏢的“尹氏姐妹”尹銳志、尹維俊。
這對親姐妹深諳“內家”武當派絕技——“五毒殛手”,格斗時可以一當十克敵制勝。在擔任孫中山的保鏢時,孫中山稱姐妹倆為“革命女俠”,并在公開場合多次說她們“十余次救過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中,尹氏姐妹主持光復會工作,積極響應武昌起義。
1909年,尹銳志、尹維俊姐妹曾攜帶炸彈,潛伏北京一年,企圖炸死清廷要員,終因清軍防守嚴密,未能得手。其時,姐姐尹銳志年僅18歲,妹妹尹維俊才14歲,后人也將姐妹倆與秋瑾共稱為“中國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
〔本刊責任編輯 袁小玲〕
〔原載《大洋網—信息時報》2013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