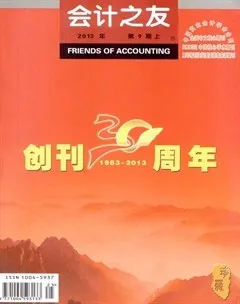高管增減持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研究
【摘 要】 文章以2006—2011年高管持股變動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高管增減持股票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研究發現: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計超常收益率為負數,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股票在減持公告日前有顯著的正累計超常收益率;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傾向于提前披露壞消息,或延遲披露好消息,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則相反;高管在增持股票過程中存在負向盈余管理行為,而在減持股票過程中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為。希望本研究結果能夠為證券監管機構加強對上市公司高管行為的監督和如何保護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參考依據。
【關鍵詞】 高管增減持; 市場反應; 盈余管理
2005年,我國資本市場實施了股權分置改革,使得非流通股的股東和持股高管能夠通過“減持”股票的方式實現其產權收益。2007年前后,股市暴漲使得高管們減持股票的現象非常普遍。2008年,股票價格的持續下跌,許多股票的投資價值凸顯,作為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人的高管們又紛紛買入自己公司的股票。高管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買賣本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利益的驅使下,高管具有很強的通過盈余管理來操縱股價的沖動,從而使自己在二級市場增減持股票過程中獲得最大化利益。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體制的改革,上市公司高管持股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高管買賣股票的行為也越來越頻繁。那么,高管在買賣本公司股票過程中是否真的存在通過盈余管理行為來影響股票價格從而達到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本文擬以高管持股變動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高管增減持過程中是否存在著盈余管理行為,從而為規范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機制、完善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一、文獻綜述
高管持股與盈余管理問題一直是公司治理中的關鍵,國外學者對于高管持股與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Fama(1980)認為,如果高管人員在公司持股比例較大,高管人員與控股股東結盟的可能性就增加。高管人員的持股比例越高,他們就越有動機去“粉飾”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并期望分享更多的私人收益,因此管理層持股比例和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Loebeecke等(1989)指出管理層持股對于公司的財務報告欺詐是個很重要的誘因。Warfield et al(1995)基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理論,研究了美國1989—1991年間3 871個上市公司年度數據,結果發現,隨著管理股權增加,可控應計項目調整幅度減小,即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與管理層持股比例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說明管理層持股比例或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提高會降低代理成本、減小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但是Warfield et al(2005)的研究又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結論,發現管理者持股可以影響盈余管理,且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正相關。Gabrielsen等(2002)采用Warfield et al(1995)的方法對丹麥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管理股權與盈余管理正相關的結論。Yeo et al(2002)研究了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股權和外部投資者對盈余信息質量的影響,發現管理股權與盈余信息質量存在非線性關系,當管理股權比例較低時盈余信息質量隨管理股權比例增加而增加,當管理股權比例較高時,由于存在防御效應使得盈余信息質量與管理股權呈負相關關系。Wang(2003)通過對臺灣上市公司數據的檢驗,認為異常盈余隨著管理股權的增加而增加,盈余管理程度與管理股權正相關,盈余質量與管理股權負相關。Sam Han(2005)為了檢驗股權結構對財務信息質量的影響,使用了可控應計項目和Dechow & Dichev(2002)的檢驗結果,發現管理股權與盈余質量負相關,與機構投資者正相關。Teshima & Shuto(2008)的研究結果驗證了高管持股比例與操控性應計利潤呈三次非線性關系的研究結論。Sawicki & Shuto & Takada(2009)首次運用日本的企業數據,研究發現了高管持股對盈余穩健性的協同效應和塹壕效應。
我國學者對高管持股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起始于股權分置改革之后,如李遠勤和劉艷萍(2006)以深市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與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自愿性披露水平也就越高,這表明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質量也就越高。黃謙(2006)以2002—2003年間的746家上市公司為樣本,運用截面的Jones模型研究上市公司經理人持股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研究發現總經理持股比例與公司的盈余管理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王克敏等(2007)對2001到2004年間的1 914個公司樣本進行研究,發現總經理持股額與盈余管理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毛洪安(2008)研究了高管持股與盈余質量之間的關系,實證研究發現,高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之間呈U型分布,相對集中的股權有利于提高盈余質量。當高管持股比例較低時,隨著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高管與股東之間存在著利益趨同效應,此時高管持股與盈余質量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當高管持股比例達到36%時,此時高管對公司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加,高管能夠運用控制力進行盈余操縱,高管層為了獲得私人收益,會通過調整會計盈余的方式來扭曲公司的業績,達到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目的,這樣會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王兵等(2009)對2001—2004年間的4 498個公司樣本進行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的盈余管理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張兆國等(2009)的研究認為,管理者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無顯著相關關系。戴新民等(2010)以2008年滬市1 486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流通股股東和高管持股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管理層持股比例和流通股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黃文伴和李延喜(2010)的研究發現,高管持股比例與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不相關。于衛國(2010)以2005—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對象,使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高管持股與盈余管理程度的關系,研究發現:高管持股市值與操縱性應計利潤正相關,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高管持股市值與線下項目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李偉、周林潔和吳聯生(2011)研究了高管持股與盈余穩健性的協同效應與塹壕效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對盈余穩健性的需求與高管持股呈非線性的關系。在高管持股水平較低和較高的區間,高管持股具有協同效應,高管持股與盈余穩健性呈負相關關系;在高管持股的中間水平,高管持股具有塹壕效應,高管持股與盈余穩健性呈正相關關系。
通過文獻回顧發現,現有文獻對高管持股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持股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因此,本文欲從高管持股比例變動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角度進行研究,檢驗這一過程中高管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公司高管在增減持股票過程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上市公司真實信息的控制人,其增持或減持公司股票行為是否侵害了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將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重點。本文圍繞高管增減持公司股票過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這個關鍵問題展開研究,通過考察高管增減持股票過程中的短期市場反應、高管增減持與上市公司重大信息披露時機選擇、高管增減持與操控性應計利潤之間的關系,探討高管在增減持公司股票過程中是否存在通過盈余管理來侵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行為。
二、研究背景與假設提出
2005年5月中國證監會發布了《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的開始,8月中國證監會等五部委聯合發出《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高管股權激勵等股權分置相關政策的出臺,股改開始大規模推進,上市公司的持股高管更加關心二級市場股價的變化。在股權分置改革之前,我國的高管股權激勵受到當時法律法規的限制,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推行,絕大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層的持股計劃實質上是一種福利形式而不是激勵制度安排。2006年中國證監會發布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表明我國正式建立起股權激勵和約束機制。2007年3月證監會發布了《關于開展加強上市公司治理專項活動有關事項的通知(證監會公司字[2007]28號),對上市公司進行股權激勵進行了條件限制,即必須完成公司治理整改才能實施股權激勵。從股權激勵的實施情況來看,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股權激勵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高管股權激勵以股票期權為主。截至2009年,我國上市公司中有114家實行了股票期權,比例達到78.6%;二是高管股權激勵方案所涉及行業分布較廣。從統計情況來看,股權激勵方案涉及制造業、信息技術行業、房地產行業以及批發和零售貿易等行業;三是大部分上市公司制定高管薪酬激勵考核指標過于倚重會計業績,這容易導致經理人行為的短期化;四是高管薪酬制定程序及獎懲措施等信息披露不透明,嚴重影響了對高管薪酬的監督。
我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政策的陸續出臺和上市公司高管股權激勵具有的這些特征為本文對高管增減持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契機。Jog(1999)的研究發現,信息不對稱會導致企業價值被低估或高估。Prior(2008年)認為,高管為了影響短期價格完全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Philippon(2006)發現,當管理層的未來薪酬與股價及期權激勵密切相關時,管理層更有可能通過主觀應計來操控利潤。Shrestha(2008)以美國上市公司為樣本,對公司內部人購買本公司股票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發現,內部控制人在購買本公司股票時傾向于調低盈余的盈余管理,而當他們賣出本公司股票時則傾向于調高盈余的盈余管理。現有文獻說明高管可能會利用信息優勢操縱股價,為增持或減持股票做好準備,實現從中賺取利潤的目的:在高管增持股票前,高管會進行盈余管理使得股票價格被低估,從而達到降低購買成本的目的;在高管減持股票前,高管會進行盈余管理,使股價上升,為出售股票創造條件。由此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1: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計超常收益率為負,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股票在減持公告日前有顯著的正累計超常收益率。
信息在資本市場價格形成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資本市場上股價的形成過程就是投資者不斷收集信息進行決策分析和決策修正的過程。上市公司重大信息的公布會引起股價的波動,這種波動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國內外大量文獻研究了信息公布對股價產生的效應,如Brown and Han(1992)實證檢驗了盈余信息的有用性,驗證了會計盈余信息對股價的作用。Kyriacou et al.(2009)的研究發現,公司高管在獲得股票期權時有操控公司信息的行為,即提前披露壞消息或延遲披露好消息,從而壓低行權價格,提高股票期權收益。Berkman等(2009)也認為如果會計盈余信息是有用的,那么它必然會影響股票的收益。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比外部信息使用者了解更多關于企業經營活動的信息,因此,高管層有條件也有動力通過選擇信息披露的時機來影響股價。具體地,如果高管層準備增持股票,那么在增持前會提前披露一些壞消息或延遲披露好消息,從而使股價處于較低的水平上,降低增持成本;如果高管層準備減持股票,那么會提前披露好消息或推遲披露壞消息,使得股價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有利于創造機會出售股票,以獲得最大的減持收益。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2: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會提前披露壞消息,或延遲披露好消息,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股票則相反。
三、數據搜集與樣本說明
2003年7月11日,“天通股份”董事長(同時也是第一大股東)通過現金交易方式減持公司股票600萬股,成為第一家高管減持股票的上市公司。由于股權分置改革之前,高管往往也是具有控制權的股東,高管并不是兩權分離意義上的高管,并且高管(同時也是股東)減持的股票往往由其他高管(股東)增持,所以無法分清樣本應該算作是增持還是減持,因此本文選擇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之后的樣本作為研究對象。從2006年2月28日,宏達股份高管減持公司股票后,陸續有很多公司高管通過競價交易或二級市場買賣等方式增持或減持公司股票。本文搜集了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間高管增持或減持公司股票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按照下列條件進行了初步篩選:一是由于金融業上市公司與其他行業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剔除金融業上市公司;二是剔除ST、PT類上市公司和退市公司;三是剔除數據缺失和因分母為零導致數據異常以及無法找到相關資料的上市公司;四是剔除高管身份兼為董事、監事或證券事務代表的樣本;五是由于樣本中有部分持股變動比例大于100%的上市公司,筆者認為持股變動比例大于100%的樣本是不合理的,因此予以剔除;六是剔除高管離職以后持股變動的樣本。經過初步篩選后,筆者進一步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一是在同一交易日內同一高管發生的多次增持或減持行為合并視為同一事件;二是在同一交易日內多個高管發生增持或減持行為,則將數據進行合并,視為一個樣本數;三是對于前后相隔30天以內的增持或減持事件,以第一次增持或減持行為為研究樣本,而短時間內的第二次或更多次增持或減持行為,由于股價容易受到第一次增持或減持事件的影響,因此沒有將短期后續增持或減持事件作為研究樣本。經過上述處理,共得到1 424個高管增減持股票的公司樣本,另外選取了同行業同時期高管持股未變動的1 424家規模相似的上市公司作為對比樣本組。本文的數據來源如下:高管增減持數據取自CCER數據庫提供的“上市公司內部人交易數據庫”,財務數據取自CCER數據庫提供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資料主要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新浪財經網站和巨潮資訊網站手工搜集和整理而得,使用Eviews6.0對數據進行處理。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高管增減持上市公司的短期市場反應
筆者運用事項研究法,以高管增持或減持公告日為基準日,研究高管增持或減持公司在基準日前后各30個交易日市場反應。參考了Dodd & Warner(1983)、Yermack(1997)和吳育輝、吳世農(2010)的研究方法,以各家公司在公告日前第31天到第181天的歷史股價數據估計市場模型,即:Rit=αi+βiRmt+εit,
其中,Rit為股票i在第t日的實際收益率,Rmt為市場指數在t日收益率;β為回歸系數;εit則代表隨機誤差項。根據公告日之前的第31至第181個交易日作為估計窗口,得到每一家樣本公司的估計參數和市場模型,并計算高管增持或減持公告日前后30天內每個交易日的超常收益率。筆者將超常收益率和累計超常收益率定義為:
ARit=Rit-E(Rit)=Rit-(■i+■iRmt)
CARi=■ARit
根據計算得到的市場模型估計參數,筆者計算了高管增持或減持公告日發布前后30個交易日共61天的平均超額收益率(AR)值,如表1所示。
通過表1可以看出,對于增持樣本來說,高管增持上市公司的AR值在公告發布日前1至5個交易日為負數,但是在公告日和公告日后20個交易日的AR值為正數。具體來看,AR值從高管增持前5天開始顯著為負,并且絕對值逐漸變大,在增持前一天AR值為-2.05%。從公告日開始,AR值開始轉為正數,公告日后第二天AR值為3%,達到最大,此后逐漸回落,公告日20天后,AR值逐漸變為負值,且不再顯著。而對于減持樣本來說,上市公司的AR值在公告發布日及公告日前1至5個交易日為正數,但是在公告日后30個交易日的AR值為負數。AR值在高管減持公告日前20天逐漸增加,到減持公告日前一天達到最大,為5.47%;之后,AR值開始逐漸減小,到減持公告日后的第20個交易日,變為顯著的-3.42%,一直到減持公告日20天后AR值雖然仍然為負數,但統計上變得不再顯著。
研究發現,不管是增持樣本組還是減持樣本組,兩組樣本公告日的市場反應都是積極的,而且公告日市場反應也可以歸結為事項的事后反應,因此,筆者將窗口劃分為(-30,-1)、(-20,-1)、(-10,-1)、(-5,-1)、(0,5)、(0,10)、(0,20)和(0,30),以進一步對比研究兩組樣本的ACAR值表現(如表2所示)。筆者發現,從高管增持樣本來看,高管增持公告日前20天開始ACAR值就顯著為負數,直到公告日開始ACAR值才開始轉為正數,公告日前ACAR(-5,-1)值達到-5.22%,而ACAR(0,5)達到7.15%,此后逐漸回落。從高管減持樣本來看,高管減持前30天開始ACAR值就開始轉為正數,到減持公告消息發布ACAR仍然為正數,公告日前ACAR(-5,-1)值達到5.79%,公告日第二天開始才逐漸轉為負數,ACAR(0,5)達到-3.78%,之后逐漸回升。
通過對比不同時間窗口的ACAR值表現,發現,無論選擇哪個時間窗口,高管增持上市公司的ACAR值在增持公告前均顯著小于0,而在增持公告日和公告日后均顯著大于0,說明高管在增持過程中獲得了超常收益。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的ACAR值在減持公告日前均顯著大于0,而在減持公告日和公告日后均顯著小于0,說明高管在減持過程中也獲得了超常收益。
通過上述研究,筆者發現:一是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在增持前20個交易日內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ACAR值)顯著為負,在高管增持后30個交易日內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ACAR值)顯著為正;二是高管減持上市公司在減持前30個交易日內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ACAR值)顯著為正,在減持后30個交易日內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ACAR值)顯著為負。假設1得到驗證。
(二)高管增減持上市公司的操控性應計利潤
Healy和Wahlen(1999)認為“盈余管理發生在管理人員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通過規劃交易以變更財務報告時,旨在誤導那些以公司的經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的決策或者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數字為基礎的契約的后果。”對于盈余管理的衡量方法有很多,主要有:應計利潤總額法、應計利潤分離法、盈余分布法和具體項目應計法,比較常用的方法是應計利潤分離法。應計利潤分離法的模型主要有: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業模型;截面Jones模型;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Guay、Kothari和Watts(1996)分別運用上述模型檢驗盈余管理與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只有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更好地揭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從而有效地識別盈余管理行為。借鑒Guay、Kothari和Watts(1996)等學者的研究,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作為檢驗高管在增、減持過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如下:
TAijp/Aij,p-1=α(1/Aij,p-1)+β1jp(ΔREVijp/Aij,p-1)+β2jp
(PPEijp/Aij,p-1)+εijp
其中,Aij,p-1為公司i第t年初的總資產的賬面價值;TAijp為公司i第t年末的總應計,即凈利潤與經營現金流量的差;ΔREVijp為公司i第t年相對于上年的營業收入的增量;PPEijp為公司i第t年末固定資產的原值;εijp為隨機擾動項。
將樣本數據代入到模型中進行回歸,得到模型參數的估計值α、β1jp、β2jp,將估計參數帶入模型后,得到實際總應計利潤與預期總應計利潤之間的差額作為操控性應計利潤的衡量指標。
本文共建立了三個計量模型來檢驗高管在增減持股票過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模型(1)和(2)用來檢驗高管持股變動的短期市場反應,被解釋變量分別為CAR(-30,-1)值和CAR(0,30)值,模型(3)的被解釋變量為操控性應計利潤(DA),用來檢驗高管增持或減持股票過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建立模型①如下:
CAR(-30,-1)=α+β1X1+β2X2+β3Lev+β4LnSize+β5ROE+β6IND+β7YEAR+ε (1)
CAR(0,30)=α+β1X1+β2X2+β3Lev+β4LnSize
+β5ROE+β6IND+β7YEAR+ε (2)
DA=α+β1X1+β2X2+β3Lev+β4LnSize+β5ROE
+β6IND+β7YEAR+ε (3)
模型中變量定義如下:ACAR(-30,-1)為高管增、減持上市公司從公告日前第30個交易日到前一日的累計超額報酬率;X1為虛擬變量,當高管增持時為1,否則為0;X2為虛擬變量,當高管減持時為1,否則為0;Lev為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上市公司的負債總額/資產總額;LnSize為控制變量,表示公司規模,以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計量;ROE為控制變量,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股東權益;IND為虛擬變量,表示樣本公司所屬的WIND二級行業;YEAR表示高管持股變動年份;CAR(0,30)為高管增、減持上市公司從公告日起到第30個交易日止的累計超額報酬率。筆者將借鑒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的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因變量,用DA表示操控性應計利潤。
對全部樣本的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其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我國高管持股變動上市公司在持股變動前30個交易日的累計報酬率平均值為0.0997,標準偏差為0.1754,最小值為-0.4987,最大值為0.6875;持股變動公告日及后30個交易日的累計報酬率平均值為-0.1601,標準偏差為0.2349,最小值為-0.6142,最大值為0.5489,累計報酬率水平總體上差異較大,反映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程度的指標DA的均值為0.018,并且在1%水平下具有顯著性,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高管在持股變動過程中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現象。X1的均值為0.3054,X2的均值為0.6946,兩者都在1%水平下具有顯著性。
在對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之前,對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進行了檢驗,發現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各變量可以同時放進模型進行回歸。運用OLS回歸方法對模型(1)、(2)和(3)進行估計的結果如表4所示。
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條件下,X1的系數為-0.060,X2的系數為0.312,兩者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高管在增持前有負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在減持前有正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其他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條件下,X1的系數為0.469,X2的系數為-0.043,兩者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高管在增持后有正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在減持后有負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其他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不顯著。模型(3)檢驗了高管增持或減持過程中是否真的進行盈余管理,X1的系數為-0.041,X2的系數為0.061,兩者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一方面說明高管在增持股票過程中,會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進行負向的盈余管理,從而降低其增持成本,提高增持收益;另一方面說明高管為了減持公司股票會進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從而獲得更高的減持收益,假設1進一步得到驗證。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與操控性應計利潤顯著負相關,凈資產收益率與操控性應計利潤顯著正相關,這與現有文獻的研究結果相同。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我們控制了行業變量,將因變量替換為不同窗口的CAR值進行了多次回歸,發現上述研究結論仍然成立,又增加了高管持股變動的年度變量,上述結論依然成立。
(三)高管增減持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
由于高管在增、減持過程中均獲得了較高的超常收益,有理由懷疑,高管在持股變動過程中存在某些影響上市公司股價波動的盈余管理行為。眾所周知,高管是上市公司信息的內部控制人和知情人,他們有動機也有能力對公司的重要信息披露施加影響甚至直接操縱公司的信息披露。比如,高管欲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時可提前披露壞消息,以此壓低股價,或延遲披露好消息,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增持后股價上升給其帶來的超額收益;減CETXdsbRghsmqKlH9NrsOQ==持則相反。通過手工搜集數據的方式搜集了高管增減持前后30個交易日的重大信息披露內容,并對信息進行了整理和分類。筆者將信息主要劃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并購重組類:主要涉及高管持股變動公司的資產重組和資產轉讓等;二是財務報告類:主要涉及高管持股變動公司相關財務報告的信息;三是盈余預告類:主要涉及高管持股變動公司業績快報和業績預告的信息;四是其他類:主要涉及高管持股變動公司的高管變更、生產經營方面的重大事項、關聯交易、再融資、擔保事項、違規事項和訴訟事項等信息。從表5可以看出,在高管持股變動前后的30個交易日內,被高管增、減持股份的上市公司總共披露了897條重大信息,其中:并購重組類信息193條,財務報告類信息238條,盈余預告類信息212條,其他信息254條。
進一步將重大信息披露分為好消息與壞消息,目前學術界對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好壞消息的判斷標準尚未統一。我們對于不同類型信息好壞的分類標準如下:一是并購重組類:如果是發布重大重組意向、重組最新進展或重組成功的消息為好消息,反之為壞消息;二是財務報告類:如果財務業績同比或環比增長的消息為好消息,反之為壞消息;三是盈余預告類:盈余預告同比或環比增長的消息為好消息,反之為壞消息;四是其他類:由于其他類信息種類較多,難以一一區分消息的好壞,筆者參考了Givoly & Palmon(1985)和吳育輝、吳世農(2010)的研究,用信息披露當日公司股票價格的市場反應作為消息好壞的判斷標準。將高管持股變動公告日前后30日內(除并購重組、財務報告和盈余預告類信息之外)信息披露當日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漲跌幅度與市場指數漲跌幅度進行比較,如果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漲幅大于市場指數漲幅2%以上或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跌幅小于市場指數跌幅2%,就稱之為好消息;反之,如果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漲幅小于市場指數漲幅2%以上或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跌幅大于市場指數跌幅2%以上,稱之為壞消息。
從表5還可以看出,總體而言,壞消息數量比好消息數量多,好消息為310個,壞消息為587個,占比分別為35%和65%。主要是由于高管減持樣本數多于增持樣本數,而對于減持的樣本而言,涉及到公司業績的財務報告信息、盈余預告信息以及公司融資和擔保等方面的壞消息數量明顯多于好消息的數量,而高管減持的動因又恰恰與這些壞消息有關。
筆者進一步將高管持股變動上市公司增、減持公告日前后30個交易日內的信息披露情況(主要指好消息和壞消息)與增、減持公告時間進行對比分析,發現:第一,對于高管增持樣本而言,好消息為243個,壞消息為67個,好消息占增持樣本的78%,說明310家高管增持的公司樣本中,絕大部分是伴隨著好消息的,只是在披露的好消息中又有57%(138個樣本)是在增持公告日后公布的,43%(105個樣本)是在增持公告日前披露的;而在披露的壞消息中有63%(42個樣本)是在增持公告日前披露的,37%(25個樣本)是增持公告日后披露的。第二,對于高管減持樣本而言,好消息為207個,壞消息為380個,壞消息占減持樣本的65%,說明1 088家高管減持的公司樣本中,絕大部分是伴隨著壞消息的。不過在披露的壞消息中又有53%(200個樣本)是在減持公告日后公布的,47%(180個樣本)是在減持公告日前披露的;而在披露的好消息中有54%(112個樣本)是在減持公告日前披露的,46%(95個樣本)是在減持公告日后披露的。這一結果初步表明,高管在增、減持股票過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即高管在增持上市公司股票過程中,傾向于在增持前發布壞消息,以阻止股價上升,而在增持后發布好消息,以刺激股價上漲,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增持收益。反之,高管在減持股票過程中,傾向于在減持前發布好消息,刺激股價上揚,以便以較高的價格減持手中股票,而將壞消息延遲到減持后發布,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減持收益。故假設2得到驗證。
五、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高管持股變動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高管增減持股票過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研究發現:第一,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存在顯著的負累計超常收益率,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股票在減持公告日前存在顯著的正累計超常收益率;第二,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傾向于提前披露壞消息,或延遲披露好消息,而高管減持上市公司則傾向于提前披露好消息,或延遲披露壞消息;第三,高管在增持股票過程中存在顯著的正操控性應計利潤,而在減持股票過程中存在顯著的負操控性應計利潤。本文的研究結果證實了在高管增減持股票過程中,確實存在高管通過操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會計政策而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從而侵害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一研究結論能夠為證券監管部門制定高管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和經驗證據。●
【主要參考文獻】
[1] 蔡寧,魏明海.“大小非”減持中的盈余管理[J].審計研究,2009(2).
[2] 李遠勤,劉艷萍.股權結構與自愿性信息披露——來自深市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統計與決策,2006(20).
[3] 吳育輝,吳世農.股票減持過程中的大股東掏空行為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5).
[4] 于海林.高管增減持、盈余管理及其經濟后果[D].安徽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