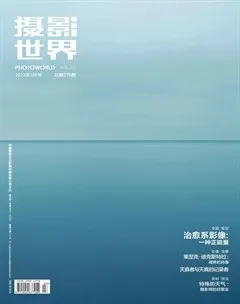從“支邊”開始的記者生涯











北京:“文藝青年”去支邊
學生時代,韓傳號從沒想過要做記者,更別說是攝影記者。在中國人民大學他讀的是中文系,自然想當“文藝青年”。偷偷寫了部小說,還未完稿,怎么看都不像“杰作”,自己又悄悄燒掉了。上百頁的手稿,化成了一股青煙。大四那年,他考研失敗,離畢業僅兩個多月時,新華社甘肅分社到人大中文系招人。時任甘肅分社副社長申尊敬見韓傳號高高大大,說:“就你了,我們需要一名攝影記者。”
在新華社總社新聞大廈東配樓5層分管室的辦公室里,我第一次見到韓傳號。分社領導到學校選了他,把他帶到總社攝影部來,讓我“相相面”,順便告訴他分社領相機的事。韓傳號瘦高個子,人很謙遜,說話也頗有禮貌。我問他家在哪里,他說江蘇。那時相機和手機都還算是奢侈品,韓傳號只用傻瓜相機幫人拍過幾次合影,單反相機摸都沒摸過——要做攝影記者,他有些“先天不足”。但甘肅分社能從人大選到學生也不容易。因此,很快就簽了合同。韓傳號是江蘇生源,到甘肅工作,還拿了個北京高校支援邊遠地區建設的證書,即“支邊證”。
1999年7月初,韓傳號到甘肅分社報到了。北京到蘭州當時要坐30多個小時的火車,他一路心懷忐忑。當時他對西北的了解,僅限于幾句玩笑話:西北遍地是黃沙,要騎著駱駝上班。
甘肅:從“菜鳥”到“熟練工”
那年年底,韓傳號入社不久,和甘肅分社攝影組組長武斌去采訪,途徑東鄉族自治縣看到有許多人頭戴小白帽在地里干活,本想去拍些照片,沒想到剛走到地頭,就被農民包圍并捆起來,綁到了不遠處的山頭……后來得知是相鄰的兩個縣因為爭奪地盤的出口發生了械斗,把后來去取證的記者打成重傷,看到又來兩個陌生人,也準備對他們下手。韓傳號回憶說,當時武斌嚇得臉都綠了,他估計自己也是臉色慘白。后來是武斌及時打電話請來“救兵”,二人才被救下。韓傳號說這是他當記者后的第一堂課——危機課,一生都不會忘記。
因為缺乏攝影基礎,韓傳號上手很慢。這只“菜鳥”讓武斌很是“頭疼”。武斌第一次帶他去采訪,他盡往別人鏡頭里鉆;文字稿發了幾篇,圖片稿還沒開張;后來他又接連搞壞了兩臺以“皮實”著稱的尼康FM2……
新舊世紀之交,膠片時代的最后幾年,攝影記者在外采訪,需要用便攜式終端“新華100”發稿,時效性強的照片要就近找彩擴店沖底片,再掃描、初步編輯,最后通過電話線傳圖,一張照片少說要傳十幾分鐘。所以每次出差采訪,除了突發新聞,時效性不強的稿子一般可以沉下心來拍,拍完可以放著慢慢處理。或許也正是這種慢節奏,成就了當時不少拍專題的“大腕”,長年跟蹤拍攝甘肅缺水、貧困等主題的武斌便是其中之一。
好在韓傳號文字基礎不錯,電腦也用得熟練。武斌發稿時常讓他打下手,一起寫圖片說明。時間長了,哪些照片能發稿、什么樣的照片是好照片,他漸漸有了點感覺。
2001年,參加工作的第三年春天,韓傳號慢慢進入角色了。中國北方風沙肆虐,甘肅分社圍繞沙漠化主題組織多名記者調研采訪。灰頭土臉地跑了近一個月,韓傳號獨立完成的組照——《莫讓河西走廊成為風沙通道》,被《新華每日電訊》、《農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用,也被評為新華社總編室每周表揚稿和攝影部部級好稿。這讓韓傳號激動了好幾天。他把幾份報紙都收齊,當寶貝似的收藏起來。
綿延1000多公里的甘肅河西走廊,是我國北方沙塵源地之一。每年春夏時節,河西走廊出現沙塵天氣,省會蘭州也要受影響。他在采訪中聽人描述說,沙塵暴來時像一堵墻,直接壓過來,半邊天都是黑的。內蒙古分社的同事就在沙漠里拍到過這畫面。韓傳號想拍沙塵“壓城”,每次聽說哪里預報要起沙了,只要條件允許,他就會趕過去。但他總也拍不到想象中的那個畫面,以至于同事都戲稱他為“定沙使者”。2010年4月底,韓傳號調到浙江分社工作后不到一周,一場規模空前的特強沙塵暴就襲擊了河西走廊,給甘肅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下9億元。
后來到了浙江,每次臺風韓傳號也總是趕不上趟,于是又有了“定風使者”的綽號,這是后話。
與風沙打交道,也會有“險情”出現。2001年10月,沙漠專家、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楊根生帶隊,到內蒙古烏蘭布和沙漠野外考察,韓傳號應邀隨同采訪。11月1日上午,在包頭附近考察黃河河道時,原本結冰、堅實的河道因氣溫升高成了“泥潭”。楊根生和韓傳號先后陷了進去。
淤泥積沙齊腰深,越是掙扎越往下陷。所幸在岸邊的司機發現了他們,并將韓傳號留在車上的三腳架放至最長,把兩人從“泥潭”中“拔”了出來。
到2003年,韓傳號已是一名“熟練工”,攝影部分管室通知他到北京參加全國兩會報道。兩會期間,愈發緊張的美伊局勢也讓韓傳號焦灼——此前他向攝影部交了書面申請,要求到戰地報道。
伊拉克:“無知者無畏”
2003年4月初,韓傳號被派增援伊拉克周邊國家,在安曼邊采訪邊待命。月底,新華社批準王波、梁有昶、馬曉霖、韓傳號四人進入伊拉克,韓傳號是唯一的攝影記者。
當時從約旦到伊拉克,只有被稱作“死亡之路”的安曼—巴格達高速公路可以通行。對于韓傳號來說,他將要踏進一個陌生的國度,戰火仍在燃燒,一路吉兇難料。美英對伊拉克開戰以來,已有12名記者在戰地報道中先后遇難。
進入伊拉克境內,路兩邊報廢車輛舉目可見,夏季暴曬后的路面上汽車極易爆胎。戰爭開始后,這條路上常有劫匪設卡打劫。韓傳號強打精神不睡覺,還不時給約旦司機抹清涼油提神。
下午3點多,汽車駛進了一個灰乎乎的城市。迎面吹來的風夾著熱氣,裹著塵土砸在臉上。街上行人不多,幾個小孩在街角踢足球,看不到荷槍實彈的美軍大兵。這就是巴格達?韓傳號的心里充滿期待和疑問。
巴格達電力供應時好時壞,分社的老式發電機聲音大得像手扶拖拉機。吃了在伊拉克的第一頓飯后,韓傳號躺在床上,頭剛貼枕頭就進入了夢鄉。正是盛夏時節,房間內熱得像蒸籠。戰爭期間,巴格達的政府建筑、外國機構多遭到搶掠和破壞。好在分社位于平民區,有雇員照看。
因市區通訊中斷,韓傳號等人發稿、對外聯絡都要依靠海事衛星,新聞來源少得可憐。有一天凌晨一點多,韓傳號發完照片,突然聽見頭頂飛機螺旋槳的聲音。同事們一直擔心,分社5部海事衛星容易形成相對集中的信號源;如果美軍截獲信號卻弄不清其目的,就有可能扔炸彈。韓傳號急忙關燈,拔掉海事衛星的電池,叫醒睡著的同事后跑到樓下關了發電機。盡管樓頂有用黑膠布拼成的“TV”字樣,兩架美軍直升機還是在分社上空盤旋了足足一小時才離開。
夜色籠罩下的巴格達并不平靜。在房間里聽得到劈劈啪啪的槍聲四起,像在放鞭炮。在巴格達的最初一周,韓傳號晚上不敢睡得太死,第二天又會疲憊不堪。后來日常采訪太累,他經常倒頭就睡。
戰爭期間,伊拉克民間武器泛濫。5月1日,巴格達火車站附近的儲油罐突然爆炸,韓傳號趕到現場,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焦味,一具燒焦了的尸體從濃煙中被抬出。后來才知道,是有人開槍慶祝巴格達部分地區恢復供電,結果子彈打在儲油罐上,引起的爆炸致6人死亡、多人燒傷。就在兩小時前,一名男孩拿真槍當玩具,不慎走火打傷了他的妹妹。
光天化日下的持槍搶劫事件屢屢發生,劫匪甚至連新婚車隊都敢搶。分社附近有一名15歲的少女遭到綁架。記者們外出需要處處小心,盡可能結伴而行,好有個照應。晚上回分社發稿時,盡管屋里熱得要命,韓傳號也只能關窗拉簾,以免招來莫名其妙的子彈。
5月6日上午,韓傳號采訪時路過巴格達的兩伊戰爭紀念館,望見兩個半桃形藍色建筑前停著一輛美軍坦克。畫面很漂亮,但他剛按下快門,就有美國兵過來沒收相機,因為這里是美軍基地。足足等了兩個小時,美軍還是扣留了3張相機儲存卡。次日,他們告訴韓傳號,存儲卡已被銷毀。后來每拍美軍,韓傳號都不厭其煩地詢問是否允許拍照。
6月中,韓傳號離開巴格達,取道約旦回國。
今年是伊拉克戰爭10周年,回憶這段戰地采訪經歷,韓傳號用“無知者無畏”形容自己。
印度:獲得拍攝機會是關鍵
2000年后,攝影部開始在國內分社選拔駐外記者。之前,僅總社記者及少數懂小語種的分社攝影記者才有機會。通過新華社人事局和攝影部組織的駐外考試后,韓傳號2005年被派往印度,任新德里分社攝影記者。
夏季新德里最高溫度往往超過40℃,即便在空調房里不干活也不停冒汗,汗珠有黃豆粒那么大。外出采訪回來,衣服上到處是白花花的鹽漬。
新華社駐外記者往往需要“一專多能”,新德里分社滿編也就4個人。除印度境內的攝影采訪,韓傳號在分社的工作內容還包括:收發文傳電報、修理辦公電器、擔任現金出納、發展攝影雇員等等。
在甘肅采訪時因新聞熱點較少,攝影記者不太會因拍一張照片而你爭我搶。到了印度情況則完全不同,絕大部分媒體是市場化的,大家都想獲得最好的畫面,所以采訪時常會互不相讓、誰也不客氣。印度攝影記者大多很敬業、專業化程度很高,重要的時政新聞,很多人會提前一兩個小時就去排隊;一些白發蒼蒼的老攝影記者,活躍程度也絲毫不輸給年輕人。
在陌生的環境里與各新聞機構頂尖“選手”同臺競技,韓傳號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但變壓力為動力,努力提高影像質量只是一個方面。他認為,最關鍵的是要獲得拍攝機會。
2006年7月6日,中印重開乃堆拉邊貿通道。從印度錫金邦進入乃堆拉關口,新華社等中方新聞機構和媒體很早就向印度外交部申請,直到開通前一天才獲得同意。錫金因處在邊境地帶被印度列為管控區域,中國、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公民此前是不能進入的。 剪彩儀式上,中國這邊忙著拍攝的只有新華社、央視等少數攝影攝像記者;而印度這邊則被紛至沓來的記者擠“爆”了。韓傳號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土坡,從高處記錄下了這一難得的瞬間。一名愛爾蘭攝影記者得知新華社攝影記者分別在中、印兩邊采訪后,羨慕地說:“這才是全方位的記錄。”
2006年7月,印度金融中心孟買發生7起鐵路連環爆炸,超過200人遇難。韓傳號趕到現場已是傍晚,被炸損的車廂里幾名安全人員在進行事故調查。由于當時只有他一名攝影師在場,因而獲準進入車廂內拍攝,條件是向他們提供部分照片。車廂內,帶血的衣物、被炸成碎片的人體,種種慘不忍睹的細節。他差點就吐了出來,但還是硬著頭皮拍完現場。 駐印兩年,韓傳號學會了幾句簡單的印地語,也會像印度人那樣輕晃腦袋、用搖頭表示同意。他說,無論貧賤還是富裕、匆忙還是悠閑,印度人從容不迫的心態最值得我們學習。
浙江:“轉型升級”
韓傳號從印度回國后,調到新華社浙江分社攝影組工作。這里可謂“兵強馬壯”,好幾個記者都是研究生,而本科學歷的他是“文化程度最低”的。浙江經濟正在轉型升級,韓傳號認為自己同樣也在經歷艱難的“轉型升級”。其實他說的“升級”也出于一些對新環境的不適應——新華社記者常常會有崗位的變動,特別是派駐國外的記者,在國外干了兩三年,回來后發現,國內變化非常之快,原來熟悉的領域、人脈關系都變化了,要重新開始找感覺。
2012年8月,強臺風“海葵”正面登陸浙江并橫掃全省。已在浙江工作3年的韓傳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參與臺風報道,被安排到登陸點附近“蹲守”。在寧波市寧海縣長街鎮,為拍臺風后農作物被淹的畫面,他趟著齊腰深的水想靠近些,不料滑進了水渠里。慌亂中他居然一手將相機舉高到頭頂,相機沒進水,但水已淹到脖子了。
“海葵”報道進入尾聲,他選擇繼續留在寧波,關注城市內澇問題。一天后,舟山市岱山縣長涂島水庫發生垮壩事故。此時身在寧波的韓傳號距舟山最近,在“大部隊”到達之前,他又及早出現在垮壩事故現場。
老是趕場拍動態新聞,大都是宣傳應景的,韓傳號也擔心以后留不下什么東西。糾結中,他感覺自己仿佛又從 “熟練工”回到“菜鳥”了。
浙江是經濟大省,財經報道是浙江分社最重視的報道領域。韓傳號拍過不少經濟類圖片專題,但總覺得“拿不出手”。
在現有的考核體系下,韓傳號的設想是結合熱點事件做專題,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從他近期的《浙江溫嶺“最牛釘子戶”被拆除》等稿件,能看出他正朝這個方向努力。長遠來看,他更愿意選擇一些“草根人物”,在一定的時間跨度內,記錄他們生命中的重要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