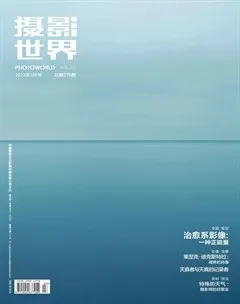再拍風景



每當我外出寫生時,必定會帶上相機,有時甚至會忘了外出本來是要畫畫還是要拍照。每次寫生歸來,相片在數量上總是遠遠超過畫作,但是這些瞬間得來的戰利品絕大多數都是雞肋,扔掉可惜,存著占地兒。
身邊熱衷于風景攝影的朋友,也不屑于看我寫生時拍的照片,他們認為我拍得不夠專注。或許他們的批評也有一定道理。我常讀到,總有攝影家在極其惡劣或者艱苦的環境下等了很久,只為抓拍到最美妙的一瞬。對于此類風景攝影作品,人們常常會情不自禁地用攝影誕生時所夢寐以求的詞句來大加贊美——“像畫一樣的照片!”因為像畫一樣,照片就更具有藝術性、更有價值了嗎?而在博物館中,面對大幅寫實油畫,我也不止一次地聽到的觀眾情不自禁地嘖嘖稱贊:“畫得像照片一樣(逼真)!”
為什么人們會下意識地將風景繪畫和風景攝影作比較呢?我猜想或許是因為這二者在視覺上與自然界呈現的表象相似,與我們的肉眼所見或觀看經驗相似。二者除了都具有擬像的功能外,它們的一些創作方法也類似。印象派畫家也有過專注描繪戶外特定時間的畫作,比如克勞德·莫奈的系列作品《魯昂大教堂》。為了研究光線、色彩和形體之間的關系,莫奈反復地描繪不同時刻光線下的魯昂大教堂。比如畫清晨時分,他會利用多個早上來完成一幅作品。莫奈的這種創作方法與風景攝影師的工作方法都是為了適應流逝的特定瞬間。然而,莫奈筆下的晨曦不是一個特定的時刻,而是一個廣義上的清晨時分。《魯昂大教堂》系列作品表現的瞬間其實并不短暫。繪畫中描繪的瞬間與攝影中描繪的瞬間是不同的。前者重共性,后者重個性。
為什么要等待某一特定時刻呢?這是寫實風景畫和攝影都要考慮的美學問題,也是風景畫與攝影的不同之處。大自然中光線瞬息萬變,對于記錄正在發生變化的事物,攝影的高效遠勝于繪畫媒介;從借物抒懷和表現共性方面,風景畫似乎有更多的施展空間。
拍攝風景與畫風景,差異是基于攝影與繪畫兩種媒介的不同,以及因此而導致的觀看的不同。那么,風景畫與風景攝影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但是,為了找出繼續觀看風景的新鮮感,我姑且將考察的范圍或基點設定在再現型風景攝影和繪畫上,對這二者做了一番比較,在繁復的思緒中大致淘揀出如下結果:
1.風景攝影需要被拍攝的對象,這個對象需客觀存在。
風景畫可以是摹擬現實的,也可以是主觀虛構的。
2.傳統風景照的一次曝光表現現實中的某一具體時刻(紀實性是基礎)。
風景畫不必表現現實中的某一具體時刻(可以表意或者表現動機)。
3.風景攝影可以被機械復制。
風景畫(除版畫外)不可機械復制。
4.風景攝影以瞬間代替恒久——凝固時間。
風景畫用長時間堆砌出瞬間。
5.風景攝影以時間描述風景。
風景畫以風景描述時間。
6.風景照片較接近于視網膜的信息過濾。
風景畫基于大腦對視覺信號的處理,是信息的主觀表達。
7.風景攝影可以轉化成風景畫。
風景畫無法轉化成風景攝影。
8.風景攝影較易上手,只需調整拍攝參數按下快門。
風景畫需要通過經過訓練的手才能更逼真,創作需要較長時間。
這些曾經隱匿在我意識深處、并且不斷煩擾我的異同之處,終于為我打開了一扇天窗。通過上述總結不難看出,不管是二者的契合還是博弈,都和現實與經驗、時間與觀看、擬像與表現方式相關聯。這兩種媒介的相異之處,也暗示出人們對它們既有屬性的依賴。簡單地說,就是人們潛意識中會不自覺地認為它們就應該這樣。其實,不管是風景攝影還是風景畫,這二者都已是主觀化的風景,是選擇的結果,是現象,是先驗引導的觀看。我想,若要找到觀看風景的新鮮點,或許應該從它們已經存在的異同之處出發。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可以轉化嗎?攝影是否也可以像繪畫一樣用長時間來表現風景?如何探尋攝影和繪畫都未曾呈現過的風景影像?如何跳出經驗的束縛,去看到就在眼前、卻從未看到的風景呢?
時間和觀看是視覺影像存在的前提,因此,這一系列現象學的疑惑,催生出了我的長時間曝光風景攝影系列作品。我也期待這些影像以及所延伸出的視覺經驗,會為我的風景畫創作帶來更多的契機。
我的此類風景攝影作品中,《自然詩畫》系列呈現的是欣賞自然之美的更多可能性,展示我們經歷而無法看到的景觀,將慣常經驗轉化為非比尋常的自然詩畫。例如,《自然詩畫 壹》的曝光時間為10小時,經歷了由日出到日落的過程。畫面中的白色弧線是太陽運行的軌跡。由于拍攝時相機機位固定,鏡頭視角范圍有限,畫面中未能記錄下最后的日落過程。在生活中看似平淡尋常的一天,通過時間與攝影耐心平靜的合作,展示給我們非凡美妙的視覺體驗和信息。
我曾經樂此不疲地混入展覽我作品的畫廊,站在觀眾背后聆聽他們的評論。“嘿,這道亮光是什么呀?”“可能是火箭?”“是節日的煙花吧。”“我認為是消防栓向外噴射的水柱。”所有這些具有創意的猜測,都豐富了這張風景照的外延,同時也體現出人們相關視覺經驗的缺乏。
有時,我會冒昧地插一句:“這是太陽十小時運行的軌跡。”“哈哈,你真會開玩笑。你是說這是用Photoshop做的吧!”這幅作品每次展出時,我總會聽到類似的分析。數碼影像編輯技術已經深深地植入許多人的慣性思維,這種慣性容易將不同媒介(比如傳統膠片攝影和數碼攝影)進行不對稱的比較,從而忽視了某一媒介的特點或優勢。
我的長時間曝光風景攝影系列作品之《房子的誕生》,記錄的是蓋房子的全過程,它的曝光時間是四個月。在這個建筑項目開工伊始,我將相機安裝在施工現場旁的一棟建筑上。將快門打開后,底片就成為了這個工地日夜不眠的守衛者。
四個月后,房子完工,我將相機拆下。沖印出的照片見證了這棟房子誕生的過程。作為目擊者,這張照片中蘊含著大量的信息,是一般快速曝光的攝影影像所無法企及的。有人說這棟建筑似幽靈一般,因為整棟房子是透明的,內部的結構都能夠看到。正是這種不同程度的透明,暗示了蓋房子的過程。由于地基最早蓋好,在蓋房子的過程中曝光最充分,所以在畫面里的整個房子中是最清楚的;而房頂最透明,正說明了它是最后蓋上去的。
在《房子的誕生》中,人為的對地貌的改造和自然本身對地貌的改造在同時進行著。例如,經歷了四個月的夏季,遠處的山巒也在發生變化——由于樹冠在不斷生長,所以山似乎也在長高。照片中豐富的影像細節,為觀者提供了不同于短時曝光的視覺體驗,可以引發對人類活動和自然變化的思考,為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做了一次嘗試。畫面左上明亮的藍色線條,是太陽在這4個月中的部分移動軌跡。如果亮藍色的線條是完整的,說明這天的這個時段天空晴朗;如果亮藍色的線條斷斷續續甚至呈現為亮點,說明那段時間是晴間多云;亮藍色線條之間的深色線條,則說明當時在陰云密布或正在下雨。這些美麗的線條,都是太陽在畫面中留下的筆觸。賓州州立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格瑞姆·蘇利文教授曾形象地把太陽的這些運行軌跡比喻為自然天空之條碼。也就是說,這些線條同時具有并傳遞著審美和科學的信息。
我的長時間曝光風景項目仍在進行著,每一幅成功的作品都會給我帶來驚喜。發現風景更加豐富的內容,讓我對自然、對身邊發生的一切有了不同以往的認識。隨著這一攝影實驗的不斷發展,一些新的關于風景攝影和風景繪畫的問題又隱隱閃現,如同舊友未辭而新朋又至。或許,這其中并沒有答案,但我卻體悟出一個道理:經驗需要質疑,知識也需要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