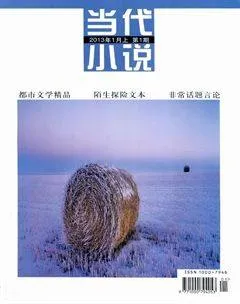經(jīng)過(guò)
天剛蒙蒙亮,三亞便推開(kāi)了大門(mén),又回身把門(mén)關(guān)上了。再回過(guò)身來(lái),目光便落在了他的車上。
三亞的車是一輛出租車,就停在大門(mén)旁邊,雖然停在了一棵樹(shù)下,但現(xiàn)在是深秋,樹(shù)上的葉子早就落光了,車身不可避免地落上了一層露水,密密匝匝的小水珠遍布車身表面,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晶瑩剔透,閃著光亮,便讓那車給人一種簇新的錯(cuò)覺(jué)。但三亞知道,天亮了,露水干了,那車就會(huì)變成一張大花臉。這是三亞不能容忍的。
三亞當(dāng)過(guò)兵,是團(tuán)機(jī)關(guān)衛(wèi)生隊(duì)的衛(wèi)生員。雖然機(jī)關(guān)不像連隊(duì)要求那樣嚴(yán)格,但只有他和另外一個(gè)衛(wèi)生員的宿舍里從來(lái)都被他收拾得干干凈凈。為此,衛(wèi)生隊(duì)那個(gè)曾經(jīng)在老山前線丟掉一只眼的獨(dú)眼龍隊(duì)長(zhǎng),有一回便用那只好眼斜著三亞,跟他開(kāi)起了玩笑。三亞啊,看你那么費(fèi)勁兒,搞得我都?jí)毫πU大的。又覺(jué)得這話不太像領(lǐng)導(dǎo)該說(shuō)的,便呵呵笑著補(bǔ)充道,也好,當(dāng)兵嘛,就該有個(gè)兵樣。當(dāng)時(shí)三亞還摸著腦袋,不好意思地笑著,但過(guò)后還是老樣子。這樣堅(jiān)持了兩年,三亞就多少有了些潔癖。雖然這時(shí)三亞退伍已經(jīng)好幾年了,但那種潔癖多多少少還是在他身上保留了下來(lái)。
以往,三亞也是這個(gè)時(shí)間出門(mén)的,他要趕去火車站。有趟火車將在不久后進(jìn)站,停下,然后又開(kāi)走。他要趕在旅客出站前把車停到站前的路邊上,等候他一天里的第一個(gè)乘客。兩年來(lái),他的每一天差不多都是這樣開(kāi)始的。
出發(fā)前他會(huì)把車從頭到尾檢查一遍,看看機(jī)油和冷卻水,看看輪胎的氣壓,確定沒(méi)有問(wèn)題了便把車發(fā)動(dòng)起來(lái),先熱著,再把車收拾一番。盛水的小桶是出門(mén)時(shí)就拎出來(lái)的,就放在車身一側(cè),他會(huì)先把車的四門(mén)全部打開(kāi),把里面的濁氣完全地釋放出來(lái),再把腳墊抽出來(lái)抖摟干凈,放在旁邊的水泥地上,然后便開(kāi)始擦車。他總是擦得很仔細(xì),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甚至連輪轂的縫隙里,到最后,也會(huì)用剩下的水沖洗得锃明瓦亮。等做完這一切,那車,好像便洗去了一天的風(fēng)塵,重又煥然一新了。等他再坐進(jìn)車?yán)铮衍囬_(kāi)上路,掃一眼一塵不染的車內(nèi)空間,心情也會(huì)跟著明朗起來(lái)。
可是今天,三亞卻沒(méi)有做這些。離開(kāi)大門(mén),他朝灰蒙蒙、空蕩蕩的街上望了一眼,能看到的范圍里只有一條不知誰(shuí)家的狗一嗅一嗅地沿路邊走著,遠(yuǎn)遠(yuǎn)地望他一眼,便心虛似的夾起尾巴跑掉了。望著那狗消失的地方,更加空蒙的街巷,三亞的腦袋里突然閃過(guò)他已經(jīng)去世的父親的面龐,那雖然只是一個(gè)短暫的瞬間,但他父親投向他的眼神,眼神里的那種凄惶,還是一下子擊中了他,讓他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酸到了心里。但他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收回目光,快步走到了車子跟前。
已經(jīng)開(kāi)了車門(mén)了,三亞還又回過(guò)頭,望了一眼他剛剛離開(kāi)的大門(mén)和院子。
大門(mén)是那種最簡(jiǎn)單的門(mén)樓和兩扇鐵皮門(mén),門(mén)樓上長(zhǎng)滿了雜草,鐵皮門(mén)上的油漆已經(jīng)脫落得有些斑駁。院子里幾乎全是房子,或者有一些也算不上房子,只是在房子和空地上搭建出來(lái)的棚子,烏烏壓壓、搖搖欲墜的模樣。開(kāi)發(fā)商和政府已經(jīng)跟村里簽訂了拆遷協(xié)議,不久后所有這些都將被拆掉,按面積給予補(bǔ)償,那將是一筆很大的款項(xiàng)。
但這跟他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
三亞看著這個(gè)兩年多來(lái),被所有人稱為他家的地方,此時(shí),他卻清晰地感覺(jué)到了一種隔閡,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jué),好像他看到的只是一張沒(méi)有溫度的,已經(jīng)泛黃的,與己無(wú)關(guān)的舊照片上的景象。
三亞把車開(kāi)出了村子。一出村子也就進(jìn)入了市區(qū)。
當(dāng)年三嬸跟他提到這家人的時(shí)候便是這么說(shuō)的,緊挨著城里,沒(méi)準(zhǔn)哪一天就拆遷了,就成了城里人,政府給的拆遷補(bǔ)貼還有占地費(fèi)啊什么的,這輩子都花不完。
可他最終來(lái)到這里真的是為了這個(gè)嗎?那時(shí)他退伍回來(lái)已經(jīng)三年了,他用退伍費(fèi)學(xué)了駕照,在一個(gè)建筑公司做司機(jī)。除了剛回來(lái)那陣子,三年里他幾乎沒(méi)回過(guò)家,即便過(guò)年他也只是讓人把錢(qián)給他母親捎回去。他只是會(huì)抽空,開(kāi)車去他父親的墳上一趟。他父親的墳在遠(yuǎn)離村子的河灘上,一個(gè)孤零零的墳堆,才幾年,已經(jīng)風(fēng)化得看不出原來(lái)的模樣。他到了那里也就是在墳堆旁邊的空地上坐一會(huì)兒,抽一地?zé)燁^又回來(lái)了。他是不愿進(jìn)到村里去的,那個(gè)他出生并長(zhǎng)大的村子,讓他感到的只有恥辱。
但是現(xiàn)在,這些似乎都已經(jīng)淡了,只有不時(shí)出現(xiàn)在他眼前的父親的眼神,一下一下刺痛著他。那眼神的出處是他退伍前最后一次探親時(shí)。假期結(jié)束,父親送他去村外路邊上等去城里的客車,臨上車了父親卻突然對(duì)他說(shuō),三兒,能不回來(lái)就不回來(lái)吧,留在部隊(duì)上。說(shuō)完這句父親眼里突然閃出了淚花,又趕忙用袖子抹了,勉強(qiáng)沖他一笑。但是馬上,他卻從父親望向別處的眼神里讀出了一份說(shuō)不出的凄惶。后來(lái),這凄惶在他退伍離開(kāi)部隊(duì)時(shí),也曾在他心里出現(xiàn)過(guò)。坐在送退伍兵去往火車站的大卡車上,望著越來(lái)越遠(yuǎn)的營(yíng)區(qū),他就有了這樣的感覺(jué),其中甚至還包含了生離死別的決絕和無(wú)奈。也正是那時(shí),他突然明白了當(dāng)時(shí)父親眼神的含義,后來(lái)發(fā)生的事情,也許那時(shí)就已在父親的預(yù)料之中了。
他其實(shí)是可以像父親希望的那樣留在部隊(duì)的,臨近服役期滿獨(dú)眼龍隊(duì)長(zhǎng)就找他談話,讓他不要做退伍的打算,隊(duì)里要留下他,他還為此開(kāi)心過(guò)好一陣子,不時(shí)的就會(huì)憧憬一下父親期望他留在部隊(duì)簽個(gè)合同兵的愿望實(shí)現(xiàn)時(shí)的情景。可是他的好心情卻隨著父親的突然去世戛然而止。消息是回家探親的王可然帶回來(lái)的。王可然家就在與他家相鄰的村子里。同時(shí)帶回來(lái)的還有王可然的憤怒。王可然說(shuō)他父親是喝藥死的,之前被老光棍劉小順給打了。王可然還想說(shuō)點(diǎn)什么,卻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只是咬牙切齒道,弄死他,回去,弄死他!
三亞給他大姐打電話,原本他大姐是不想說(shuō)的,被他問(wèn)得緊了,大概也是想這事早晚也是瞞不住的,便吞吞吐吐地說(shuō)了,咱娘那樣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這么大年紀(jì)了還是不知道顧個(gè)臉面,她和劉小順那個(gè)熊黃子在一起,被咱爹碰上了,咱爹罵了他們,結(jié)果被那個(gè)熊黃子給揍了一頓,想不開(kāi)就喝了藥。完了大姐還一遍遍叮囑,這不管你的事兒,咱娘愿意的誰(shuí)也管不了,人家又沒(méi)有灌咱爹喝藥,你在部隊(duì)好好呆著吧,千萬(wàn)別回來(lái),再說(shuō)現(xiàn)在他們也跑了,也不在家了。可是大姐還沒(méi)說(shuō)完,三亞便把話筒砸在了話機(jī)上,他感覺(jué)自己的牙就要咬碎了。如果這時(shí)劉小順站在他面前,他一定會(huì)一刀捅了他的。
等平靜下來(lái),他也想不管了,怎么管呢,丟人呢,可是他一這樣想,父親的那雙眼睛便在他眼前不停地晃著,他心里的怒火便會(huì)重新被點(diǎn)燃。他想怎么也得好好教訓(xùn)教訓(xùn)劉小順那個(gè)熊黃子,他就想到了打斗的場(chǎng)面,萬(wàn)一要是控制不住呢,他想他也許會(huì)打死他的,他心底里是有種要打死他的渴望的,甚至這渴望還特別強(qiáng)烈。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就想還是脫掉這身軍裝吧。他不想給這身軍裝染上哪怕一丁點(diǎn)的污點(diǎn)。于是宣布退伍前幾天他找到了獨(dú)眼龍隊(duì)長(zhǎng),堅(jiān)決要求離開(kāi)了部隊(duì)。但是后來(lái),事情卻沒(méi)有朝著他預(yù)想的方向發(fā)展。
他回來(lái)不久便在城里的一個(gè)出租屋里,找到了他母親和劉小順,可是他揮起的拳頭最終卻沒(méi)能落下去。那時(shí)候他娘就跪在他的腳邊上,抓緊了他的褲腿,她說(shuō)你打吧,你把我們都打死吧!她說(shuō),他是你爹!
他舉起的拳頭便懸在了半空里,被他抓住領(lǐng)口的劉小順還保持著躲閃的架勢(shì),瞪大了眼睛看著他,但那眼神里除了一點(diǎn)點(diǎn)害怕,卻沒(méi)有一絲一毫的敵意,反倒順著他娘的話說(shuō),沒(méi)錯(cuò)沒(méi)錯(cuò),你娘說(shuō)得沒(méi)錯(cuò)。透著說(shuō)不出的討好和巴結(jié)。
其實(shí)從小到大,三亞沒(méi)少聽(tīng)了村里人對(duì)他娘和劉小順的風(fēng)言風(fēng)語(yǔ),甚至說(shuō)他不是他爹的種的,可這時(shí)從他娘嘴里說(shuō)出來(lái),一時(shí)間,還是讓他感到震驚、茫然、無(wú)所適從。他再次感到自己的牙就要咬碎了,可是拳頭卻失去了落下去的方向。
他甚至哆嗦著一句話都說(shuō)不出來(lái)。
然后他一拳砸在自己的另一只拳頭上,甩開(kāi)他們,從屋里跑了出來(lái)。站在大街上了,他的身體還在不停地抖著,篩糠似的,根本控制不住。那時(shí)正是隆冬,風(fēng)一吹,讓他的身體好像整個(gè)都洞開(kāi)了,風(fēng)一直灌進(jìn)他心口里,說(shuō)不出的冷。
后來(lái)他母親和劉小順又回到了村里。他們?cè)揪褪菫榱硕闳齺啿排艹鰜?lái)的,既然三亞沒(méi)把他們?cè)趺礃樱僬f(shuō)他們也沒(méi)錢(qián)再呆在城里了,也就臉一抹回去了,索性還住到了一起,兩口子一樣過(guò)起了日子。也就是那之后,三亞再也沒(méi)有回過(guò)村里。
他三嬸來(lái)找他時(shí)說(shuō),像你這種情況,你說(shuō)怎么辦,還不如找個(gè)好人家倒插門(mén)算了。后來(lái)三嬸就帶他來(lái)到了他現(xiàn)在的這個(gè)家,見(jiàn)到了后來(lái)成zuCalofYFJYCiegOCnxEpQ==了他老婆的魏月芝和她的父母。魏月芝的父母只有三個(gè)女兒,沒(méi)有兒子,前邊兩個(gè)女兒都已經(jīng)出嫁了,剩下最小的魏月芝,就打算讓她招一個(gè)上門(mén)女婿,老兩口也好老了有靠。
那時(shí)三亞覺(jué)得這家人還是不錯(cuò)的,魏月芝的爸爸是個(gè)退休教師,雖然是民辦教師熬上來(lái)的,可還是比一般他這個(gè)年紀(jì)的村里人顯得有文化多了。而那時(shí)魏月芝在城里一個(gè)服裝店打工,看攤賣衣服,加上本身就是城郊長(zhǎng)大的姑娘,很會(huì)收拾,看上去跟城里女孩似的,很洋氣。魏月芝和她父母對(duì)三亞也沒(méi)什么意見(jiàn),怎么說(shuō)三亞都是當(dāng)過(guò)兵的人,看上去就非常精神。或者在魏月芝的父母看來(lái),三亞有家不能回的情況,對(duì)他們一家反倒不是什么壞事兒。
后來(lái)三亞和魏月芝便訂了婚。
進(jìn)市區(qū)不久三亞便把車停在了一家銀行門(mén)口的路邊上。天已經(jīng)大亮,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都多了起來(lái),但街上的嘈雜好像跟他完全就是兩個(gè)不同的世界,相隔的不僅僅是車門(mén),好像是一堵厚厚的、難以穿越的城墻。
銀行還沒(méi)有開(kāi)門(mén),電鍍的卷簾門(mén)仿佛水銀瀉地,安靜、光潔,冷冷地反著光亮。三亞坐在車上,把那盤(pán)灌滿《打靶歸來(lái)》的歌帶塞進(jìn)了錄音機(jī)里,響起的歌聲仿佛又把他帶回到在部隊(duì)的日子,跟著救護(hù)車去靶場(chǎng)保障,時(shí)不時(shí)他也會(huì)打上幾顆子彈,射擊的快感讓他迷戀,但更讓他迷戀的還是打靶結(jié)束,撤離的隊(duì)伍在調(diào)整好步伐后一定會(huì)唱起這首歌。一個(gè)隊(duì)伍伴著步伐的合唱雄渾、蒼勁,那種震撼顯然不是錄音機(jī)里的歌聲可比的。事實(shí)上,這時(shí)響在三亞心中的,也許正是那穿越時(shí)光而來(lái)的歌聲。
平時(shí),三亞都是早上剛把車開(kāi)出來(lái)的時(shí)候放這首歌的。他專門(mén)買的空白磁帶,把整盤(pán)磁帶都錄滿了這首歌,這保證了只要他把磁帶塞進(jìn)錄音機(jī),響起的就一定是這首歌的旋律。只是他每天聽(tīng)這歌的時(shí)間并不是很多,每當(dāng)他一天里的第一個(gè)乘客上車時(shí),他已經(jīng)提前把它換成了收音機(jī)里的交通臺(tái)。這首歌,他似乎不太愿意與人分享,或者潛意識(shí)里,他是怕乘客會(huì)對(duì)這首歌指手劃腳,或者有不恭的言辭,那樣可能會(huì)傷到他。
某種意義上,這是屬于他一個(gè)人的歌。
歌聲里,他的眼淚開(kāi)始不停地流下來(lái)。以往聽(tīng)這首歌時(shí),他也會(huì)有這樣的沖動(dòng),但他馬上便會(huì)自嘲地笑一笑,讓淚水也就是在眼眶里打個(gè)轉(zhuǎn)兒,就回去了。但這時(shí),他卻絲毫沒(méi)有把眼淚阻斷的念頭,反倒希望它們盡情地奔涌出來(lái)。洶涌而出的淚水好像正把他心里淤積的某些東西不斷地帶出體外,漸漸地讓他心里好像湖水一樣越來(lái)越安靜、澄澈。當(dāng)眼淚自然而然地止住時(shí),他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guò)的輕松。
他的對(duì)面,太陽(yáng)從一個(gè)房頂上探出頭來(lái),紅彤彤的。陽(yáng)光穿過(guò)前擋玻璃晃著他的眼。他隨手把遮陽(yáng)板拉了下來(lái)。遮陽(yáng)板背面的小鏡子映出了他的臉,但過(guò)了好長(zhǎng)時(shí)間,鏡子里的臉才在他的大腦中清晰起來(lái)。同時(shí)清晰起來(lái)的還有他額頭上的傷痕和兩天前的那個(gè)晚上。那個(gè)晚上,三亞收車到家時(shí)已經(jīng)十一點(diǎn)多了,堂屋里仍燈火通明,不時(shí)響起麻將和笑鬧聲。土地賣完了,有了錢(qián),也有了閑的村里人便把打麻將當(dāng)成了職業(yè),不知從哪天起,他們家便有了個(gè)固定的牌局,從早到晚,總會(huì)聚著一些人,把堂屋里弄得烏煙瘴氣。
但三亞已經(jīng)習(xí)慣了,或者也并不關(guān)心,他跑了一天車,累了,晚飯還沒(méi)吃,回到家,堂屋也沒(méi)去便進(jìn)了廂房,也就是他和魏月芝的房間。換下衣服,又去了廚房。如果沒(méi)有剩飯他會(huì)下上一碗面條,以往他也都是這樣對(duì)付的。沒(méi)想到這天他剛剛走進(jìn)廚房,魏月芝便從堂屋里跑了出來(lái),怒沖沖地叫著他的名字,三亞,你給我說(shuō),那錢(qián)哪來(lái)的?
三亞一時(shí)沒(méi)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但很快也就想到了他放在床下盒子里,又塞在一件舊軍裝口袋里的一千來(lái)塊錢(qián)。那是他從每天的收入里一點(diǎn)一點(diǎn)摳出來(lái)的。每天收車回來(lái),魏月芝都會(huì)把他包里和身上的錢(qián)翻出來(lái),留下些零錢(qián),剩下的便都收了去,幾天湊個(gè)整數(shù)再存到銀行里。開(kāi)始是說(shuō)這樣存著,湊個(gè)大點(diǎn)的數(shù)就把買車借的錢(qián)先還一些。買車的錢(qián)一部分是三亞攢的,還有一部分是向他大姐和王可然借的。可銀行卡在魏月芝手里,一年多時(shí),想想也該有幾萬(wàn)塊錢(qián)了,三亞想先還一部分,可每次三亞一提出來(lái),魏月芝總說(shuō)慌什么,放銀行里還能生些利息呢。三亞第一次跟魏月芝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就是因?yàn)檫@事兒。三亞覺(jué)得錢(qián)是借人家的,既然有了就該還給人家。可魏月芝好像并不這么想,看她那眼神兒,就讓人覺(jué)得,到了她手里的錢(qián)再讓她拿出來(lái),簡(jiǎn)直比割她的肉更讓她心疼。一開(kāi)始,銀行卡放在他們房間的抽屜里,魏月芝在上面加了把小鎖。有一天三亞便瞞著她把鎖撬了,拿了卡,又拿了她的身份證,準(zhǔn)備到銀行取了錢(qián),先還了再說(shuō)。可那天他剛剛出門(mén),便被魏月芝發(fā)現(xiàn)了,追出來(lái),把他堵在了離他家最近的她存錢(qián)的那家銀行里。那時(shí)三亞正在排隊(duì),魏月芝沖上來(lái),把他拖了出去,銀行卡也到了她的手里。三亞覺(jué)得自己不是一個(gè)特別敏感的人,但那次他卻對(duì)自己現(xiàn)在的生活產(chǎn)生了很深的質(zhì)疑。后來(lái)他站在銀行門(mén)口,望著魏月芝騎上電瓶車遠(yuǎn)去的背影,突然覺(jué)得屬于他的那顆心似乎被人丟在了腳下,屬于它的溫度正一點(diǎn)點(diǎn)的被什么抽走,這時(shí)他看到了地上的樹(shù)葉,冬天里枯干的樹(shù)葉,在地上,胡亂地被風(fēng)吹著。他感到自己好像就是一片那樣的樹(shù)葉,沒(méi)有了依附和重量,沒(méi)有了水分。
三亞也沒(méi)想到自己會(huì)對(duì)魏月芝動(dòng)手。他摳下這錢(qián)是打算給他母親和小愛(ài)國(guó)的。小愛(ài)國(guó)是今年春天他跑車時(shí),在路邊撿的一個(gè)小男孩,當(dāng)時(shí)才出生不久的樣子,被他送到派出所,又被送到了福利院,起名福愛(ài)國(guó)。這時(shí)小愛(ài)國(guó)已經(jīng)七八個(gè)月了,見(jiàn)了他就會(huì)笑,還朝他揮舞著小手,找他抱的樣子。三亞經(jīng)常去福利院看他,給他帶點(diǎn)吃的和錢(qián)過(guò)去。只是三亞沒(méi)把這事告訴魏月芝,他只是對(duì)魏月芝說(shuō),那錢(qián)是他準(zhǔn)備讓人捎給他母親的,無(wú)論他母親怎樣,這都是他做兒子的該盡的義務(wù)。可魏月芝根本就不想聽(tīng)他解釋,她似乎更想把事情還原一下,便揪著三亞的衣服把他拽進(jìn)了臥室,把錢(qián)從床下他那件舊軍裝的口袋里摸了出來(lái)。顯然,為了想象中的這個(gè)場(chǎng)景,她提前并沒(méi)有把錢(qián)收起來(lái)。魏月芝把錢(qián)拿出來(lái)之后便在三亞眼前不停地晃著,不停地嚷,行啊三亞,你真有辦法啊,你就這樣對(duì)付你老婆啊,你娘那個(gè)熊樣你還給她錢(qián),我給要飯的也不給她。這樣說(shuō)時(shí),她手里的錢(qián)幾次都碰到了三亞的臉。
三亞就是這樣被激怒的,他一把將錢(qián)從魏月芝手里奪了過(guò)來(lái)。魏月芝伸著手撲過(guò)來(lái),也許是想來(lái)抓三亞的臉的,也許只是想把錢(qián)搶回去,但她的手還沒(méi)有夠到三亞,便被三亞一把推倒在了她拉開(kāi)的床盒子里。
魏月芝的母親聽(tīng)到動(dòng)靜先跑了過(guò)來(lái),隨后她父親也跑來(lái)了。
她母親還只是嘴里叨叨著,怎么了?怎么了?而她父親,到了門(mén)里,看著坐在床盒子里扭動(dòng)著身子,哭嚷不止的女兒,又看著三亞,眼睛里突然便冒出火來(lái),那樣子,就像誰(shuí)動(dòng)了他的心頭肉一般,突然便將手里拿著的一個(gè)玻璃茶杯,連水一起,狠狠地砸向了三亞,并大吼了一聲,滾!給我滾!然后又叫囂道,什么東西,還反了你了!
但是現(xiàn)在再想起來(lái),三亞已經(jīng)沒(méi)有了當(dāng)時(shí)的憤恨,好像那件事情根本就不是發(fā)生在他身上的,好像他穿過(guò)他父親的眼神所看到的景象一樣模糊和虛幻,倒是后來(lái),一家人都將自己心中的不滿發(fā)泄完了之后,他一個(gè)人躺在床上的那種感覺(jué)依然清晰。他躺在床上,卻明顯地感到心已不在了那里。可是心在哪里,他也說(shuō)不清楚,只是又想起了他和魏月芝第一次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時(shí),他在銀行門(mén)口看到的那些地上的樹(shù)葉。
那些樹(shù)葉被風(fēng)裹著,飄起又落下。
那天晚上之后,魏月芝便睡去了另外一個(gè)房間里。
接下來(lái)的兩天里,三亞出車回來(lái),也沒(méi)有主動(dòng)走到她和她父母的跟前去。兩天里,大家甚至都沒(méi)有照過(guò)面,冷戰(zhàn)一樣。有時(shí)三亞穿過(guò)院子去房間時(shí),還聽(tīng)到過(guò)從堂屋傳來(lái)的顯然是故意說(shuō)給他聽(tīng)的一些話,那些話里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確的,好像是如果不是他們,他三亞不過(guò)是個(gè)無(wú)家可歸的人,他這樣對(duì)魏月芝讓他們很氣憤,后果很嚴(yán)重。
三亞也覺(jué)得后果很嚴(yán)重,他甚至很清楚地看到了一道裂痕,橫在他和他們之間,很清楚地感到了這道裂痕的不可彌補(bǔ)和難以逾越。
三亞的計(jì)劃大概就是從這時(shí)候開(kāi)始的。他也想過(guò)別的辦法,比如直接提出來(lái)離婚,比如干脆不聲不響地搬出去算了。但是,他馬上便否定了自己的這些念頭,他覺(jué)得很累,心里似乎已經(jīng)聚不起處理這些事的力氣。昨天他路過(guò)一家藥店時(shí),便下車把藥買了。藥是兩種。當(dāng)年的衛(wèi)生員三亞對(duì)各種常用藥品的藥性了如指掌。他知道,這兩種藥品合在一起,將產(chǎn)生足以讓人致命的劇毒。
銀行的卷簾門(mén)終于被人推了上去,運(yùn)鈔車開(kāi)來(lái)又開(kāi)走了。下車前,三亞又看了一眼額頭上的疤痕。才兩天時(shí)間,上面已經(jīng)結(jié)了一層硬硬的痂,呈現(xiàn)出暗紅的顏色,假以時(shí)日這層痂會(huì)逐漸脫落,露出泛白的底痕,再逐漸跟周圍的膚色變得一致。可三亞知道,這個(gè)過(guò)程可能已無(wú)法完成了。想到這里三亞甚至還苦笑了一下。對(duì)著鏡子里的自己苦笑了一下。
三亞下了車,鎖上了車門(mén)。上班的人流高峰已經(jīng)過(guò)去,街上已經(jīng)安靜下來(lái)。這個(gè)秋天里明朗的日子,陽(yáng)光很好,空氣雖有些涼了,但卻干凈,清爽,可以看得很遠(yuǎn)。大團(tuán)的云彩把天空襯托得很高,遠(yuǎn)處的山巒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三亞怔怔地朝遠(yuǎn)處看了一眼,似乎那峰巒疊嶂處,那無(wú)法明確的遠(yuǎn)方,給了他很大的勇氣。他這才走進(jìn)銀行,在一個(gè)柜員窗口前坐了下來(lái),從口袋里掏出銀行卡以及他和魏月芝的身份證。有了他撬鎖那件事之后,這張卡便被魏月芝放在了隨身的包里,這時(shí),卡上似乎還帶著她包里各種化妝品的氣味。這氣味也許曾浸到了三亞心里,也許沒(méi)有。這味道同樣讓三亞感到茫然。
印象中,魏月芝在他心里始終是有些陌生的,結(jié)婚時(shí)他們才認(rèn)識(shí)兩個(gè)來(lái)月。結(jié)婚后他便開(kāi)始跑出租了,早出晚歸,也就是晚上才能跟她聚在一起。開(kāi)始,他對(duì)那樣的相聚是有所期待的,畢竟在魏月芝之前,他甚至連女朋友都不曾有過(guò)。他是想給她那種他想象中的丈夫?qū)ζ拮拥膶檺?ài)的,可慢慢地他卻發(fā)現(xiàn),魏月芝對(duì)他似乎并沒(méi)有太多熱情。他甚至搞不懂魏月芝對(duì)他的那種態(tài)度,好像夫妻就是那樣一個(gè)身份,丈夫做丈夫該做的事,妻子做妻子該做的事,除此之外都是多余的。
三亞也想過(guò),除他之外魏月芝是不是還有別人,但他也只是那么想想,毫無(wú)頭緒。在這個(gè)家里他就是一個(gè)外來(lái)者,他對(duì)他們生活的圈子知之甚少。清晰的只有他和魏月芝之間的那種距離感,始終困擾著他。
這么胡思亂想著,三亞把銀行卡和身份證從窗口遞了進(jìn)去,讓里面的柜員,一個(gè)面無(wú)表情的中年人,幫他查了卡上的余額,又幫他計(jì)算了兩筆款項(xiàng)加利息的總數(shù),然后他才報(bào)出取款的數(shù)目,還又多取了一些。
里面的中年人幾次露出不耐煩的神情,不時(shí)地掃一眼外面的大廳,如果大廳人多,有人排隊(duì),三亞知道他的不滿一定會(huì)發(fā)泄出來(lái),但現(xiàn)在還早,大廳里冷冷清清地,幾乎看不到幾個(gè)人,于是他的不滿也只好憋了回去。看著他的模樣,三亞感到心里突然像秋天里的這個(gè)日子一樣通透起來(lái),他朝窗口里面保持了歉意和卑恭的神態(tài),直到完事。后來(lái),三亞已經(jīng)開(kāi)車上了路,還在努力回憶著他這時(shí)的心情,他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會(huì)突然變得明朗起來(lái),但是他希望自己能保持這樣的心態(tài),這至少會(huì)讓他看上去要正常一些。
三亞的大姐家在一個(gè)叫劉王莊的村子里,離市區(qū)十幾里路。但就是這十幾里路,卻讓這個(gè)村子跟靠近城市的村子有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城邊的那些村子幾乎看不到像樣的新房了,多的是各種建材搭建的棚子,在死心塌地地等待著有一天被鏟車推倒。而這里的人們還要繼續(xù)他們?cè)谶@里的生活和希望。可以看到,很多二層三層的小樓從老舊的平房里伸出頭來(lái),仿佛枯草中冒出的新枝,高挑,雀立,生機(jī)盎然。
這個(gè)季節(jié),麥子種下后,地里沒(méi)什么活了,村里人起床都晚,三亞進(jìn)村時(shí)很多人家都還沒(méi)有起床,但很多人家的大門(mén)卻是敞著的,三亞知道,那一般是家里有上學(xué)的孩子的,孩子早早起來(lái),吃點(diǎn)東西便去了學(xué)校。三亞記得他小時(shí)候也是這樣的,走時(shí)總忘了把大門(mén)關(guān)上,回來(lái)便少不了被爹娘訓(xùn)斥一頓。
但那樣的訓(xùn)斥沒(méi)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陰影,再想起來(lái),甚至有種說(shuō)不出的溫暖,細(xì)細(xì)地在心里流轉(zhuǎn)。于是父親和母親的樣子就又晃動(dòng)在他的腦袋里了。
父親總是胡亂地坐在那里,抽著煙默不作聲,看到他卻會(huì)突然冒出一句,餓了吧,你姐做飯呢。母親總是不在家的,她在別人家的大門(mén)口,在街角的大樹(shù)下,袖著手,跟街上的男人女人們?cè)谡f(shuō)話,不時(shí)便會(huì)爆出哈哈的笑聲,她笑和說(shuō)話的聲音隔著半個(gè)村子都能聽(tīng)見(jiàn)。然后風(fēng)風(fēng)火火地回來(lái),嚷著小菊,你個(gè)死妮子,你死哪去了,要么就嚷趙大河,地里的草都把莊稼吃沒(méi)了,你還有閑心在那里抽煙,少抽棵能死人呀。趙大河是他父親的名字。聽(tīng)到他母親的吆喝,父親也只是用鼻子哼一聲,繼續(xù)又沒(méi)了動(dòng)靜。
小菊便是他的大姐秀菊。三亞的印象中大姐是沒(méi)有上過(guò)學(xué)的,大姐總是呆在廚房里,咣當(dāng)咣當(dāng)?shù)乩L(fēng)箱,煙霧從廚房的門(mén)檐下溜出來(lái),散開(kāi),家里便有了煙火味。那味道讓放學(xué)回到家肚里嘰里咕嚕的三亞,感到特別踏實(shí)。
他還有一個(gè)二姐的,叫小惠,可是三亞沒(méi)見(jiàn)過(guò)二姐,二姐被人領(lǐng)走時(shí)他還沒(méi)有出生。那還是他長(zhǎng)大了才聽(tīng)人說(shuō)的,送走二姐就是為了給他讓路,不然他是沒(méi)機(jī)會(huì)出生的。那時(shí)已經(jīng)開(kāi)始計(jì)劃生育,超生是要被重罰的,有些人家甚至因此被扒了房子。
二姐是被一個(gè)四十多歲的女子帶走的,那是臘月里一個(gè)家家都在準(zhǔn)備年貨的日子,那女子穿著貂皮大衣,戴著金項(xiàng)鏈和耳環(huán),手里拎著一個(gè)很小的、亮閃閃的銀色的包包,從一輛黑色的兩頭長(zhǎng)得一樣的車?yán)锵聛?lái),在村里一個(gè)叫二得子的人的帶領(lǐng)下,扭啊扭啊地便進(jìn)了他家,再?gòu)乃页鰜?lái)一個(gè)手里便牽了小惠。那時(shí)小惠才三歲,邊走邊哭,向后扭著身子,叫著爹和娘。很多年后,對(duì)面胡同里眼睛已經(jīng)半瞎的大奶奶再說(shuō)起這一節(jié),爛桃子一樣的眼睛里仍會(huì)有眼淚流下來(lái)。連個(gè)年也沒(méi)過(guò)上呢,大奶奶總是這樣說(shuō)。
三亞心里對(duì)從未見(jiàn)過(guò)面的二姐是存了一份很深的歉意的。當(dāng)兵回來(lái),三亞去省城找過(guò)在那打工并已安家的二得子。他沒(méi)想把二姐找回來(lái),只是想見(jiàn)上一面,可是二得子告訴他,當(dāng)初把小惠送給人家時(shí)便說(shuō)好了的,不能再聯(lián)系,另外那女的是他剛到省城打工時(shí)的老板,十幾年沒(méi)聯(lián)系了,他也不知道她現(xiàn)在什么地方。
三亞把車停在了大姐家門(mén)口,要下車了才發(fā)現(xiàn)自己臉上全是淚水。他用袖子抹了抹,拉下遮陽(yáng)板,從鏡子里看了看,眼睛有些紅腫,他便把兩只手附在上面使勁兒按著,他不想讓大姐看到自己這個(gè)樣子。自從父親去世之后,他是把大姐家當(dāng)成了自己家的,把大姐當(dāng)成了心理上惟一可以依賴的親人。這樣想著,他心里便禁不住一陣絞痛。
大姐秀菊推開(kāi)大門(mén)看到三亞的車時(shí),三亞在車?yán)镆呀?jīng)坐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秀菊是出門(mén)去趕集的,她和她丈夫農(nóng)閑時(shí)販賣雞蛋,平時(shí)用三輪車?yán)俗呓执铮昙憷郊先ベu,他們的兒子小鎮(zhèn)已經(jīng)上了初中,住在學(xué)校里。
兩口子看到三亞的車,便高興得嚷了起來(lái),叫著三亞的名字,跑過(guò)去。他們都快到了跟前了,三亞才發(fā)現(xiàn)了他們,忙朝鏡子里看了一眼,調(diào)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從車?yán)锵聛?lái)。可是先跑過(guò)來(lái)的秀菊還是從他臉上看出了事兒來(lái),問(wèn)他怎么了,三亞笑笑,說(shuō)沒(méi)事。秀菊顯然不信,叨叨著,卻是無(wú)力的,他們沒(méi)欺負(fù)你吧?又說(shuō),你在人家家,凡事得讓著人家。三亞只是應(yīng)著。
到了家里,三亞把錢(qián)從包里拿出來(lái),大姐看著那錢(qián),又看著三亞,一臉的狐疑,說(shuō)慌什么,三亞說(shuō)有了,大姐便遲疑著問(wèn)多少,三亞便說(shuō)了加上利息一起的數(shù)目,一旁姐夫便不高興了,姐夫說(shuō)三亞,你要用就先拿著,要是不用了就當(dāng)初拿了多少還多少,我和你姐要是拿了你的利息,你讓我們還怎么出門(mén)見(jiàn)人。大姐說(shuō),聽(tīng)你姐夫的。
三亞不想跟他倆爭(zhēng)執(zhí),他覺(jué)得只要一張口他就會(huì)禁不住嚎啕大哭。他從里面抽出一些把剩下的放在了桌上。從大姐家出來(lái),大姐一直跟到他車門(mén)前,還不住地追問(wèn)著,三亞,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因?yàn)檫€錢(qián)的事兒你們吵架了,要是那樣你拿回去就是了,我和你姐夫也不是沒(méi)錢(qián)花的。三亞只說(shuō)了聲沒(méi)事,便坐進(jìn)了車?yán)铮遣桓胰タ创蠼愕模m然他很想再多看大姐一眼,可是想象中大姐的眼神已經(jīng)讓他沒(méi)了再多看一眼的勇氣。
三亞又去了王可然家。等他趕到市里的福利院時(shí)已經(jīng)是上午的十點(diǎn)來(lái)鐘了。在福利院門(mén)口的路邊上,他坐在車?yán)锝o魏月芝發(fā)了一個(gè)短信。他告訴魏月芝,銀行卡被他拿走了,還了借的錢(qián),其他都留在了卡里。
發(fā)完短信他還又等了一會(huì)兒,并沒(méi)有短信回過(guò)來(lái),他知道她肯定還沒(méi)有起床,或者忘了開(kāi)機(jī)。但他并沒(méi)有在意,按計(jì)劃,今天里他還會(huì)給魏月芝再發(fā)一個(gè)短信,等他去福利院看過(guò)小愛(ài)國(guó)之后,他會(huì)直接開(kāi)車去他父親的墳上,到了父親的墳上之后,他會(huì)用短信告訴魏月芝,找個(gè)會(huì)開(kāi)車的人,把車從他父親墳上開(kāi)回去。
是的,在有了這個(gè)計(jì)劃之后,他就已經(jīng)把接下來(lái)的這些事情想了很多遍了,仿佛都已經(jīng)成了發(fā)生過(guò)的事情。
到了父親的墳上之后,他會(huì)用車上帶的那把小鐵鍬在父親墳堆的旁邊挖上一個(gè)坑,不用很大,只要他躺進(jìn)去,身體不會(huì)露在上面就行了,然后他會(huì)躺在里面,把準(zhǔn)備好的藥片一起吞下去。他甚至都想到了自己那時(shí)的心態(tài),躺在那里,土里的涼氣會(huì)一絲絲地透過(guò)衣服,刺著他的身體,那樣子就像小時(shí)候他跟著父母下地,躺在地頭上玩耍一樣。他會(huì)看到天空、太陽(yáng),還有云彩,他會(huì)用最后的時(shí)間想著他的親人們甚至他從未見(jiàn)過(guò)的二姐。
他覺(jué)得只有那樣用力地想著他們,等他到了那個(gè)世界,才不至于將他們遺忘,才有可能在將來(lái)重新遇到他們。他甚至希望,如果可能,在另外那個(gè)世界里他們還是一家人,他們還是自己的姐姐、父親和母親,只是那個(gè)世界里,不要再有現(xiàn)在的這些事情。
他會(huì)淚流滿面,但一定沒(méi)有哭聲。他甚至還想把車盡量開(kāi)到離墳很近的地方,他會(huì)打開(kāi)車門(mén),打開(kāi)錄音機(jī),把音量放到最大,那樣,他躺在那里時(shí)耳邊便會(huì)回蕩著《打靶歸來(lái)》那首歌的旋律。他就會(huì)想起他的那些戰(zhàn)友們,獨(dú)眼龍隊(duì)長(zhǎng),還有跟他在一個(gè)宿舍里住了兩年的戰(zhàn)友劉軍。他會(huì)非常非常地想念他們。
想到父親時(shí),他心里可能還會(huì)冒出一點(diǎn)點(diǎn)就要見(jiàn)到他的喜悅,甚至對(duì)他想象中他們相見(jiàn)的場(chǎng)景產(chǎn)生了一絲迷戀。
可是事情并沒(méi)有朝著三亞想象的方向發(fā)展。
在福利院里,他沒(méi)有見(jiàn)到小愛(ài)國(guó),福利院那個(gè)一見(jiàn)了他便笑瞇瞇的院長(zhǎng)大姨,仍然笑瞇瞇地看著他,說(shuō)小愛(ài)國(guó)被送到省城的兒童醫(yī)院做手術(shù)去了,是先天性心臟病突發(fā)。還說(shuō),當(dāng)初小愛(ài)國(guó)被遺棄,可能就是因?yàn)檫@個(gè),只是并不嚴(yán)重,一直都沒(méi)有發(fā)現(xiàn)。
從福利院出來(lái),三亞已經(jīng)忘記了他原本的安排,他心里幾乎全被要看一眼小愛(ài)國(guó)的愿望給占滿了。他不知道小愛(ài)國(guó)到底怎樣了。雖然院長(zhǎng)大姨笑瞇瞇的,可他還是禁不住擔(dān)心,他甚至看到了小愛(ài)國(guó)躺在手術(shù)床上的模樣,和他可憐巴巴的眼神兒。這樣的想象仿佛一只大手緊緊地攥住了他,他想都沒(méi)想便把車開(kāi)出了市區(qū),開(kāi)上了通往省城的高速。
到省城只有兩個(gè)多小時(shí)的車程。魏月芝給三亞打電話時(shí)他已經(jīng)到了醫(yī)院,但他還是沒(méi)有見(jiàn)到小愛(ài)國(guó)。小愛(ài)國(guó)正躺在手術(shù)室里,手術(shù)要三個(gè)小時(shí)后才能結(jié)束。等在手術(shù)室門(mén)口的除了三亞和福利院的兩個(gè)人,還有我。我便是三亞當(dāng)年的戰(zhàn)友劉軍。
我退伍后便到了省城,三亞來(lái)這里尋他二姐時(shí)我們?cè)?jiàn)過(guò)一面,一晃好幾年了,剛剛在醫(yī)院門(mén)口的停車場(chǎng)里,接三亞電話提前趕到的我,第一眼竟沒(méi)有認(rèn)出他來(lái)。站在我面前的三亞看上去異常憔悴、消瘦,整個(gè)人仿佛一張紙,仿佛一陣風(fēng)便能把他吹跑。后來(lái)在手術(shù)室門(mén)前轉(zhuǎn)來(lái)轉(zhuǎn)去的三亞,還讓我想到了在我們當(dāng)兵的山里,經(jīng)常能看到的那種孤狼,在遠(yuǎn)處的山梁上飄來(lái)飄去,哪怕有一絲風(fēng)吹草動(dòng),都會(huì)驚惶得仿佛沒(méi)頭的蒼蠅。
這時(shí),三亞兜里的手機(jī)響了。
突然響起的鈴聲把三亞嚇了一跳。真的是嚇了一跳。我看到,他的腳交替著離了地,再落下來(lái),穩(wěn)住神,才伸手到口袋里把手機(jī)摸了出來(lái)。三亞接起電話,剛喂了一聲,電話里便傳出一個(gè)女人歇斯底里的吼聲,你在哪里?三亞沒(méi)有回答她,只是趕忙把電話掛了,又慌慌張張地關(guān)了機(jī)。然后三亞便坐到了我旁邊,眼睛緊緊地盯著手術(shù)室的門(mén),兩只手不停地在腿上絞著。已經(jīng)稍微有些涼的空氣里他的額頭和鼻尖上竟然滲出一層細(xì)密的汗珠。
坐在我旁邊的三亞一遍遍地問(wèn)我,沒(méi)事吧?不會(huì)有事吧?我說(shuō)放心吧,對(duì)這樣的大醫(yī)院來(lái)說(shuō),這都是很成熟的手術(shù)了。可他似乎還是很不放心,還是在一遍遍地問(wèn)著。
小愛(ài)國(guó)的手術(shù)很成功,在兒童醫(yī)院住了兩周便出院了。我再跟三亞通電話時(shí),他們已經(jīng)回去一段時(shí)間了。三亞在電話里告訴我,小愛(ài)國(guó)恢復(fù)得很好,他已經(jīng)離婚了,在城里租的房子,還在跑出租。聽(tīng)口氣,他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我跟他開(kāi)玩笑,問(wèn)他,那兩瓶藥呢?
他就有了些不好意思,嘿嘿笑了兩聲。扔了,他說(shuō)。
責(zé)任編輯:劉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