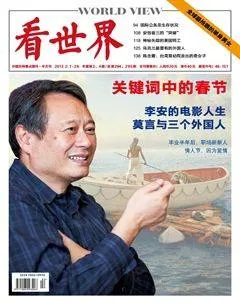說說蕭紅:片刻溫暖與一生命運
近些年,有不少人將蕭紅與張愛玲相提并論。從文字的力量論,這樣的對比有些道理。那個時代的女作家,文字能如雕刻者,僅得她們二人。有人以為她們的相同之處在于未能練達世情,此言差矣。張愛玲不過是不善言辭,心底卻算仁厚;蕭紅則是練達過頭了,一味看重一己得失。
蕭紅(1911-1942),才華過人但紅顏早逝。蕭紅一生主要跟隨了三個男人,她對他們充滿怨恨,一直都在不停地、不斷地抱怨:自己的性別、故鄉的大家庭、父親的冷漠、未婚夫的大家庭、未婚夫的絕情、蕭軍的大男子主義、端木蕻良的軟弱、社會的不公等等等等。
較之同代女性,蕭紅似乎“無原則”且害怕孤獨甚于一切。她在少年時代本來與未婚夫已情深意切了,卻冒冒失失隨表哥“私奔”去北京讀書,在那個年代這意味著什么?她的父親因“管教不嚴”,官職被貶得很低;隨后父親將她“請”回了東北的家,不讓她再去北京,她又偷逃出去;其未婚夫的哥哥因其種種行為建議廢止婚約,她又跑去法庭起訴他,未婚夫為保護哥哥,被逼無奈只好說是自己想“休妻”;當蕭紅真的得到了婚姻自由的時候,她卻又跑回去求未婚夫的家庭收納她,以至于引出了日后未婚先孕遭棄的事端。蕭軍正是與同事去解救她時兩人漸漸相知。而在如愿與蕭軍結婚后,她與兩蕭共同的朋友端木蕻良關系亦不錯,后來因與蕭軍生了嫌隙離婚后,很快就與端木住到了一起,卻又常常寫信要求蕭軍去看她。
她一生總在尋求倚靠。譬如說魯迅很賞識她,有段時間她便天天跑去他家。善良的許廣平因在照顧她和照顧魯迅之間難以兩全,在以后的回憶錄里頗有微辭,說蕭紅一坐就半天或一天,不太理會別人在干什么或需要干什么,有次許廣平為了陪她而沒能顧及魯迅,魯迅在樓上沒蓋被睡過去而著涼,大病一場。
有一個研究過蕭紅的人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她不肯殘忍地面對自己,所以輪到別人殘忍地對待她。”
我一直認為,如果一個人對生活充滿抱怨,那一定不是生活的緣由,而是自己的問題。蕭紅亦如是。記得一位朋友說過一句話:“人生有些委屈一定要受,有些眼淚一定要流。”那時同為大學生的我和她獲邀參加一個演講活動,正好我講完后輪到她講,聽到此語心有所動。隔了歲月的煙云,如今因蕭紅,再次憶及那時的場景。這些年,我們也都是遵照這句話各自行走,雖無大成,亦無大的遺憾。
為了一時一事的溫暖,躲避了生活本有的沉重,總有一天要付出代價。天才作家蕭紅,以為自己會是生活的寵兒,以為她可以只是得到不必回報,最終卻付出了比所得慘重得多的種種,乃至生命。
性格決定命運。對于女子尤其如此,學會認識這個世界不是為某個人而設,學會在順境中面對不期而至的磨難,學會慎獨并能享受獨處的美好,而不是一意要依靠在某個人、某件事、某個機遇的邊上取暖。能否得到幸福人生,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只能每天都怨天尤人,抱怨生活怎會如此不公。其實,無論在什么時代,都不會有絕對的不公平,只會有絕對的不自醒。
可惜了蕭紅在文學上的天才,囿在了如許庸常的性格里。還記得她自己堅持到底的冷漠:在她與未婚夫的孩子出世后,為了能夠順利與蕭軍走到一起,她堅決不認那個女孩,任憑剛降生的孩子在醫院隔壁房間里號哭震天,任憑奶水打濕了前襟,任憑周圍人的苦勸。如此連續6天,那個襁褓中的女嬰沒見到給她生命的母親一面。直到第7天,孩子被送給了他人,從此一生無掛礙。身為作家的她也從來沒有給這個孩子寫下片言。僅從此事,就可看出蕭紅的“絕對自我”。至她將逝時,委托端木蕻良代她去找尋那個孩子。可是,人海茫茫,你又怎能找得回丟掉的人情人性?人有再多的才能天分又怎樣?如果一味推卸成年人應該擔當的那份責任,那還不如做個普通人吧。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盡管如此,她依然還是令人同情的,在那樣充滿悲情的年代,苦難是“過了這村,還有那店”般綿延不絕的。聰慧的蕭紅看通了這些,一意尋求自保,終未能夠。盡管如此,她的文學才情不容忽視,她的勤奮筆耕不容略過。了解這些“底色”,或許有助于從她冷峻的筆調里,讀出另一層真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