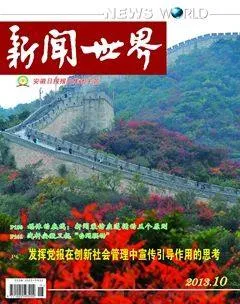淺析我國音樂選秀節目中的狂歡化現象
【摘 要】本文以2013年選秀大季中的電視欄目《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中國夢之聲》和《快樂男聲》為研究對象,從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視角分析此類音樂真人秀節目的特點,主要從評審、參賽者和歌曲三個方面剖析這些節目在制作和傳播中呈現的狂歡化特色及這種狂歡化所折射出的社會心理,以及這種現象所帶來的傳播效果。
【關鍵詞】音樂選秀 狂歡化
在2012年《中國好聲音》迅速躥紅后,各大衛視都摩拳擦掌,準備在2013年制作出可以與《中國好聲音》比肩的高收視率音樂選秀節目。首先,是湖南衛視在2013年開年與韓國MBC電視臺聯手引進頂級歌手競賽真人秀節目《我是歌手》,為湖南衛視“領SHOW2013”奠定開篇之作,隨后上海東方衛視制作大型音樂選秀節目《中國夢之聲》,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第二季開播,湖南衛視的傳統優勢節目《快樂男聲》相近開播等等,2013年夏天各大衛視聯手在中國電視市場刮起一陣音樂選秀節目的風暴。在這些層出不窮的音樂選秀節目中展示出各式各樣的娛樂狂歡現象。正是豐富多彩狂歡化的呈現,使得音樂選秀節目在2013年的中國電視市場獨閃光耀。本文從狂歡化的視角出發,解讀這四檔電視欄目在娛樂狂歡中的體現和影響。
一、評審權力的顛覆
巴赫金把狂歡生活當成生活的“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是有序的、有節制的生活,巴赫金稱之為“日常的生活”。在日常的,即非狂歡節的生活中,人們被不可逾越的等級、財產、職位、家庭和年齡差異的屏障所分割開來,是有等級劃分的生活。①就拿音樂來說,在第一世界中,專業歌手肯定在音樂的選取和評價上有絕對的主導權,但當今的音樂選秀節目正是在一步步的顛覆專業音樂人在選秀節目中的主導地位,去年《中國好聲音》的走紅,很大程度上來自其賽事的創新。隨著電視音樂選秀節目的增多,觀眾對已有的評委點評參賽選手的模式已經厭煩,但《中國好聲音》卻別出心裁的將“導師制”替代“評委制”,弱化了競爭意味,讓選秀的舞臺瞬間變成了一個學習的“教室”,喚起人們對學習知識過程中的溫暖回憶,讓心與心的距離貼得更近。②更重要的是,《中國好聲音》的環節設置,讓具有權威的導師從“神壇”上走下來,隨著導師轉椅的瞬間,權力便完成了倒置,優秀的學員往往獲得不止一位導師的青睞,而學員此時就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導師。這種導師與學員的互選增強了節目在權力上的顛覆性,更多人在節目狂歡中感受到精英與大眾平等的體驗。
巴赫金還說:“民間文化的第二種生活、第二個世界是作為對日常生活,即非狂歡節生活的戲仿,是作為‘顛倒的世界’而建立的。”嚴肅性是處于統治狀態的第一世界的外在表征。而狂歡創造了一個“顛倒的世界”。狂歡世界脫離常軌,是同現實世界相悖的“反面世界”。③今年湖南衛視的開年之作——《我是歌手》,將這種權力顛覆展現得更淋漓盡致。《我是歌手》在節目設置上有三大核心,分別是歌手、專家顧問團以及五百位成員組成的聽審團,歌手傾情演唱,觀眾則僅憑借當時的聽感來判斷是否選擇他或她。這種節目設置,給觀眾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狂歡快感,他們不再是真人秀節目的競爭者和表演者,現在他們可以成為這些節目的主導者,他們不僅可以看到各大牌歌手的激勵競爭,還可以在場下評判這些表演的特色,甚至決定明星的去留,這種設置將比賽的決定權由精英過度到大眾手中,甚至在比賽中代表精英階層的歌手要想辦法取悅廣大觀眾以使得自己不被淘汰。
所以,如果說《中國好聲音》是讓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在舞臺上真正實現了一次自由與平等的交鋒,重構了電視話語格局。那《我是歌手》就是讓大眾話語第一次在電視上主導了精英話語,在最后的決賽中,《我是歌手》不僅僅憑五百位“知音聽審團”投票,而且將電視機前觀眾的短信支持也計入在最后的決賽結果中,實現了節目權力的徹底倒置。
二、參賽者的全民化
巴赫金多次指出狂歡節是全民性的,認為“全民性是狂歡節的本質特征”。④巴赫金說:“人們不只是做狂歡節的單純旁觀者,反倒是(暫時)生活于其中,并且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為就理念而言這是全民的。狂歡期間,所有的人除了狂歡節的生活之外便無其他生活,因為已超越生活界限,人們就無從離開狂歡節。在狂歡節期間,人們只能按照它的規律,即按照狂歡節自由的規律生活。”⑤也就是說,少數人的參與無法構建狂歡,狂歡需要絕對龐大的參與人群;在山呼海嘯的狂歡節中,所有人都被裹挾在一起制造著狂喜、成功、英雄、慶典,所有人都呈現出集體無意識的特征,所有人都對周遭發生的一切深信不疑。這一點在2013年《快樂男聲》海選和《中國夢之聲》上格外突顯。《快樂男聲》在北京、廣州、杭州、成都、西安、長沙和香港設立七大賽區,從賽區設置上可以看到,《快樂男聲》的賽區不僅僅包攬了經濟發達地區,也照顧到經濟相對落后的賽區,這樣不僅僅是給生活富裕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也給許多有音樂夢想的底層百姓一個展現自我的機會。并且在節目剪輯時,對唱山歌的大爺、創作民謠的農民等表演毫不避諱,給他們曝光的機會。從參賽者來看,有學生、流浪歌手、酒吧駐唱、農民工、教師、個體戶等等,可以看出,快男在全民化的狂歡上做的是很不錯的。
但相比之下《中國夢之聲》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愛上比《快樂男聲》更勝一籌。在《快樂男聲》中,那些弱勢群體的表現往往是滑稽可笑的,不過兩輪就會被淘汰。但在《中國夢之聲》中,由盲人歌手岳雷、農民歌手郭帥和鄧小坤組成的星光合伙人組合卻將弱勢群體的歌唱天分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曾與其他選手一樣受過正規的聲樂訓練,也沒有想一夜爆紅的功利心,這樣一個組合,只是在喧囂的音樂選秀節目中帶來弱勢群體的一聲吶喊——別忘了,我們也有個音樂夢!星光合伙人組合的出現,打破了平常選秀節目中農民滑稽的表演模式,他們獨特的嗓音和背后與眾不同的故事打動了許多觀眾,也為這樣一場全民狂歡的盛宴留下自己驚鴻的一筆,給更多社會底層的觀眾一種體驗感和參與感。
三、對經典歌曲的解構
當今的音樂選秀節目中,選手在選歌時十分忌諱唱爛大街的口水歌曲,倘若要表現出自己的與眾不同,選手往往選擇改造經典的流行曲目或者直接選擇無人問津的民間創作歌曲。這樣的選擇也變相的折射出參賽者和觀眾對流行歌曲去中心化和反權威的心理狀態。
巴赫金認為,狂歡打造的是一種“怪誕”而又“去中心”的“廣場文化”。狂歡的廣場沒有高聳入云、讓人感到咄咄逼人的西方塔形建筑,也沒有層次分明、讓人感覺等級森嚴的中國廟宇。廣場平坦、沒有吸引人眼球的“中心”。人人都是對話的“中心”和“權威”。每個人都在廣場上休憩、聊天、狂歡,亦莊亦諧,縱情玩樂,放縱本能。⑥這種去中心化,在選手對歌曲的改編上尤為凸顯。無論是在哪一檔選秀節目中,有才能的參賽選手都盡力通過改編知名曲目,融入更多自己的音樂元素。比如,在《中國夢之聲》12進10的淘汰賽中,何大偉將《黃土高坡》與英文歌《American Boy》相結合,侯磊將寧夏民謠與經典英文歌《Yellow》相結合,都給觀眾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正是因為受眾在觀看時具有強烈的獵奇心理,選手在這種心理驅使下都竭盡所能展現出自己與眾不同的一面,希圖通過對歌曲的改編讓觀眾能迅速記住自己。而這些對傳統經典歌曲的解構,都迎合了觀眾獵奇和反權威、反經典的心理。
其次,在眾多選秀節目中,選手別出心裁的選歌也幫助觀眾注意到那些未曾被權威肯定的民間創作歌曲,最典型的是《快樂男聲》中坐立演唱的《董小姐》和《中國夢之聲》中許明明演唱的《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前者因為美妙的旋律和觸人心底的歌詞而迅速串紅,后者則是因為荒誕滑稽的歌詞而流行開來。原本這些民間具有張揚個性的音樂作品只得到小眾的傳播與欣賞,但當有選秀歌手通過電視這個平臺傳達出去時,這些歌曲就刮起了一陣流行旋風。當今許多娛樂圈內的歌手發片、發曲都不能引起廣泛關注,但這些略帶市井氣息的音樂作品卻能得到受眾的一致好評,其原因是這些歌曲是由民間歌手創作,且歌詞又描繪著普通人的心理或能帶來娛樂的快感,所以觀眾都十分樂意并參與這些歌曲的傳播中來。在觀眾的眼里,這樣的音樂選秀節目沒有真正的權威,什么樣的歌曲都有可能成為流行,只要樂意創新,能夠迎合觀眾獵奇心理的都是好的歌曲。
所以,從這三個方面可以看到,在今年的音樂選秀節目中,各大衛視都出“奇招”,通過不同形式狂歡元素的設置來搶分受眾市場。但在這些喧囂的狂歡聲背后,節目制作人和觀眾也應該反思。畢竟這樣的狂歡只能存在在虛擬的電視節目中,正如巴赫金所說:“狂歡節是一種全民性的、大眾性的生活常態‘倒置’。”人們終究要回到現實,不可能永遠沉浸在狂歡之中。狂歡節之外,體制化的嚴肅的生活才是常態的生活;而在狂歡節之內,非體制化的、快樂的(這些在平時被視為非常態的)生活,才暫時被允許當作“常態”的生活。狂歡表現的其實是與真實生活對立的一面,是脫離體制、脫離常規的非常態。它塑造的是一個虛擬的小生態環境,申張的是常態下被視為異端的價值取向。⑦大眾可以狂歡,但不能過度狂歡,此類選秀節目只能作為日常生活中一味調節劑和減壓閥,不可在各種選秀節目中迷失自己的價值取向;電視媒體則應該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選秀節目中弘揚真正的中國大眾音樂文化。
參考文獻
①③⑥[俄]巴赫金 著,兆林、夏忠賢等譯:《巴赫金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②趙紅勛、賴黎捷,《中國好聲音緣何造就收視奇觀》,《傳媒觀察》,2012(11)
④[美]德弗勒、[英]丹尼斯 著,顏建軍 等譯:《大眾傳播學通論》,華夏出版社,1989
⑤[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4
⑦陳涵、羅夢、沈窮竹,《淺析當前電視文化語境下選秀節目的狂歡特性》,《大眾文藝》,2009(9)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傳媒學院)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