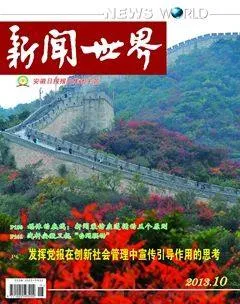從新記《大公報》看“文人論政”
【摘 要】“文人論政”是近代中國獨有的一種特殊現象,它的存在為我國近代的思想開放、社會進步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本文以新記《大公報》為切入點,通過對其最具文人論政色彩的版塊——“星期論文”和“社評”進行包括人員配備、編排策略、行文風格等視角的考察分析,探討近代中國“文人論政”的特點和主要表現形式,以期對現代社會知識分子輿論空間的構建提供指導意義。
【關鍵詞】文人論政 大公報 星期論文 社評
“文人論政”簡言之就是文人以辦報寫文章的形式抒發對時事的看法,這里的時事主要是國家大事,即關乎國計民生的事。新記大公報時期主要指1926年至1945年期間,由張季鸞、胡政之和吳鼎昌接手續辦期間的大公報,由于其秉承“登載確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言論”的宗旨,堅持“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原則,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也是“文人論政”的典型。
一、《大公報》的“文人論政”策略
作為“文人論政”的典型,《大公報》中最具“文人論政”色彩的部分是“星期論文”和“社評”兩個版塊,下面將分別從這兩個板塊入手展開分析,探討《大公報》上文人的論政策略。
1、“星期論文”版塊
1934年1月1日,《大公報》在要聞版的顯著位置,加框刊出了“本報特別啟事”: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聞,或有提前推后的情況,但一定刊出。由主編親自約稿、選稿和定稿。星期論文板塊的開創,是《大公報》文人論政思想的典型體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固定的版面開設專欄,位置醒目易引人注意。《大公報》將“星期論文”安排在報紙的二版(即社評的位置處),醒目而引人注意。根據對讀者閱讀習慣的觀察,我們很容易發現,在一式四版的報紙中,二版是除了頭版外最醒目和吸引人注意的版塊。《大公報》將星期論文放在這里足以顯示出其對國家大事的責任感和熱情度,希望通過文人的言論和見解啟民智、解民惑、請民愿、還民權、救危國。
(2)邀請社外一流的學者發表時事文章,知名度高、更具權威。“星期論文”是一個以社外學者為主要撰稿人的專欄,根據傳播學的相關原理我們知道學者因其知識淵博、閱歷豐富、知名度高,而更具有權威性,很容易成為讀者的意見領袖。因此,學者有關時事見解的文章更容易引起民眾對時事的關注、激起民眾的強烈反響、獲得民眾的支持和信賴。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大公報》的知名度,而且還為加強報紙與社會各方面的廣泛聯系提供的場所。
(3)包容性強,允許各派發表不同意見。“星期論文”的這種包容性使其在有關時事的觀點上更加豐富(既有某位學人一人之宏論;亦有學人之間的論戰;還有學者聯名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新聞的客觀性,還為各派文人營造了一個自由的時事輿論空間,調動了各派文人關注時事、參政議政的積極性。
如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張熙若、胡適等就獨裁與民主問題進行論戰時,有些文章就在“星期論文”中出現。1935年1月13日,“星期論文”張熙若《獨裁與國難》,批評“唯有專制才能統一,唯有獨裁才能渡過國難”之說,認為“統一不須專制,專制或于統一有礙;獨裁救不了國難,國難或因獨裁加重。”民主政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明的政治制度。1月20日,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認為“中國今日的政治原來是舊式專制……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并稱‘我寧可在獨裁政治之下做一個技師,不愿意自殺,或是做日本的順民’”。2月17日,胡適在“星期論文”中發表《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里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的文章,提出以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為“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即“走上民主憲政的路”。從這些《大公報》“星期論文”板塊中有關“獨裁與民主”問題的論爭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在相近的時間段內,不同的學者針對獨裁和民主分別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論斷,而且這些論斷的觀點相差極大。這充分顯示了《大公報》文人論政空間的自由性和獨立性。
又如1945年5月20日,“星期論文”發表戴世光、鮑覺民、費孝通、伍啟元等聯名的《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鴻雋、王云五、宗白華、儲安平、吳世昌、陳銘德、趙超構等二十人聯名發表《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文中說這一秘密協定“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今后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記錄。”從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些知識分子群體以意見交流場所為支撐,聯名發表的文章矛頭直指權勢集團,就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表達了他們獨立的看法,充分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價值。而《大公報》就是提供這個意見交流場所的,這在客觀上是對知識分子議政、關心國家大事的鼓勵,是辦報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
2、“社評”版塊
社評板塊,也是《大公報》文人論政思想的典型體現。其與“星期論文”不同,主要由社內文人所編撰,是報社同人的意見集合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密切聯系時事,挖掘隱藏在事實背后的真相。社評板塊是最能夠顯示《大公報》文人對時事挖掘深度的地方。他們不會將眼光停留在發生的單純的事件表面,而是結合相關的背景和環境,深層次挖掘新聞背后的真正新聞。
如1935日本挑起“河北事件”,強迫中國簽訂《何梅協定》。中央軍被迫撤出河北。此后日寇得寸進尺策劃華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任委員長)。隨即,張季鸞發表《勿自促國家之分裂》向宋哲元提出意見,當時日寇侵入關內,“自治”之聲甚囂塵上,宋能留駐實乃與日辦交涉之結果。“無論如何,要之不能自促國家之分裂。……既當局者須以自身之名義,公開負責,萬勿托詞于民意是也”此文觸怒宋哲元,他下令對《大公報》停止郵遞,但又迫于輿論壓力一周后停止處分。《大公報》沒有停留在事實的表面,而是深入分析其中利益關系,挖掘侵略者的陰謀,是在不可能絕對言論自由的當時為民族興亡作出堅決斗爭的典范。
(2)敢言又善言,發揮輿論監督兼顧輿論引導的作用。在《大公報》看來,批評只是一種手段,幫忙才是目的。因此,該報發表評論時特別注重言論的技巧,集中表現在其在批評政府的同時,積極向政府提出建議,有意識地將輿論監督與輿論引導結合起來。如1934年2月8日大公報社論中《政府應速挽救經濟總崩潰》一文提出,“像政府一面用空文調查苛捐雜稅,一面用實力加緊尅國民,這只有促進經濟的總崩潰,我們希望當局嚴重警戒!”從中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大公報雖然對政府提出了批評,但更多的是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挽救經濟崩潰的問題。這對于政府吸取教訓解決問題是很有幫助的,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政府查封報紙的風險。
(3)替民請命,代民立言。在《大公報》中,“反映人民的疾苦”、“替民立言伸冤”是較為重要的內容取向。
如1943年2月2日,王蕓生讀了記者張高峰采寫的《豫災實錄》通訊,心情激蕩,揮毫寫下《看重慶,念中原》的著名社評:“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干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于今日的事實。”此文一出,人們爭相傳閱,由于其尖銳的筆鋒直至政府,受到蔣介石的懲罰,《大公報》被罰停刊三天。
從這則社評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其代民向政府立言的膽量,這不是他們膽子大,而是他們身上擔著強烈的社會責任、心里系著水深火熱的人民同胞,想通過自己的力量解決民眾疾苦問題。
(4)不署名原則。又被稱為“事業前進,個人后退”的原則。他們認為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有時要犯嚴重錯誤,甚至貽害國家,誤了報人應盡之責。通過這個原則的制定和執行,我們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文人辦報者迫切希望以自己的力量為國家盡責、為人民謀利的決心。
二、“文人論政”的特點
1、原則上,堅持“政論無所苛”
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文人論政時多追求各抒己見、百花齊放,不強求有關政論觀點的一致。但是,他們會因為彼此觀點的不同而展開激烈的論爭,在論爭中增加彼此對政事的考量,更有利于國事輿論導向的確立。
2、立場上,堅持無黨派立言
文人論政中的文人常以中間勢力自居,就事而論,依據事實說話,傾向于獨立性的發表言論,雖然在實際的行文中會不可避免的偏近那個黨派的言論,但這足以說明當時的文人已經有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啟蒙思想。這也是文人建立起言論公正的堅實基礎。
3、內容上,訴民之疾苦、關注國家利益
文人論政的內容常常是反映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與老百姓生存、生活相關的、描寫老百姓疾苦的,如前面提到的王蕓生的《看重慶,念中原》;二是關乎國家利益的主權問題、政權問題等,如前面提到的張季鸞發表的《勿自促國家之分裂》。
4、文風上,帶有強烈的批評色彩
一方面,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是歐美、日本等國家的留學生,在接受教育期間,看到了西方社會的飛速發展以及文明民主的進程,回國后看到中國的發展的落后、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熱,遂迫切想要改變自己國家現狀。作為文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一支筆”。這只筆因為強國心的迫切而充滿批評。另一方面,文人論政的根本目的是改造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希望通過犀利的文字喚起政府的注意,敦促政府采取種種措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狀況、改良中國的外交環境、維護國家利益。因此,其文章中充斥著對政府的批判。
參考文獻
①方蒙:《〈大公報〉與現代中國》[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194
②范泓,《在“民主與獨裁”中的胡適》[J].《書屋》,2004(9):10
③吳麟,《大公報星期論文編輯經驗探析》,http://www.cddc.net/cnnews/
xwyw/200909/6460_3.html,2009-09-24
(作者: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