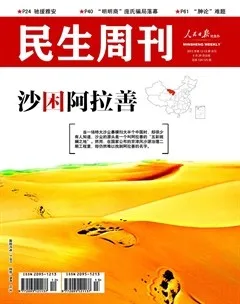少年聽雨歌樓上
那年初夏,臺南的雨下個不停。
在和日本人作戰的日子里,他遇見了她。
她是高山族部落的美麗女子,有最攝人心魄的明眸,如曾經的某個晚上他睡在濁水溪邊所見到的叢林上空的星辰。
而她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被他勇敢、堅定的神情而深深地吸引了……
她決心加入他們的隊伍,做一名抗擊入侵者的女兵,或是隨行照顧他的愛人。
他們在一起,以天為被以地當床,以臺南蓊郁的叢林為帳以月亮為紅燭,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時光。
戰事持續了很久,最后他們的抗爭歸于失敗,于是他只能回到大陸,同樣在一個下著雨的深夜里,坐著一條破爛的漁船,在她的目送下,消失在南中國海茫茫的波濤中……
她安然無事地回到了自己所在的部落,心中珍藏著對他的深愛,從此,無論多少族人勸說和外族人提親,她都不愿出嫁。
而他回到大陸后,也并沒有娶妻生子。他參加了每一次革命,身上傷痕累累,換來的只是統治國家的新的一代人更加墮落、腐敗,日本人開始打進大陸來,于是他在故鄉湘西的寺廟里出家,做了一名年老的僧人。
經常在寺廟的屋檐下,或是自己那小小的禪房里,他聽到多雨的故鄉,竟然下著和臺南一樣的雨。
抗戰勝利以后,臺灣回歸,已經七十多歲的他給她寫去了一封信,因為他一直把她所在部落的地址寫在一本書上,所以他確信她一定能夠看到他所寫的內容。
信在兩個月后到達臺南,又輾轉送到她的手上,那時她也已經很老了,只是眼睛依然明亮如少女時。
她展開那封用寺廟里的紙箋寫下的信函,打開一看,是她當年分離時剪下來送給他的頭發中的一半,信上工整地抄寫著宋人蔣捷的詞《虞美人》,那是他當年教她漢語時用過的,所以每一個字她都還牢牢地記得: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讀完這首詞,她把自己關在木樓上,哭瞎了她如少女般明媚的雙眼。過了好多天,部落年老的婦人上樓去看,發現她已經死去多時了。
她一定知道,他在每個孤獨的夜晚,都曾經因思念她而流淚,每一個夜晚對于他來說都是聽雨的夜晚……
一如他們曾在臺南的叢林里一起聽過的那些打在高高的樹木枝頭的雨水。
他在她逝去的同一天,也在寺廟中圓寂了,后人在他的行囊里發現了一本宋詞選集,書中夾著她少女時送給他的一綹青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