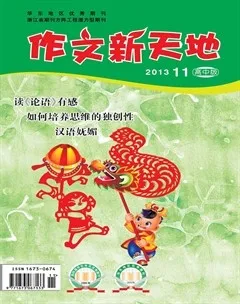漢語嫵媚
在王翼奇先生的大著《綠痕廬詩話·綠痕廬吟稿》中,收有《詩人喜為偶對》一文,說的是:“胡銓貶朱崖,行臨高道中,知有‘買愁村’,古未有對,因以‘聞喜縣’對之,于馬上口占一絕云:‘北望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荒煙正斷魂。’”王翼奇先生評論說:“喜為偶對,詩人幼學所養積習也。仆仆風塵中猶不禁技癢,愁亦為之解,想見其掀髯一笑之態!”其實,作為浙江省辭賦學會會長,王翼奇先生在“喜為偶對”上,比之文中的胡銓亦不遑多讓。
王翼奇先生曾屢次贊嘆:杭州西湖是一座楹聯的大觀園!古往今來,對西湖山水人文的品題,詩詞而外,楹聯佳制堪稱夥頤,且大多膾炙人口,尤為游客所喜聞樂見,成為一大人文景觀。諸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鑄金”……常被大眾傳誦,文人稱引。這其間王翼奇先生創作的諸多楹聯,或放筆長揮,靈動飄逸;或微墨短寫,質實沉雄,為西湖環水抱山的面面有情點睛。作為漢民族獨具特色的一種傳統美文形式,楹聯可以寫景,可以抒情,也可以懷人。如他的“題杭州白蘇二公祠”聯:“黎庶至今思,湖山俎豆雙賢守;風華終古在,唐宋詩詞兩大家。”動靜相偕,切地切題。這種抒懷敘事上的風韻,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做到的,而是學識、人情、閱歷在時間這個熔爐里煅煉出來的。又如杭州孩兒巷有古宅,傳為陸游名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所詠處,今已辟為陸游紀念館,王翼奇先生參與考察時,即席撰聯云:“世味依然,入巷重尋聽雨地;詩情何似,登樓長憶賣花聲。”既滄桑厚重,又精致工麗,終不能移置他處也。其他如“題杭州雷峰塔”聯、“題吳山伍子胥廟”聯、“題秋雪庵兩浙詞人祠堂”聯等,無不吞古納今,豪邁靈動,既有歷史的深度,又富于當代性,從而毋庸置疑地成為該景點的主題聯。
長久以來,王翼奇先生創作的楹聯,真如晉人所言:如行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我的朋友、杭州出版社副社長尚佐文認為,王翼奇先生的楹聯,于鍛句煉字頗為考究。他舉例說:“人有一聯求正于先生,中以‘恬淡青山’對‘玲瓏別墅’。先生改‘別墅’為‘綠野’,改‘恬淡’為‘嫵媚’。以裴度綠野堂別業指代別墅,而‘綠野’對‘青山’甚工;‘嫵媚青山’,用稼軒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語,而循其典源,為唐太宗語‘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上下聯既典雅切題,復暗含唐代二名臣故事,耐人咀嚼尋味,洵點金有術也。”
很多人都知道,王翼奇先生不僅是楹聯高手,更是駢文大家,紹興大禹陵的祭文等都出自他的手筆。駢文作為一種字句對仗、音律和諧、典故繁富的獨特文體,如今會寫的人屈指可數,能將駢文寫得篇篇精到、句句出彩的更屬鳳毛麟角。雖然對于駢文,我喜歡的不多,以為大多虛張聲勢,華而不實,但王翼奇先生創作的《重建錢王祠碑記》《重建楊公堤碑記》等,卻讓我覺得描寫一座城市的地理歷史、人文景觀、特產風貌等,駢文無疑是最好的文體。因其句式靈活,長短適中,“有厚德載物之致”,用以“敷陳圣德,典麗博大”,實在是相宜的。一篇充滿文采的駢賦甚至可能成為一座城市的“名片”。
張中行先生說,好的文章,是不用力來寫的,此系誠懇之語。而碑記一類的駢文,則是需用力為之的文體,僅少數文學修養高深雅博者,方可駕輕就熟,不為規則所累。王翼奇先生的駢文,大多典麗靜穆,有一種開闊的文化視野。譬如坐落于景行古橋旁的《重建楊公堤碑記》,就被社會各界譽為“新西湖美文”。王翼奇先生在碑文中,除了追溯明代杭州知府楊孟瑛筑堤經過以及該堤后世變遷歷史,還著重描繪了楊公堤豐富悠久的人文內涵,藻聲繪色,文采斐然:“以白蘇為伯仲,堤復成三;通南北而逶迤,橋又有六。從此西湖以斯堤為聚景之中軸,攬勝之長廊。西進之水域一碧遙接諸峰,頗饒幽野逸閑之趣;人文之遺址多姿紛呈異彩,彌暢觀瞻游憩之懷。西望金沙、茅埠、三臺,綠灣碧澗,曲折幽深,蘭舫輕移,青旗微現;東連曲院、劉莊、花港,玉帶晴虹,風荷水竹,樓臺罨畫,煙雨藏詩。又有燕南寄廬,都家舊館;汾陽別業,玉岑高軒。張伯雨黃篾之樓;趙悲庵白石之碣。茅鄉之上香古道;麥嶺之留記摩崖。竹園奇石,峰縐秋云;花圃幽蘭,香凝朝露。吳俊卿之蟫葉遺刻;康長素之蕉石鳴琴。光懸日月,潭畔于謙之祠;誼證中韓,山間高麗之寺。村居古俗,觀百年黎庶遺風;越調吳歌,聽一曲桃花流水……”而鐫刻在錢王祠的《重建錢王祠碑記》,則別有一種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氣度和精神:“獎勸農桑,浙地至今富庶;招邀商賈,錢塘從此繁華。而花開陌上,雋語溫溫,佳話清談,流傳于世;潮射江頭,英姿勃勃,雄風奇氣,想見其人……”我記憶猶新的還有他的《錢塘江下沙大橋碑記》,氣勢雄強,遣語雅馴,既是對當年杭州“構筑大都市,建設新天堂”的別開生面的記錄,從中也可看到“精致和諧,大氣開放”的杭州人文精神。
那么,這些美輪美奐、字字珠璣的碑記,王翼奇先生是怎么創作出來的呢?以文辭清暢、韻律流美、廣受好評的《中國越劇百年誕辰碑記》為例,王翼奇先生說,去年他為了寫這篇碑記,閱讀了許多歷史資料,對越劇發展歷程作了一個梳理,前后做了三四個稿子。“但我這種梳理和考據不同,要看詳細史實可以去看《中國越劇發展史》。我的這種梳理是為了在敘事中作一些穿插,理一個脈絡。比如越劇最早由男班創始,但碑記中沒有提到男班,以一句‘新創女子科班’涵蓋了。所以大家看這個碑文時把它當成一種文學樣式來看,碑記是一種傳統駢文的表達,不是詳盡歷史記錄。”由于越劇是通俗的戲曲,王翼奇先生在碑記中也極力避免用一些生僻的詞句。“我得讓關心越劇的人看得懂啊,所以用詞時很注意雅俗共賞”。
尤須一提的是,王翼奇先生于年前出版的《綠痕廬詩話·綠痕廬吟稿》,雋永可誦,識見特出,不獨有傳統根柢,更有民主自由之視角,洵老辣作文者之翹楚也。
在我想來,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古而不朽,舊而常新,也即董橋所謂“新和舊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多少前朝舊宅的深深庭院里,處處是花葉掩映的古樹。房子和樹是老的;花和葉是新的”,與王翼奇先生等既能入乎典籍之內,又能出乎其外并能引發他義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是大有關系的。王翼奇先生以其高深的文化造詣、豐厚的生活積累所創作的楹聯、碑記,預示著漢語的博大、厚重,還遠未開掘盡呢。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今天,偶爾獲讀此種游心于古今之際,意會于情意之間,裁剪風物,熔鑄文史的文字,對漢語書寫的振興,當會有一種信心吧。我們期待著王翼奇先生有更多更好的楹聯、碑記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