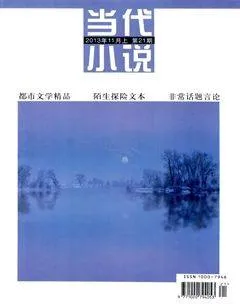除夕
早晨一睜眼,老太從昏迷中醒來。她躺在炕上,直挺挺的,女兒給鑲的假牙,嫌礙事早就拿出來了,腮和嘴癟了下去。她呼吸微弱,全身酸疼,沒一點力氣。她抬起眼皮,混濁的眼珠,在屋里緩慢地轉了一圈。她見自己的上身,穿了一件交織著黃色、藍色、綠色和深紅色斑點的綢緞褂子,棉褲外面,是一條黑褲子,腳上套雙白色線襪和黑幫白底布鞋,依稀記得是第三次穿壽衣了。突然,她迷糊中聽到大兒媳一聲咳嗽,如枯井的心,竟泛起一層漣漪。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怕了,閉眼前,她就想扎古一下那個不肖媳。
于是,老太又裝作昏死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她聽到一家子人仍在哭哭啼啼。她可憐兩個兒子,就睜開了眼。二兒子睡老太的炕西頭,每晚給老太翻身,擦洗,接小便,逼她咽點牛奶。她想笑也笑不出來,聽見當村委的大兒子守在炕前,就闔上眼皮。大兒子拉開窗簾,看著院外薄薄的雪,對二兒子說,你回家拾掇下吧,貼上對聯,買掛鞭,割點肉,買點魚,蒸鍋饅頭,也別冷清清的。
二兒子嘟囔說,哪有心思?虧著女婿送了些。我就擔心娘,千萬別今天……那年,大生他爺爺,不就是大過年走的?晦氣,不好聽。
大兒子不作聲了。碰上那樣的事,他也怕村人笑話,不吉利。傳出去,兒孫臉上也無光。他嘆了口氣,拿出一包牛奶,燙在水里。娘躺了一個月了,時常昏迷,有三四次,就剩一口氣了,姑和四嬸子都說,嫂子,放心走吧,走吧。可娘又頑強地還過魂來了。實話說,如果,娘年前走了,兒女們痛一時,可省心多了,因為年總是要過的。退一步,要走的話,等過了年,哪怕初一也好。這幾天,他的神經,就一直繃得緊緊的。
昏沉中,老太聽見從沒踏進西屋門的大兒媳,倚在門框邊,吸著煙,咳嗽一聲,靜靜地往這邊看。她的身子,不由得哆嗦一下,臉上的肌肉,不禁抽搐起來。她壓低呼吸,一動不動,原先觸摸壽衣的手指,也松開伸直了。過了一會兒,她的心臟,隔著壽衣,又撲通撲通跳起來。隱約地,聽見大兒媳轉身,到了院子里,喂豬去了,接著又去了廚房。她暗地呼出一口氣,懶得睜眼。不多時,大兒媳好像將蘋果和餅干,供奉在堂屋桌上的觀音像前,不久,就聞到一股燃香的氣味。她的聲音很細,很輕,似在輕輕祈禱,愿四世同堂之家,菩薩保佑,就讓華華他老奶奶,過完這個年,再走吧。
可不,老太就是大兒媳眼里的沙子。她心里,會經常詛咒這個老不死的。是誰說媳婦子過了門,感冒了也不給藥吃?那時不是窮嗎。是誰躲躲閃閃,整天往娘家偷東西?是誰三年不給肉吃,反說是老糊涂了?是誰鬼鬼祟祟,想在飯里下藥投毒?又是誰晃著根木頭棍子,比量著要打人?傷天害理啊。盡管說了沒人信,可心里還沒個數?這不,這禍害,受驚了吧?后悔了吧?活該!唉,原想裝死嚇唬她,經了她的上香,就不埋怨了,還有點可憐她。老太的眼角,滾出幾滴淚。
華華回家了,先進了老太的屋,殷勤地喂她奶。半天,她才痛苦地咽下一口。華華歡喜地蹦著高,告訴奶奶去了。華華和爸爸在大門上,貼了鮮紅的對聯,但懂事的華華說,今晚不放鞭了,別嚇著老奶奶。
午飯后,在陰沉的氛圍中,老太強撐了一個時辰,忽又陷入了昏迷。
當她恢復意識時,看見從城里趕來的女兒,緊緊地攥著她的手。大兒子、二兒子,與村里的死尸客,在堂屋,商議著她的后事。一切都準備好了,萬一不好,也不聲張了,等過了年再說;有什么法子呢?人不見天見,都已經盡力了。不過,他們在買骨灰盒的價格上,起了爭執,女婿想買貴一點的,說是人在那邊,也要住得好一點。可大兒子不同意,大兒媳也聲援說,人死如燈滅,花那些冤枉錢,做給活人看,不值得,不如活著多孝順。
老太心里哼了一聲,腦子里一片空白,呼吸有一陣幾乎消失了。女兒嗚嗚地哭起來,引得大家圍了過來,哭鼻子抹淚。大兒媳面朝東屋站著,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二兒媳捂著心口窩。二兒子有主見,將手放在老太的手腕上,蹙緊的眉頭,慢慢松開了,搖著下巴說,沒事,沒事,還咚咚的。
入夜,鞭炮聲里,鄰居家的狗狂吠不止,屋頂上,也傳來一陣陣凄厲的貓叫。
午夜電視里的鐘聲響起,除夕過去了。再看老太,竟睡得十分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