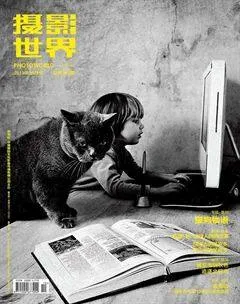王子瑾:記錄飽含歷史的人物




我常常被歷史中的許多名字吸引。
我們的歷史向來鮮少呈現個人面目。但歷史是人構成的,事件只有歸到個體名下,才獲得意義;名字也只有放置在具體的生命細節中,才能活出一個攜帶歷史的生命。
在中國照片檔案館,我常去找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關注“默默”的人
翻閱新華社上海分社女攝影記者王子瑾留在中國照片檔案館中的幾千幅照片,我驚訝地發現她在1960~1980年代拍攝的教育家/科學家/醫學家/藝術家多達三百余人,而且個個有名有姓,對其中一些人物更是持續采訪二三十年。上海城中,教育家蘇步青、謝希德、周谷城,文史學家鄭逸梅,醫學家姜春華、裘沛然、陳中偉、湯釗猷、吳孟超、周良輔,數學家楊樂、張廣厚,科學家彭加木、李國豪,作家巴金、熊佛西、丁玲,表演藝術家趙丹、白楊、張瑞芳、俞振飛、周信芳、蓋叫天,導演應衛云、謝晉、湯曉丹,畫家豐子愷、張樂平、王個簃……各行業杰出的人物都被王子瑾一一記錄。
2010年,我采訪了王子瑾,80歲的她這樣陳述:“很多人認為,只有大題材,只有到很遠的地方才能找到有意義的報道。但實際上,偉大的人就在我們身邊,最好的故事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做記者,我們總這么想:不先進,我報道你什么呢?所以我們更多盯著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典型人物、紅光亮人物,價值大的人物。對那些真正默默為國家做貢獻的人物卻報道得少,中間人物報道得少,對老百姓更是少。我長期采訪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科學家、教育家、醫生、藝術家,就是因為我認為他們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很重要的人。”
在王子瑾那里,最平常的東西也許最有價值,深度關注社會并不意味著你總站在新聞的最前沿。
持續記錄“他們”
1960年,王子瑾從山西調回家鄉上海,被分配到新華社上海分社做攝影記者,開始負責文教報道,一做就是30年。沒有人告訴她要拍什么東西,怎么拍,拍成什么樣……她只好天天看報紙,摸情況,找線索,因為她要知道上海文化科學界都有些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一查資料她才知道,上海科技/教育/醫學/文化界有這么多杰出人物啊!她明確了自己工作的目標:自己的攝影必須要關注人—國寶級人物要關注,默默無聞為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做出貢獻的人要關注,普通人的生活也要關注,而且要一直關注。
持續記錄是攝影記者的基本功。王子瑾的持續拍攝讓她和很多被訪者做了一生的朋友。
1961年,王子瑾第一次見到巴金。那時,巴金剛完成了一部10萬多字的創作,在做最后校訂。拍攝時,王子瑾帶了幾只老式閃光燈,需要接到巴金家中的電線上,結果一按,就把人家的電門爆掉了。巴金也因此記住了這位小小個子,背著碩大燈箱和器材包,滿頭大汗努力工作的新華社女記者,并一直稱呼她“小姑娘”。此后,王子瑾再去巴金家,熟悉到不用事先打招呼。1980年代,在一次采訪結束后,巴金叫人追上王子瑾,送上一捆自己全部簽好名的著作。
采訪必有始有終
1961年,王子瑾推開進賢路一座老式房子的大門,采訪豐子愷。豐老在家中作畫,同女兒一起翻譯俄羅斯柯羅連科(Keluolianke,1853~1921)的名著《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四卷,指導上海中國畫院的青年畫家,給推門而入的小朋友講故事……這些場景,都被王子瑾記錄在照片里。王子瑾在一旁拍攝時,豐子愷全家都不會覺得別扭,因為他們已把這個從不會打攪一家人正常生活的記者當作家人。
5e2a73dddcf9b7aad4cf700a559fb29a1962年,王子瑾采訪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時,他已經是復旦大學副校長。在采訪中,蘇步青從文化大革命中的低谷一直聊到改革開放之后重新被重用。每次他看到王子瑾來,說:“王子瑾你來啦,我要和你談談我的苦經啊。”晚年他還對秘書說:“我太忙,不要多安排采訪,但王子瑾來采訪,可以。”
1964年,王子瑾拍攝了時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彭加木給上海科學院子弟小學學生講課的情景。彭加木于1957年患惡性腫瘤,卻鎮定如恒,堅強樂觀,1958年到1964年,他5次到新疆做科學研究和資源考察工作。后來王子瑾多次到他的研究室采訪,關注他出席上海科技工作會議。最后,直到彭加木失蹤前1980年在新疆羅布泊地區考察,1981年10月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舉行的他的追悼會,王子瑾都參與了報道,可謂有始有終。
1965年9月,中國首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實驗的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一個能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國家;1985年,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2000年與原中科院上海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整合,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又從1升細菌培養液中分離出40毫克胰島素原的融合蛋白,為我國運用遺傳工程學填補了空白。
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功是新聞,但是王子瑾覺得什么人在研究,怎么研究,研究過程是什么樣更應該關注。從1976年到1986年,對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老研究員王德寶、陳長慶到年輕一代研究者郭禮和,她都堅持記錄。
王子瑾愿意一次次去采訪這些真正的大家,正是在他們身上,她看到鍥而不舍、忠誠、高尚、平易近人的品格。她認為,相機讓自己能夠進入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內心,并用圖片記錄下來使之長留,這是一名記者的幸運。
王子瑾采訪過很多書畫家,而那些畫家的畫,她一張也沒有。王子瑾說:“大家都要老畫家的東西,都向他伸手,他怎么應付得過來?人家的畫是人家的心血,人家的勞動。”她還說:“記者不能伸手問人家要東西,這是起碼的職業道德。難道你是廚師,就可以隨便點一桌菜吃?難道你是醫生,就可以隨便躺到手術臺上做手術?”
王子瑾的照片飽含記憶。讀她的照片,能感受到她是因為熱愛去拍,而不是不得不拍;她拍那些真正吸引她的事物,而不僅僅當作領導分配的任務;她為歷史工作,而不僅僅把自己當成攝影師。
在進行“新華典藏”項目時,我一直在尋找那些畫面樸實,有足夠歷史痕跡,甚至能夠解讀一段歷史的照片;同時我也在尋找深入拍攝一個地區、一個人群、一個主題的攝影者。基于此,王子瑾成為這個項目入選圖片最多的攝影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