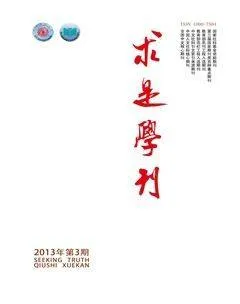意識的哲學理論史
摘要:意識是哲學內部一個復雜且充滿爭議的議題,并總是以心身問題的形式廣泛地呈現于西方哲學史中。當前,絕大多數哲學家已在如下方面取得共識:意識的核心問題在于理解主觀性本身的性質與起源。然而,從古至今,幾乎所有意識的哲學理論都沒有擺脫突現論與泛心論之間的交織與爭斗。未來的意識研究仍然亟待走出上述認識論上的兩難境地。
關鍵詞:意識;心身問題;突現論;泛心論
作者簡介:威廉·西格(William Seager),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教授,從事心靈哲學、意識哲學研究。
譯者簡介:陳巍,心理學博士,紹興文理學院教育學院心理學系講師,浙江大學“985工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員,從事認知科學與哲學心理學研究。
校者簡介:郭本禹,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西方心理學史與理論心理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現象學對認知科學的意義”,項目編號:10YJC720052;南京師范大學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培育項目“邁向整合腦與意識經驗的認知科學:神經現象學研究”,項目編號:2011BS0003
中圖分類號:B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3)03-018-012
一、問題的提出
一旦觸及意識問題,就不可能逃避回答這樣一個基本的疑問:何為意識?但是總體而言,要回答這個問題并非易事。如果有人真的缺乏任何關于何為意識的想法,那么將難以想象如何將任何信息傳遞給他們(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曾經說過的那樣,當詢問什么是爵士的時候,其實你并不知道自己問的是什么)。“意識”(consciousness)這一術語包含了大量的心理現象。有時它指對我們自己的心理狀態的復雜的反思鑒別,就像我們體驗這些心理狀態一般。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心理活動。另一方面,意識有時也僅僅等同于覺醒(wakefulness)或感覺的覺知(sensory awareness)(這是麻醉師所采用的定義)。大概動物(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會比較受用于這類意識,同時很可能只有人類才能反思其自身的心理狀態。意識狀態的最鮮明的例子的確可以算是感覺狀態:一個成熟番茄的炫目紅色、小號的尖銳聲、炎炎夏日里品嘗一杯冰啤酒的滋味,以及所有經由這些感覺形式體現出的東西。但是,意識的分類也應該包括有意識的思維(conscious thought),及其牽涉我們思維的內容與更朦朧的認知層面,諸如當我們忽然認識到我們理解了某物的時候的感覺,一種典型的意識狀態超越了我們所能把握的內容。至于我們有意識思維的內容,其保留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哲學問題:要么是否所有涉及意識的思維均需身披某些感覺的外衣(它可能以如下形式出現,心理意象,或者聽覺的,或視覺的),要么是否存在著某些“純粹”的智力理解(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s)。進一步地,意識的分類需要包括意識的基本感情狀態,其范例是疼痛和愉悅。這些狀態的動機性力量使得它們與眾不同,而它們遺留下來的重要性也許甚至使人認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所有意識狀態的原初形式。情感超出了簡單的刺激-反應式的疼痛與愉悅。這體現出了一系列意識的情緒性狀態。諸如憤怒、愛或恐懼等情緒組成了一些我們最強烈的有意識的經驗,并且由于涉及了這些狀態,所以它們超出了赤裸裸的情感、感覺或智力形態。
有人可能對在這些多種多樣的心理狀態名單中發現任何核心或共同的特征感到絕望。意識那多少有些捉摸不定的本質是主觀性的(subjectivity),在那里使用的是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的著名表述方式:成為一個擁有意識狀態之主體所是之物。1火箭或者煙灰缸不具備主觀的方面,也沒有“內部”(interior)的生命。撇開所有構成意識的不同類型的心理狀態的細節,意識的核心問題在于理解主觀性本身的性質與起源。
我們必須感謝意識問題是作為一個更普遍的議題的一部分出現在西方哲學史中的,這便是所謂的心身問題(mind–body problem)。既然存在這樣的事實,即意識是心理的區別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它將心理從其他自然物中分離出來,因此,人們不會期望存在著任何關于心靈的問題可以從意識問題中脫離出來。由于意識是一種屬性,從而產生了大量問題——意識是某物的一種特征,并且這種“事物”可以被稱為心靈。這個主題與真實的古老問題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這一問題是:當身體遭到明顯的摧毀之后,是否仍然有一些東西幸存下來,這種最終能被人類所認識之物將會給他們的塵世生活(earthly existence)帶來一種必然的終結。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種強烈的趨勢去相信(或希望)我們是以某種方法幸免于死的,并且為了這種幸免能成為我們自己的,它不得不保留意識且將它想當然地視作一種在類型上與身體截然不同的事物。
盡管意識問題的現代形式是一種相對的近期發展,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這與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興起以及隨后對世界的科學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是意識使得我們不同于(其他)自然的物質。因此,為了理解意識問題,理論哲學家建議要想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回顧心身問題的悠久歷史。
二、早期歷史
身處古代地中海地區的前蘇格拉底(pre-Socratic)哲學家的觀點通常被世人視作令人憐憫的荒謬而加以嘲諷與否認:萬物由水構成(everything is made of water),萬物皆不動(nothing can move)。但是,就提出世界應該依據自然力量和理性探究而予以解釋的想法而言,我們可以將它們歸置于一場廣泛的討論之中。這些知識先驅的積極觀點錯得離譜并不令人感到詫異,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呈現的觀點為科學革命奠定了早期的基石。
前蘇格拉底的準自然主義者的觀點指引他們去詢問一個關于世界的結構與組織的根本性問題,他們遺留下的答案至今仍在爭論之中。這就是突現(emergence)與我們所謂的(因為缺少更好的術語)內在性(inherence)。世界包含了大量的不同事物,這些事物展示出一種令人驚愕的復雜特征與交互作用。但是,很明顯的是,這種復雜性中的某些東西可以依據參與實體(participating entities)的交互作用而加以解釋(這在我們所構想的人工產品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并且有時忘記了手藝高度熟練的古代人是怎樣設計工具和簡單的機械的)。這種觀察認為,也許世界中的萬物可以借助少數擁有一些簡單屬性的基本特征而予以解釋。這樣的思路自然地招致反對者的挑戰,某些事物是不能就這樣被“還原”(reductively)而解釋的。
有人認為,存在著一些關于世界的簡單的基本特征,它們的基本屬性和交互作用引起萬物體現出一種突現論(emergentism)的形式。任一客體都有一屬性,此屬性是組成整體的各個部分所不曾展示出來的。例如,太陽系展示出一個復雜的動態結構,這是其任何的組成成分均不(或甚至不能)具備的。但是,太陽系的組織完全是由其組成成分之間受規律支配下交互作用的產物,并由這些成分的屬性而產生(例如,質量、位置、速率)。因此,動態結構是一種突現的特征。前蘇格拉底時代最著名的突現論者是原子論者(atomist)德謨克利特。他堅持信奉萬物可以被“還原”為簡單的屬性和原子的運動。
但是,我們很容易就將某些特征認作突現是合理的,這并不意味著萬物皆是如此。以顏色為例予以考量。假設原子是沒有顏色的,那么,顏色又是如何從原子的交互作用中突現出來的呢?為了反對德謨克利特的突現原子論(emergent atomism),阿那克薩哥拉斷然否定了突現的可能性,并選擇了以所有特質內在于萬物的觀點作為替代:世界的多樣性可以用任一具體事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混合屬性加以解釋。現代的原子論者——我們所有人——對顏色的例子沒有留下多少印象。顏色僅僅是由根本上的非顏色屬性的物質作用于我們的視覺系統而產生的。或許當德謨克利特晦澀地宣稱“按照慣例是顏色……但事實上卻是虛空(void)與原子”的時候,他已經預測到了這種回應。
在心身問題內部,這種基本的二分法產生了兩個關于意識本質的理論:突現論和泛心論(panpsychism)。突現論者相信心靈和意識是由源自非意識先質(nonconscious precursors)的非意識的部分產生的,反之,泛心論者堅持認為心靈是世界的一個基本特征,并且萬物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擁有一種意識的形態。當然,存在著許多種不同的方式來表述上述觀點。一個泛心論者可能會強調這樣的觀點:意識不能從非意識的成分中突現出來,但也并非宣稱萬物絕對都有心理方面。
無論如何,在這種二分法的歷史中形成了心身問題的背景。就此而論,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兩位古代哲學先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完全缺乏前蘇格拉底時代還原論者的精神,并且在《斐多篇》(Phaedo)中對此進行過攻擊。柏拉圖的替代性建議是心靈與身體不同,它多少是具有“活力的”(animated)。自然地,柏拉圖提出了一些論據來闡明心靈是從身體中分離出來的觀點。這樣a9f03b3c632796093feb2f859370459016c6f5ae112d5378dbf7c62a1575e634的論點之一極其抽象并源自其著名的形式說(doctrine of Forms)。理念是完美的實體,而物質實在僅僅是近似于理念的,例如,在幾何學中,我們證明一個物體是圓形的,但是在物質世界中不存在這樣的事物。所有圓形的客體——并且在有的時候很明顯是由幾何學家所描繪的粗糙的圖形——不可能是完美的圓形,因此,嚴格講來,都算不上是圓形。然而,柏拉圖怎么可能說我們的心靈為了進入到智力中需要與這些極端的非物質實體(nonphysical entities)發生聯系?我們與它們在概念上的熟識使得我們認為心靈類似于非物質的。柏拉圖也在其回憶說(recollection)中發展出該論證的一個不太抽象的版本。因為我們知道理念在知覺中從未遭遇其實體,我們的知識必須基于某些其他類型的覺知。柏拉圖相信這只能借助我們的存在的非身體的狀態(nonbodily phase)才能解釋,這是我們對自己的身體的存在的朦朧回憶(事實上柏拉圖甚至認可一種輪回學說[reincarnation])。雖然他的論證不是特別令人信服,但是這些論據確實指出了思維的一個非常奇特的特征:它具有將客體獨立于其存在的能力(一種隨后被稱之為思維意向性的特性)。
乍一看,亞里士多德作為自然主義者是站在柏拉圖的對立面的。他否認了理念說,代之以客體可以用其在形式(form)和物質(matter)之間的區分來加以理解的觀念。這里的形式(form),亞里士多德指的是某些類似于組織或結構的東西,而物質(matter)則是構成所討論的客體的一切“非結構化的質料”(unstructured stuff)(因此,水的物質是氫和氧,蟻群的物質是螞蟻)。亞里士多德將靈魂(或心靈)定義為“一個具有潛在的生命的自然化身體的形式”。這意味著心靈是一種作為我們特征的物質存在而不是某些縹緲的、屬于另一個世界的質料。然而,亞里士多德并非一個徹底的自然主義者。就像柏拉圖一樣他也認為,心靈存在一些極其特殊之處,這種特征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心靈超越了物理物質。他有時把心靈之于身體的關系比作舵手之于船舶,并明確地堅持心靈至少在一個方面上——理性思維的能力,他稱之為“主動理智”(active intellect),可以脫離身體而存在。亞里士多德是在對二元論的論證過程中展開其形式概念的。心靈可以思維任何事物,而且這是因為思維對象以其形式來告知心靈(例如,當你想到一頭獅子的時候,獅子的形式告知了你心靈中的“物質”),這意味著心靈可以呈現任何的形式。但是,沒有物質器官可以呈現每一種形式(亞里士多德的例子如下:眼睛只能夠呈現視覺的形式,或者耳朵只能呈現聽覺的形式)。因此,心靈不是物質。亞里士多德的論證非常有趣,就像柏拉圖的回憶論證一樣,關注心靈的不可思議的能力使其進入到與其他潛在存在的聯系之中(或者甚至非存在,當我們回憶時,我們能輕易地思考不可能的事物)。
亞里士多德還引入了一個迄今為止仍然具有影響的觀念,即所有有意識的心理狀態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關于其本身的或是自我表征的(self-representing)。對此的論證是如果心理狀態是經由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這是第一狀態[first state])而引起覺知,隨后就應該有一種第三狀態將第二狀態帶入到覺知中去,以致產生了一種惡性的無窮倒退。值得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潛在地假設了所有心理狀態都是那種我們能有意識地覺知它們的狀態;否則,無窮倒退就會停滯在第一狀態這種并非意識的狀態中。這不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吹毛求疵。因為,僅僅是將無意識心理狀態的概念視作是清晰的之前,就需要花費我們很長的時間,更不用說將其視作一個嚴肅的猜想了。
三、科學革命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伴隨一些值得注意的扭曲與擠壓,服務于主導中世紀的教會約束下的哲學。在那里當然存在著有關心靈及其內容的本質與結構的諸多爭論(我們將心理狀態映射到客體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或指向性[directedness]等重要概念歸功于中世紀學者,心理狀態是“關于”[about]某物的)。但是,這個觀點在關于心靈與遠離中央舞臺的自然世界如何發生關系上存在一些問題。并且心靈的概念需要用那些并非當時出現的自然主義的術語加以解釋。當科學革命忽然降臨歐洲的時候,這種對事物認識的自滿視角被徹底地顛覆了。伽利略為區分首要特質與次要特質(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做好了準備。前者是物質在數學上便于處理的屬性(mathematically tractable properties of matter),比如形狀、質量和運動,而后者是在意識中所設置的首要特質的顯現。次要特質是有意識的心靈的唯一屬性。在伽利略撰寫的《試金者》(The Assayer,1623年出版)一書中寫道,迄今為止滋味、氣味、顏色等只是我們用來將其鎖定于客體的名字而已,它們均存在于意識之中。因此,如果生物體一旦改變,所有這些次要特質也必將被抹去或消失殆盡。
這種區分使得世界對科學變得安全。隨后科學可以在這一范圍內聚焦于物質世界的客觀特征,并采用純粹的數學理論加以解釋。但是,有關次要特質本質的文本難題僅僅是暫時地被規避了而已。世界中生機勃勃的科學化圖景,那些隨后并且一直渴求的完滿,不能再忽略室中巨象了1。
最著名的回應——來自笛卡兒——直截了當地在心靈和物質世界之間施加了一種完整的分割,并以一種迅速被命名為笛卡兒二元論(Cartesian dualism)的理論所闡述。如果有人贊同心靈是與身體分割開來的假設,那么,笛卡兒的觀點就非常符合常識了。這種理論允許心靈與身體之間的因果互動,所以踢一下脛骨會產生一種疼痛的意識(這位于那些笛卡兒曾經非常感興趣的甚至預言的物理學詭計之后),相反,一種憤怒的感覺導致手臂執行報復性的打擊。笛卡兒二元論同樣向天主教的靈魂不朽與身體復活學說敞開了大門——這是一種存在于文化之中的重要原因。這種文化時常火焚異教徒,例如,它曾臭名昭著地強迫伽利略撤回對哥白尼主義的辯護并宣判其畢生監禁于牢獄。
但是,笛卡兒二元論同樣面臨著大量精致的哲學難題。心靈與身體之間的因果互動威脅著世界的科學圖景的完整性。心靈時常以某種方式干預或改變物理世界,這終究是物理上無法自圓其說的,并且使其在相當程度上違反了基本的規律,比如能量守恒定律。其次,在更形而上學的層面上,心靈(沒有空間,沒有位置)與身體這兩個在根本上如此迥異的領域之間產生因果互動又是如何可能的呢?這一困境在笛卡兒剛提出他的理論時已經眾所周知了。作為他的皇室讀者,伊麗莎白公主在1643年坦率地質問他:“一個人的靈魂如何決定他身體的精神,以至產生自主動作(voluntary action)?”笛卡兒的正式回答是心身的聯合是一種無理性的事實,由上帝所創立,這超出了人類理解的范疇。
為了回應這些困難,一大批可供選擇的二元論者的理論被設計出來。斯賓諾莎提供了一種具有兩面性的解釋。在此種解釋中,心靈與物質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無限的屬性,潛在于他稱之為“上帝”的那種實質之下(這種褻瀆在于其暗指上帝擁有物質的屬性)。雖然,并不存在不同屬性之間的交互作用,但是它們卻作為彼此的完美鏡像矗立著,因此,呈現出一種因果交易的面貌。
萊布尼茨的理論通過假定一種無限的個別心靈(他稱之為單子[monads])的集群,從而避免了斯賓諾莎那廣受詬病的泛神論(pantheism)。這些心靈的知覺是由上帝(上帝是至高的單子)設立的,因此完美地與物理世界中的事件保持預定的和諧(preestablished harmony)。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萊布尼茨首次賦予某些心理狀態是無意識的觀點以地位,即他所謂的“微知覺”(petite perceptions)。
另一種對心身關系相當奇特的解釋來自馬勒伯朗士的偶因論(occasionalism),該理論猜想上帝才是心靈與物質之間的仲裁人,所以任何意向性動作或感覺簡直是一個奇跡。這樣的理論強有力地揭示了已認識到的心理因果關系的棘手性。
這種以反突現論者身份出現的二元論者對心靈的解釋一度成為時代的主導趨勢,但是依舊存在一些卓越的思想家,他們至少可以被貼上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s)的標簽(例如,霍布斯、伽桑狄)。然而,他們作為唯物主義者的核心觀點是拒絕一種可以脫離身體而存在的分離的心理實體。他們甚至沒有宣稱心理屬性是同一于物質屬性的。例如,霍布斯認為人類是物質客體,可以借助微粒的運動得到充分的解釋,這些微粒組成了大腦與身體。但是他補充道:“我們所稱之高興或煩惱即是那種微粒運動的顯現或感覺。”這種顯現屬于意識的領域,并且在這些早期的唯物主義者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些有時被為屬性二元論(property dualism)的主張(與之對立的是笛卡兒的實體二元論[substance dualism])。他們并未冒險超越早先已經存在的極端觀點,即人類和靈魂都是徹底的物質客體。
四、科學哲學的興起
當然,唯物主義在當時并未形成任何重要哲學發展的核心,哲學反而追求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idealism)的反突現論者的理論,這些理論宣稱自然界中所有的存在從根本上講都是心理的。多種唯心主義的形式被公之于眾,肇始于貝克萊和康德,并且直至20世紀初,唯心主義一直處于一種主導地位。盡管它對哲學史的意義是廣泛的,但是唯心主義并非是本文首要關注的,因為它將意識接納成物理世界的本體論基礎,這意味著唯心主義在相關意義上是不存在意識問題的。然而,一種由唯心主義者發展出來的被稱之為現象學的衍生物卻尤其值得關注(可以溯源至弗朗茨·布倫塔諾和埃德蒙德·胡塞爾的工作),這種學說力求借助內省檢驗(introspective examination)證明意識經驗的精確結構和內部構造。
在意識問題的發展中更有意義的是在該領域所引發的驚人關注以及從笛卡兒時代到19世紀末的科學的解釋能力。此外,科學的普遍延伸,使得其中的兩類發展趨勢顯得尤為重要:以達爾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為標志的進化生物學的誕生,以及心理學從哲學的一個分支轉變成獨立的科學學科。進化論希望假設復雜性是怎樣從簡單形式中突現出來的,其明確的意義處于有機體領域內,但含蓄的意義則來得更加深遠——直至囊括生命本身從無機物的原始材料(nonorganic precursors)中的起源問題。這迫使突現問題變得更為突出。當然,這一時期也存在一些否認意識可以在缺乏無意識的情況下形成的可能性。對從無意識到意識的不連續遷躍的討論,威廉·克利福德(William Clifford)寫道:“我們無法設想從一個生物到另一個生物的巨大跳躍應該發生在進化過程的任一節點之上。”這種反對突現的“基因的”(genetic)論證所保留的意見至今尚存。基本的問題源自對突現的正常模式的觀察,進化論將新異能力產生自更高級組織的復雜性的認識奉為圭臬(例如手工計算器與超級計算機之間的差異)。論證進而宣稱正常模式無法解釋諸如意識等獨一無二屬性的出現。同時,這種論證具有一些直覺的力量,使得可供選擇的方案變成接受心理是宇宙的一種基本特征的主張,并從一開始就直接建立在創世說的基礎之上。這樣的泛心論與在直覺上的可接受相去甚遠——相反,我們的經驗強烈地建議意識是伴隨動物體內復雜的神經系統的發展而在某一時刻突現的。
19世紀后期的許多思想家信奉這樣或那樣形式的泛心論者的說法(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威廉·詹姆斯)。但是突現論者,包括約翰·穆勒與C.勞埃德·摩根,以“摩根法則”(Morgan’s Canon)而聞名,同樣發展出了一種充滿活力的理論,即自然將被視為在突現層次中的有序等級。這種有序等級源于基本的和不可還原的自然法則,它作為潛在的復雜性的發展支配著這種突現。這種形式的突現從根本上打破了上述討論的正常模式,并且常常被稱之為激進突現(radical emergence),以區別于普通的突現形式。根據激進突現的理解,從潛在結構(submergent structure)中推演出突現,甚至在原理上也是說不通的,除非有人也將不可還原性的和不可預測的“突現法則”(laws of emergence)考慮在內。突現論者將物理領域中普通的化學過程當作激進突現的一個清晰而非爭論性的例子,并將這個觀點拓展到生命與意識。當然,這種觀點撇下了意識的顯現(appearance of consciousness)作為一種最底層的謎團,它甚至接受常識的觀點,不是變形蟲而是狗才具有意識。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坦言:“刺激神經組織為何會出現如此明顯的意識狀態?就像阿拉丁擦拭其神燈時為何會出現精靈那般難以理解。”
激進突現的學說暗中與經典物理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量子力學的發展似乎完全顛覆了化學的關鍵性實例,即化學成分的基礎早在1925年就已經基本上可以被解釋的事實(從那時以來所有跡象均顯示物質的化學屬性完全依賴于物理屬性,并且無須實施激進突現的魔法就可以排列其成分)。在生物學中,這種學說的發展以發現遺傳的化學基礎而達到頂峰,隨后摧毀了生命作為一種激進突現現象的合理性學說,這遺留下意識作為突現的唯一候選物,沒有其他任何例子可以為突現提供支持。
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興起,同樣也反對激進突現的觀點。在最初將意識視作一個特有的研究對象攬入懷抱之后,在20世紀初,心理學對心靈的內部方面感到厭惡,并陷入到一種奇特的和對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長期癡迷之中——行為主義的核心(或唯一的)觀點是:在心理學中唯一合適的研究對象是被試可以觀察的、客觀的身體運動。
從一個行為主義者的視角來看,意識問題的確存在,但是太容易被解決了:意識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可以借助特定的物理身體(physical bodies)的運動而加以定義的(或者在特定的條件下以特定的方法安置物理身體的運動)。在哲學中,行為主義獲得了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ts)的某些形而上學和方法論學說的鼎力支持,尤其是他們提出的意義的證實理論(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證實主義(Verificationism)意味著任何陳述只要是無法被客觀地觀察或測量所公開證實,那么,事實上其便是無意義的(meaningless)或荒謬的(nonsensical)。這種荒謬的一個例子來自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關于“什么時候是太陽上的5點鐘”的問題。當有人試圖宣稱并不存在可公開觀察的方法來證實他們自己的理論的意義時,證實主義者往往會表現得極為惱怒。
行為主義對心靈的科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從本質上將除了可以借助可觀察的行為而被明確定義的內部心理狀態統統拉入了黑名單。同樣的,意識的研究往好處說被視作非科學的,往壞處說則是完全無意義的或者類似于嘗試研究獨角獸或采訪福爾摩斯。行為主義對哲學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如果不是其官方的教條,那么,就是行為主義者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強烈地影響諸如維特根斯坦與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等哲學家。他們或多或少地共同發展了這樣一種對心靈的解釋觀,這種觀點將關于心理狀態的詞匯(像“機靈”、“疼痛”或“想象”)當作是行為的模式而不是被試的內部狀態。然而,也許對行為主義而言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推動了隨后的自然化的初始哲學計劃(nascent philosophical project of naturalization)。
將某物自然化即是證明在沒有對該世界觀設置壓力的情況下如何將其流暢地融入到世界的科學圖景之中。例如,在19世紀中,活力論(vitalism)也曾是一種享有盛譽的生命科學理論,并且像漢斯·杜里舒(Hans Driesch)這樣的活力論者也在類似胚胎學的領域中進行了奠基性的工作。但是,活力論聲明生命取決于一種神秘的和非物質的“生命沖動”(elan vital),這種主張無法與物理學化的心靈思想家(physically minded thinkers)所支持的唯物主義觀相調解。20世紀生物學的一個偉大成就是與伴隨有機化合物的化學物質和有機體過程的物理屬性等大量發現一起發現的基因編碼的化學基礎,這一基礎服務于自然化的生命。現在生命被視作一類化學過程(可以確信的是一種巨大的復雜體),這一過程既不違背自然規律,也沒有將一種非物質的實體引入到自然之中。
行為主義提供了一種朝向自然化心靈的相似進路。如果心理狀態真的僅僅是生物體行為的復雜模式,并且如果生物體本身就可以“還原”為伴隨它們與環境之間的純粹物理的交互作用而在它們內部進行著的化學過程,那么,心靈將不會對世界的科學圖景構成任何威脅。
雖然行為主義已不復存在,但隨之而來鼓勵自然化的做法卻逐漸成為了意識的哲學理論的核心特征,直至20世紀中葉。在自然化運動背后,一股極其強大的力量是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的廣泛接受——該學說堅持假設性的實體是經科學所假定的真實存在,但其典型特征對人類感覺而言是不可見的。當然,這一時期也存在著某些真正意義上對該觀點的抵制。19世紀有關化學結構的早期工作被視作只是一種組織可測量的化學傾向(chemical proclivities)的有效方法。一般而言,原子理論也曾同樣被視作一種有用但并非實際存在的模式,激起了諸如威廉·奧斯瓦爾德(Wilhelm Ostwald)、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等20世紀初期的杰出的科學家的一致反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簡·佩蘭(Jean Perrin)在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方面的工作在傳統上而言常被引為反原子論(antiatomism)的致命一擊。無論如何,自此科學有權利與能力宣稱世界的不可見的深層結構變得可以被廣泛地認識。盡管原子的存在符合激進突現論的主張,但顯然在原則上將化學還原為量子力學的建議反而認為世界完全是在一種僅受量子層面上的規律支配的少量特異的量子實體(exotic quantum entities)的交互作用基礎上運行的(在一種非常不穩定的合作關系[uneasy partnership]中與極其巨大物體的廣義相對論原理相伴隨)。
科學的顯著能力宣告了存在于現象“背后”的世界的特征,澄清了并非是直接的可觀察性才導致行為主義的狹隘看上去是不必要的阻礙甚至是愚蠢的,并且該學說的式微終究使其被一種巧妙地模仿其他科學并假設存在內部心理過程、狀態與事件的認知心理學所替代。這種內部心理活動僅僅是間接地并與產生的行為相一致。此外,自動機的論證(automaton argument)也揭示了內部狀態的重要性。如果對心靈歸屬(ascription of mind)而言,行為即是所有東西,那么一種被預編程序的、其動作看似好像擁有一個心靈的機器創造物,實際上也應該具有一個心靈。這種推斷看似違背了一種強烈的直覺:即行為事件之原因的作用(在僵尸[zombie]與真正的人類之間存在著差異)。
五、近期的意識研究取向
為了回應已被日益接受的科學實在論和行為主義的衰落,哲學家(尤其是J.J.斯瑪特[J. J. C. Smart]與U.T.普特斯[U. T. Place])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一個唯物主義的激進形式,該理論認為,不僅人類完全是物質客體,而且心理屬性也同一于物理屬性,特別是同一于大腦的屬性(properties of the brain)(或狀態)。這種中樞狀態的同一論(central state identity theory)宣稱意識的狀態,比如對疼痛的感覺或顏色的經驗只不過是在大腦中所處的狀態或過程。這并非指大腦狀態與心理狀態相關或引起后者,而是激進地認為疼痛的屬性僅僅是一種神經屬性(neurological property)。非常明顯,這樣的觀點充分地符合世界的科學圖景(其目的即在于與之相符合),避免了行為主義者荒唐地否認存在著內部心理狀態的做法,并且躲開了交互主義者的二元論(interactionist dualism)的所有問題。同樣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交互主義者的二元論也是突現論的一種形式,但不是上述討論的激進類型,而是遵循正常突現模式的一種溫和的類型。在這種類型中,突現是可解釋的新奇事物(explicable novelties)。世界的科學圖景充斥著這種類型的突現(龍卷風、熱力學屬性等),并且同一論者能夠利用其理論將這種突現類型添加到科學之中。
然而,不久伴隨同一論也出現了許多值得注意的嚴肅問題。將心理與物理屬性同一起來的概念在形而上學上看多少有些可疑,但是擁護者指出,在科學中存在相當數量的屬性同一,其中最頻繁地被提及的是一種氣體的溫度同一于其構成分子的平均動能。反思這些由經驗發現的同一性的啟示引出了大量重要的哲學進展。但是,除了形而上學顧慮之外,更加坦率的反對同樣得到了發展。“神經沙文主義”(neural chauvinism)就是問題之一(這一術語由內德·布洛克[Ned Block]創造,他是這種反對的早期支持者)。假設我們邂逅了一位外星人,從外表推斷他是有智慧與意識的生命。隨后我們發現他們的內部心理活動與我們自己的心理活動存在天壤之別——他們并沒有我們熟知的大腦。那么,由此可以將他們從心理擁有者的隊伍中排除出去嗎?許多不同的內部系統可以產生意識,這在直覺上看似合理,但是這卻直接違背了同一論。同一論的另一軟肋在于,因為其將心理同一于物理狀態,這在解釋主觀性本質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所有的物理狀態都完全是客觀的并且在原則上是完全可以認識的。但是,有意識的狀態的主觀特質好像無法經由物理結構的知識和大腦的運作而被揭示(這一系列的論證在該領域內非常普遍,最初是由托馬斯·內格爾與弗蘭克·杰克遜[Frank Jackson]提出的)。因此,為什么特定的物理屬性是主觀的,這一點似乎變得撲朔迷離(我們不能僅僅說它們具有主觀特質或特征,因為同一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所有這些特征是嚴格同一于物理屬性的)。
同一論的一個變種稱之為“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它將同一論的核心問題歸結為一種對特定的分析水平的錯誤同一(misidentification)。按照功能主義的理解,在神經硬件內部無法發現心理狀態,作為替代的大腦的功能性架構(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brain)可以等同于心理狀態。數字計算機的運作作為一個頻繁的類比引領出功能主義者的口號:軟件之于硬件猶如心靈之于大腦。正如相同的程序可以在不同類型的計算機上運行那般(并且,在原則上,一臺計算機可以由任何成分組成),心理狀態也可以在許多不同的物理載體中執行或實現。全部所需的就是內部狀態系統與合適的組織方式相互作用,引起內部的改變與外部的行為共同符合擁有一個心靈的狀態。功能主義具有一種明顯的吸引力:它利用當前的技術性類比(在解釋心靈的謎團時常常通俗易懂),在沒有詆毀腦研究的同時,還鼓勵一種心理或認知架構的抽象領域,并且它允許一種朝向自然化心靈的相當清晰的可接受的進路。這在避免神經沙文主義反對同一論的同時,回避或至少在形而上學上消弭了同一論那令人不安的屬性同一性(property identifications)特征。而且功能主義在適應當前科學理論方面,尤其是與年輕的生機勃勃的認知科學的跨學科領域保持互動上并不亞于同一論。認知科學含蓄地將功能主義者的觀點接納為其核心的視角。平心而論,以這樣或那樣形式遺留下來的功能主義逐漸成為有關心靈本質及其如何融入自然世界的諸多理論中最被廣泛接受的觀點。
然而,功能主義依舊面臨著其本身的一系列問題。不受任何特殊物理載體約束的優點卻也潛藏著一種心靈太過自由式分布(liberal distribution)的缺陷的威脅。如果任何系統擁有合適的組織便可認識到有意識的心理狀態,那么,我們可以正視某些非常奇異的實現形式。我們可以采用一個由內德·布洛克率先發展而來的例子:組織一(非常大)群人來回反復地傳遞文本訊息以便模仿一個心靈承受劇烈疼痛的功能性架構。很難相信這樣一個系統可以產生任何所承受的疼痛(除了參與者可能感受到的折磨人的厭倦)。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奇異的實現形式被排除出去,那么,問題也就接踵而至:就像對同一論一樣,對于意識主觀狀態的存在的解釋究竟是什么?然而,忍受這種奇異的實現形式并未使得問題消失。正如在同一論中存在著為什么物質的特定組織結構應該擁有(或實現或執行)意識的主觀特征這樣的深層次的問題。事實上,功能主義也許會比同一論變得更糟。僅僅是一種組織如何產生彩色的現象?1
功能主義明確而不是隱晦地表達了另一種折回到笛卡兒時代的擔憂。如果心理是一種組織特征,那么,它將不同于其物質載體,但是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其又如何被實現,均仰賴于物質并由物質所決定。既然如此就產生了有關心理因果性的另一個問題。組織依靠本身看上去無法引起任何東西,只能從任何可能是被組織起來的質料中“借用”因果效力(causal efficacy)。一個簡單的例子,考慮一下颶風是如何導致死亡與摧毀的。颶風等諸如此類的現象是正常模式的突現。將這類突現看成大氣的組織特征貌似合理,它完全依靠并由溫度、氣壓等潛在的大氣屬性所決定。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颶風并不等同于地球的潛在屬性——各種各樣的氣體配置能夠產生颶風(例如,它們或者類似于木星中的漩渦擾動,其所形成的大氣與地球上的大氣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但是,如果我們質問颶風的因果效力位于何處,又會怎樣呢?顯然不存在于颶風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其潛在的特征(如風速)之中。轉而思考意識的情況,其擔憂在于,例如疼痛只有借助潛在載體的力量,而無法借助存在疼痛去引起任何東西。這一點與直覺嚴重相悖。因為我們很難否認疼痛在其本身中擁有因果效力。當我們詢問如此抽象的心理狀態(比如對意義的覺知)可以擁有任何真正的因果效力時,這一問題將變得更加尖銳。
這種從高階屬性流向低階屬性的“因果疏導”(causal drainage)是自然化工作的一個普遍特征,并且它看似在遠離意識的領域內完全無害。我們能很好地理解一次颶風是如何借助其成分而肆虐的,但不太愿意承認我們的意識狀態僅僅是借助完全無意識的實現這些狀態的組成成分而起作用的。與感覺意識相對照,有意識的思維看似更糟。當前最受追捧的關于心理狀態如何獲取意義的哲學理論在本質上也牽涉外在于心靈的實體。因此,這些觀點也被稱為外在主義(externalism)。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介紹了一個著名的哲學思維實驗,假設有一個遙遠的行星,表面上與地球難以區分,但是一個特別之處不同于地球:我們的水(H2O)被孿生地球的另一相似的適宜飲用的液體物質(XYZ)所替代。根據意義理論的觀點,外部關系是一種將內容分派給有意義狀態的機制的本質部分,我們對于H2O的指稱決定了“水”的意義,而在孿生地球上對XYZ的指稱同樣決定了在孿生地球上使用的“水”的意義。當我的孿生兄弟在孿生地球上思考“我想要一杯水”時,他所思維之物在內容上是與我相異的,不管我們在物理層面上可能有多相似(忽視與哲學不相干的不便事實——所選擇的例子僅僅是思維實驗的產物——我們主要是由水組成,而我們的孿生兄弟主要由XYZ組成)。此外,關于外在主義,還有一些由泰勒·伯吉(Tyler Burge)所倡導的極具誘惑力的論證。這些論證強調意義的社會維度,即主張我們的思維內容受惠于我們的語言環境。例如,我們可以思考合法契約,即便我們對這一概念的承擔一無所知。有人可能進行誤導性的思考,比如,契約必須是書面文件。雖然他們錯了,但是他們的思維的確與“我們”的合法契約有關。在孿生地球上,也許契約并非必須被書寫下來,所以,我們的孿生子正在思考著一種關于“他們”的合法契約的真實姿態。
總之,外在論者關于思維的考慮是這樣的,即如果兩個物理層面完全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中,那么,他們可以思維不同的內容(并且我要強調的是這的確應該是這樣,即便環境的不同沒有影響到參與其中的個體的心理狀態)。對此可以想象一個粗糙的類比,兩張相同的紙可以在它們的地位上存在不同,比如其中之一是“貨真價實的美元”。可以爭辯的是,因果力(causal powers)存在于執行其心理狀態的物理結構之中,并且這些結構對于環境的差異并不敏感。因此,依賴其內容的內容——承載(content-carring)的心理狀態并不是有效的(“存在一種貨真價實的美元”的屬性所具有內在的因果效力已經不存在),當我們考慮外在因果關系的力量時,即使內省化地通向我們思維的內容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再一次嚴重地違反了直覺。
心理因果性的問題同樣出現在D. 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稱為“異態一元論”(anomalous monism)的著名理論中。該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斯賓諾莎主義的革新形式——斷言心理與物理領域并非且不能由任何科學的心理物理學法則連接起來,即便可以對事件進行心理與物理上的描述(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斯賓諾莎的身心兩面觀[dual aspect view])。戴維森承認心理與物理事件因果性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并非像看到的那樣是由于事件的心理屬性引起的,而是由于事件的物理屬性引起的。同時戴維森注意以極大的懷疑態度討論“由于……引發”(causing in virtue of),并將其視為我們理解因果性的一種極佳特征。例如,假設一塊磚砸在你的腳趾上并且你感到疼痛,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這是由于磚的重量而不是其顏色造成的。所以在異態一元論中的擔憂是,事件的心理屬性在因果性上是無效的(至少在物理世界中是這樣)。
最近,意識的問題、內容與自然化在某些令人激動的理論中被聯系到了一起,這些理論將心靈的表征力(representational power)當作了意識的成分,因此,削弱了自然化意識帶來的問題,并將其設想為是相對容易的自然化表征(naturalizing representation)的任務。其中的兩大取向需要簡單地提一下。其一是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亞里士多德,將一種有意識的心理狀態定義為作為另一種心理狀態的目標的心理狀態,這是一種高級的心理狀態。即,僅僅當某人正擁有一種思維以便使其處于S之中,那么某人的心理狀態S才是有意識的(這種滯后的思維不必是有意識的,并在一般情況下將不會是有意識的,除非或直至已經出現了關于這種思維的高階思維[higher-order thought, HOT])。顯而易見,這類理論被稱為意識的高階理論(HOT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這類理論存在大量不同的版本,但是它們均共享這樣一個觀點:一個心理狀態是通過成為另一個心理狀態的目標而變得有意識的。我們所有的意識狀態具有一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似乎可以立即用來內省。高階取向將這種特征作為一種意識本身的定義性特征。一個心理狀態的本質對內省的“可用性”(availability)依舊處于爭論之中——從將這種可用性等同于主動的內省(active introspection)(因就像大衛·羅森塔爾[David Rosenthal]獨創的高階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到將其等同于潛在的內省(potential introspection)(正如彼得·卡拉瑟斯[Peter Carruthers]所改進的高階理論),又抑或將其等同于描述控制語言產生系統的心理狀態的獲得狀態(在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解釋中涉及的)。
反對高階取向的論證在于否認對一種稱為有意識的狀態而言無須任何形式的高階理論,而只需假設意識可以借助一階表征(first-order representation)就可予以闡明(該觀點的兩位著名的支持者是雷德·德雷特斯基[Fred Dretske]與邁克爾·泰爾[Michael Tye])。我們意識到的僅僅是那些我們正在表征的心理狀態。一個支持這種取向的著名論證源自所謂的心理狀態的透明性(transparency)。透明性是意識的現象學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在意識的對象和我們的經驗之間似乎一無所有。嘗試一下實驗。d+MSB+VsfCmrJE9k03RERxfh+VmHhOsg/JjzF0pWSIY=仔細注視一個鄰近的咖啡杯。現在嘗試將你的內省主義聚焦到看這個杯子的視覺經驗屬性上面。你將會發現在意識中除了杯子本身的特征并沒有出現任何東西。因此,經驗是透明的。這鼓勵意識的一級表征理論擁護者去反思,如果我們能夠發現在知覺或思維過程中大腦如何表征物體,那么,我們就將有可能解決意識的問題。并且,當然,如果意識能夠被還原為表征,那么,自然化視角的前景將會變得更加光明。較之主觀意識,“表征”將被視作更加直截了當的目標(在這一點上,一階與高階取向都同意),并且事實上當前大量自然化表征的理論正在兜售上述主張(盡管,作為有代表性的哲學理論,它們都飽受自身致命缺陷之苦)。該取向的一個問題是表征看似非常容易發現,若將其視為意識的本質則不免過于廉價了。如果有意識僅僅意味著去表征,那么,意識的出現豈不是隨處泛濫了嗎?我們可以憑借有意識的存在的約定將書籍、電影等諸如此類的事物視為衍生的表征(derivative representation)而不予考慮。然而,也許即便是原始的表征也過于寬泛,并且一種泛心論也會威脅侵入我們的信息負荷的世界。標準的回答是在認知系統中制定某些特殊的表征領域作為意識的歸屬地。然而,反復出現的解釋問題恰恰是這些表征為何喜歡回歸主觀性。
擁護一階理論并不重視內省在接近我們自己的意識狀態中的重要性,但是他們沒有考慮這種接近正是意識的特點。恰恰相反,內省是一種“增添”的可選擇的附件,只有生物才能以相當復雜的概念裝備(conceptual equipment)來利用內省。意識本身是心靈的一種相對簡單的、更初級的特征。因此,在兩種取向各自面對動物意識的態度中可以發現一種有益的比較。在一階理論看來,動物的意識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動物擁有表征其身體及其環境的不同特征的認知系統(最為顯著的是,這種特征的相對生物性價值是在我們稱之為疼痛與愉悅的信息源中的最基本的層次上被編碼的)。因此,可以預料的是,我們與它們共同分享一種基本意識的根本性類型。高階取向認為,動物的意識并不能如此輕而易舉地予以解釋。因為一種心理狀態是有意識的,其必要條件是只存在一個關于這種心理狀態的思維,動物只有在掌握那些用以思考它們處于心理狀態的概念的情況下才會是有意識的。換言之,僅僅為了感覺疼痛,動物將不得不具有心理狀態的概念,至少具有那種將疼痛作為一種心理狀態的概念。毫不夸張地說,動物要想掌握這些概念在直覺上是看似不可能的。對這一問題產生了許多回答,從“溫和”地宣稱意識所需的概念歸根到底并非真的非常復雜,到“激進”地認為概念的缺失恰恰顯示了動物并非有意識的生物(這里我們發現了另一種對笛卡兒學說的奇特共識,動物只是自動機讓這種觀點聲名狼藉)。
綜上所述,伴隨這些近期源自對表征或意義的外在主義者解釋的呼吁取向產生了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在這種呼吁中表征的內容只有在適當地與其關指的狀態聯系起來的時候才能帶出一種狀態。一個直接的問題是:正如隨意創造一張恰巧與美元鈔票完全相同的紙并不會是真正的貨幣那樣,太過隨意地創造恰巧等同于人類的實體也不會擁有任何表征狀態。如果意識在某種程度上等同于或者甚至只是依靠表征,那么,也可以得出這種隨機創造的人類將會是完全無意識的。例如,表現在其行為(無法與我們的相區別)、神經過程(等同于我們的)、聰明的交流能力(從表面上看)方面等等,這一結論似乎非常值得懷疑。
表征理論依舊處于蓬勃的發展之中,雖然它們可能并沒有證明這就是意識問題的答案,但是它們還是提供了大量有關意識的發人深省的解釋。然而,所有自然化意識的嘗試都面臨著這些看上去令人怯步的難題,并且近來某些哲學家又已經重新冒險趟進了這個古老的形而上學泥潭之中:或捍衛二元論的一種現代形式(大衛·查莫斯[David Chalmers]),或甚而為一種激進的泛心論加以辯護(加侖·斯特勞森[Galen Strawson])。
因此,意識的棘手性依舊,并且其主要問題保持著在歷史上的熟悉性。心理狀態如何產生世界中的事物?心理過程如何產生意識或成為意識的基礎?意識又究竟為何存在著?意識可以或應該被理解成世界的一個突現特征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又是何種類型的突現?或者,意識以某種方式代表了世界的一種根本性的和不可還原的方面,這些方面還未被物理學所窮盡嗎?
[責任編輯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