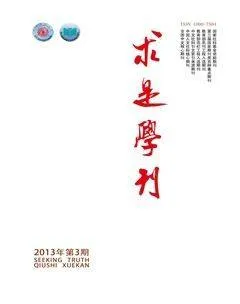中國文學生態的權力結構與文學經典的生成
文學經典的“文化權力”問題首先起于比較文學,涉及種族、地域、性別、殖民、古今等諸多領域。“文化權力”給出了考察文學、文學經典、文學史等問題全新的角度,以之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眾多與經典相關的文學史事件、文學現象,就會產生很多文化研究的特別意義。
一、權力結構
文學,看似只是一個藝術問題,但由于它對社會生活廣泛的包容性,自然也就無法超然于世事之外。因此,文學經典問題不可能在“純粹”的、理想化的藝術言說場域中進行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鮮明地呈現著中國文化生態,在文學批評與文學史言說場域中,有三種文化權力共同影響著經典的生成。
首先是政治的主導權。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作為兩個獨立學科成立的前因便始于政治的介入,當下將兩者整合的意圖漸成共識則源于社會政治強制介入的減弱,由是可見社會政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言說過程中的主導性作用。這種主導性更多地體現為對于言說空間的框定,強烈時是對言說界限、方向、方式、基調的全方位的限定,等于不給言說空間;溫和時則只作或界限或基調的局部限定。具體到經典的生成,“樣板戲”的經典化就是最典型的個案。首先,通過“會議紀要”方式全面否定中外、古今(包括十七年)一切文學,為“樣板”的生成構筑評價機制,拓開存在空間;以政府公告形式先后公布三批所謂“樣板”;以中央政府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級文藝團體學習和表演。社會政治在這個過程中起了絕對主導的作用,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窺視到這樣的主導背后其文化統治的意圖。其實任何文化政策背后都有文化統治意圖在作基礎支撐,只是“手法”的優劣差異,給予的言說空間不一罷了。
再者是學者的闡釋、敘述權。對文學作品作怎樣的闡釋及如何在文學史中加以敘述,在經典的生成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不可小覷的權力,而完成這些工作的是相關學者。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闡釋自其發生就相應出現,相關的文學史敘述不久也漸次出現。“魯、郭、茅、巴、老、曹”經典作家敘述口徑在文革前逐漸形成,而在文革后又重新被確認。學者在獲得話語空間后并沒有停留于此,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作家熱度飆升,在闡釋、敘述中已經逼近甚至超越原來的六大家。錢理群、王一川干脆對現當代作家作重新排名,也突顯出學者權力的直接。學者在構建經典的過程中,以其文學價值立場取舍,終免不了文化上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當然,各異的文化資源也會催生出不同的“啟蒙”論調,有諸如人性、自由、平等等相對普適的言說資本,也有與中國文學語境相對較遠的旗號。
還有就是讀者的選擇權。文學可以成為政治工具、研究對象,但其最主要的功能與價值還在于被閱讀。當然,文學也可以沒有讀者,但要成為經典,必然是在廣泛認可的前提下的。所以,在經典生成過程中讀者也必然擁有其獨特權力——對作品的選擇權(當然這種權力的體現是非個體的)。是行政權力指定經典也好,學者闡釋、敘述以框定經典也罷,讀者最終選擇什么樣的作品往往不受這界限所累。即如時下盛行的網絡文學(當然,網絡文學作為一個文學現象,尚不能納入經典的言說界域內),顯然所擁有的讀者常常遠勝已被“界定”的經典。讀者閱讀雖各存動因,但在當下消費文化盛行之時,文學作品作為消費品的特征愈發鮮明。這種作為消費品的文學與其他流行藝術一樣以滿足消費者——讀者需求為要務,而當下藝術消費的主體是娛樂性消費,這就自然地催生出娛樂性文學。為“經典”的落寞而痛心疾首只怕也只能是一相情愿了。
二、權力關系
三種權力是共生的文學生態,彼此之間也就不可避免會產生關聯。由于三種權力狀態的非恒定性,就決定了三者的關系也總在變化之中,下面就影響經典生成與否的三種關系加以剖析。
在中國當代文學生態中三種權力之間是明顯的“影響”關系,即政治主導權影響闡釋、敘述權,闡釋、敘述權影響選擇權。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生存機制與空間的不健全,當代學者們在從事闡釋與敘述工作時,常常不得不受到政治主導權的直接轄制;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不健全,學者們在從事文學的闡釋與敘述工作時,又常常主動迎合政治主導權的影響。而學者在闡釋與敘述時,是以專家姿態出現的,這就勢必對讀者評判和選擇產生牽引,發生影響。比如魯迅,雖然到目前為止當代的任何歷史階段都將之列為經典作家,但其“經典”的實質卻是不相一致的。官方的政治主導長期突顯其“斗”的精神,與之相應的是教材(尤其是中小學教材)在選編和闡釋中也圍繞“斗”字展開,于是讀者接受的也是一個好“斗”的魯迅。當“與……斗其樂無窮”的時代過后,政治直接干預闡釋的力度式微,學者未能及時匡正教材的編選與闡釋,接受好“斗”魯迅的教育工作者繼續老路,引起的是對魯迅的反感與厭倦。
如果說影響是種被動式聯系,那么,“依存”則是一種主動式聯系。依存表明一種潛在的結構關系,即讀者選擇是學者闡釋、敘述的基礎,而學者的闡釋、敘述又是社會政治主導的基礎。于是,文學史敘述的變化也隨之而來,現代文學著史先行者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幾乎只字不提通俗文學,其弟子錢理群等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則每個階段都設專門章節來談通俗文學、通俗作家、通俗作品。客觀上,這樣的敘述反映了讀者的選擇,對通俗經典合法性確認起到了推動作用。另一方面,社會政治要將其主導權向社會呈現時,也必須依靠學者的闡釋、敘述來建立或點綴其合法性。所以,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與文學相關的批判、批斗,真正產生輿論圍剿作用的是學者和所謂學者們筆下的“棒子”,政治權力借著這些“棒子”取消了許多經典作家、經典作品的歷史地位。
如果說影響與依存是三種權力在相同言說語境下常見關系的話,那么,當三者的言說語境各異,缺乏“共識”時,就會呈現出“錯位”關系。時下的文化生態,三種文化權力雖偶有附和之聲,但所著力點其實是大相徑庭的,以至各唱各調,各行其是。政治主導權依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動機而主張高揚“主旋律”,于是,“五個一”工程里一批頌盛世、唱明君的作品獲了獎。部分學者堅守著精英文化立場,試圖通過對文學經典的闡釋和敘述來介入社會、影響讀者,但總難免被巨大的“后現代”狂歡聲浪所淹沒;更多的所謂學者則或因“義氣”或因“利益”而忙于推薦、吹捧一些所謂的當代“經典”。讀者則依循自己的需要,經典也好,不經典也罷,“我”喜歡就好,開心就好。可以或嚴肅或娛樂或消遣地閱讀,也可以干脆不閱讀。在這里,政治意志、學者意志與讀者意志鮮有交集,互不影響。因此,嚴格說來在“錯位”的當下只會產生“沒有共識”的“經典”。
三、權力延迭
如果說三種身份對應的三種文化權力具有某種穩定性,那么,權力的效力卻是具有時間性特征。這種時效性并不是絕對的此時此效,有些效力卻是此時彼效或彼時此效。20世紀是一個無論內容或是節奏變幻都異常迅猛的時代,這個世紀的中國文學也無法逃脫這樣一種狀態。變幻的本質是宣告某種權力結構效力的消解,當然,消解的同時也是一種新權力結構的生成。
第一,歷時性遺忘。經典化的過程就是歷史化的進程。當過去轉變為歷史,成為一種可敘述的對象時,它必定是經過了沉淀與淘洗,必然是一個簡單化過程。與歷史一樣,經典的生成也有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遺忘。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蕪雜無序的枝蔓逐漸被淡化,主干的線條慢慢清晰。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它有客觀歷時性遺忘與主觀選擇性遺忘兩個部分。客觀歷時性遺忘是一個自然過程,包括文學在內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這樣的自在狀態。無論是官方某一政治語境下的經典、學者某一文化階段鼓吹的經典,還是讀者某一消費熱潮搶購的經典,隨著時間的推移,絕大部分會被“遺忘”。但文學又并非一個全然的自在狀態,人的主觀介入也常常發生效力。文革封存圖書館,社會上只有被刪改的魯迅與樣板戲(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是試圖以某種意志來選擇記憶,強制遺忘。可能沒有一次努力能絕對成功,但哪一次沒有造成文化的斷裂呢?正是在這樣的斷裂中,經典逐漸在文學歷史的骨架中突顯。
第二,逆時性鉤沉。與歷時性遺忘相反,逆時性鉤沉則重返歷史,對經典的生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前所述,因為權力的效力都有時效性,這就給學者提供了錯時研究的可能性。(權力效力除了時效特征外,還有空間性特征。這就給學者提供了錯空研究的可能性。比如海外學者如夏志清在美國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即是一種錯空研究)學者通過對歷史資料的鉤沉,實現對既成的經典言說的反叛,即通過錯時研究部分消解了文化權力在歷史言說中的規約,形成新的言說可能性。1928年,胡適推出了他的著作《白話文學史(上)》,斷言凡有價值的文學必是白話文學,文言文學概無價值,中國兩千年間只有些“死文學”。書中把漢以后的文學史定性為文言文學與白話文學彼此爭斗、彼此消長,白話文學不斷戰勝文言文學的歷史。顯然,為白話文爭得“正統”、“正宗”地位的歷史是其根本動機,但是,也正是胡適的鉤沉,中國文學史上的白話文學創作重新被正視,被重視。“文言”的絕對話語權在包括此書在內的努力中消解。
經典在權力的制衡中形成多元性,在遺忘與鉤沉中形成相對的穩定性,然后在新語境中形成新的制衡,再有新的遺忘與鉤沉……在若干的循環中形成相對超越歷史語境、超越權力的超穩定結構的經典。這時的經典才具備了相對永恒的特質,而之前被稱作經典的只能被命名為“階段性經典”。足見,文化“權力”影響著但又不能絕對控制經典的生成。是“憎恨”也好,是“影響的焦慮”也罷,學者以創新的視野在經典中找尋“特別”的切入點客觀上豐富了作品的闡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