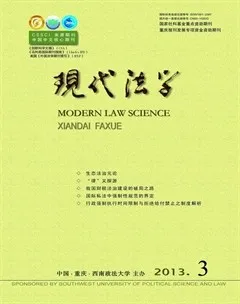“律”義探源
文章編號:1001-2397(2013)03-0018-24
收稿日期:2013-02-20
作者簡介:陳寒非(1984-),男,湖南岳陽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博士生。
摘 要:從“律”字的兩個基本構件入手,先后分析了“聿”和“ㄔ”的含義。甲骨文 “”字本義可能為“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而其引申之義為“統一、協調、標準、區分、界限”等。甲骨文中的“ㄔ”記為“”, 此即為甲骨文中“行”()的半邊,“ㄔ”之義為“小步”,其義大概來源于“行”。“步”在古代為測量單位,引申為“標準”。古人借助已有的“聿”和“ㄔ”組合成“律”字用來指稱定音標準。“律”之本義為“音律”,作為調音或定音工具,因而具有“規范、標準”之義,后演變為“軍律”、“歷律”。商鞅“改法為律”之后,由于統治者更為重視法律的“規范”功能,逐漸以“律”取代“法”,用以指稱成文法典。
關鍵詞:律;聿;行;ㄔ;訓詁
中圖分類號:DF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3.03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一詞成為一組基本的語詞,被人們在不同語境和場合下使用,法律本身也與現代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在英文中,“法”與“律”似乎并未截然分開,而是等同互用,均由英文單詞“law”來表達在其他西語中可譯為“法”、“律”或“法律”的詞,拉丁語為Jus和Lex,希臘語為δι′καιο和νóμο,法語為Droit和Loi,德語為Recht和Gesetz,西班牙語為Derecho和Ley,意大利語為Diritto和Legge。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西語詞匯中,前者一般表達為廣義的法、抽象的法,而后者一般表達為狹義的法、具體的法律規則。 ,包括正義、權利等含義卻由英文單詞“right”來表達。然而,如果我們試圖探尋中國漢字的源頭及其含義,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古文“法”字和“律”字的含義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更不同于今天所指涉的含義。漢語中“法”與“律”兩字組合用來指稱“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通過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體系”目前國內大多數法理學教材中對“法律”語詞的定義基本上與此大同小異。關于“法律”的這一定義,可參見:付子堂.法理學初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5.的現象直到近代才出現,“法律”二字是從近代日本引進的詞匯[1] 。在今天中西傳統法律文化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由于“中西方思維、文化及心理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中英文表述上的不同”[2]。因此,避免對中西傳統法律文化的誤讀及語詞的誤用,有必要正本溯源,探尋“律”字之古義。
與古埃及象形文字、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古印度文一樣,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也是獨立地從原始社會最簡單的圖畫和花紋產生出來的,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象形文字。在沒有發明文字之前,上古之人通過“結繩”來記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體事務,鄭玄《周易注》云:“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與此同時,繪畫也是一種重要的記錄方式[3]。先民們通過繪畫,用圖形表現出觀察到的一些自然現象,形成一些具體的符號。只不過這還不是文字,而僅僅只能稱之為“圖形符號”。但是,后來的象形文字即在此基礎上衍生而來,象形文字再經過漫長的演化發展形成今天的漢字。從這個意義上講,“漢字不僅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系統,而且是一種承載著漢民族文化的特殊符號體系”[4]。“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5] ,所以,從中國古文字的結構入手,解讀漢字所承載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通過尋找最初的“律”之本義,可謂是我們理解中國早期法律文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經過考證,在現存甲骨文中,并無“法”字和“刑”字,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才出現古體“灋”字和“刑”字。關于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灋”與“刑”的具體寫法,可參見:容庚.金文編[M]. 張振林,馬國權,摹補.北京:中華書局,1985:679,291,351. 與此相反,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律”字就已出現并廣泛使用。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在與古代法律實踐活動有關的古文字中,‘律’字的歷史可能比‘刑’字、‘法’字更久遠,其產生和沿革的途徑也更豐富而復雜”[6]。 因此,相較于“刑”、“法”等字,更有必要探尋“律”之古義。
現 代 法 學 陳寒非:“律”義探源 為了探尋“律”字最初的含義,深層次理解中國早期法律文化,筆者試圖用訓詁及考據的方法,對“律”字各個義項進行分析和考證,從而綜合得出其形體結構上的含義。事實上,通過訓詁研究早期法律文化的現象早在兩漢時期就已出現。隨著“兩漢經學使用的訓詁學方法的成熟以及體系化,有中國特色的法律解釋學開始產生,并正式成為一門成熟的學問,這改變了中國古代方法之學不發達的面貌”[7]。這樣的研究進路將會使得“律”之本義直觀具體地展現在我們眼前;通過對“律”字各個義項的訓釋,中國古代早期的法律價值、法律觀念及其發展歷程將會呈現出一個更為清晰的畫面。再者,雖“法”、“律”二字為世人常用,但“自來考釋‘法’字者多,而探究‘律’字者少”[8],因而,此項研究同時也是對“律”字研究的一種補益性工作。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深感古文字學功底淺薄,故不揣淺陋擬將近期的一些研究心得在此妄加闡述,以乞教于方家。
一、“律”字古今訓詁成果綜述
(一)古人對“律”字之訓釋
晚清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云:“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小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由此可見,小學乃經學之基礎,而訓詁學作為傳統小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然存在許多古漢字訓釋專著,這使得古人對“律”字的訓釋成果頗豐。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詞典《爾雅·釋詁》篇中對“律”字義訓曰:“典、彝、法、則、刑、范、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宋邢昺疏:“律者,常法也。”《釋詁》又訓曰:“柯、憲、刑、范、辟、律、矩、則,法也。” 疏曰:“此亦謂常法,轉互相訓。……刑、范、律、矩、則,皆謂常法也。”
《爾雅·釋言》篇云:“律、遹,述也。” 疏曰:“皆敘述也,方俗語異耳。律管所以述氣。遹者,述行之也。《大雅·文王有聲》云‘遹駿有聲’之類是也。”《釋言》又訓曰:“坎、律,銓也。”郭璞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疏曰:“謂銓量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郭云‘《易》坎卦主法’者,《說卦》云:‘坎為水。’水平,故主法。云:‘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者,《白虎通》云:水之為言準也。《律歷志》云:‘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又曰:‘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兩者,兩黃鐘律之重。’是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也。”
《爾雅·釋器》篇云:“律謂之分。”郭注:律管可以分氣。疏曰:“律,一名分。鄭注《月令》云:‘律,侯氣之管也,以銅為之。’《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令自大廈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則為六律,雌鳴則為六呂。陽管為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氣為呂。《律歷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以其分候十二月氣,故又名分。郭云:‘律管可以分氣。’是也。”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訓曰:“律,均布也,從ㄔ,聿聲”,清段玉裁注:“均律雙聲。均古音同勻也。《易》曰:師出以律。《尚書》:正日,同律度量衡。《爾雅》:坎、律,銓也。律者,所以范天下不一而歸于一,故曰均布也。”
《廣雅·釋言》云:“律,率也。”清王念孫疏曰:“《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律之為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又引宋均注云:率,猶遵也。續《漢書·律歷志》注引《月令》章句云:律者,清濁之率法也。《周官典》同注云:律,述氣者也,述與率通。《中庸》:上律天時。注亦云:律,述也。”
《玉篇》:“律,六律也。”
《廣韻·術韻》云:“律,律法也。”《廣韻》:“律,呂也。”
除上述古籍對“律”字訓釋外,在其他文獻中存在著許多訓釋結論。如《淮南子·覽冥篇》高誘注:“律,度也。”《淮南子·主術》:“樂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風,此聲之宗也。”《荀子·非十二子》:“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奸心。”楊倞注:“律,法。”《國語·周語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管子·七臣七主》:“律者,所以定紛止爭也。”《尚書·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孔傳:“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晉書·刑法志》曰:“秦漢舊律,起自李悝,悝者著網捕二篇,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又爵命之等曰律。”《禮·王制》曰:“有公德于民者,加地進律”。疏曰:“律即上宮九命繅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游之等是也。”等等。
(二)近人及今人對“律”字之訓釋
近代以來,不少學者紛紛對“律”字進行訓釋。一方面,今人的訓釋是建立在古人的訓釋基礎之上,并結合新的資料和自己的理解進行新的闡釋。另一方面,自國學大師黃侃創立了訓詁學的現代觀念并對訓詁學進行重新界定之后,使得新訓詁學驟然興起,并拋棄了傳統訓詁學的一些弊病。作為訓詁學的延伸,現代訓詁學在更高層次上緊密結合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等學科[9],這直接影響到今人對“律”字的訓釋。
沈家本(1840-1913)在《歷代刑法考》中先后援引了《爾雅·釋詁》、《漢書·律歷志》、《釋言》、《廣韻》、《管子·七臣七主》、《淮南子·覽冥篇》、《說文解字》以及《釋名》等文獻,在綜合各家觀點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三個重要觀點。第一,《史記》之《律書》乃兵書也,古者大刑用甲兵,則刑亦在其中矣。律為萬事根本,刑律其一端耳。今則法律專其名矣。第二,王注(王筠《說文解字句讀》)本于桂氏《義證》(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是律之本義,段《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乃后來引申之義也。第三,《史記》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六律”。《漢書·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頤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 又云:“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蓋六律之密必無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應如是,故亦以律名。《釋名》以累心為訓,非定律之本旨[10] 。
程樹德(1877-1944)在《中國法制史》一書中綜合援引了《爾雅》、《說文解字》、《說文解字義證》、《說文解字句讀》、《史記·律書》、《后漢書·律歷志》、《周語》和《唐律疏義》等古籍中對“律”字的訓詁,認為“蓋自秦漢以來,法之與律,遂為通用之文字矣”[11] 。
章太炎(1869-1936)認為:“律,從聿者,筆也。筆以竹制,律呂亦竹制。其聲與類近,引申為法律。”[12]雖然章太炎先生對“律”字的訓釋只有短短的一句話,但是卻向后人傳達了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將“律”訓為“筆”;二是,因“筆”與“律呂”之“律”聲與類相近,故引申為法律之義。
梁啟超(1873-1929)贊同許慎《說文解字》和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中的觀點,認為“律”字語源為樂律。“《漢書·律歷志》言同律度量衡,而度量衡又皆出于律。夫度量衡自為一切形質量之標準,而律又為度量衡之標準,然則律也者,可謂一切事物之總標準也,而律復有其標準焉,曰黃鐘之宮。黃鐘之宮者,十二律中之中聲音也,以其極平均而正確,故謂之中聲。所以能為標準之標準者,以其中也,故律者,制裁事物之最嚴格者也。……其后輾轉假借,凡平均正確固定可為事物標準者,皆得錫以律之名。”[13]此外,在對“《釋名》以累心為訓”問題上,梁氏持不同于沈家本的意見,認為“《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是名其為事物標準之義。”
楊樹達(1885-1956)在《積微居小學述林》之《釋律》中,通過對《說文解字》、《禮記·禮運篇》、《呂氏春秋·仲夏紀》、《北堂書抄》等文獻進行考證后,認為“必知聿筆為一字,律從聿聲之故乃可說……若然,以竹管束毫書事謂之聿,以竹管侯氣定聲謂之律,律從聿聲,實兼受聿字之義也”[14]。由此可知,楊樹達先生的觀點主要有二:一是聿筆為一字;二是律從聿聲且兼受聿字之義。這極大地啟發了我們對“律”字的研究。
陳顧遠(1896-1981)對“律”字詞源的考察起源于對“商鞅何故以‘律’改‘法’,而不用其他名稱”這一問題的思考。陳顧遠先生提出了三種可能性猜測。第一,為音律。“律原為六律六呂之律,亦為度量衡標準之律,罪之輕重不容錙銖之差,此或刑書之以律名歟?”第二,為竹制器物之名。“古代竹制之器曰律,刑書書于竹簡之上,鄧析竹刑之得名以此,或為商鞅改法為律之故也歟?”但是,對于上述兩種猜測,作者難以信服,“然律之如上解釋,多為后起之義,嘗非商鞅所熟知也”。第三,將軍法之律移作刑典之稱,“易師卦既有‘師出以律’、‘失律兇也’之語,乃系對軍法而用者,商鞅為避免法刑用語之混雜,遂以軍法之律,移作刑典之稱,亦不得已而為之耳。”[15]
蔡樞衡(1904-1983)認為:“秦漢有律、令而無禮法。律當是箻的省筆。而箻實是的或體。當是竹名引申而成的簡冊名稱”,又:“可見趙國刑法名稱恢復了因竹名簡,因簡名刑的傳統習慣。……史遷不知九章律的律原是箻的省筆,理應與簡書同義,而竟雜揉音律和刑法。”[16] 蔡樞衡先生的觀點與前人的大相徑庭,僅僅將“律當是箻的省筆”,而箻與同,只是一種“因竹名簡、因簡名冊”的命名習慣使然。蔡樞衡的觀點與陳顧遠的有一定共通之處,即都曾將“律”視為“竹制器物之名”。
丘漢平(1903-1990)認為,“律”字起源于樂律,“律的語源不是用于法律的律字,卻是在于樂律的律字。‘樂’是有和諧的音調,一定的高低或拍子。這就是說‘律’字具有標準的意思。……后來用到行為規則的法律上,律字幾乎代法而用,所以明嚴限也[17]。這一觀點與梁啟超等人的觀點類同。
北京大學歷史系祝總斌先生對“律”字的訓釋觀點主要有五。第一,戰國之前并不以律管定音,故“律”字原指律管之說應當予以否認。第二,“聿”字原義與“筆”字不可分,“聿”字由手握筆以刻畫甲骨器物之狀,引申指刻畫工具——筆,由于上古之人圖騰崇拜并會用筆在甲骨器物上刻畫不同徽識以區分不同氏族,故“聿”同時逐漸有了區分之義,進而又有了界限、規矩、行列之義。第三,甲骨文中起初出現的只有一個“尹”字,像手握筆以刻畫甲骨器物,后因尹字逐漸向官名發展,于是便另用繁文“聿”字來承擔原意。第四,“聿”“律”二字很可能本為一字,“律”乃“聿”之繁文。第五,從音韻上來看,“尹”、“聿”、“律”很可能本為一音,后來因“尹”字向“官”義發展,“聿”、“律”保留原來的筆、區分、界限之義,讀音便略生變異[6]15-18。
武樹臣教授通過總結前人訓釋,認為“律”的含義被概括為四種:一是音律、樂律、聲律;二是用來校正樂音的管狀器具;三是指軍令、紀律、法律;四是與“率”同義,可互代。在對“律”進行深入研究后,武樹臣教授認kXiJLXJJQu6Tp8fj/s8/mwzw6OQp2W7AWDel02ZL3sY=為甲骨文“律”字衍生的宏觀路徑有三:第一個發展方向是以職官為中心,肀→尹→史→君;第二個發展方向是以制度為中心,肀→→聿→率→律;第三個發展方向是以器物為中心,肀→→聿→筆 [5]105-113。除此之外,還可參見: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84-146.
李力教授早年贊同“甲骨文中‘師惟律用’(《懷特》B·1581[18] ;《屯南》119[19] )與《易·師》‘師出以律’中的‘律’同義”這一觀點,認為《懷特》B·1581和《屯南》119兩片甲骨主要反映的是軍律一類的號令[20]。但在后來的研究中,他認為難以確定甲骨文“師惟律用”中的“律”字是否專指商代的軍法,而商代晚期金文中出現的“律”(如戍鈴方彝銘文中“己酉,戍鈴尊宜于召,置庸,帶九律帶”)應與音樂有關,可以理解為音律之義,而這正好可以補正甲骨文卜辭“師惟律用”的“律”為音律[21]。 此外,李力教授贊同祝總斌先生的觀點,認為自商鞅“改法為律”后,“律”才成為一種法律形式,“律”才作為“法律”講[19]48。
香港中文大學沈建華教授通過考釋殷墟卜辭中“聽”字,認為“聽”指樂師,為商王室職官,稱之為“王聽”。樂官的“聽音”與“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卜辭中的“律”有些并非“律令”之“律”,而是“音律”之“律”,如“師惟律用”的“律”即為音律。君王通過六律聽音,規范行為道德,又被視作制定歷律的標準。“律”有可能從“建”字分化出來[22]。
錢劍夫持馬克思主義階級法學的立場,從社會政治變遷史以及中國古代律學發展史的角度探討了律的特性,認為法律在奴隸社會叫“刑”,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變革的時候叫“法”,封建社會成熟以后就叫“律”,直到清代。商鞅改法為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律”從一開始就是維護和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的工具和手段[23]。
徐忠明從“道”和“器”兩個層面解讀傳統中國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認為:(1)法律之律與歷律、音律之間存在密切的淵源關聯,從而賦予法律“法天之學”和“精密計算”的精神品格;(2)承襲早期中國的法吏傳統,緣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變法和戰爭的特殊背景,這種具有確定性、統一性和計算性特征的律,滿足了帝國集權統一與行政科層組織的需要;(3)伴隨秦漢時期儒法帝國的最終形成,律與禮義、道德、情理出現了合流的趨勢,由此形成了傳統中國法律與司法的基本特征[24]。
吳建璠認為,律本來是音樂的術語,是調整音調的標準,后來把律用到軍事上,有軍律的意思。軍律是最有權威、最有分量的,改法為律就正是借用了軍事上的律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強調它的必須遵守[25]。
劉釗在《卜辭“師惟律用”新解》一文中指出,“師惟律用”中的“律”應該是指“音律”之“律”,與“律令”之“律”毫不相干[26] 。
田濤認為,“律”字最初是指定音,是律呂之“律”,后來發展成為歷法之“律”,在戰國時期發展成為律統之“律”,“律”具有統一的含義[27]。
張玉梅認為,“律”的本義,原指古代樂器中的調音工具。古人把音階分為十二,陽六稱為律,陰六稱為呂,故音律又稱為“呂律”或“律呂”。《說文》:律,均布也。均,指均鐘,類似于現代樂器中的“定音器”,用以使音調均布和諧。律的字義經過引申有了“律,所以定紛止爭也”的義項,人們選擇這個字,是希圖以一種“均布和諧”的精神來解決法律上的糾紛和事件[28]。
(三)古今訓釋成果述評
概而言之,古今對“律”字本義的訓釋,主要有五種代表性觀點。第一,音律、樂律或者校正樂律的定音器。這一觀點占主流,如梁啟超、丘漢平、武樹臣、李力、田濤、沈建華、吳建璠、劉釗等基本上持這一觀點。第二,歷律。這一觀點認為,“律”從音律發展到歷法之“律”,歷法的制定參照音律中的“十二律”定音標準。如田濤、徐忠明等。第三,軍律。如武樹臣、李力等。第四,筆。如章太炎、楊樹達、祝總斌等。第五,尹。如祝總斌、武樹臣等。
盡管學者們為“律”字的訓釋提供了多種結論,也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有利于后輩學人在此基礎上進行更好的研究,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由于時代、材料和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導致了前人對“律”字的訓釋存在諸多不足之處。這種不足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料。前人對“律”字訓釋缺乏考古學資料支撐,可能也就大大降低了其結論的可信服程度。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使得新的文獻資料不斷被發現,研究手段也在不斷提升,這一切為我們研究古漢語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例如,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發現,此后甲骨學的研究不斷深入,這為古文字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來考古發現的新材料使得我們對上古社會文化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也為我們探尋“律”字本義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材料,為我們佐證前人的訓釋結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苛求于前人,畢竟科學技術是不斷向前發展,研究資料也在不斷地更新。本文對“律”字的訓釋,將大量參考一些新的資料,特別是考古學方面的成果。
第二,方法。前人對“律”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學領域(包括訓詁、文字、音韻等),這一領域無疑也是最重要的領域。但是,由于學科領域的限制,研究方法也呈現單一化。李玲璞教授曾經指出,“當前的漢字文化學研究似仍存在著兩種傾向,或偏執于文獻學一端,僅囿于文字學領域而未能完成文化學意義的跨越;或脫離傳統小學的優秀傳統,借助文字去附會主觀臆測。”[3]24近年來的語言文字學研究,除采用傳統小學的研究方法外,越來越重視與文化人類學、考古學、古文獻學、古器物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結合,綜合采用多種研究方法,將古文字置于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來進行考察,進行詳細而深入的文化闡釋。本文將主要采用這種注重文化闡釋的綜合研究方法。此外,本文還將采用“二重證據法”王國維于1925年提倡運用“二重證據法”考古代歷史文化,“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參見:王國維.古史新證[G]//王國維.王國維考古學文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25.) 此外,1917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兩文是王氏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甲骨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G]//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59:53-61.) ,即“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一種研究方法。
第三,路徑。“律”字為合體字,由兩個構件“聿”、“ㄔ”構成。前人對“律”字的研究大多直接從“律”字本身入手,而沒有首先分析“律”字中“聿”“ㄔ”的含義,從而導致對“律”義理解上的偏差。事實上,漢字構件在構字時都體現一定的構意,具有如表形、表義、示音、標示、替代等功能。古人在構字過程中將某些單字進行組合形成新字,自然融入了他們對某個單字的理解。職是之故,在研究路徑上,本文選擇從“律”字的各個構件入手,全面分析其個構件的基本含義,試圖求得“律”的本相,即“律”字通過形體構造表現出來的真正意義。概而言之,張永和教授對“灋”字的訓釋路徑主要是從“灋”字的基本構件“氵”、“廌”和“去”等入手,逐項訓釋,嚴密論證,層層推進,可謂訓詁考據的經典之作。(參見:張永和.“灋”義探源[J].法學研究,2005,(3):151;張永和.法義[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3-38.)在此基礎上再對“律”字語義的輾轉演變做出全面的考察。
二、釋“聿”
語言的產生早于文字,這大概沒有太多疑問。關于語言的起源,語言學家有模仿聲音說、情感刺激說和經驗說等幾種推測。起初,人類與動物一樣,都有喜怒哀樂需要表達,由于情感刺激的“種類”和“強弱”的不同,語言的發音可能會呈現一定的差別,比如形容情感強烈的語言可能發出的聲音較大,而情感較弱的語言發聲可能就會較為微弱。在表達情感方面,原始人可能也與動物一樣,聲音的強弱大小代表著情感的強弱程度。因此,最早可能會產生一些以元音為主的語言。隨著人類模仿能力的增強,自然界和動物界的一些聲音也開始被吸納進語言之中,比如風聲的呼嘯、雷聲的轟鳴、鳥兒的鳴叫、動物的哀嚎等。在模仿的過程中,一些輔音開始出現,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元音和輔音的完備的語言系統。但是,由于在語言交流過程中,聲音指稱實物時會出現一些混淆和歧義,無法達到精確表達的目的,而且隨著人類智力的發展,一些較為抽象的含義也無法用聲音表達出來,語言變得越來越復雜,這個時候作為語言的輔助——文字就隨之而產生了。
文字產生之后,自然會隨之出現關于文字形體結構方面的理論。中國古代對漢字形體結構進行研究的理論是“六書”。“六書”一語最早見于《周禮·地官·保氏》,書中列舉的周代用來教育貴族子弟的“六藝”項目中提到“六書”:(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但是,《周禮》并沒有具體闡述“六書”理論。直到漢代,“六書”理論才趨于成熟。盡管當時古文學派學者如劉歆、鄭眾、許慎等人在“六書”稱謂上存在差異,但一般都認為“六書”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六個方面。所謂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詁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參見:許慎.說文解字·敘[M].徐鉉,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楊雄《訓纂篇》及許慎《說文解字》正是以“六書”為基礎并將其發展成熟,后世的“六書”理論也差不多都是以許慎《說文解字·序》中闡述的為主。從“六書”理論來看,漢字的發展規律應該是先有象形、指事,后有會意、假借,最后才有較為復雜的轉注和形聲。
然而,“六書”理論在解釋漢字的形體構造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象形、指事、會意三類用意符造成的字(表意字)之間界限的模糊性以及轉注概念的模糊性[29]。唐蘭先生在批判傳統“六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三書”說,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聲文字。但是唐蘭先生的“三書”說亦遭受到其他學者的批判。陳夢家先生認為,唐蘭先生的“三書”說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象形、象意的劃分意義并不大”;二是唐氏“三書”理論將假借字排除在漢字基本類型之外,這樣的做法不合理。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三書”理論,即象形(包括許慎說的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和形聲[30]。裘錫圭先生對陳氏的“三書”理論作出適當修正,認為“象形”應該改為表意(指用意符造字),這樣才能使漢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書”說里都有它們的位置。這樣,“三書”理論應該是指表意、假借和形聲 [27]106-107。筆者認為,無論是“六書”理論抑或是“三書”理論,都為后人研究漢字的形體構造方面提供了方法,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只不過在歸類方法和概念周延性上可能存在差異。鑒于此,本文在漢字形體構造理論的選擇上將以傳統“六書”理論為主之所以選擇以傳統“六書”理論為主,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傳統“六書”理論畢竟經過2000余年的發展,是目前為止較為成熟的理論。并且,它奠定了后世文字學研究的基礎,較好地闡述了漢字的發展演變過程,能夠為我們研究“律”字的演變提供了一種較為清晰的脈絡。第二,盡管幾種理論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各有優劣,無法判斷哪種理論絕對正確,學界對此也沒有統一的意見,從而為我們的選擇提供了較大的自由余地。第三,筆者從事古文字學研究,最初接觸的理論即是傳統“六書”理論,能夠較為嫻熟地運用此理論進行研究。鑒于此,本文選擇以傳統“六書”理論為主,其他理論為輔。,兼采唐蘭先生的象形、象意和形聲“三書”理論以及陳氏和裘氏的“三書”理論。
中國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最早可能從圖形符號演化而來。唐蘭先生認為,由原始文字演化成近代文字的過程里,細密地分析起來,有三個時期:由繪畫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聲文字到完成是近古期。(參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M].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83.)伴隨著語言的產生,最早的原始圖形與聲音結合起來,用來指代一些具體的實物,例如在原始繪畫中“犬”的圖形記作“”,而在甲骨文中記作“”[31]或“”[32]。不難發現,這兩者之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甲骨文可謂是對原始圖形的一種簡化,并且保留了原來圖形所指代實物的基本特征。當圖畫發展到象形文字之后,由于象形文字一般是指代一些具體實物,無法表達更為復雜的含意。因此,象形文字需要不斷進行分化,或是在形體上分化,如某些單個的象形文字進行組合或是形態發生變化;或是在意義上延伸而出現“引申”;或是在發音上出現“假借”。象形文字不斷分化和演變的結果就是產生了象意文字和形聲字。因為,隨著人類智力的發展,一些指稱具體實物的象形文字無法表達抽象的語言,因而需要采取象形文字圖形中的一部分,賦予它們新的意義,這時就產生了象意文字。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一方面,“律”字的產生,大概也經歷了從圖畫到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再到形聲字的過程。再者,漢字的一般發展規律是由簡到繁,由單體字到復合字,“律”字的產生過程,極有可能是先出現“肀”,再有“”和“聿”,最后再出現與“ㄔ”相結合的“律”。另一方面,“律”作為形聲字,符合形聲字的演變規律。此演變規律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從名詞變作動詞的部分,每一個字有主動的和受動的兩方面,以主動的為形,受動的為聲;二是在主語上加以詮釋或補充而成的文字,每一個字里有主語和附加的兩方面,則以主語為聲[33]。“律”字應該是屬于后者,即主語為“聿”,而“ㄔ”為附加。是故,許慎《說文解字》曰:“律,從ㄔ,聿聲。”由此可見,在“律”字的兩個義項中,“聿”毫無疑問是最為主要的一個義項,構成“律”字中的主語,而“ㄔ”可能是輔助表達某種含意,“律”字在形聲字演變的過程中通過增益、歸納、轉注等方式“孳乳而生”。此外,“律”在甲骨文中作“”[34] ,“聿”字在甲骨文中作“” [32]319,一期,京一五六六、“”[32]319,一期,乙八四〇七或“”[32]319,三期,京四三五九,“”字右半部分與“”同。職是之故,“律”字得義應從“聿”處探求。
需要指出的是,甲骨文中出現的“律”字有:
京都二〇三三 地名
京都二〇五三 日戊王弜…律其…亡…弗每
懷八二七 …律在…
懷一五八一 師惟律用
小屯一一九 師惟律用
盡管如此,由于京都二〇三三中的“律”作為地名,而京都二〇五三、懷八二七殘缺過多,無法知曉其本意。懷一五八一和小屯一一九“師惟律用”中的“律”究竟何意,是否與《易經·師卦》“師出以律”中的“律”同義,自來學術界爭論較多,有人認為是指音律,也有人認為是指軍令、軍律等,答案不一而足。究其原因,在于沒有對“律”字本義進行系統的探討,也沒有對“律”字中的一個關鍵義項“聿”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導致了上述爭議的存在,無法有力說服對方。因此,下文將首先從“聿”入手,分析該義項的基本含義,力求全面探尋“律”字之本義。
稍稍對比一下甲骨文中的“”、“”或“”,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三個字都由兩個共同的符號“”和“”組合而成。我們首先來看下“”。甲骨文中“”被釋作“又”或“右”。《說文解字》云:“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于省吾先生通過總結羅振玉、王國維、王襄、吳其昌等人的觀點后認為,“”字本象右手形,與“”象左手形相對,卜辭中“”與“”有所區分,亦有個別例外,在偏旁中則無別[36]。故“”可作又、右、祐、有、侑等。盡管甲骨學者對“”釋讀不一,但將“”視為手形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這并無太多疑問。
學者們對“”的一般解釋是筆形。徐中舒先生認為,甲骨文中“”從又執,象以手執筆形[32]319。于省吾先生認為,、聿、筆初形均當作“”,象手持筆形,其后以用各有當,以聿為語同,筆為專名,許慎歧而為三,解其形體為從巾,從一,實誤[36] 。然而,楊樹達先生認為,“聿甲文作,金文作。……甲文之,中直畫即象竹管之形,非秦時始用竹為管而謂之筆也。若然,以竹管束毫書事謂之聿……。” [12]55 應該說,楊樹達先生的觀點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思路:一是甲骨文中“”可能與“”同;二是“”不一定僅僅只是指筆形;三是“丨”可能是指竹管或者某種棍狀物。《說文·丨部》云:“丨,上下通也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席。凡丨之屬皆從丨。古本切。”段玉裁注:“囟之言,進也。”《廣韻·混韻》云: “丨,古本切。”《集韻》云:“丨,古本切,讀若袞。象數之縱也。”也就是說,“丨”的發音有兩種,從上而下寫發袞音,從下而上寫發退音。故“丨”音袞,古為上聲;今讀去聲,即今天所謂“棍”的發音。
倘若上述結論成立,“”中的“丨”可能是指竹管或者某種棍狀物,那么它可能指的是律管、筆管或權杖。這三種實物之間因為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從而被古人抽象出來,用來指代不同的含意。下文將分述之。
(一)手執律管之“”
如果“”中的“丨”指的是某種管狀或棍狀實物,那么這種實物最早可能指的是律管。要論證這一淵源流變,我們需要借鑒音樂考古學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
人類與生俱來的功能就是“聽”和“說”,聽說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基礎。早期人類可能會模仿動物和自然界的一些聲音。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認為,“從語言的最早時期到我們今天,人們不可能從未意識到他們的一些詞語來源于大家都聽到的聲音。例如,在我們現代英語里,模仿的成果就很明顯。蒼蠅‘buzz’(嚶嚶),蛇‘hiss’(咝咝),爆竹或啤酒開瓶的pops(嘭),加農炮或麻鴟鳥的booms(隆隆)。在世界各種語言中,表示動物的詞和表示樂器的詞,聽起來常常是動物叫聲和樂器音調簡單模仿。如戴勝鳥名為‘hoopoe’,樹懶名為‘kaka’,東方人名為‘tomtom’的是一種鼓,非洲人名為‘ulule’的是一種長笛,薩摩亞人名為‘khorgbong’的是一種木制的手風琴……。因而,存在一些帶有模仿聲音名稱的樂器,如‘shee-shee-quoi’是紅色印第安人醫生的神秘串鈴,……鼓,在豪薩人語言中為‘ganga’……當象聲詞和表意詞這兩類詞的變化過程一起進行時,一方面,象聲詞改變了它的原始聲音,另一方面,它的意義也轉變為另外的事物。例如,英語的‘pipe’(笛)這個詞,拋開我們賦予它的獨特的發音不說,我們可以往后引證它的中世紀的拉丁語或法語的發音:‘pipa,pipe’。在我們前面有一個顯然模仿聲音而命名的樂器名稱,這個名稱源自于一種類似的聲音,這種聲音常用來表現小雞的唧唧叫聲。……阿爾袞琴印第安人也根據‘pib’這個音構成了他們本地的長笛的名稱:‘pib-e-gwun’。…… ‘pipe’一詞也已經由樂器轉而表示它最初所屬的東西,并且用來記述各種各樣的管子:煤氣管、水管和普通的管子。” [37]我們從泰勒的這段描述可以看出,人類起初依靠自身聽覺功能模仿聲音,從而創造出一些表示聲音的語詞,用以指代某些具體的實物。一旦象聲詞和表意詞相結合,象聲詞的發聲發生改變,而且其意義也相應發生轉變。當人們發現某種樂器的聲音與動物界或自然界的某種聲音有些類似的時候,自然就會用這種類似聲音來指稱樂器及具有相似屬性的實物。那么“聿”字的產生正是這么一個過程。
人類一個十分重要的感覺器官就是聽覺,當人類有了聽覺后,音樂的產生才有可能。音樂起源問題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研究的熱門話題,這至少可以追溯到盧梭(Rous-seu)、達爾文(Darwin)、孔百流(Conbariou)和格羅塞(Grosse)等。當前我國學者也紛紛從語言學、生物學、宗教學、考古學、藝術人類學、民族學等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種種理論。關于音樂的起源,目前至少有六種學說:一是認為音樂起源于對自然界音響現象的模仿;二是認為音樂起源于語言;三是認為音樂始于情愛;四是認為音樂起源于巫術;五是認為音樂起源于勞動;六是認為音樂起源于表達思想情感的需要。(參見:王士達.音樂是怎樣產生的[J].音樂學習與研究,1993,(Z1);袁宏平.史前音樂起源之我見[J].音樂探索·四川音樂學院學報,1988,(2);包德樹.對音樂起源的再認識[J].音樂探索·四川音樂學院學報,1996,(1);黃厚明.中國原始音樂起源的考古學觀察[J].中原文物,2003,(4);姬文革.對音樂起源問題的再探究[J].黃河之聲,2009,(20).)應該說,這些理論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都是對音樂起源問題的有益探索和思考。然而,單純把音樂的起源歸結于某一理論,難免要犯簡單化的錯誤。更何況,本文也不是一篇專門探討音樂起源問題的論文。因此,本文將采用一種綜合的態度來對待音樂起源問題,不刻意去追求某種理論的立場,而是根據本文論證的需要采用某一理論。
一般認為,聲樂要早于器樂,這大概沒有太多疑問。人類在勞動的過程中,會發出一些比較具有節奏的聲音,這可能是最早的聲樂。后來,根據勞動的需要和狩獵的方便,產生了一些模仿自然界發聲的擬聲工具,這可能就是最早的樂器。據近期考古發現,在距今約8000余年的河南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墓葬中發現了十多枝“骨笛”。這種用鶴類尺骨制成的樂器長22.2厘米,上有7個同規格的音孔,在末孔上端另有一小孔,骨笛呈淺土黃色,光澤明亮、制作規范,經測試具備音階結構,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參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第六次發掘簡報[J].文物,1989,(1).對于“骨笛”測音、形制、演奏等方面的研究可參見:方建軍.中國古代樂器概論(遠古—漢代)[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129-133.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骨哨和陶塤參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78,(1).此外,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兩只鹿笛,吹起來一支象公鹿的叫聲,一支象母鹿的叫聲。聚居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和黑龍江省大小興安嶺原始林區的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等族也通過鹿笛誘捕獵物。吹奏時,奏者常隱蔽于林間逆風之處,單手持笛站立豎奏。嘴角斜對吹口,鹿笛吸氣發音,笛吹氣發音,其音尖細而清亮,筒音常為f3-a3。吹奏比較省力,通過口形的變化和氣息的控制,可以模擬鹿在不同季節里發出的不同叫聲,以此來誘捕鹿。,都是用于生產勞動中的擬聲工具。用這種擬聲工具,或者作為狩獵的信號,以指揮協調人們的行動;或者模仿禽獸的鳴叫,以引誘獵物進入狩獵包圍圈,以便獲得更多的獵物。到了商周,管樂繼續發展。《詩經·商頌·那》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的記載,說明商代管樂仍然存在。自新石器時代至殷商,吹管樂器的發展應該不會中斷,因此商代除骨笛和塤以外,當有產生其他吹管樂器的可能,如利用天然的竹管制成的吹管樂器[38]。 殷商時代距今已三千多年,竹管樂器埋于地下無法長久保存,大多會腐朽或者碳化,因而我們今天很難再見到古代的竹管樂器。但是,根據西周早期的考古發掘,發現存在大量的管樂器,這足以證明管樂自新石器時代到商周一直都在發展,并且在材質上極有可能采用更方便更悅耳動聽的竹管取代動物尺骨。故《北堂書抄》引蔡邕《月令章句》:“截竹為管謂之律”,《大戴禮記》:“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另外,甲骨文中“竹”作“”或“”(竹之象形)[34]3127 ,“” 或“”中的一半“”、“”或“”恰與“”中的“”同。當“”從“丨”到“”,恰好可以印證管樂材質從動物尺骨到竹管的演變。
另外,據音樂考古學對古代樂器演奏方法的研究,賈湖骨笛的演奏方式是以一端管口作為吹口,以氣流激發管端邊棱發音;河姆渡骨笛可用手指堵住一端管口橫吹或豎吹;曾侯乙墓篪(篪與笛均為遠古至漢代考古中發現的單管吹奏氣鳴樂器,蔡邕《月令章句》有“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記載)的吹奏方式為雙手掌心向里,置篪于兩虎口間,以拇指和小指穩定笛身,橫吹;長沙馬王堆漢墓漢笛與篪的奏法一致,長沙楊家灣漢墓中的吹笛俑也可作為參證[39]。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某人手拿骨笛或竹管吹奏的畫面:在狩獵的過程中,獵人手握笛吹奏,聲音既可以作為狩獵的信號,又可以指揮協調人們的狩獵行動,還可以用來誘捕獵物。上古之人根據具體的場景,形象地描繪出這一畫面,具體指向的可能就是手握骨笛或竹管吹奏捕獵這一活動。按照傳統漢字形體構造“六書”理論,甲骨文中的“”字恰好是“會意字”(即會合兩個以上的意符來表示一個跟這些意符本身的意義都不相同的意義的字)[27]126,其中一個意符為“”,另一個意符為“丨”或“”,兩者相結合產生“”字,乃是從人手(“”)執骨笛或竹管(“丨”、“”)會吹奏之意,故該字的本義可能為“用管吹奏”或“用管吹奏之音”。在甲骨文中還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如“”[32]289,三期,甲三九一三(及)表示追到人并將其抓住,“”[32]292,一期,粹一五二二(取)表示以手取耳,古人在捕獲獵物或戰爭殺敵后,一般會取下左耳作為計功的憑據。
前文已述,在狩獵活動中,上古之人發現通過骨笛或竹管吹奏不僅可以誘捕獵物,而且還能在捕獵的過程中有效地統一指揮人們的行動,進行團隊合作來捕獲獵物。這當然只是樂器在勞動生產中的功能。當人們在勞動之余,發現如果對捕獵中使用的擬聲工具稍加改進,就可以吹奏出優美的樂曲,如伴之以舞蹈,可緩解疲勞,使人興奮,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同時,為了更好地滿足興奮和激烈的情感表達需要,一些節奏感比較強的膜鳴樂器(如“鼓”)出現。《竹書紀年·帝舜元年》:“擊石柑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呂氏春秋·古樂篇》:“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這生動地描繪出原始人載歌載舞的場景。
在古代,戰爭可能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在戰爭中,如何協調統一人們的行動,更有效地擊潰敵人,最初可能是戰爭指揮者頗感費力的一件事情。音樂在狩獵過程中所具備的統一和協調功能逐漸彰顯出來,鼓因其聲音大、傳播遠、節奏強而被應用于征戰役事之中。鼓通過敲打革面,產生節奏感較強的音律,從而傳達指令。這在古書中有不少用例。《詩經·小雅·采芑》:“征人伐鼓,陳師鞠旅”,又“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詩經·大雅·靈臺》曰:“鼉鼓逢逢”。《繹史》卷五引《黃帝內傳》云:“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左傳·桓公五年》云:“旝動而鼓”,又《成公二年》:“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孫子兵法·軍爭篇》引《軍政》曰:“言不相問,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孫臏兵法·官一》:“辨疑以旌旟,申令以金鼓。”《管子·匡君小匡》曰:“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又《輕重甲》曰 :“湩然擊鼓,士忿怒。槍然擊金,士帥然策,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
除軍事上使用之外,鼓的用途還見于廟堂祭祀、宮廷慶典、日常生活等方面。這在古籍中亦有不少例子。《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鄭玄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神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儀禮·大射》曰:“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呂氏春秋注》曰:“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古今注》云:“街鼓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冬冬鼔。”由此可知,街鼓的功能是通過鼓聲官府向居民傳遞開閉城、坊、市門的信息,代替金吾將士巡邏外郭城街道時的昏曉傳呼。《太平御覽·天部二》引《漢雜事》曰:“鼓以動眾,鉦以止眾。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鉦鳴則息。”這正是“晨鐘暮鼓”的由來。
既然鼓在軍事、祭祀、慶典以及日常生活中應用如此廣泛,那么它與本文所探討的“聿”有何關聯呢?“鼓”在甲骨文中作“”[32]517,三期,甲一一六四、“”[32]517,一期,鐵三八·三或“”[32]517, 三期,人一八三九,從“”(壴),從“”(殳),“”或作“”(支),同,象手持鼓錘擊鼓之形;“”象鼓形,為名詞;“”象擊鼓之形,是動詞。[32]517 故《說文》云:“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從壴,支象其手擊之也。”段玉裁曰:“凡外障內曰郭,自內盛滿出外亦曰郭。……從壴、支,象手擊之也。” 徐鍇曰:“郭者,覆冒之意。”《玉篇》云:“瓦為椌,革為面,可以擊也。樂書,鼓所以檢樂,為羣音長。” 鼓字中的“支”部作“”、“” 或“”,其中的“”指手形并無太多疑問,而指代鼓槌部分的細微差異可能是由于傳寫中誤差而導致。單從構字來看,“”中的“”與甲文中的“” [32]639, 四期,遺八九〇(木)應屬于同一字,前者可能是后者的省筆,而與“” 或“”中的一半“”、“”或“”同形。故《說文》云:“支,去竹之枝也。從手持半竹。”桂馥義證云:“疑作去枝之竹也。”從“”所象之形來看,這是個“上下結構”的會意字,下半部的“”是象“手”之形,上半部成為“半竹”的“”作為“去竹之枝”,應當是用來敲擊的“鼓槌”。至于為何以“半竹”為“鼓槌”,這可能與原始狩獵活動相關。在原始狩獵活動中,有一種稱之為“矢”的獵具,這種獵具為斷竹所制。“矢”在甲骨文中作“”[32] 581, 一期前四·四九·一,一期合一五八,篆文中作“”。其上部為箭頭,狀如“”形,下部為箭座,象弓弩矢形。《說文》云:“矢,弓弩矢也。從入,象鏑括羽之形。”而甲骨文“”字中的左半部分為“”(壴),壴為古樂器置架。對于“壴”,《說文》云:“陳樂立而上見也。從屮,從豆。凡壴之屬皆從壴。”段玉裁注:謂凡樂器,有虡者豎之,其巔上可望見……“豆”,有腳而直立……屮者,上見之狀也,草木初生見其巔,故從“屮”。對于“壴”下半部分的“豆”,《說文》云:“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故“豆”的本義是指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有點像帶高座的盤)。我們據此可以推測,原始人以“竹矢”捕獵,在獲取獵物之后,又用“陶豆”來煮食獵物,在他們懷著狩獵成功的興奮、懷著填飽饑腸的愉悅之時,怎會不以手中的 “竹矢”去敲擊眼前的 “陶豆”? 于是“鼓”的聲音出現了,“敲”的動作或者說“舞”的動態也出現了[40]。 《詩經·小雅·賓之初筵》有:“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的描述,《風土記》有:“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的記載。由此可見,古人起初是用“竹矢”擊食器“豆”,形成比較有節奏感的鼓樂。但在后來鼓出現之后,將鼓置于陳列架上后,改用專門的鼓槌來擊鼓,故在字的構造上,“”中的“”與“”及“” 或“”中的一半“”、“”或“”同形。這正是其詞源學上的解釋。
綜上所述,手執管吹奏與手執木擊鼓,兩個動作基本類同,都是發出具有一定節奏感的聲音,其目的都是為了傳達某種信號或指令,統一協調人們的行動,同時發聲都必須遵循一定的標準或者方法(如戰場上擊鼓之節奏快慢、鼓聲大小、擊鼓之次數多少等可能與進攻或撤退等作戰指令相關)。無論是管樂還是鼓樂,無論是手執竹管還是手握鼓槌,兩者都在古代軍事中得以廣泛應用,只是后來由于鼓樂具有聲音大、節奏強、傳播遠的特點而逐漸取代管樂。故《六韜·虎韜·軍略》云:“晝則登云梯遠望,立五色旗旌;夜則設云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其中,笳就是古代一種竹制的管樂器,與鼓、鐸等一樣都用于戰爭中傳遞軍事信號。可見,音樂在戰爭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為這種內在契合性存在,古人據此而產生聯想,在書寫的過程中將這兩個動作分別表示為“ 一直以來,將“”釋為筆可謂是主流觀點,這大概是受許慎《說文解字》的影響。許慎《說文解字》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從,一聲。凡聿之屬皆從聿”,又曰“,手之疌巧也,從又持巾,凡之屬皆從”。又有筆字,謂:“筆,秦謂之筆。從聿,從竹”。段玉裁注:聿者,所用書之物也。《爾雅·釋器》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然而,古人僅僅只是將“”釋為筆,而似乎忽略了其中“”字的含義。按照傳統“六書”理論,“”應該為“”(手)與“”(筆,見下文的闡述)結合而成的會意字,兩字結合應該為一新義,而《說文解字》對“”的解釋顯然只是注意到甲骨文中“”的含義,而人為地抹殺掉“”的含義。另外,如果“”指涉“筆”,那么,這種“筆”究竟為何種質料的筆?古人使用這種筆書畫的方式如何?為什么具有筆義的“聿”會出現在“律”字之中?等等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們對“”義的闡釋,進而也影響到我們對“律”義的理解。
祝總斌先生曾經指出,“”的本義是指稱手握筆刻畫甲骨器物,由于上古之人有圖騰崇拜習俗,需要通過刻畫不同徽識以區分不同氏族,因此“”除了筆義外同時逐漸有了區分之義,進而又有了界限、規矩、行列之義[6]15-16。祝總斌先生的觀點具有兩個重要啟示:一是“”除本身的筆義外,可能還指涉“手握筆刻畫”;二是“”可能從筆義引申出其他含義。然而,祝總斌先生在文中并未進一步思考筆的具體材質及書寫方式。武樹臣將“”解釋為“執廌尾”,其理由有三:一是、聿二字以手所執之形,與甲骨文“廌”和金文“灋”字中廌的尾部均一致;二是遠古社會有執獸尾而舞的習俗;三是以“隸”字作為佐證,認為“隸”為以手執獸尾之義。故武樹臣認為“廌之尾”為筆之初形,并用其涂抹五刑之象[5]111-112。 武樹臣這一觀點的可取之處就在于,擺脫以往對“”簡單解釋為“筆”的桎梏,開始思考“筆”的具體材質以及書寫方式問題,從而在此基礎上試圖對“”義進行重新釋讀。但是,武樹臣在論證中將筆等同于廌尾的觀點卻存在疑問,值得商榷。質疑的理由有三:第一,廌為古代傳說中的神獸,在《異物志》、《后漢書·輿服志下》等古籍中雖有記載,但畢竟屬于傳說,故古人在實際生活中是否用“廌之尾”來書畫,其答案不得而知;第二,甲骨文中“廌”記作“”[32]1077,四期,南明四七三,其尾部記作“”,這與“”(聿)的尾部“”并不完全一致,且“廌”在篆文中作“”,其尾部更是相差甚遠(況且,按照文字發展規律,即使文字發展會使筆畫簡化,但能夠代表原字一些典型特征的符號往往會被保留或傳承);第三,中國古代最早的書寫工具可能是硬筆,雖也有用羽毛、獸毛等描繪圖畫的現象存在,但這并不是主要書寫工具,這一點可從考古學上得到印證。
從中國書寫工具發展史來看,“古人用毛筆書寫的傳統起始于何時”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文字學者認為“自從有墨跡可考以來,漢字即為用毛筆書寫” [41] ,書法家認為“書法即為用毛筆書寫”[42]。錢存訓先生則認為中國遠古時期就有了毛筆,河南仰韶與半坡文化等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彩陶上的花紋和符號都是用毛筆所畫;商周的卜辭也是先用毛筆畫好然后刻畫在甲骨器物之上,而甲骨文中的“”字則是手握一管飽濡墨汁或筆毛分散的筆[43]。 然而,敦煌研究院李正宇教授對這種“唯毛筆觀念論”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李正宇教授通過考證手寫筆畫與加工筆畫的區別,出土器物上文字的筆畫特點,硬筆書寫運筆方法,并輔之以實物證據,認為新石器時代的彩陶花紋、符號、甲骨文、小篆、古隸、秦隸等均是由硬筆書寫,故從新石器起到秦代,基本上都是硬筆的天下,而戰國時期及秦代則是硬筆、毛筆兼用的過渡時期(其中一個重要的實物證據就是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三枝秦代“毛筆”,通長21.5厘米,筆桿為細竹竿,斷面直徑0.5厘米,筆桿上端削尖,可蘸墨書寫,實為硬筆和毛筆合體兩用之筆)[44]。 概而言之,中國古代硬筆的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原始硬筆,即用竹、木、骨、角、石等作為材料,削磨出鋒刃,用其鋒刃在陶器、龜甲、獸骨、金石或竹木面體上直接刻畫,這包括木筆、竹筆、骨筆、角筆、錐筆、刀筆;第二類是改良硬筆,即可用劃痕的同時也可以蘸墨書寫;第三類是無需蘸墨而自帶其色的硬筆[42]9-10。
若然,那么甲骨文“”、“”中的“丨”、“”極有可能指的就是帶有鋒刃的原始“楗梃”硬筆和契刻硬筆。而從“丨”到“”、“ ”、“”再到“”,下端部分所展現的正是契刻的鋒刃。故《易經·系辭下》云:“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孔穎達《尚書正義》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其中的“契”就是指用硬筆鋒刃刻寫。馬敘倫先生亦指出,古用刀刻識,“”像刀柱及銳鋒之形[45]。 李正宇教授等人的論證結合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全面分析了硬筆和軟筆書法的特點,其結論似乎更能令人信服。倘若如此,那么甲骨文中的“”應該是指“手執硬筆”或“手執硬筆書寫”,而不是指“執廌尾”。
如果更進一步具體推測的話,那么上古之人使用較廣的硬筆可能是竹筆。上文已述,在文字出現之前,上古初民采用結繩、刻劃、圖畫等方式記事。在這幾種記事方式中,結繩是通過手編織完成,而刻劃和圖畫則需要借助于某種工具。其中,刻劃借用的工具可能是前文已提到的骨、角、石等,而圖畫則可能是利用手指、竹棍或木棍,用其蘸獸血或其他顏料來畫出符號。隨著文字產生之后,文字的刻寫需要用更加精細的書寫工具,需要對書寫工具的刻寫部位進行改進,使其更加銳利便于刻寫。因此,前者發展成原始硬筆中的骨筆、角筆、錐筆、刀筆,后者則發展成竹筆,李正宇教授將其稱之為契刻硬筆和楗梃硬筆。關于竹筆,不少古籍中有相關記載。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文云:“古者無紙筆,用刀削木為筆,及簡牘而書之。”宋趙彥衛《云麓漫抄》卷七云:“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書簡,以竹為之而書以漆。” 宋馬永卿《嫩真子》云:“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元陶宗儀《輟耕錄》中也有同樣記載。元方回《桐江續集·鐵瓶吳處士善畫序》云:“古筆用竹,亦必始于羲、頡……《舜典》始言‘作繪’,則五采五色之畫亦古矣。第其時未有后世之筆紙,則其筆必用竹筆而繪五色于于絹繒之上耶?”明羅頎《物原·文始》云:“伏羲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之以刀書。”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古玩》云:“上古無墨,竹梃點漆而書。”竹梃為筆在考古學上也得到了印證:武山出土仰韶文化彩陶瓶鯢魚紋就是用竹梃類硬筆涂抹而成;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有鐫刻和書寫的陶文;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祀”字甲骨上的朱墨字跡亦為硬筆蘸寫。可見,上古以竹為筆確實是存在,并非憑空臆測。雖然古代竹筆蓄墨性能差,書寫不流暢,但是其取材簡單,且輕巧方便,故逐漸取代其他種類的硬筆而成為蘸墨漆書寫作畫的正式工具,后來再發展成功能和形制都與之類似的毛筆。
先民在對手執竹筆書寫之事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后,在造字過程中自然會將竹木之形借鑒到“”字之中。前文已經提及,“” 或“”中的一半“”、“”或“”恰與“”中的“”同,而甲文中的“”為“”之省筆,擊鼓之鼓槌最早可能取材為“半竹”,后由木替代。可見,手執律管之“”與手執硬筆之“”之間存在某種共通性,這種共通性不僅體現在動作之形上,而且還存在于工具材質上。故先民造字將這兩者均記為“”。更進一步說,手執硬筆之“”與手執律管之“”不僅所表動作之形相同,而且兩者引申義也基本類同。手執硬筆之“”的引申義可能為“區分、界限、標準、統一”。
原始人改造世界和認知世界的能力有限,認為周圍的事物都存有靈性,對其持有一種敬畏心理。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提到,歐洲雅利安人對樹神崇拜的習俗,出現一些對樹的禁忌,比如古老的日耳曼法律嚴懲剝去活樹樹皮的行為。因此,他認為圖騰便是一種類的自然物,野蠻人以為其物的每一個都與他有密切而特殊的關系,因而加以迷信的崇敬[46]。圖騰產生后,往往會作為氏族或部落的崇拜物及標志,具有一種標記的功能。根據摩爾根的考察,氏族組織往往會以某種動物或無生物命名,如美洲各地的土著和新墨西哥的摩基村的印第安人中,氏族成員聲稱他們就是本氏族命名的那種動物的子孫,而在某些部落中,氏族成員不吃本氏族命名的那種動物的子孫,并且“氏族名稱創造了一個世襲譜,其作用就在于使凡屬擁有此名稱的人即同出一系這樣一個事實得以留傳勿忘”[47] 。涂爾干對澳洲土著圖騰制度考察后也認為,用來命名氏族集體的物種被稱為圖騰,圖騰作為氏族的名字而存在,而且這一圖騰為該氏族所獨占。隨后,他還分析了圖騰的標記功能,認為“圖騰是一種標記,一種名副其實的紋章”,圖騰不僅出現在原始人房屋的墻上、獨木舟的兩邊、武器上、日用品和墳墓上,而且還出現在人的身體上[48]。 由此可見,圖騰為氏族特有標記,用以區分于其他氏族,一個部落中每個氏族之間的圖騰標記是不可能相同的,否則就喪失其區分和標記之功能。最早可能在一些相關器物之上刻畫某種圖案,作為氏族的徽號和標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類似的氏族徽號文字,如高明《古文字類編》中就收錄有自商代甲骨文至秦篆文中的徽號文字。(參見:高明.古文字類編[M].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三編“未識徽號文字”)刻畫的工具就是前文所提及的契刻硬筆和楗梃硬筆,故“”指“手執硬筆刻畫”,而刻畫圖騰的目的是為了便于識別氏族成員,賦予氏族成員以某種特殊標記,因而引申出“區分、界限”之義。又由于圖騰具有特定的形狀,有固定的圖案和色彩,并因具有某種神圣性而不容隨意篡改,因此氏族神職人員在刻畫圖騰需要嚴格遵循某種既定之標準,從而從“手執硬筆刻畫”引申出“標準、統一”之義。祝總斌先生也提到過類似的觀點,可參見:祝總斌.“律”字新釋[J].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2):15-16. 至此,我們認為,“”的本義可能是“手執硬筆刻畫”,而非僅指筆義,其引申之義為“區分、界限、標準、統一”。
(三)手執權杖之“”
甲骨文中,“尹”字的寫法有“”、“”、“”、“”、“”、“”、“”以及“”等九種[32]286。稍加對比就能發現,“”與“”在外形上極為相似,在甲骨文卜辭中有不少證據表明二字同源[49]。祝總斌先生從文字、音韻、訓詁三個層面進行舉出證據,認為“尹”“聿”二字可能原本為一字,而且起初出現的只有一個“尹”字,象手握筆以刻畫甲骨器物,后因“尹”字逐漸向官名發展,于是便另用繁文“聿”字來承擔原意 [6]17。武樹臣亦認為,古尹字和、聿字可能均源于肀,“”沿著職官的方向發展,其過程為肀→尹→史→君[5]108。從前人的詳盡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一是古“尹”、“聿”兩字可能為同一字;二是“尹”為職官。對于第一個結論似乎沒有太多疑問,而且也能舉出不少文字學上的證據。對于第二個結論,筆者認為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可能還需要更為深入的探討。甲骨文“”從又執丨,丨像杖,以手執杖,似握有權力以任者。“尹”在殷商甲骨文中亦有三種性質:一是職官之稱;二是方國名;三是貞人名。所以,我們認同“尹”為職官這一觀點。然而,大多數人的研究僅僅停留于此,并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因此本文認為可能需要在以下兩個問題上作出努力:(1)如果“尹”在殷商甲骨文中指官職,那么具體是何種官職?(2)在文字分化之后,作為官職的“尹”字與“聿”和“律”之間又有何種內在關聯?
《甲骨文合集》14925片刻有四方風名卜辭,由此引發學者對殷商時期四方風名進行考證,對此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對該片卜辭“辛亥卜內,生二月哉有(聽)”與“哉亡其(聽)”句,饒宗頤先生認為該句中“聽”與“圣”相同,“聽在新《甲骨文編》中釋為圣字,余謂和(圣)當是一文之異寫,可以釋為聽”[50]。甲骨文中“圣”字左邊是耳朵,右邊是口字。《說文》云:“圣,通也,從耳,呈聲。”段玉裁注:圣從耳者,謂其耳順。《管子·四時》云:“聽信之謂圣。”又“聽”在《說文》中的解釋為:“聆也,從耳德,壬聲,他定切。”段玉裁注:凡目不能偏而耳所及者云聽……耳德者,耳有所得也。古“圣”(聖)字與古“聽”(聽)字均從耳,字形義同源,兩字相互假借。故在商代,聽指樂師,為商王室職官,稱之為“王聽”,如:王聽惟禍(《甲骨文合集》808反);貞王聽惟孽(《甲骨文合集》110正)[20]8。
據此可知,“聽”在商代是指樂師,且樂師官職的名稱為“王聽”,其可能承擔的職能可能有如下四項。第一,聽協風而定天時。《國語·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國語·周語上》:“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又云:“是日也,瞽師、音官以土風。”韋昭注:“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瞽,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又:“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可見,瞽師樂官等是通過音律來考察土風,土風變化會反映在瞽音上,故可據此預測天時。第二,吹律聽聲而明軍心。前文已述,樂官在戰爭中吹律聽聲會起到統一軍心、鼓舞士氣的作用。如《周禮·春官·大師》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兇。” 鄭玄注: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征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第三,承擔祭祀職能。古代的巫是全能的,集知識、宗教、政權等各種權力于一身,巫在殷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故最早并無單獨的樂師之職,樂師往往由巫來擔任,如奏鼓樂祭祀等,都是由巫來進行。只是到后來,巫的職能分化之后,才有專門的樂師出現。而“王聽”還保留有古時全能巫的部分職能,承擔著祭祀的職能。(關于巫與樂師的關系,詳見下文“‘聿’義”部分的論述)第四,協助王統治及管理。“王聽”不僅能聽協風,定天時,明軍心,通祭祀,并且還能勸戒君王,輔助君王統治管理。樂師將其所采集、記誦的歌曲、史事獻給君王,以達到勸戒的目的,如周代以《詩》諷諫政治制度。《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周禮·大司樂》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外,“聽”本身就有治理之意,兼聽萬事、聽政、聽訴等,這大概也是從“王聽”之職能衍生而來。
古時樂官名稱可能有多種,“王聽”可能僅僅為其中一種,而且是在甲骨文中有確切記載的一種。倘若如此,那么上述職能可能并不僅僅只是針對“王聽”,而是所有樂官都可能存在的一種普遍職能。如果我們能夠證明,甲骨文中的“尹”為樂官,那么這正好符合我們的預設。在甲骨文中,我們找到了“辰王有聽;己巳王方征”(;,《甲骨文合集》20624)兩條卜辭,這兩條卜辭又可釋為“□辰卜,王;己巳卜,王方征”[51]。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為樂師名根據沈建華先生的考證,“”與王聽一樣,都是古代的樂官。(參見:沈建華.卜辭中的“聽”與“律”[J].東岳論叢,2005,(3): 8.),卜辭中記為“”。“”字分為“”和“”,其中“”為“纟”,而“”則為“尹”,此字應為形聲字,“尹”為聲旁。古人在造字中,將具有“職官”之意的“尹”與“纟”旁結合,用來指稱樂師“”,這恐怕不是一種偶然。在我看來,“”字中含有“尹”具有兩種可能:一是由于“尹”指官職,故將其借用指代樂官;二是“”為“尹”之繁體,兩者本為一字。但不管這兩種情況如何,“尹”這一官職最早可能都與音樂有著密切聯系,很有可能就是樂官,其承擔的職能也與“王聽”類同。故《說文》云:“尹,治也。從又丿,握事者也”,此處“事”即指“政事”,“握事”即可理解為管理政事,這正是“協助王統治及管理”職能之體現。再者,“”手執之杖最早可能為祭杖,為巫祝之類的人物使用的法器,而不僅僅只是指權杖,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中出土的一柄木芯金皮杖可以證明這一點。1986年7月,在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中出土了一柄木芯金皮杖。這柄杖的金皮長142厘米,重約500克,金皮展開后的寬度在8厘米左右。在杖上端雕刻有精美的紋飾圖案。圖案上下各一組,兩組圖案間用兩條平行線作間隔。下組圖案內容為前后對稱的兩人頭,人頭戴鋸齒紋冠,耳微曲,耳垂上戴圓角等腰三角形耳飾。人頭為寬眉,棱形立眼,眼較大,圓鼻,仰月形大口,寬圓下領。兩人頭之間用雙勾紋相隔。人頭戴鋸齒紋冠的形象常見于巴蜀銅兵器上的圖案,在祭祀坑中也出土有這種黃金冠飾。耳垂上戴的等腰三角形耳飾和一號祭祀坑出土的“玉佩”形制相同,從而可知這種“玉佩”應是一種餌飾。這個人頭的身份應是代表的神人之類的人物。下組圖案分別由鳥、魚、箭等圖形組成。上方是魚,魚身上鱗、鰭均有,魚頭端有胡須,分尾,應是鯉。鯉魚前是兩只鳥,鉤嚎,大頭,昂首,豎尾,展翅,作飛翔狀。一支箭橫置于鳥背上,被鳥駝負著。箭為長桿,箭尾有羽,箭頭一端射進魚的頭部。從整個下組圖案來看,像是四只鳥成隊駝負著魚飛翔而來。從金杖圖案來看,顯然是巫祝之類的人物使用的法器。(參見:陳德安,等.三星堆——長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9.)如果“”中的“丨”為祭杖的話,那么執祭杖者為巫祝之類的人物,在古代巫祝往往同時又擔任領袖、樂師等角色,兩者身份存在一定重合(這一點詳見下文的分析)。故“尹”應指樂官之職,只是后來隨著全能巫職能的分化,樂師成為一種專門的職能,其權力色彩弱化,“
表1:“
甲骨文象形甲骨文象形“引申義重合義手丨律管硬筆權杖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手執權杖管理統一、協調、標準區分、界限、標準、統一統治、管理統一、標準、區分、界限 我在閱讀張永和教授《“灋”義》一文時受到啟發[52],即要想證明“聿”具有“區分、界限、標準、統一”等義,還應該在包含“聿”的其他字中找出“聿”意指“區分、界限、標準、統一”等意思。我選擇了“畫”、“晝”、“肆”、“肄”等字。
甲骨文、金文中的“畫”字上部為“聿”,象以手執筆形,是“筆”的本字;下部象畫出的田界。整個字形,象人持筆畫田界之形。故本義為“劃分,劃分界線”。《說文》云:“畫,介也,從聿,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段玉裁注:介,畫也,從八從人,人各有介。田之外橫者,二直者二,今篆體省一橫,非也。另據同治十二年陳昌治復據嘉慶十四年孫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對畫的解釋為:“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凡畫之屬皆從畫。”《康熙字典》云:又分畫也。界限也。《左傳·襄四年》: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注》:畫,分也。《禮·檀弓》:哀公使人吊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吊焉。《注》:畫地為宮象。《管子·明法解》云:“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漢書·地理志序》云:“畫野分州。”顏注: 畫,謂之界分也。故將“畫”訓為“界限、區分”之義。
“晝”在《說文》中的釋義為:“晝,日之出入,以夜為介,從畫省,從日。” 《易·系辭》云:“晝夜之象也。”《子夏易傳》曰:“晝復則夜往,夜至則晝往,無時而不易也。”《陸氏易解》云:“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禮記·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鄭玄注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六韜·虎韜》云:“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由此可見,“晝”為夜之分界,這種晝夜分界直接影響到生活,古人將其進行嚴格的區分,無論是陰陽屬性還是日常生活的安排。據此,可以反映出該字本身具有的“界分”之意。
“肆”在《說文》中釋為:“極陳也,從長,隸聲。”段玉裁注:陳當做敶,敶列也。極陳者,窮極而列之也。傳注有但言陳者,如《詩·小雅·楚茨》有“或剝或享,或肆或將”,《詩·大雅·行葦》有“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注是也。經傳有專取極意者。凡言縱恣者皆是也。《釋言》曰:肆,力也。毛傳《大明》、《皇矣》傳曰:肆,疾也。皆極陳之義之引伸也。又《釋詁》曰:肆,故也。肆,今也。毛詩《綿》傳、《思齊》傳曰:肆,故今也。此以為語?也。其他或以肆為遂。或以肆為。或以肆為肄。葢皆假借。從長。崧高。其風肆好。傳曰:肆,長也。按極陳之則其勢必長。此字之所以從長也。隸聲。 《廣韻》亦云:“肆,陳也。”然而,對于“陳”字,《廣雅·釋詁》云:“陳,列也”,《玉篇》釋為:“列也,布也”。《書·咸有一德》云:“乃陳戒于德。”《詩·小雅》云:“陳饋八簋。”又《史記·李斯列傳》云:“所以飾后宮,充下陳。”顏注:下陳,猶后列也。同時,“陳”亦同“陣”,表示“軍伍行列”之意。由此觀之,“肆”當有“陳列、行列、整齊、統一”之義。
《說文》中“肄”之本義為“習”。《廣韻》:“肄,習也。”《左傳·文四年》云:“臣以為肄業及之也。”《禮記·曲禮下》云:“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心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 鄭玄注:“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為也。肆,本又作肄,同以二反。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孔穎達疏:“此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為也。其大夫則與士先習學所為之事,備擬君之所使。‘在官言官’者,此是君命所使之事,言猶議也。若君命之在官,則臣當展習言議在官之事。‘在府言府’者,命之在府,亦當習議在府之事也。‘在庫言庫’者,命之在庫,亦隨而習議在庫之事也。‘在朝言朝’者,命之在朝,亦隨而習議在朝之事也。”從這可以看出,“肄”當為“習”義,而事君者均應謹習其事 習之以禮法,即當明其標準,知其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故其引申為“標準、界限”之義。
綜上所述,通過對“畫”、“晝”、“肆”、“肄”等字含義的考察可知,這幾個字基本上包括了“聿”字所具有的“統一、協調、標準、區分、界限”等義,這正好證明了前文對“聿”義探尋所得出的結論。那么,作為“”字本義的“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為何在引申義上出現了重合呢?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古代巫以及巫文化。
巫術可謂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53],文化人類學上對此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弗雷澤在《金枝》中認為,在原始人的眼中,自然界是按照某種不變的秩序演進的,并將這種秩序視為固定不變的。弗雷澤將巫術的自然性原則歸為兩類:一是“相似律”;二是“接觸律”或“觸染律”。前者發展成為“順勢巫術”或“模擬巫術”,后者發展成“接觸巫術”。這兩種巫術統稱之為“交感巫術”[44] 15-50。泰勒認為,巫術是建立在聯想之上而以人類智慧為基礎的一種能力,但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同樣也是以人類的愚鈍為基礎的一種能力。這是我們理解魔法的關鍵。人早在低級智力狀態中就學會了在思想中把那些他發現了彼此間的實際聯系的事物結合起來[35]93。由此可見,巫術是原始人對事物之間聯系產生的一種錯誤看法,這是許多文化人類學者的共同認識。從古代中國的情況來看,巫術出現的時間可能較早。根據考古發掘,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了原始的靈魂信仰現象,在新石器時代的一些原始巖畫中,就有從事原始宗教活動的記錄。此外,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等文明遺跡中,發現有祭祀場地、祭祀器具、神像等。這些都表明中國的巫存在歷史極為久遠。在文獻記載上來看,最早對巫的記載見于《國語·楚語下》:“古者民神不雜……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天通地。”從這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巫的普遍性及其分工性。另據《說文》訓“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屬皆從巫。,古文巫。” 又“覡”字釋為:“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從巫從見。”徐鍇曰:“能見神也。”可見,如果要細分的話,那么古代巫可分為男巫與女巫,男巫稱之為“覡”,女巫稱之為“巫”,但兩者統稱為“巫”。
早期的巫與政治的關系密不可分,很可能具有宗教和政治的雙重身份。陳夢家先生認為,由巫而史,而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域領袖,同時仍為群巫之長[54]。童恩正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在文明與國家逐漸形成的時代,巫的身份逐漸發生了分化,即一小部分巫師與氏族首領的身份合二為一,氏族首領往往同時執行巫師的職能,古代巫既是政治領袖,又是宗教領袖。巫不僅擁有政治權力,也享有宗教壟斷權力。在早期社會中,巫可能與頒行法律、創造文字、發明天文歷算、醫學等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且,由于通靈的需要,古代的巫師,必然是最早的樂師和舞人,因為他們將鼓、音樂和歌舞作為溝通人神兩界的手段[55]。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巫在古代社會中的活動領域較為廣泛,不僅會通靈占卜、預測吉兇,而且承擔著統治管理職能,并且可能會從事與音樂相關的活動。正因為巫身份的這種多重性,導致“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的主體極有可能就是“巫”。
首先,由于“巫”與“王”的身份重合,那么巫最初可能是“手執權杖管理”之人,只是分化之后發展成為專門的官職。《史記·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 《今本竹書紀年》云:“命巫咸禱于山川。”等等這些文獻記載都說明巫具有的統治和管理職能。故“”中的“丨”既可能為祭杖,又可能為權杖。
其次,“巫”與樂師的身份重合,那么巫最初也可能是“手執律管吹奏”或“手執鼓槌擊鼓”之人。因為溝通人神兩界的需要,巫往往擅長于音樂及舞蹈,將此作為致神愉神的手段。由于音樂歌舞是巫術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所以從最初的巫術直到西周的祭祀活動,音樂與歌舞緊密結合,故有“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之謂。一些音樂民族志研究成果甚至認為音樂歌舞起源于古之巫術。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亦指出:“歌舞之興,其起于古之巫術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
最后,由于巫要觀象制歷,占卜吉兇,故在當時的社會中巫極可能通曉文字。巫一方面承擔觀象記事職能,另一方面需要記錄占卜活動,掌握文字為現實之需。記事職能為后來之史官取代,故巫也被視作史官之源。楊向奎先生認為,“史之源流,乃神、巫、史相傳。由神而巫,由巫而史。”[56]占卜之職得以保存,甲骨文卜辭就是由巫來刻寫,作為占卜之后的驗證。
由此可見,“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在主體上出現重合,三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文化共通性。巫所從事的此三項活動,均帶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而且三種動作之形又極相類似,我們據此可以理解,當古人見到某類固定人群經常從事某種很難加以明確區分的活動時,用某個特定的符號來指稱這類活動當屬可能。因此,古人結合動作的基本構件,選擇用“”來指稱此三項活動,以至于在文字分化后在引申義上出現重合。
三、釋“ㄔ”
“律”字的兩個義項為“聿”和“ㄔ”,對于“聿”前文已經進行了分析,本部分將對“ㄔ”的含義進行探討。在以往對“律”義的研究中,或者直接從“律”字本身入手,或者只側重對“聿”義的探討,而對“ㄔ”義關注較少。毋庸置疑,“聿”是“律”字中一個十分關鍵的構件,理應加以重視。然而,“ㄔ”旁也是“律”字中的一個重要義項,對“ㄔ”的理解直接關系到對“律”義的理解,只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研究,才能完整全面地揭示出“律”字之本義。
祝總斌先生并未對“ㄔ”進行深入闡述,而是認為“聿”與“律”本為一字,“律”乃“聿”之繁文,并指出“‘律’字本義不能僅來自‘ㄔ’”[6]17。武樹臣認為,“聿”字加上“ㄔ”便演化成“律”,而“ㄔ”是行()的半邊,表示街道、路口、村落。“聿”演變為“律”與社會生活從游VNtqMOMvIcB9qYZIw76ydg==牧轉向定居有關,故將戰鼓放置在村中央某處,通過鼓聲通知眾人開會、納糧、出丁之類[5] 110-111。以上是學界對“律”字中“ㄔ”義的兩種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ㄔ”僅僅作為形旁,“聿”與“律”本為一字,“律”乃“聿”之繁文,故“律”之本義主要來自于“聿”;第二種觀點認為,“ㄔ”表示街道、路口、村落。然而,仔細推敲的話,這兩種觀點似乎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筆者認為,“律”中的“ㄔ”應該具有特定的含意,其義不可省,而且是決定“律”字本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律”為形聲字,許慎《說文解字》云:“律,從ㄔ,聿聲。”“聿”當為其聲旁,而“ㄔ”當為其形旁。按照黃侃先生《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的觀點,形聲字之子母必須相應,形、聲、義三者必須相應,但當假借之法用于造字之后,就會出現諸如:聲與義同一;聲之取義雖非其本義,而可以引申者;聲與義不相應者等三種情形[57],故“律”字從聿聲,而“聿”之本義又為筆,實難與“律”字“均布”之義相應,此當屬聲與義不相應者之類,究其原因可能是構字中出現假借,只能因聲而推其本字,進而求其義,如此方能使形、聲、義三者相應。此其一也。
其二,合體字的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類屬,聲旁則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發音。無論是聲旁還是形旁,都是“律”字本義的組成部分。“ㄔ”旁指示“律”字之意思或類屬,當有重要的含義在內。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將“律”歸為“ㄔ”部,而未將其歸為“聿”部,應當考慮到了“律”字之屬。故“ㄔ”義應當是我們探求“律”之本義的另一個重要切入點。
其三,“ㄔ”之本義是否可以簡單地解釋為街道、路口、村落,這一點尚存疑問。《說文解字》云:“ㄔ,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集韻》云:彳亍,足之步也。《元包經》:爪丮血,趾彳亍。《潘岳·射雉賦》:彳亍中輟。《注》徐爰曰:彳亍,止貌。張銑曰:行貌,中少留也。故從前人對“ㄔ”的訓釋來看,“ㄔ”之本義并不是街道、路口、村落,應為“行走、行列”。對此,另一個佐證就是,《說文》中從“ㄔ”的字也大多與“行走、行列”相關,如行、衙、衛等。
鑒于此,筆者認為,如果要探尋“律”字本義,需要重新對“ㄔ”義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全面,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才能令人信服。盡管前人對“ㄔ”義的研究存在不足之處,但畢竟為后世學人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可以將其作為參照。
甲骨文中“律”作“”,其左半部分記為“”, 此即為甲骨文中“行”() [32]182,一期,后下二·一二字的半邊。因而,要探尋“ㄔ”義,首先應從“行”字入手。羅振玉先生在《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認為,“”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這是將其解釋為“道路”之意。然而,在甲骨文中,“行”的詞義有三種:一是行走之義,卜辭為“”(乙丑王不行自雀)[29]947 ;二是貞人名;三是方國名。根據卜辭原文,“行”的詞義應當為“行走”,這與許慎《說文解字》中的釋義基本一致。《說文》云:“人之步趨也。從彳從亍。凡行之屬皆從行。”段玉裁注:“步,行也。趨,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析言之也。引伸為巡行、行列、行事、德行。” 又注曰:“彳,小步也。亍,步止也。”《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爾雅·釋宮》云:“行,道也。” 故“行”訓“步趨、行走”,去也之也往也還也,皆行之義也,并由“步趨”之義而生“道路”之義。
根據以上分析,“行”當訓為“步趨”,此“行”之本義,后引申為“巡行、行列、行事、德行、道路”等。而“ㄔ”之義為“小步”,其義大概來源于此。但更為重要的可能還在于“行”與“ㄔ”作為“步”而具有的測量標準功能。
當人類進入到文明社會,特別是進入農耕社會之后,經常會出現計算測量之事。然而,古時測量工具有限,并沒有比較精確的測量工具,故最早以“肘、虎口、掌、步”等人之身體部位長度為標準測之,如“半步為跬”、“八尺為一尋”等。《孔子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其中的寸、尺、尋等分別是以人的指長、掌寬、肘長等為標準來測量。現實生活中也常常會用腳步來測量土地的范圍和距離。《說文解字》云:“六尺為步,百步為畮。”正因為“步”為測量的標準和長度單位,故古人在造字時,將有“步趨”之義的“行”和有“步”之義的“ㄔ”借用,取其作為長度標準的固定不變、規范以及準繩之義,并與“聿”相結合,組成而成“律”字。當然,為何將兩者相結合,以及“律”義的演變,下文將繼續討論。
四、釋“律”
前文已對“律”字兩個構件——“聿”和“ㄔ”的含義進行了探尋,“聿”字本義也可能為“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而其引申之義分別為“統一、協調、標準”、“區分、界限、標準、統一”以及“統治、管理”等。“ㄔ”之義為“步”,“步”作為古代的測量之單位,引申為長度標準的固定不變、規范以及準繩之義。然而,古人之所以將“聿”和“ㄔ”結合而造“律”,主要是因為“聿”和“ㄔ”均有標準、統一之義,故用以指稱音律,即為審定音高標準的一種定音器。
從音樂史角度來看,我國古代很早就已經產生了樂器,并且一些學者對這些出土樂器進行測音研究后發現,這些樂器已經具備較為完備的音階,并有調音孔。例如,舞陽骨笛一般長20多厘米,直徑約1.1厘米,圓形鉆孔都分布在同一側,一般為7孔,制作規范。有的骨笛上劃有等分記號,表明制作之前先經過度量、計算,然后劃線,再鉆孔。個別笛子的主音孔旁還鉆有小孔,專家認為是調音孔,可見制作者已有生律規范的意識,開孔后先要試音,如果音律不諧,再開小孔作微調。這表明,當時的人們己經對音階音程關系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還掌握了生成音階與音程關系的方法。(參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第六次發掘簡報[J].文物,1989,(1).)然而,“律”作為專門的定音或調音工具,在東周與漢代考古中才發現。如湖北江陵雨臺山21號戰國楚墓出土殘竹律4支,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西漢時期的竽律1套工12支,它們都是用刮去表皮的異徑細竹管制成,開管,管上有墨書律名,其名稱與傳統的周律名相同。(參見:方建軍.中國古代樂器概論(遠古—漢代)[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146.)此外,我國最早的律學大約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律制根據五度相生法增加律數,起初是“宮、商、角、徵、羽”五音構成“五聲音階”,后來加入“變宮”與“變徵”,構成“七聲音階”,再在此基礎上產生了“黃鐘、大呂、太簇、 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由于我國古代是用管制律,即以竹管管長為標準,而非以振動數為標準,故制律之法為“三分損益法”。所謂“三分損益法”,具體而言,就是將一管均分為三段,舍其1/3,取其2/3,名為“三分損一”;將管均分為三段,加其1/3,成4/3,名為“三分益一”。如此上下互生,遂成各律。(參見:繆天瑞.律學[M].修訂版.北京:音樂出版社,1965:67-68.)當“三分損益法”最早見于《管子·地員篇》記載時,已經是比較成熟的生律法了,而此前的制律之法卻無從考證。另根據《呂氏春秋·古樂篇》中記載:“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令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然而,關于黃帝令伶倫制律也只是傳說,亦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可以從出土樂器來推斷,在樂器產生之后,樂器的制作者們已有生律規范的意識,并且對音階音程關系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直到產生完善成熟的“三分損益法”。用“三分損益法”可以定五音,所制的律管,也成為其他樂器的定音工具。因為,只有樂器具備統一的音程音階,才能協奏出優美的樂曲。《周禮·大司樂》鄭玄注:“以律立鐘之均。”《周禮正義·典同》孫治讓疏曰:“八音之樂器,其律度通以鐘為本也。”
為了表達出這種定音標準的含義,古人借助已有的“聿”和“ㄔ”組成了“律”字。一方面,由于“聿”的本義為“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而用“律”定音時吹奏又與“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等類似,從事此類活動之人多為巫,身份上又出現重疊,再加上“聿”的引申義恰為“統一、協調、標準、區分、界限”等,正好與“定音標準”相符合。另一方面,由于“ㄔ”之本義為“步”,“步”作為測量單位之后,引申義為“標準、規范”等,也正好符合“定音標準”之意。故“律”字之本義當為音律。《說文》云:“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故曰均布也。此處的“均布”,可以理解為“音調的均布和諧”,而“范”則可理解為“規范”,“一”則可以理解為“統一”。正是由于“律”作為調音之器,因而引申為“規范、統一、標準”之意。具體而言之,“律”之引申義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由于“律”具有“規范、統一、標準”之意,故“律“與計量單位聯系密切。《尚書·舜典》云:“同律度量衡。”孔穎達疏:“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漢書·律歷志》云:“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艾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又:“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量者,龠、合、升、斗、解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權者,株、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株。”由此可見,古時直接將“律”作為計量單位的參照標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作為定音器的“律”本身就是固定的,可以作為度量衡之標準或準繩。
其二,由于“律”具有“規范、統一、標準”之意,故“律“與歷法聯系密切。《禮書》陳樣云:“樂器待律然后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后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漢代劉歆亦認為,黃鐘長九寸,九是周易系統中的天數之極;黃鐘管徑三分,象征參天之數;管重十二銖,兩管重二十四銖,與二十四節氣對應。又如林鐘管長六寸,管圍六分,六六三十六,與一年之日數相當等等。可見,歷法之制定與十二律有著莫大的關系。當然這兩者都受到陰陽五行學說、天人模式等觀念的影響,但是“律”作為定音標準具有的“規范、統一、標準”之義,與歷法制定之目的相符合,后者之制定正是為了達到“統一”,為人們的生產生活JTbQ1aUj0vJzvvRh4eXIjfU+q/hVQ2oyWjRmV5F4y5M=提供一定的標準。
其三,由于“律”具有“規范、統一、標準”之意,故“律“與樂政聯系密切。既然音律具有如此功能,故為古代君王所重視。殷人“嗜樂”,治樂序政,樂政體系已框架初具[58]。 故《周禮·春官·樂師》云:“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西周建立起完備的“禮樂制度”,不僅將音樂用于祭祀禮儀,而且用以規范人們的行為。
其四,由于“律”具有“規范、統一、標準”之意,故“律“與軍律聯系密切。這可能涉及到對甲骨文“師惟律用”以及《易·師》“師出以律”的理解。對于“師出以律”之“律”,歷代注家有不同的說法。本文認為,“師惟律用”與“師出以律”中的“律”應屬“樂律”,后演變為“軍律”。前文已經提到,古代巫可能身兼軍事、教育、樂師等職,在戰爭中尤其扮演重要角色。故“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中的“大師”可能指“巫師或長老”之類的人。許倬云在《西周史》中提到,“‘師’的原義,大約是長老,故可兼具領軍、祭祀與教育諸般功能。后世分化為師旅與教師、樂師三種意義。在西周的朝廷上,音樂人員也以師為職名,不必與師旅之師混淆。”[59] 另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其中,“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充分表明了樂師在古代戰爭中的作用,可能直接決定著一場戰爭之成敗,故周武王在樂師到周之后決定“以東伐紂”。古代樂師之所以在戰爭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很可能是由于他們為巫職人員,掌握著能夠“聽音而知吉兇”的“五音占”或“風角術”之類的巫術。故有《周禮·春官·大師》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兇。” 鄭玄注: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征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這說明,在古代當有大的軍事行動時,大師手執律管,聽將士發出的呼聲,以預告勝敗兇吉;同時吹奏音調的選擇直接關系到戰爭的成敗(如選商調吹奏則會鼓舞軍心,容易取得勝利)。只是后來隨著巫的職能分化,“五音占”巫術逐漸失傳,音律由其最初的占吉兇功能逐漸轉變為“統一”指揮發號施令的軍律。上文所述“聿”義之一就是“手執律管吹奏”或“手執鼓槌擊鼓”,音樂可在戰爭中傳遞軍事信號,協調和統一指揮人們的行動。當軍樂響起,則令行禁止,故音律逐漸演變為軍令、軍紀和軍律。這在文獻中亦有許多記載。《荀子·議兵》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史記·自序》云:“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左傳·莊公十年》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些都表明,音律在古代社會生活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這正好是“律”義的一個注腳。
論述至此,還有一個問題沒有探討,那就是作為音律之“律”和作為歷律之“律”,是如何演變為法律之“律”的。軍律具有“規范、統一、紀律”的功能,歷律也具有“規范、標準”之意,這已在前文探討。但關于何時用“律”來指稱成文法典,目前學術界存在爭論。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以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商鞅“改法為律”為標志,“律”即被正式用來指稱成文法典。對于“律”被用來正式指稱成文法典的時間,存在一種通說:即“商鞅傳法經以相秦,改法為律,當系改法經之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而以律名之,此為律統之首先建立者”。(參見: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32. )持相同觀點的論述可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847;程樹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華書局,1963:11;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50.但是,近年來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商鞅“改法為律”不可信,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祝總斌與江必新的觀點。如江必新認為:(1)《唐律疏議》、《唐六典注》、《睡虎地秦簡》都不足以證明商鞅“改法為律”是一個歷史事實;(2)從有關商鞅變法的秦漢史籍中,也未見“改法為律” 的痕跡;(3)從《商君書》中也找不到商鞅“改法為律”的根據。(參見:江必新.商鞅“改法為律”質疑[J].法學雜志,1985,(5);祝總斌.關于我國古代的“改法為律”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2).)那么,我認為,在商鞅“改法為律”之前,就已經存在使用“律”來指稱成文法典的情況,只是那時主要是以“法”來稱之,而不是用“律”。理由主要有三點,可相互佐證,而非孤證。
第一,戰國李悝作《法經》六篇(分別為《盜》、《賊》、《網》、《捕》、《雜》、《具》),商鞅以之為藍本,受之以相秦。雖然,后世所見《法經》六篇均是以“法”命名,但是在一些文獻中也稱之為“律”。如《晉書·刑法志》引張斐《律表》云:“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可見,后世也有將其稱之為“律”者,這足以說明在李悝所處時代“法”與“律”均有可能用來指稱成文法典,只不過以“法”為主。除《法經》之外,其他諸侯國以“法”命名成文法的還有楚國“仆區之法”、“茅門之法”、“雞次之典”,晉國“被廬之法”、“夷莞之法”等。
第二,《睡虎地秦墓竹簡》所存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以前的法、律和令共計三十四種,其中秦制法律如《田律》、《廄苑律》、《倉律》、《軍爵律》、《游士律》、《戍律》等共計三十二種。這三十二種法律大多是以“律”命名。由此可見,此時“律”逐漸已經取代“法”,而成為成文法之主流。
第三,從文字學上來看,“法”與“律”一樣,其義也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許慎《說文解字》中訓“灋”為:“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張永和教授通過考證認為,“灋”字中的“氵”義項指涉“平”;“廌”承載著古人理念中的公平和正義;“去”為“祛除”。“法”承載了“灋”的“公平、正義”之意。關于古體“法”字的訓釋,可參見:張永和.“灋”義[G]//張永和.法義.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38.正因為“法”具有諸如“公平、正義”等含義,所以古代的“法”更多的是代表一種較為抽象的且類似于自然法意義上的原則。陳顧遠先生認為,法的別義為“常”,而“常”為刑,“‘刑’一方面指刑罰之意,為‘’字之本義;另一方面變為‘型’字之意義,型為模型,指‘鑄器之法’而言,于是人類行為模型之事物,亦可脫離刑之觀念,而單獨稱其為法,《易傳》云:‘見乃謂之象,刑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此處的‘法’即有‘有物有則’之意,當指‘自然法’也”[13]322-323。可見,“法”的含義廣泛,而不是單指“刑”。故商鞅“改法為律”,將《法經》之盜法、賊法、網法、捕法、雜法、具法,改為盜律、賊律、網律、捕律、雜律、具律。究其原因,就在于“律”之本義為音律,本身就是指“定音之具體標準”,演變為“軍律”之后逐漸具有“紀律、軍令”等含義,再到后來的“歷律”也是指一套具體的規范。所以,與“法”相比,“律”更多的是代表一種具體的規范或規則。這一點可能與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家出現之后,需要用更為具體可行的一套規范體系來治理和約束人民,需要更為精確地衡量罪之輕重,而以往具有抽象意義的“法”卻越來越不適合這種需要。所以,以“律”取代“法”成為一種必然。
五、結語
本文從“律”字的兩個基本構件入手,先后分析了“聿”和“ㄔ”的含義。對于“聿”,我們認為甲骨文中的“” 由兩個共同的符號“”和“”組合而成。“”被視為手形,而對于對“”,學者們一般解釋為筆形。筆者從楊樹達先生的研究中得到啟發:一是甲骨文中“”可能與“”同;二是“”不一定僅僅只是指筆形;三是“丨”可能是指竹管或者某種棍狀物。故我們將“丨”解釋為律管、硬筆以及權杖,因此“”字本義也可能為“手執律管吹奏”、“手執硬筆刻寫”和“手執權杖管理”,而其引申之義分別為“統一、協調、標準”、“區分、界限、標準、統一”以及“統治、管理”等。
關于“ㄔ”,我認為,“律”中的“ㄔ”應該具有特定的含意,其義不可省,而且是決定“律”字本義的一個重要義項。甲骨文“律”中jd6T3lFHsd7jCv2qcHq75Q==的“ㄔ”記為“”, 此即為甲骨文中“行”()的半邊。通過考證,筆者認為“行”當訓為“步趨”,此乃“行”之本義,后引申為“巡行、行列、行事、德行、道路”等。而“ㄔ”之義為“小步”,其義大概來源于“行”。而“步”在古代具有測量標準的功能。
我國古代在樂器產生之后,樂器的制作者們已有生律規范的意識,并且對音階音程關系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在三分損益法產生之前,應該還存在著某種生律之法或定音之器。為了表達出“律”這種定音標準的含義,古人借助已有的“聿”和“ㄔ”組成了“律”字。“律”之本義為“音律”,作為調音或定音工具,因而具有“規范、標準”之義,后演變為“軍律”、“歷律”。由于“律”具有“規范、標準”之義,故在商鞅“改法為律”之前,就已經存在使用“律”來指稱成文法典的情況,只是那時主要是以“法”來稱之,而不是用“律”。直到商鞅“改法為律”之后,由于統治者更為重視法律的“規范”功能,因而逐漸以“律”取代“法”,用以指稱成文法典,一直延續至后世。
通過考證,本文認為今天所言之“法律”實則不同于古代之“法”或“律”,不僅如此,古代“法”與“律”兩字的含義也不盡相同。盡管今天已經沒有這種區分,往往兩者混用,但是仍然有必要對其作出“正本清源”的努力。一方面,我們可以認識到其最初的含義,以避免誤用;另一方面,我們也得以一窺古代法文化與法治實踐之面貌。
圖1:“律”義演變圖
ML
參考文獻:
[1]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M].譚汝謙,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329.
[2] 王建.法律法規名稱英譯研究[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2,(6):128.
[3] 蓋山林.中國巖畫學[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193.
[4] 雷漢卿.《說文》“示部”字與神靈祭祀考[M].成都:巴蜀書社,2000:2.
[5]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C].葛信益,啟功,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86:202.
[6] 武樹臣.尋找最初的“律”——對古“律”字形成過程的法文化考察[J].法學雜志,2010,(3):105.
[7] 陳銳.兩漢經學與漢代的法律解釋[J].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1,(6):4.
[8] 祝總斌.“律”字新釋[J].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2):15.
[9] 殷孟倫.略談訓詁學這門科學的對象和任務[J].文史哲,1957,(6).
[10]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809-811.
[11] 程樹德.中國法制史[M].上海:上海華通書局,1931:2-3.
[12] 章太炎.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M].朱希祖,等,記錄.王寧,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90.
[13] 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G]//梁啟超論中國法制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5-16.
[14]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5.
[15]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324.
[16] 蔡樞衡.中國刑法史[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36,96.
[17] 丘漢平.法律之語源[G]//何勤華,李秀清.民國法學論文精萃: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
[18] Xu Jinxiong,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M].[S.I.]: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9:1581.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0:119.
[20] 李力.甲骨文、金文所反映的法律思想[G]//張國華.中國法律思想通史:第1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146-147.
[21] 李力.追本溯源:“刑”、“法”、“律”字的語源學考察[J].河北法學,2010,(10):47-48.
[22] 沈建華.卜辭中的“聽”與“律”[J].東岳論叢,2005,(3):7-10.
[23] 錢劍夫.中國封建社會只有律家律學律治而無法家法學法治說[J].學術月刊,1979,(2):44-49.
[24] 徐忠明.道與器:關于“律”的文化解說[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5):65-73.
[25] 吳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G]//《法律史研究》編委會.中外法律史新探:第2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211-212.
[26] 張永山.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141-142.
[27] 田濤.國學在法學中的運用——“刑”、“法”、“律”的另類視角[G]//曾憲義.法律文化研究:第2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9-31.
[28] 張玉梅.從漢字看古代“法”“律”的文化內涵[J].漢字文化,2002,(3):44-46.
[29] 裘錫圭.文字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98-100.
[30] 陳夢家.殷墟卜辭研究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73-80.
[31] 董作賓.小屯·殷墟文字乙編[M].一期,二六三九
[32]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一期,五六六三
[33]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M].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113-115.
[34]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165
[35]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6:881.
[36]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6:3126.
[37] 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M].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64,171-172.
[38] 方建軍.商周樂器文化結構與社會功能[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50.
[39] 方建軍.中國古代樂器概論(遠古-漢代)[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132.
[40] 于平.中華鼓舞的歷史隱蹤與文化密碼[J].民族藝術研究,2011,(5):7.
[41]李正宇.硬筆:中國書寫工具的始祖(上)[J].尋根,1999,(5):5.
[42] 趙英山.書法新義[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43] 錢存訓.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M].上海:上海書店,2004:139-140.
[44] 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筆書法:兼論中國書法新史觀[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9-17,79-120.
[45] 馬敘倫.說文解字文書疏證(第二冊)[M].上海:上海書店,1985:83,87.
[46] J.G.弗雷澤.金枝(上)[M].徐育新,等,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113.
[47]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M].楊東莼,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60,168.
[48] 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8,105-106.
[49] 裘錫圭.說字小記[J].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8,(2).
[50] 饒宗頤.四方風新義[J].中山大學學報,1988,(4):68.
[51]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029.
[52] 張永和.“灋”義[G]//張永和.法義.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12.
[53] Radcliffe Brown. Preface to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21.
[54] 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J].燕京學報,1936,(20):535.
[55] 童恩正.中國古代的巫[J].中國社會科學,1995,(5):187-196.
[56] 楊向奎.再論老子——神守、史老、道[J].史學史研究,1990,(3):23.
[57]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8-41.
[58]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523.
[59] 許倬云.西周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220-221.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 of “律”
CHEN Hanfei
(Law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two basic components of the character “律”,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 of “聿” and “ㄔ” will be analyze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 may be “holding a pitch pipe to blow”, “holding hard brush to inscribe” and “holding a scepter to administer”. Its extended meaning may even be unification,coordination,standards,differentiation,boundaries,among others.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ㄔ” is “”,which is half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of “行”(). The meaning of “ㄔ”is “a small step”, which probably derives from the “行”.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 “step” is a standard for measurement. The ancient people made use of the characters of “聿” and “ㄔ” to combine into the character of “律”, which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standard of setting sou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律” was “temperament” as a tool of setting sound. It had the meaning of “norms” and “standards”, and later evolved into the law of military and the standard of calendar. Shang Yang changed the “法” to the “律”, since the norm function of the law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reafter, the character of “律” gradually replaced “法” and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the code of law.
Key Words: 律;聿;行;ㄔ;exegesis
本文責任編輯:龍大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