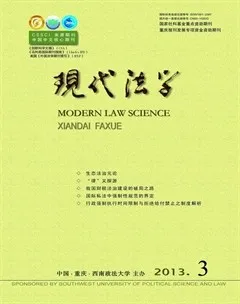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
文章編號:1001-2397(2013)03-0116-14
收稿日期:2013-03-21
基金項目: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犯罪成立罪量因素研究”(12CFX033);2011年度南京師范大學優博培育計劃(2011BS0002)
作者簡介:王彥強(1981-),原名王強,男,四川郫縣人,南京工業大學法政學院講師,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博士生。
摘 要:法定刑升格條件確有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必要。不具備違法推定機能、不是故意認識內容的首要分子、作為報酬的違法所得等升格條件是典型的量刑規則;具備犯罪個別化、違法性推定與故意規制三大機能的時間地點、行為方式、加重結果等升格條件是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要素;而多次、數額巨大等升格條件,僅表征違法程度、不體現行為類型變異,雖是故意的認識內容,卻無法發揮犯罪個別化機能,既非典型的加重構成要素,也非典型的量刑規則,應屬于罪量加重構成要素。罪量加重構成有行為規模類與結果程度類之分,結果程度類罪量加重構成是基于基本犯結果的危險性而加重刑罰的,當基本犯未遂時,即喪失加重之依據,不能論以加重犯的未遂犯。情節嚴重作為升格條件,則應當根據具體化的情節事實,依據上述標準判斷各具體事項的歸屬。
關鍵詞:法定刑升格條件;加重構成;量刑規則;罪量加重構成
中圖分類號:DF61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3.11
張明楷教授在《清華法學》2011年第1期上撰文,明確主張應當嚴格區分加重犯罪構成與量刑規則,刑法分則單純以情節(特別)嚴重(惡劣)、數額(特別)巨大、首要分子、多次、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犯罪行為孳生之物數量(數額)巨大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時,只能視為量刑規則;只有因為行為、對象等構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使行為類型發生變化,進而導致違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時,才屬于加重的犯罪構成[1]。
“區分說”的系統提出的確給“將大多數法定刑升格條件均視為加重構成,廣泛承認情節加重犯、結果加重犯、數額加重犯、對象加重犯、手段加重犯等概念”的傳統“加重構成說”該說的詳細論述可參見:周光權,盧宇蓉.犯罪加重構成基本問題研究[J].法律科學,2001,(5):66-76;盧宇蓉.加重構成犯罪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34-35; 王志祥.犯罪既遂新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320-324. 理論帶來了不小沖擊。
兩說差異何在?區分說是否有意義?在筆者看來,兩說的差異主要在于犯罪未遂的認定和處置方面。以數額為例,我國刑法中的經濟財產型犯罪常根據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等確立兩個甚至更多的法定刑檔(法定刑幅度)。“數額較大”作為基本犯成立的構成要件要素,并無太大異議,而“數額(特別)巨大”之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性質,究竟是加重構成還是量刑規則,對數額犯(未遂)量刑之法定刑基準的確定,則有著決定性影響。因為加重的犯罪構成存在未遂犯,而量刑規則不存在未遂犯,這意味著,若采加重構成說,則可能成立數額加重犯的未遂犯,比照數額加重犯既遂(數額(特別)巨大)的法定刑從輕、減輕處罰;若采區分說,認為數額(特別)巨大是量刑規則,只要客觀上沒有達到“數額(特別)巨大”,就不得適用加重法定刑,就無所謂數額加重犯未遂,即便處罰未遂也只能比照基本犯的法定刑從輕、減輕處罰。那么,哪種觀點的處理結果更合理?法定刑升格條件是否確有必要區分為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如果有,區分標準何在?本文嘗試一一展開。
一、區分量刑規則與加重構成的可能性
(一)量刑規則是否是量刑情節
現 代 法 學 王彥強: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罪量加重構成概念之提倡量刑情節,是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以外的,反映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或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程度,并在法官裁量刑罰時必須考慮的,據以決定刑罰輕重或者免于刑事處罰的各種事實情況。但因為對量刑概念有不同理解,學者對量刑情節的范圍也有不同認識:一種觀點主張,量刑情節以某種法定刑幅度的確定作為前提和基礎,是實現刑罰個別化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同宣告刑有著必然的聯系[2]。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量刑情節是選擇法定刑與決定宣告刑的依據;量刑包括法定刑的選擇,影響法定刑選擇的情節屬于量刑情節[3]。顯然,對于選擇法定刑(幅度)的依據是否屬于量刑情節,兩種觀點認識不同。如此,基于前一種量刑情節概念來批判“將數額、情節等視為量刑情節”的觀點[2]316,382-384就顯得無的放矢了。換言之,主張加重構成說的學者將量刑情節局限在既定法定刑之下影響具體宣告刑的情節,故認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皆為構成要件要素;而區分說論者則認為,量刑情節也可以包括部分作為選擇法定刑依據的情節,因此,法定刑升格條件的具體內容根據一定標準可以區分為量刑情節(規則)與加重構成。可見,兩說之爭,部分原因是因為對量刑情節概念的不同理解。
(二)量刑規則不同于德國刑法中量刑規則范例
德國刑法理論明確區分構成要件的變異(加重構成與減輕構成)與單純的量刑規則及其通例(范例)。參見:耶塞克,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330-333; 韋塞爾斯.德國刑法總論[M].李昌珂,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61-64; 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M].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24. 加重構成與減輕構成,是在基本犯構成要件基礎上就特別特征方面作了擴展(如對于時間或空間方面的規定、對于實施方式上的規定、對于使用一定行為手段的規定、對于行為人與受害人關系上的規定)。這些變異之所以具有“構成要件”上的質量,是因為它們在對行為的無價值產生影響,以及它們對法官而言是一個在具備這些情況時必須適用的,也只能在具備這些情況時才可以適用加重或減輕的刑罰框架的一個完整的和強制性的規則。而法律規定為“情節特別嚴重”或“情節較輕”的不確定的加重刑罰和減輕刑罰事由情況以及通過規則的例子形成的特別嚴重情節的范例(例如德國《刑法》第243條第1款德國《刑法》第243條第1款規定:“犯盜竊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個月以上十年以下自由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常屬于情節特別嚴重:①在實施行為時侵入、翻越、用假鑰匙或者其他不屬于正當開啟的工具進入建筑物、辦公或者商業空間或者其他封閉的空間或者隱藏在該空間中;②從封閉容器或者其他有防盜設備的場所盜竊物品的;③職業盜竊的;④從教堂或者其他服務與宗教活動的建筑物或空間中盜竊獻于神職或者服務于宗教崇敬的物品;⑤盜竊處于一般可進入的收集場所中的或者被公開展覽的具有科學、藝術、歷史或者用于技術發展意義的物品……。” ),不涉及行為構成的理論,只是構成刑罰量刑規則。對于量刑規則及量刑規則的范例,法官原則上可自由裁量決定。量刑規則的范例的特殊性在于:雖然這些范例“通常”屬于情節特別嚴重,但具體案件中,盡管有范例存在,法官仍然可以拒絕認定特別嚴重情節;反之,如果沒有范例要素,法官同樣可以認定具有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
首先,量刑規則及其范例之所以不屬于行為構成,正是因為法官對其的自由裁量權,量刑規則及其范例并不具備作為犯罪構成要件類型的完整性和強制性的特征。據此,反觀我國刑法中的法定刑升格條件,作為抽象的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節特別嚴重”本身就是一種整體的評價要素,法官依據具體案件的事實情況,判斷行為是否達到情節特別嚴重的程度,的確體現了自由裁量的特點;但大量的司法解釋已將“情節特別嚴重”具體化為各種事實范例,而對于具體化后的事實范例,法官卻又失去了自由裁量權,即如果達到或符合具體化后的事實范例,法官只能認定為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沒有拒絕的權利。情節特別嚴重的整體性評價轉變為具體事實范例的符合性判斷(抽象的法定刑升格條件變成了具體的法定刑升格條件),符合即適用加重法定刑,自由裁量權因此消失。當然,因為不可能完全列舉情節特別嚴重的所有情狀,立法和司法解釋在列舉具體事實情狀的基礎上,常保留“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兜底條款。就此而言,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還有一定保留。不過,留有的自由裁量權注重入罪而非出罪,這與德國法對量刑規則的范例也強調出罪意義上的自由裁量并不相同。 可見,德國法意義上的量刑規則及其范例,在我國刑法中并不存在,反倒是我國刑法中法定刑升格條件適用的強制性,更像是一種行為構成要件要素的規定。
其次,從德國刑法中罪量規則范例的具體內容來看,范例多為時間空間、行為對象、行為手段、被害關系、身份等具體內容,這一點與加重構成要素的內容并無差異。換言之,當法官通過自由裁量決定依據符合范例的事實來適用為量刑規則配置的加重刑罰時,這些符合范例的案件事實能夠加重法定刑的實質理由仍然是基于違法性、法益侵害程度遞增的考慮;既然是表征違法的客觀要素,那么,符合范例的事實在入罪時自然也應當適用或者準用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相關犯罪論規則。正因如此,區分行為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學者也承認這些通常例子在一些方面(例如錯誤理論和競合理論中)可以像行為構成的特征一樣被處理,又表現出它與行為構成的變化非常相近。參見: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M].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24.另有學者指出,對于法律為之列舉了常見例子的特別嚴重的犯罪情節,它們的未遂也應適用同樣的規則(即與加重犯未遂相同的規則——引者注)。(參見:施特拉騰韋特,庫倫.刑法總論Ⅰ:犯罪論[M].楊萌,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63.)也因如此,更有學者直接認為量刑規則的范例仍屬于構成要件[4]。
以上分析表明,德國法中的行為構成與量刑規則的范例的區分,無法照搬到我國刑法中。對此,區分說也是贊同的。(參見:張明楷.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區分[J].清華法學,2011,(1):9.)反倒是,如果按照德國法認定量刑規則范例的標準,我國刑法中的法定刑升格條件更符合加重構成要件要素的特征,而非量刑規則。
(三)應當從與構成要件要素相區別的角度把握量刑規則概念
盡管對量刑情節概念的理解不同、可資借鑒的域外經驗又沒法提供幫助,但就此得出加重構成說的結論仍為時尚早,因為雖然從正面探求量刑規則概念難有突破,但我們還需要嘗試從與之相區分的加重構成概念上尋求突破口。本文看來,正是在與構成要件要素相區別的意義上,量刑規則概念才成為可能,區分說的立場方有意義。
變體(派生)構成要件,系指在基本犯構成要件的基礎上,加以修正變化而成的不法構成要件。任何變體的規定,都必須具備構成要件的品質,才足以稱為加重或減輕的構成要件[5]。這種品質的突出表現在于:作為(客觀的)構成要件,必須是行為違法性的表征,并規制著故意的認識內容與意志內容,即構成要件的違法性推斷機能和故意規制機能。這里暫不討論主觀目的、動機等主觀違法或責任要素。 法定刑升格條件要被視為加重的構成要件,也必須接受這兩個品質的檢驗:
首先,刑法分則中因行為、對象等構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而使行為類型發生變化,進而導致違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的要素,屬于加重的犯罪構成。加重構成本身就是在基本構成基礎上的依附性變體,這種依附性雖然不改變犯罪的本質屬性,但通過“特別要素”的增加,從而使得基本犯性質(行為類型)發生局部的、非本質的變異。這些特別要素包括:行為時間、空間情狀(如入戶搶劫、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等)、行為方式手段(如持槍搶劫)、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身份或關系(如我國臺灣地區法律規定的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行為結果(如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等等,此可謂“典型的加重構成要件要素”。對此,加重構成說與區分說均無異議。
對于典型的加重構成,盡管在我國刑法中沒有就加重構成確定新的罪名,但從構成要件的意義上分析,典型的加重構成作為構成要件的部分質變,其實際上是確立了一個新的犯罪構成。因此,不僅新增的“特別要素”是違法性表征的客觀要素,是行為人主觀認知的內容,而且,加重構成也存在自己的未完成形態、共犯形態和犯罪競合。
其次,在立法或司法解釋中,也常將(作為犯罪報酬的)違法所得數額巨大、首要分子等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違法的本質是法益侵害,而非行為人獲利,盡管可以說行為人違法所得越大,法益侵害越嚴重,但卻不能說違法所得越小,法益侵害程度就一定越低。可見,違法所得與違法性(法益侵害)之間沒有邏輯上的關聯,不是違法性的表征,自然也不應當作為故意的認識內容;而首要分子,是在犯罪構成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人,但首要分子不是特殊主體,只不過是刑法對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進行綜合評價的結果而已,易言之,是行為的違法性決定了行為人是否是首要分子,而不是首要分子決定了行為的違法性大小,因此,首要分子也不可能成為故意的認識內容。可見,違法所得、首要分子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時,并不符合構成要件之品質,不能當作加重構成。此不妨稱作“典型的量刑規則”。無視此類量刑規則,是加重構成說的錯誤。
典型的量刑規則,不是違法性、法益侵害的表征,不是主觀罪過的認知內容,只有具備或達到這些條件,才能引起法定刑升格、適用加重法定刑。
最后,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作為財產損失的)數額巨大”、“多次”、“犯罪行為孳生之物數額巨大”等,此類升格條件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典型”:一方面,從前述構成要件的兩個品質來看,數額、多次(如多次搶劫)、行為孳生之物(如偽造貨幣數額特別巨大)等法定刑升格條件,作為行為規模或結果大小的表征,與違法性、法益侵害程度有著邏輯上的關聯性,也應當成為故意的認識內容,對于“多次”,只需要行為人對每一次行為有認知即可。 因此,這些條件不同于典型的量刑規則;而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也不同于典型的加重構成,因為它們并沒有行為類型的變異,只是行為規模、違法程度上有差異。作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基本犯是奶油蛋糕,那么,典型的加重構成就是水果奶油蛋糕、芝士奶油蛋糕、巧克力奶油蛋糕;而這里的非典型的升格條件,則只是增大了尺寸的奶油蛋糕而已。 這些非典型的升格條件的屬性,正是問題爭論的焦點。
綜上,盡管我們不能照搬德國刑法中的量刑規則概念,但借用量刑規則概念來概括我國刑法中不具有構成要件品質的法定刑升格條件,還是合適的。違法所得、首要分子等法定刑升格事由的存在,充分證明將法定刑升格條件一律視為加重構成是不切合立法實際的。在這種分類意義上,我們可以給我國刑法中的量刑規則作一個粗糙的界定:量刑規則,即刑法中所規定的,決定犯罪的法定刑幅度(法定刑檔)的選擇,但又不具備加重構成要件特征的法定刑升格條件。
二、數額(特別)巨大的屬性:量刑規則抑或加重構成?
(一)數額(特別)巨大是否屬于量刑規則
如上所言,典型的加重構成與典型的量刑規則的歸類,不應該存在太大異議;“數額(特別)巨大”等非典型的法定刑升格條件是加重構成還是量刑規則,才是問題的焦點。
既然是在區別于加重構成的意義上使用量刑規則概念,那么,也應當從構成要件的特征入手判斷各個升格條件的歸屬——不具備構成要件特征的,就不是加重構成,應歸于量刑規則。如果僅從構成要件的違法性推定機能和故意規制機能兩方面來看,數額巨大等非典型升格條件的確更像是加重構成,因為它們是法益侵害程度的表征,也應當是行為人主觀認知的內容。法定刑升格條件為嚴重財產損失時,行為人應當對之有認識。這是主張數額(特別)巨大屬于量刑規則的論者也認同的觀點。(參見:張明楷.法定刑升格條件的認識[J].政法論壇,2009,(5):84-94.)但對于“多次”和“作為犯罪行為孳生之物”,該文則認為它們是不需要認識的內容。本文認為,“多次”是刑法對行為人每一次行為的累計綜合評價,只要認識到作為評價依據的基礎事實,即對每一次行為有認識即可(這一點,該文也是認可的);而類似“偽造貨幣數額特別巨大”這樣的行為孳生之物,本文傾向認為,此數額是行為規模的表征,應當是需要行為人認識的內容。 可問題是,除了上述兩個機能,構成要件還有犯罪的個別化機能,即構成要件是犯罪的類型或定型,是區別某一犯罪與其他犯罪之功能[6][7]。也正是因為在這一點上的缺失,區分說將這些非典型的升格條件視為量刑規則——“‘構成要件是刑罰法規規定的行為類型’。‘并不是使行為成為犯罪的當罰的、可罰的要素都屬于構成要件要素;只有某犯罪中所固有的、類型的可罰的要素,才是構成要件要素’參見:町野朔犯罪論の展開Ⅰ[M]東京:有斐閣,1989:52,59.。根據違法類型說的觀點,只有表明違法行為類型的特征才屬于構成要件要素。而情節嚴重、數額巨大、首要分子、多次(或者對多人實施)、犯罪行為孳生之物數量(數額)巨大、違法所得數額巨大,雖然是表明違法性加重的要素,但并不屬于表明違法行為類型的特征。”[1]10
依據這種觀點,只有表征違法行為類型的要素才是構成要件要素,數額巨大等非典型升格條件,沒有行為類型或特征的變異,僅有違法程度的不同,因而不是加重構成。這一觀點在德日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規定中,不會有多大問題。因為在這些國家或地區,具體個罪立法一般采取僅定性的行為類型模式,罪狀是對某一類型的行為的特征或要素的描述。因此,構成要件自然也是被理解為“違法行為(作為刑法上禁止對象的行為)的類型(作為違法行為類型的構成要件)”參見:山口厚.刑法總論[M].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7. 盡管學說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構成要件概念,但至少作為底線的“作為違法行為類型的構成要件概念”得到了公認。 。
可是,我國刑法卻不相同,不少個罪采“定性+定量”的“行為類型+行為程度”立法模式,通過數額、情節等罪量規定,將犯罪與同一性質類型的一般違法行為區分開來。如此,只要還是在“刑法規定的,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須符合的,作為可罰行為的前提條件”的意義上理解構成要件概念(狹義的構成要件概念),那么,犯罪成立所需的、表征違法程度的罪量要素也當然應被視為構成要件要素。張明楷教授也承認基本罪狀中的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等,仍然是構成要件要素。(參見:張明楷.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區分[J].清華法學,2011,(1):10-11; 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588.) 可見,在我國刑法視域下,構成要件不僅是行為類型,也要求行為程度;即構成要件既有罪體要素,也有罪量要素。一方面,承認數額較大、情節嚴重是(基本)構成要件要素;另一方面,卻又以“只有表明違法行為類型的特征才屬于構成要件要素”為由,將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等界定在(加重)構成要件的范圍之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基本的構成要件與加重的構成要件都是構成要件,將決定違法性程度的罪量要素(數額較大、情節嚴重)視為基本構成要件要素的同時,又認為同樣決定違法性程度的罪量要素(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不應當視為加重構成要件要素,無論如何都缺乏理論的一貫性。
區分說還指出:除了數額不影響行為類型之外,還有其他理由。例如,對受賄罪的處罰也適用《刑法》第383條的規定,倘若認為《刑法》第383條第1款第(一)至(三)的內容是貪污罪的加重構成,那就意味著受賄罪的加重構成與貪污罪的加重構成是完全相同的。可是這種結論是不成立的。但我們可以說,受賄罪與貪污罪的量刑規則是相同的。刑法分則中對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規定屬于量刑規則[1]10。
這種觀點也值得商榷:一方面,加重構成對基本犯犯罪構成具有依附性,必須結合基本犯犯罪構成來看待加重構成的內容;也就是說,所謂“受賄罪的加重構成與貪污罪的加重構成是完全相同的”的提法,只是孤立地、單獨地比較加重要素的結果,如果堅持加重構成的依附性的話,受賄罪的加重構成就應該是“受賄數額在××元以上的”,貪污罪的加重構成則是“貪污數額在××元以上的”,如此又何來相同呢?實際上,上述論證混淆了加重構成要件與加重構成要件的加重要素兩個概念,加重構成要件實際上是由基本構成要件+加重構成要素構成的。另一方面,上述論斷與論者的某些結論也是矛盾的。依照論者觀點,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強奸致使被害人死亡、搶劫致人死亡都是結果加重犯,加重結果(加重構成)都是“致人死亡”,如果依照上述論斷,那就意味著故意傷害罪的加重構成、強奸罪的加重構成與搶劫罪的加重構成也是完全相同的,如果這種結論也是不成立的話,那么,“致人死亡”也只能被視為量刑規則。顯然這是不能接受的結論。
此外,區分說還認為:從表面上看,“某人盜竊數額巨大未遂”的說法,似乎沒有不合理之處。但是,“某人盜竊情節嚴重未遂”(或“某人的盜竊行為有達到情節嚴重的可能性,故認定為情節嚴重的未遂”)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數額(特別)巨大實際上也只是情節嚴重的一種表現形式。眾所周知,司法解釋針對情節(特別)嚴重所規定的情形,首先就是數額較大或者巨大。既然如此,說“某人盜竊數額巨大未遂”就是難以成立的。否則,就會出現如下難以令人理解的現象:不存在情節嚴重的未遂,但當司法解釋將情節(特別)嚴重量化為數額(特別)巨大時,則存在數額巨大未遂;根據刑法條文的規定,原本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但經由司法解釋便存在情節嚴重的未遂。顯然,只有將數額(特別)巨大作為量刑規則看待,才可以避免上述不當現象[1]11-12。
雖然這只是將數額巨大作為量刑規則的旁證,但似乎也值得商榷。
一方面,情節嚴重是“情節”嚴重。即首先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情節嚴重”評價的基礎是作為客觀事實的“情節”。縱觀立法與司法解釋的規定,這些客觀事實,有的是強調特定時空領域、特定身份、行為方式、行為對象、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加重結果等“典型的加重構成”;有的是首要分子、行為報酬之違法所得數額等“典型的量刑規則”;還有的就是這里討論的數額(特別)巨大等非典型的升格條件。顯然,應當根據“情節”的具體內容來判斷具體的法定刑升格條件是量刑規則還是加重構成。如果將情節嚴重作為一個整體,僅以“不存在情節嚴重的未遂”為由,就認為數額(特別)巨大是量刑規則,恐怕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例如,對于《刑法》第263條搶劫罪所規定的8種加重處罰情節,區分說主張其中第(四)項“多次搶劫或者搶劫數額巨大”屬于量刑規則,其他內容都屬于加重的犯罪構成[1]14。而根據1979年《刑法》第150條搶劫罪第2款之規定:“犯前款罪,情節嚴重的或者致人重傷、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比照新舊刑法不難發現,新刑法所規定的“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之外的7種情節,無非是新刑法概括舊刑法時期的司法解釋、司法實踐,將舊刑法之“情節嚴重”規定具體化而已。按照區分說的觀點,既然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那么,作為情節嚴重具體化的具體內容也不應當承認其未遂,否則就是“根據刑法條文規定,原本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但僅由司法解釋便存在情節嚴重未遂”的不當現象。如此,作為情節嚴重具體化的7種情節都應作為量刑規則看待才對。
又如,《刑法》第318條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規定了7種法定刑升格條件,區分說認為,第(三)至(五)項屬于加重的犯罪構成,其他則屬于量刑規則[1]15。可是,根據第(七)項兜底條款“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表述可以看出,前六項內容無非是“特別嚴重情節”的舉例而已,依照區分說,如果說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所例舉的情節嚴重的具體內容也不應該承認未遂,各具體情節都應當視為量刑規則,而不是根據前六項特別嚴重情節的具體內容,區分為加重構成和量刑規則。
再如,張明楷教授主張,搶奪致人死亡的,應屬于搶奪情節特別嚴重。這種場合完全應當按照結果加重犯的原理處理,即只要行為人對死亡結果具有預見可能性即可[4]91。可是依據區分說的觀點,既然情節特別嚴重是量刑規則,經學理解釋作為情節特別嚴重具體化內容的致人死亡,當然也只能被作為量刑規則看待才是,又何來結果加重犯呢?
可見,以“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為由,認為作為情節嚴重具體表現形式的數額(特別)巨大也不應當有未遂,從而主張只能將數額巨大看作量刑規則,理由并不充分,并沒有將情節嚴重各個具體表現形式一視同仁,與自己區分說的主張也存在自相矛盾之處。
另一方面,情節嚴重是情節“嚴重”,即情節嚴重是立足于客觀事實“情節”基礎上的一種整體的評價要素。先有客觀事實情狀,再有對該事實情狀是否達到“嚴重”標準的整體性評價。而行為既遂、未遂是行為的一種終極形態,是事實情狀,是“是否屬于情節‘嚴重’評價”的素材和基礎。可見,所謂“某人盜竊情節嚴重未遂”本來就是錯誤的表述,它顛倒了作為評價前提的事實——未遂“情節”與對情節事實的評價——情節“嚴重”之間的邏輯順序。“情節嚴重未遂”不成立,但“××未遂”卻可以評價為情節“嚴重”。例如,作為搶劫犯加重情節的“入戶搶劫”,如果行為人入戶搶劫未遂,當然應當屬于情節嚴重的搶劫未遂,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為基準從輕、減輕處罰。司法解釋也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的,應當定罪處罰。”“詐騙未遂,……,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定罪處罰。”
可見,“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的命題實際上是基于情節“嚴重”之整體性評價特征而得出的結論。以所謂“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為由,得出也不應當承認“(作為情節嚴重具體化或表現形式的)數額(特別)巨大未遂”的結論,進而主張數額(特別)巨大是量刑規則。這種觀點混淆了法定刑升格條件——情節嚴重中的“情節”事實與“嚴重”評價:用基于后者所推導出的命題,來判斷作為前者的數額等客觀事實的性質是加重構成還是量刑規則,自然值得商榷。
另外,如前所述,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意義在于是否存在未遂犯,即加重構成存在未遂,量刑規則不存在未遂。一方面,將是否存在未遂犯視為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適用效果(后果);另一方面,又以“不存在情節嚴重未遂”為標準,得出數額巨大是量刑規則的結論。如此,“是否存在未遂”既是區分的效果,也成了區分的標準。盡管“是否存在未遂”的確是檢驗某法定刑升格條件是加重構成還是量刑規則的試金石,但作為適用結果的它絕不能同時成為我們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判斷標準,否則不過是無益的循環論證而已。
綜上所述,區分說將數額(特別)巨大視為量刑規則的理由,或者缺乏理論的一貫性,或者有自相矛盾、循環論證等嫌疑。
(二)數額巨大是否屬于典型的加重構成
既然將數額巨大視為量刑規則的觀點值得商榷,那么,是否意味著數額巨大就是加重構成呢?如前所述,本文主張以構成要件的品質為標準,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但凡符合構成要件品質的法定刑升格條件就是加重構成,否則即是量刑規則。數額巨大等非典型的法定刑升格條件,因為僅僅是違法程度的表征,而未表現違法行為類型的變異,自然無法承擔“犯罪的個別化”這一構成要件的機能(品質),因而不屬于典型的加重構成。但是,考慮到在基本犯中,同樣只是違法程度表征的數額較大等要素,都被認為是基本構成要件要素。那么,就沒有理由將同樣是違法程度表征的數額(特別)巨大等要素排除在加重構成要件要素之外,因為無論是基本構成還是加重構成,都是構成要件,具有共同的品質。
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著筆者贊同加重構成說,一方面,因為加重構成說并沒有注意到數額巨大等加重構成與典型的加重構成之間的差異,而是將所謂數額加重犯與典型的加重構成等同視之。例如,持加重構成說的論者指出:數額加重犯相對于數額犯而言,并非一種簡單的量變,而是存在一種由量變到質變的問題,其具有不同于數額犯的罪質和罪責。當然,這里的“質變”不是一種根本性的質變,而僅僅是一種階段性部分質變。根據哲學原理,只要事物的本質屬性未變,事物總體上仍然處于量變過程,但如果非本質屬性發生了重大變化,事物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這就是總的量變過程中階段性的部分質變。參見:李秀林,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127. 這種階段性的部分質變沒有使數額加重犯形成一種截然區別于數額犯的獨立的罪質,而只是使罪質的內部呈現一定的層次性變化[2]382。論者將數額加重犯也視為一種部分質變,并配以哲學原理的論證,從而使數額加重與結果加重、行為方式加重、對象加重等典型的加重構成保持在同一性質。但無論如何,數額加重只是單純的違法程度的提高,亦即“加重法定刑的數額與基本犯的數額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或者說是量差不同而已”[8]。這與典型的加重構成“通過違法行為類型的局部變異從而導致違法性增加”的特質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即便將數額加重視為部分質變,這種質變也是不同于典型加重構成的另一種質變形式。前者是縱向的程度差異,而后者則是橫向的類型區別。這種性質上的區別表明,將二者等同視之的加重構成說的觀點同樣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罪刑均衡是檢驗上述學說的試金石,而對加重構成說最重要的詰難恰恰是認為該學說是對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違背。誠如區分說所言:假定盜竊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與特別巨大的起點分別為1000元、1萬元與10萬元。若A盜竊9萬元既遂,B意圖盜竊11萬元未遂。按照加重構成說的做法,對A可能判處的最低刑為3年徒刑,可能判處的最高刑為10年徒刑,而對B可能判處的最低刑為10年徒刑,可能判處的最高刑為無期徒刑。誠然,對B可以適用刑法總則關于未遂犯的處罰規定,盡管如此,對B的處罰仍然會重于對A的處罰。然而,A的盜竊行為已經給他人財產造成了實害,B的盜竊行為只是有造成他人財產損失11萬元的危險,所以,B的盜竊行為的違法程度肯定輕于A的盜竊行為的違法程度。不難看出這種做法有悖罪刑相適應原則[1]13。司法實踐中,對盜竊罪等數額犯的刑罰裁量,常以實際發生的數額為準,選擇相應的法定刑檔;但同時對于盜竊金融機構等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分文未取的情狀,則常依照司法解釋,以盜竊罪(未遂)定罪,并以數額(特別)巨大的法定刑檔為基準從輕、減輕處罰。如果同時貫徹上述做法,那么,同樣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盜竊目標的甲乙二人,甲盜竊了2000元;乙當場被擒,分文未得。對甲以所得數額至多科處3年徒刑,而乙則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基準上從輕、減輕處罰,量刑不公可見一斑。
綜上,加重構成說將數額巨大等法定刑升格條件與典型的加重構成要素等同視之,忽視了二者在內容和性質上的重大差異,同時其適用效果的確與罪刑均衡原則有悖,同樣值得商榷。
在筆者看來,如同基本構成有罪體與罪量之分,加重構成也應當有罪體加重構成(要素)與罪量加重構成(要素)的區分。罪體加重構成要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典型加重構成,而數額巨大、多次等非典型的法定刑升格條件,則基本上可以視為罪量加重構成(要素)。如同基本犯中的罪量要素是構成要件要素一樣,內容和性質相同的加重罪量要素也應當視為(加重)構成要件要素;也如同基本犯的罪體要素與罪量要素之間存在差異一樣,罪量加重構成要素也有著不同于罪體加重構成要素的特征,不能將兩類加重構成要素等同視之。
(三)罪量加重構成(要素)概念之提倡
如果給罪量加重構成要素下一個定義的話,即罪量加重構成要素,是指刑法分則中規定的,通過單純提高基本構成要件的某一特定要素的規模或程度,修正基本構成要件,而成立的加重處罰(加重其法律效果)的不法構成要件要素。罪量加重構成要素與罪體加重構成要素,二者都是加重構成要素,罪體加重構成具備構成要件的三大機能(品質)——犯罪的個別化、違法性推定和故意規制,是典型的構成要件;而罪量加重構成,則是中國刑法“定性+定量”立法模式的產物——因為如果說基本犯中的數額較大等罪量要素屬于基本犯構成要件要素的話,那么,具有相同內容(都是關于行為或結果的程度與規模)和性質(都是違法程度的表征,與行為類型無關)的數額(特別)巨大等加重事由,就沒有理由將其視為與(加重)構成要件相對立的量刑規則。
罪量加重構成,特點有二:其一,它是罪量“加重構成”。作為罪量加重構成具體內容的各要素,應當符合(加重)構成要件的特質,即必須是違法性程度的表征,也應該是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其二,它是“罪量”加重構成。即罪量加重構成要件要素并不涉及行為類型的局部變異,僅僅是因違法程度的增加而加重處罰。
從內容上看,罪量加重構成的具體要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行為規模;另一類是結果程度。
1. 行為規模類(行為類),即通過對行為規模或者行為內容量化標準的提高,從而增加違法程度,加重法定刑的情形。例如:將“多次(或者對多人)實施”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形。如刑法中強奸婦女、奸淫幼女多人,多次搶劫,多次聚眾斗毆,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多次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多次強迫他人賣淫等等。多次是對各次犯罪行為的累加。可以認為行為累加起到了使行為規模、違法程度提高的作用,故而加重法定刑。根據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多次一般指三次以上,倘若行為次數不足三次,自然不能適用加重法定刑,亦即,倘若行為人已經實施了兩次搶劫行為,正意欲實施第三次,但尚未著手,此時不能將其認定為多次搶劫的未遂。因為多次并非判斷行為得逞與否的要素,與犯罪既、未遂認定無關。如果行為人三次搶劫,三次都未遂,能否認定為多次搶劫未遂,比照加重法定刑從輕或減輕處罰?如果三次搶劫,一次既遂兩次未遂或者兩次既遂一次未遂,如何處置,值得進一步研究。 另一種表現是部分有關行為對象的數額規定。例如走私、販賣、運輸毒品罪中的毒品數量,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走私假幣罪中的假幣數額等。這些行為對象數額的特點是,在行為伊始、著手之時,客觀的數額是基本確定的,行為人主觀上對此也有認識(至少有概括性認識),而犯罪的既、未遂則取決于行為的完成與否。因此,倘若行為人針對數額(數量)巨大的假幣、毒品而實施走私、運輸等行為未完成、未得逞的,就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的走私、運輸犯罪的未遂,比照加重法定刑從輕、減輕處罰。可見,這種行為規模類的數額巨大等罪量加重構成要素,因為與本罪的既、未遂認定之間沒有直接關聯,因而,在未遂犯法定刑基準的選擇問題上與典型的加重構成并無太大差異。
2. 結果程度類(結果類),則是通過對“行為給法益所造成的現實侵害結果”或者“行為孳生之物”的量的提高,增加違法程度,加重法定刑的情狀。前者如盜竊罪、詐騙罪中的數額(特別)巨大,受賄罪中的受賄數額對受賄罪的既未遂區分標準還有爭議,但是,考慮到我國受賄罪具有財產犯罪的一面,以行為人利用手中的職務獲取財產為內容,從此意義上講,將行為人是否實際獲取財物作為判斷受賄罪是否既遂的標準,是有其道理的。(參見:黎宏.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59.)當然,對索賄型受賄可能存在不同看法。(參見:張明楷.刑法學[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77.) 等;后者如偽造假幣罪的假幣數量、制造毒品罪中的毒品數量等。此類數額與行為規模類最大的區別是,在行為伊始、著手之時,對于行為結果的規模、數額是不明確的。完全可能出現這樣的情形:行為人意圖盜竊、詐騙數額巨大的財物,實際上卻分文未得;行為人意圖偽造、制造數量巨大的假幣或毒品,結果僅偽造、制造出一小部分就被查處。這些情況當如何處置?如何選擇法定刑基準?這正是量刑規則說與加重構成說爭論的焦點,提出罪量加重構成概念的意義也正在于此。
如上所述,基于數額(特別)巨大的法定刑升格條件與數額較大的基本犯罪量構成要件要素的相同性質與內容,我們賦予這些升格條件(加重)構成要件要素的地位;但同時,也基于這些要素與典型的加重構成要素之間的差異,而不能將二者等同視之。
在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中,加重構成是在基本構成的基礎上,加入特定元素修正的產物。加重構成要素的加入,使得基本構成發生變異,從而形成相對獨立的加重犯、加重構成;但變異是局部的,加重犯的成立依附于基本犯,即需要借助、回溯基本構成要件來判斷該依附性變體的構成要件[5]106。就未遂而言,加重犯的既、未遂形態也需要借助、回溯到基本犯的既、未遂形態來判斷。誠如耶塞克教授指出:“在加重構成要件情況下,(未遂)同樣取決于行為人是否直接開始實現構成要件。若行為人開始實現加重要素(例如,在縱火前使滅火器不能使用),僅限于基本構成要件由此能夠直接實現的場合,始可認定未遂。加重結果的行為(例如在實施搶劫罪時攜帶射擊武器)在基本犯的預備階段(例如在接近搶劫行為地)即實現的場合,行為人只能因基本犯未遂而受處罰。”參見:耶塞克,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617. 類似觀點也見:施特拉騰韋特,庫倫.刑法總論Ⅰ:犯罪論[M].楊萌,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63. 以我國刑法中公認的典型加重構成——入戶搶劫為例,“入戶”是該加重構成區分于普通構成的“特別要素”(加重構成要素),決定能否適用加重搶劫之法定刑,而“是否劫取財物”既是基本犯也是加重犯犯罪既遂或未遂的標準。我國臺灣學者也指出,如果夜間侵入竊盜罪只是一個屬于加重類型的廣義的結合犯,那么這個犯罪的基本構成要件還是在竊盜罪的部分,而所謂著手,在基本概念上,也必須是竊盜行為本身的著手,而不包括侵入住宅行為的著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其犯罪構成要件還是在于竊盜的部分,所以其既遂犯罪之構成當然以竊盜既遂為要件。(參見: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50,255.) 可見,在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中,決定犯罪形態的因素與加重事由(加重構成要素)是分開的,二者各司其職。當然,我國刑法中加重構成的規定也可能存在例外。例如,如果承認故意的結果加重犯,則行為人意圖殺人劫財,并已著手殺害行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致人死亡的,即使強取到了財物,也可成立“搶劫致人死亡”的加重搶劫犯未遂。再如,刑法中將又犯他罪作為加重法定刑的所謂結合加重犯的場合,如綁架罪中“殺害被綁架人”,對于綁架殺人未遂的,就有主張,依然適用《刑法》第239條“殺害被綁架人,處死刑”的規定,同時適用刑法關于未遂犯從輕、減輕處罰的規定。(參見:張明楷.刑法學[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96.)
而在結果類罪量加重構成中,情況確有不同:其一,數額之載體——結果,既是判斷行為既、未遂的“行為人所希望放任的,行為性質決定的侵害結果”,同時也是加重法定刑適用的條件。依據加重構成說,如果行為人意圖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未得逞的,即認定為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未遂,比照數額(特別)巨大既遂的法定刑從輕、減輕處罰。此時,行為人主觀上希望的,行為性質決定的可能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客觀危險性,既是未遂成立的實質條件,也是適用加重法定刑的客觀理由,這樣,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數額(特別)巨大就從客觀的實害事實轉換為可能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危險狀態。這一點顯然與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存在差異,因為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是在基本犯罪構成基礎上附加某些“特別要素”、以該特別要素的實現、客觀存在(而非存在的可能性、危險性)作為適用加重法定刑的條件的。既然如此,姑且不論加重構成說“成立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未遂犯”的結論是否成立,至少從該結論的具體論證中可以發現,罪量加重構成與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在適用條件、未遂犯的認定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而將“一切法定刑升格條件都視作加重構成”的加重構成說的基本主張中,卻并未注意到這一差異,有欠妥當。
其二,根據客觀未遂論的主張,未遂犯處罰的根據在于發生法益侵害的緊迫危險性。“行為人意圖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未得逞的”以未遂犯論處,無非是因為行為具有可能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客觀緊迫危險性。那么,這種客觀緊迫危險性究竟是盜竊基本犯未遂成立的實質條件,還是盜竊加重犯未遂成立的實質條件呢?盡管我國刑法總則規定原則上處罰所有故意犯未遂,但這并不現實,刑法理論一致認為,未遂犯的處罰具有例外性,必須實質考察具體故意犯罪的特殊形態的可罰性。因此,“罪質嚴重的未遂應當以犯罪未遂論處,如故意殺人未遂、搶劫未遂、強奸未遂等;罪質一般的未遂只有情節嚴重的,才能以犯罪未遂論處,如盜竊未遂、詐騙未遂等;罪質輕微的未遂不以犯罪論處。”[3]310甚至有學者提出,以最高法定刑為3年有期徒刑區分重罪與輕罪,重罪考慮處罰其未遂形態,輕罪則沒有必要處罰其未遂形態[9]。正因如此,司法解釋才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這里的“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正是使罪質一般的盜竊行為未遂,達到可罰違法程度,以盜竊罪(未遂)論處的客觀違法性提高的因素。在筆者看來,這里作為情節嚴重范例的“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盜竊目標的”,正是表明行為可能盜竊數額巨大財物的客觀危險性,從而提高客觀的違法程度,使得罪質一般的盜竊行為未遂能以犯罪論處。如果主張這種情況成立“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未遂犯”的話,豈不是將“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盜竊目標的”(行為可能盜竊數額巨大財物的客觀危險性)既作為盜竊未遂行為達到可罰違法程度、成立犯罪的客觀標準,又作為加重法定刑的升格條件,這難道不是有違禁止重復評價的刑法原則嗎?相同意見參見:黎宏.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51. 黎宏教授還指出,如果以盜竊既遂數額巨大的量刑檔次作為量刑基準,會出現對于盜竊未遂的,要么不定罪,要么一定罪就是在數額巨大的量刑檔次處罰的情況,出現對于盜竊未遂量刑檔次斷檔脫節、不協調的局面。
其三,事實上,在“行為人意圖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未得逞”的事例中,基本犯也是處于未遂狀態,這就涉及基本犯罪未遂的行為是否仍以結果加重犯未遂罪論之。這一點德國刑法理論的觀點值得參考借鑒。德國實務及學說對于基礎犯罪未遂的情況下能否適用結果加重未遂犯規定的問題,大致有3種說法:第1個說法是所謂的結果危險理論(Lehre von der Erfolgsgefhrlichkeit),認為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的構成,原則上只有一種情況,就是基礎犯罪已經既遂,但是行為人具有故意的加重結果的部分未遂。此一理論的主要理由是,結果加重犯之所以加重其處罰,其原因是基礎犯罪的結果具有特殊的危險性,因此,如果基礎犯罪沒有既遂,則已經喪失加重的依據。第2個說法是所謂的行為危險理論(Lehre von der Handlungsgefhrlichkeit),認為不管哪一種結構的結果加重犯,如果基本犯罪部分未遂,但已經導致加重結果的發生,則均構成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此一理論的論點是,結果加重犯之所以加重其處罰,其原因是基礎犯罪行為的本身已經具有特殊的危險性,因此,即使基礎犯罪未遂,其行為本身的危險性已經符合法律加重處罰的理由,所以應該構成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第3個說法是所謂的區別理論(differenzierende Theorie),認為基礎犯罪部分未遂而已經導致加重結果的發生,是否可以論以結果加重未遂犯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而是必須依照個別的結果加重犯的規定來判斷。如果某一特定的結果加重犯的規定是基于基礎犯罪行為本身的危險性而加重處罰,那么,雖然基礎犯罪未遂,仍應論以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例如德國《刑法》第177條第3項所規定的強奸致被害人于死,或第251條所規定的強盜致人于死即是。至于如果某一特定的結果加重犯的規定是基于基礎犯罪的結果的危險性而加重刑罰,那么,基礎犯罪未遂,已經喪失加重之依據,即不得論以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例如德國《刑法》第224條第1項所規定的傷害致重傷害罪,或第226條第1項所規定的傷害致人于死罪即是。參見: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53-254.
根據上述觀點,結果加重犯未遂罪的成立,要么是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結果發生;要么是基本犯罪既遂,而故意的加重結果未發生,“意圖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分文未取”的事例顯然不屬于這兩種情況。誠然在中國刑法中,也可能成立“基本犯罪未遂,且故意的加重結果未發生”這種類型的加重犯未遂。但這種類型的加重犯未遂,僅針對類似搶劫殺人、拐賣婦女中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等存在復數行為和復數結果、具有結合性質的特殊的加重犯而言[2]377、[10]。在“意圖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分文未取”的事例中,不僅加重結果“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未發生,而且基本犯罪“盜竊數額較大的財物”也只是未遂。難以想象,像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這樣僅有單一盜竊行為、單一盜竊結果的加重犯類型,也能肯定“基本犯未遂且故意的加重結果未發生”這種類型的加重犯未遂的成立。
反倒是區分理論“如果某一特定的結果加重犯的規定是基于基礎犯罪的結果的危險性而加重刑罰,那么,基礎犯罪未遂,已經喪失加重之依據,即不得論以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的觀點,非常符合我國結果數額加重規定的情況。加重數額是在基本數額基礎上量的提升,是基于基礎犯罪的結果危險性而加重刑罰,沒有基本數額,也就喪失了加重的依據,自不得論以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還以奶油蛋糕作比喻:典型的罪質加重構成(未遂),就像是被咬掉或切掉一塊的芝士(水果、巧克力)奶油蛋糕,它依然還是芝士(水果、巧克力)奶油蛋糕,只是不完整了而已;而結果類的罪量加重構成與基本構成的關系是12寸奶油蛋糕和8寸奶油蛋糕的關系,如果將12寸奶油蛋糕咬掉或切掉一塊,尺寸變小,已經不再是12寸了(不能夠說是不完整的12寸奶油蛋糕)。 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教授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將結果加重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像故意傷害致死那樣,由第一結果即傷害導致第二加重結果即死亡;二是像搶劫罪那樣,以暴力行為為手段,一方面發生了第一結果即取得財物,同時又發生第二結果即死傷。在后一種場合,即使沒有發生第一結果,有時也可能發生第二結果,如果第一結果未發生,有可能認定為結果加重犯的未遂(可能存在未遂的結果加重犯)。在前一種場合,由于不發生第一結果就不會發生第二結果,既然已經發生第二結果,就不能說是未遂;反之,如果沒有發生第二結果,則不能認定為結果加重犯,也不能認定為結果加重犯的未遂(不可能存在未遂的結果加重犯)[11]。事實上,持加重構成說的論者也注意到了典型的結果加重犯與這里的結果型數額加重規定(即論者所稱數額加重犯)之間的差異:在結果加重犯中,加重結果與基本結果的性質可能有所不同。而在數額加重犯中,加重數額與基本數額在性質上沒有任何差異。在加重結果與基本性質不同的情況下,兩者可以并存,而加重數額與基本數額之間則存在當然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不可能并存[2]389。這一論斷實際上與區分理論的觀點已基本相當,既然“加重數額與基本數額性質上沒有差異、存在當然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那么,就同樣不應該承認“基本犯未遂,且故意的加重結果也未發生”這種類型的所謂數額加重犯未遂的成立。
基于此,本文主張,對結果類罪量加重構成規定,以盜竊罪為例,若行為人意欲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分文未得的,應當以盜竊罪(未遂)論處,依據刑法總則未遂犯之規定,在盜竊數額較大的法定刑基準上可以從輕、減輕處罰;如果由于意志之外的原因僅取得數額較大的財物,則以盜竊數額較大的財物的既遂犯論處。可見,在適用加重法定刑的標準問題上,量刑規則、罪體加重構成要件(故意的結果加重犯除外)和罪量加重構成要件都是以加重條件的客觀存在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量刑規則與違法無關,無所謂既、未遂;罪體加重構成要件和行為類罪量加重構成要件,加重要素與既、未遂認定的標準相分離,存在所謂的加重犯未遂;而結果類罪量加重構成,加重要素與既、未遂認定標準合一,加重犯未遂意味著基本犯也是未遂,這種意義上的加重犯未遂是難以成立的。
綜上所述,罪量加重構成概念,意在概括那些不改變行為類型,只是通過單純地提高行為違法程度,從而加重法律效果的法定刑升格條件[12]。從具體內容上看,包括行為規模和結果程度兩大類。不過從實際意義上看,罪量加重構成概念的真正意義在結果程度類罪量加重構成要素,此類規定是基于基本犯的結果的危險性而加重刑罰,如果基本犯之結果沒有發生(基本犯未c549380bead8dd74071144e7b00078f8遂),那就已經喪失加重之依據,即不得論以結果加重犯的未遂犯,只能以行為可能侵害更大規模和程度的法益的客觀危險性為由,認為屬于“罪質一般的未遂只有情節嚴重的,才能以犯罪未遂論處”的情狀,以基本犯的未遂犯論處。
三、情節(特別)嚴重的屬性
區分說認為,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節(特別)嚴重,也只是量(違法程度)的變化,不會是違法行為類型發生變化,故不應屬于加重的犯罪構成,只能視為量刑規則[1]11。的確,情節嚴重是一種整體的評價,綜合客觀事實,如果認為案件符合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節嚴重的要求,即適用相應的加重法定刑,反之,不能適用相應的法定刑。可見,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節嚴重,的確具有類似量刑規則的適用特點。不過,也有兩點疑問:
第一,與“作為基本犯構成要件罪量要素的數額較大與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數額(特別)巨大之間的關系”相同,在基本犯的罪狀描述中同樣存在“情節嚴重”要素,區分說認為,基本罪狀中的情節嚴重是構成要件要素,是一種整體的評價要素[13]。那么,與情節嚴重要素具有相同內容和性質的“情節特別嚴重”,也應當同樣認為屬于(加重)構成要件要素才對,而不應僅僅是量刑規則。在此,區分說恐怕缺乏理論的一貫性。
第二,情節嚴重的確是一種整體評價,但評價的前提是客觀存在的具體情節。必須區分作為評價結果的情節“嚴重”與作為評價基礎的“情節”嚴重。我國刑法常常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將情節嚴重的情節具體化,而對于具體化后的各具體情節,如果客觀行為符合該具體情節時,原則上就必須認定為情節嚴重。換言之,隨著情節嚴重的情節在立法或司法解釋中的具體化,情節嚴重的整合綜合評價已經為部分事實的符合性判斷所取代。這些被具體化的情節事實,是加重構成要素還是量刑規則,則需要結合上文的標準逐一判斷。如同前文所舉的搶劫罪的例子,舊刑法中作為搶劫罪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節嚴重”,在新刑法中被具體化為7個具體的法定刑升格條件,就需要我們根據7項內容,具體判斷各自的屬性。
可見,情節嚴重型法定刑升格條件的屬性,恐怕不能一概而論。當立法或司法解釋將情節嚴重具體化為若干客觀具體情狀時,應當首先根據其具體內容,判斷該客觀情狀是加重構成還是量刑規則。只有剩下的“其他情節嚴重的”的兜底條款,因為還保有整體評價的本性,還勉強留有類似量刑規則的適用特點。
根據上述觀點,當情節嚴重具體化為首要分子、作為報酬的違法所得等內容時,應當視為典型的量刑規則;當情節嚴重具體化為特定時間地點、特定行為方式、特定主體、致人重傷死亡的加重后果或與基本犯不同質的他罪行為或結果時,則應當視為典型的罪體加重構成;而當情節嚴重具體化為多次、數額等與違法行為類型無關、但在量上增加違法程度的客觀要素時,則應當將它們視為罪量加重構成要素,尤其是其中作為行為指向的法益侵害結果和作為行為孳生之物的結果這兩種結果類罪量加重構成,對于這種結果類罪量加重構成要素,不可以承認所謂“加重犯未遂”,只有客觀具備該加重結果時,方有升格法定刑的適用。
例如,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規定:“詐騙未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詐騙目標的,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定罪處罰。利用發送短信、撥打電話、互聯網等電信技術手段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6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一)發送詐騙信息5000條以上的;(二)撥打詐騙電話500人次以上的;(三)詐騙手段惡劣、危害嚴重的。實施前款規定行為,數量達到前款第(一)、(二)項規定標準10倍以上的,或者詐騙手段特別惡劣,危害特別嚴重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6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依照本文觀點,其中的“詐騙未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詐騙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就是所謂“意圖詐騙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未得逞”的情況,詐騙罪的“數額巨大”是結果程度類罪量加重構成要素,詐騙結果未發生,不能認定為所謂詐騙加重犯未遂。因此,如果意圖詐騙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實際分文未得時,應當以基本犯詐騙罪(未遂)論處,適用數額較大的法定刑,并適用總則未遂犯規定;如果意圖詐騙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而實際取得數額較大的財物時,則以數額較大的詐騙罪既遂論處。
而其中的“詐騙未遂,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從具體內容上看,除第(三)項兜底的整體評價內容外,第(一)、(二)項實際上是對行為手段、行為程度的特殊化,可將其視為典型的加重構成或者是與典型的加重構成具有相同處置效果的行為規模類罪量加重構成,亦即承認所謂詐騙加重犯未遂。唯有如此,方能合理理解司法解釋根據行為規模的不同而規定不同的適用效果的情況——“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6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和“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6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兩檔不同的詐騙罪(未遂)處罰標準。ML
參考文獻:
[1] 張明楷.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區分[J].清華法學,2011,(1):7-15.
[2] 王志祥.犯罪既遂新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316.
[3] 張明楷.刑法學[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02-503.
[4]張明楷法定刑升格條件的認識[J].政法論壇,2009,(5):89
[5]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06.
[6] 陳子平.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96.
[7] 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2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72.
[8] 唐世月.數額犯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99.
[9] 黎宏.刑法總論問題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27.
[10] 盧宇蓉.加重構成犯罪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65.
[11] 平野龍一.刑法總論II[M].東京:有斐閣,1975:309.
[12]陳捷.量刑規范化問題研究——以西安市碑林區人民法院為例[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1,(6):91.
[13] 張明楷.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38.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ggravating Conditions and Sentencing Rules
WANG Yanqiang1,2
(1.Law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The statutory sentencing aggreg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aggravating condition and sentencing rule. Sentencing rules include certain chief culprit, and illegal income. Aggravating conditions would consider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behavior, among others. The conditions, such as frequency and the varying amount, are not typical aggregating conditions or sentencing rules. Both behavior and result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 essential offense is an attempted crime, which has lost aggravating reason,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hat an attempted crime of aggravated crime is established. As for the term “serious”, if legislation or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have specific provisions, these provisions should be applied.
Key Words: statutory sentencing aggravating conditions; aggravating conditions; sentencing rules; aggravating conditions for serious crime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