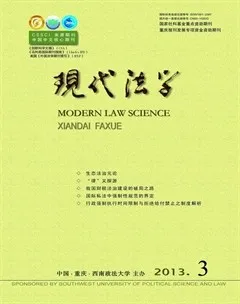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的界定
文章編號:1001-2397(2013)03-0149-10
收稿日期:2013-01-30
基金項目: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外國公法在國際私法中的運用研究”(12CFX107);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消費者債務清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12YJC820003);2012年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1SJB820015)
作者簡介:卜璐(1983-),女,江蘇淮安人,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摘 要:《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條于我國國際私法中首次明確規定我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應予直接適用。作為多邊選法體系的例外,強制性規范理論在適用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是識別哪些規范屬于需要直接適用的國際強制性規范。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僅指國際強制性規范。比較法上提出界定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隨之產生僅采客觀標準和兼采主客觀標準兩種立法模式。《關于適用<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0條對何為我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進行了定義,并以不完全列舉的方式來解決可操作性問題,但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仍存在缺失。
關鍵詞:國際強制性規范;客觀標準;主觀標準;立法缺失
中圖分類號:DF9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3.14
一、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法律適用法》)第4條在我國國際私法立法中首度引入強制性規范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涉外民事關系有強制性規定的,直接適用該強制性規定。”但對于哪些規范屬于該條中直接適用的強制性規定,《法律適用法》未作界定,這導致第4條在司法實踐中屢被錯誤適用。在2012年上海伽姆普實業有限公司與Moraglis S.A.承攬合同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滬高民二(商)終字第4號。 中,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判決中將《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作為《法律適用法》第4條中的“強制性規定”,推導出該案若為涉外買賣合同糾紛則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結論。在2011年楊某訴鐘某等海上人身損害責任糾紛案廣州海事法院(2011)廣海法初字第373號。 中,廣州海事法院援引《法律適用法》第4條去適用《民法通則》第146條第2款(當事人雙方國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適用當事人本國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認定加害方和受害方共同住所地法(中國法)是該案的準據法,誤將一條沖突規范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涉外民事關系的強制性規定”。
對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概念的錯誤認識已嚴重影響到這一新理論在我國涉外民商事審判中的運用,不進行明確界定容易造成實踐中濫用該條款而折損國際私法的功效。誠如費舍爾(Vischer)教授所言:“對于強制性規范的直接適用原則,立法者和司法者面臨最困難的任務便是識別哪些規范屬于依其本身特殊性需要直接適用的規范。”[1]因此,強制性規范理論作為多邊方法的例外適用于國際民商事案件時,必須解決的問題便是哪些法律規范屬于此類需要直接適用的強制性規范。
這一問題的回答建立在如下思考之上:首先是界定的對象,強制性規范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在國際私法語境下進行界定的前提,是明確何為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其次是界定的標準,這是從內涵的角度出發解決如何界定這一核心問題;最后是界定標準的立法表現,關注如何將理論上的標準轉化為實踐中的立法。
二、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概念的形成
要對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進行界定,必須首先探求這一概念的形成機理。“強制性規范”并非現代漢語中的固有名詞,作為一個徹底的“舶來品”,要界定其內容,必須從外來語中找尋根源。然而,這種常規的概念界定方法在這里遇到了極大的阻礙,因為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的外來語來源異常混亂,根源便在于強制性規范概念產生于對既存現象的多角度描述。
(一)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的緣起:現象先于理論
現 代 法 學 卜 璐: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的界定——兼評《關于適用<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0條現代國際私法的多邊選法體系發端于薩維尼(Savigny),他在遵循羅馬法中公私法嚴格劃分的基礎上建立了“以法律關系本座說”為中心的法律適用體系。但薩維尼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中也注意到存在一些絕對性的強制規范,承載著立法國的重要政策,這些規范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質和實體內容能夠對抗法律的普遍主義[2]。普遍主義正是薩維尼構筑多邊選法體系的基石,所以他認為,這類規范屬于國際私法多邊體系的例外,是一種異常現象,因為隨著人類交往的自由化和單邊主義的沒落,這類規范必然消失[2]38。但歷史已證明了薩維尼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3]。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薩維尼發現了絕對性強制規范的存在,但他認定的該類例外既包含了現今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也包含了公共秩序保留的例外,因此,他并沒有提出強制性規范的直接適用理論。該理論產生的直接原因是1930年代美國債券持有人在美國發起的針對德國債務人的訴訟,引發了德國學者對強制性規范進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德國制造業1920年代在美國發行了大量債券,但德國1931年進行的嚴格外匯管制導致債務人無法支付這些債券的利息,美國債券持有人在美國法院提起訴訟并且適用美國法,德國債務人提出了特別法(Sonderstatut)理論,認為案件雖不適用德國法,但德國外匯管制法由于其強制性也應得到考慮[4]。其后,德國學者溫格勒(Wilhelm Wengler)溫格勒在1941年《論國際私法上的強行債法聯系》一文中首創“Sonderanknüpfungstheorie”(特別聯系理論),旨在賦予作為準據法的外國法中的強制性規范和內國強制性規范同等地位,采用相同的適用條件。(參見:Wengler.Die Anknüpfung des zwingenden Schuldrechts im internationalen Privatrecht[J].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Rechtswissenschaft,1941,(54):168-212.) 和茨威格特(Konrad Zweigert)茨威格特在1942年《因外國禁止給付而不履行的基礎》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特別聯系理論”,認為合同準據法國以外的外國強制性規范在存在特別聯系的條件下,也可以適用于合同案件。(參見:Zweigert.Nichterfüllung auf Grund auslndischer Leistungsverbote[J].Rabels Zeitschrift für ausl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1942,(14):283-307.) 等進一步完善了特別法理論。
雖然194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第2款(b)項該條款規定:“凡涉及一會員國貨幣的外匯合同,若違反該會員國依本協定實施的外匯管制法,則在所有成員國境內一律無效。” 進一步強化了外匯管制法律在外匯合同法律適用中的特殊地位,但薩維尼建立起來的多邊選法體系承受的最大壓力并非來源于外匯管制,而是來自于福利國家的出現。福利國家導致了一系列含有社會公共利益的法律規范(如消費者保護、最低勞動保障等),這些規范既非純粹的私法,也非純粹的公法。在這些規范出現的領域,私人意思自治和合同義務可以被此類規范所推翻,傳統的法律適用體系不再適用,于是急需界定這類規范在國際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法國學者弗朗西斯卡基斯(Phocion Francescakis)弗朗西斯卡基斯在1958年《反致理論與國際私法的制度沖突》一書中發現,在法國法院的實踐中,法院地國的一些法律由于其實體內容在沖突規范的雙邊體系中獲得了特殊的地位,可排除一般沖突規范的指引而得到直接適用,他將此類規范定義為“loi d’application immediate”(直接適用的法)。(參見:Phocion Francescakis.La Theéorie du Renvoi et les Conflits de Systeèm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e?[M].Paris:Sirey,1958.) 、荷蘭學者溫特(Louis Izaak de Winter)溫特在1964年《國際合同中的強制性規范》一文中提出:“對合同自由的限制不應由強制性規范構成——其限制性太強,也不應由公共秩序構成——其過于寬泛,而應由強制性規范中具有重要社會功能以至于在國際合同中不能忽略的那類規范構成。”(參見:T. C. Hartley.Mandatory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The Common Law Approach[J].Recueil Des Cours,1997,(266):357.) 等對強制性規范存在的現象進行了深入研究,不僅對立法和實踐荷蘭最高法院在1966年Alnati案中便直接援用了溫特的觀點。Alnati案是第一個明確提及第三國強制性規范可以直接適用的案件,在第三國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問題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引發了國際私法中關于強制性規范理論長達幾十年的討論。直到此時,曾被薩維尼認為是一種異常現象的強制性規范直接適用才變成沖突法制度中的固有部分[1]153。
(二)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的概念:實同名異的不同表述
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現象早已存在,學者們提出的各類理論觀點只是對既存現象的描述和探索。在現象描述過程中,對此類規范進行命名時出現過多種概念,包括但不限于:強制性規范(mandatory rules)、國際強制性規范(international mandatory rules)、警察法(lois de police)、直接適用的法(loi d’application immédiate)、必須適用的法(lois d’application necessaire)、優先條款(overriding statutes)、自我限定規范(self-limiting rules)、帶適用范圍的規范(spatially conditioned rules)、干預規范(Eingriffsnormen)[5],有學者甚至總結出多達15種概念[6]。在這些概念中,“警察法”是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引入強制性規范理論時最早采用的概念李浩培教授在1984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中編寫了“警察法”詞條。(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委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332-333.) ,后來為學者廣泛使用的卻是“直接適用的法”[7],但《法律適用法》最終采用了“強制性規定”的提法。
不同概念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國際私法中此類特殊規范進行描述,那么,哪種概念更能勾勒出這類規范的輪廓呢?第一,“直接適用的法”“loi d’application immediate”由柯澤東教授介紹入我國臺灣地區時,被譯為“即刻適用的法”,故臺灣學者多沿用此名稱。(參見:柯澤東.從國際私法方法探討契約準據法發展新趨勢——并略評兩岸現行法[J].臺大法學論叢,1993,23(1):292-297.) 是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廣泛使用的名稱,強調此類規范的適用機制。但以“直接適用的法”命名那些需要直接適用的法律規范,未免有循環論證之嫌。第二,雖然“直接適用的法”由弗朗西斯卡基斯首創,但他隨后在對該問題的闡釋中卻傾向于采用“警察法”的概念。“police”一詞源于希臘語中的“politeia”,指國家的秩序,因此,弗朗西斯卡基斯將“警察法”定義為保護一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而必須適用的那些規范[8]。與“直接適用的法”相比,“警察法”更強調此類規范的內容而非適用方式。“警察法”雖為1980年《歐洲共同體關于合同債務的法律適用公約》(以下簡稱《羅馬公約》)和2008年《關于合同之債法律適用的第593/2008號條例》(以下簡稱《羅馬條例Ⅰ》)的法文版本采納,但這一概念也存在缺陷。在現代福利國家,從廣義上講,所有的法律規范都是為了保障經濟或社會利益,“警察法”和一般法律規范之間的差別并不在于其保護利益的特殊內容,而在于其所保護利益的重要程度上。“警察法”的概念顯然不應該只反映質的差異,而忽略量的問題,因此,只能將“警察法”所保護的社會利益量的衡量問題留給對各法律條款進行具體分析[9]。第三,多數德國學者和《羅馬條例Ⅰ》的德文版使用的是“Eingriffsnormen”(干預規范),這是從強制性規范適用效果的角度形成的概念。但有學者指出,“干預法是指國家通過特別法令變更原本的私法規則,通常是公法;強制性規范可能經常但并不必然具有這種特殊的干預性質,有些不具有干涉性的實體法規范也可以直接適用,例如一些社會法。” [1]154在強制性規范理論之下,上述概念都是對同質規范在不同角度的描述,因此并無區分之必要。但從性質角度進行歸納的“強制性規范”更能反映這類規范最根本的特質——強制作用于落入其適用范圍內的所有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
我國《法律適用法》第4條最后采用“強制性規定”這一源于英語的名稱,可能基于如下考量:一方面是來自域外的影響,自《羅馬公約》第7條采用“mandatory rules”之后,“強制性規范”的名稱在多國立法中得到采用,其中就包括作為20世紀國際私法立法標桿的1987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8條、第19條使用的“強制性規定”(dispositions impératives)。另外,諸如2004年《比利時國際私法》第20條雖使用“特別適用規范”(Règles spéciales d’applicabilité)等其他名稱,但英文譯本仍采“強制性規范”。至少在該理論的英文文獻中,“強制性規范”已得到全面采用。另一方面是來自于本土傳統的影響,在《法律適用法》以前,我國國際私法立法中并未體現強制性規范理論。但根據《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的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該條雖為法律規避條款,但在實踐中曾被最高人民法院援用作為直接適用國內強制性規范的理由[10],因此第4條引入強制性規范的直接適用理論時基本延續了第194條中“我國強制性法律規范”的表述。
(三)國際私法中強制性規范的定位:國際強制性規范
我國《法律適用法》第4條對“強制性規定”的采用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如何區別民法中的強制性規范和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該條試圖從調整對象入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涉外民事關系的強制性規定”來作區分,并不能完全反映二者之間的聯系和差異。在國際私法中,這兩類規范是有差別的,前者被稱為國內強制性規范(domestic mandatory rules),后者被稱為國際強制性規范(international mandatory rules);也有學者分別稱之為合同法強制性規范(contracts-mandatory rules)和沖突法強制性規范(conflicts-mandatory rules)[11]。二者之間的差異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上述分類的標準并非調整對象不同,而是法律規范本身的強制性水平不同。“強制性規范”是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與“任意性規范”相對的概念,一般認為是指不能以當事人之意思加以變通適用的規范。國內強制性規范的強制性要求是廣義的、最基本的;國際強制性規范除了不能由當事人約定減損這一基本要求外,還對強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
其次,國內強制性規范和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差別在于其在法律適用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國內強制性規范服從于沖突規范的指引,作為準據法的組成部分得到適用;國際強制性規范要求不經沖突規范的指引或當事人的選擇,無論涉外案件準據法為何都必須適用。《羅馬公約》和《羅馬條例Ⅰ》都對這兩者予以區別對待,特別是《羅馬條例Ⅰ》的英語文本更加明確地在第3(3)條、第6(2)條和第8(1)條中將“國內強制性規范”稱為“不得通過協議減損的條款”(provisions that cannot be derogated from by agreement),而取代《羅馬公約》第7條“強制性規則”的第9條則以“優先適用的強制性條款”(overriding mandatory provisions)命名,以強調兩類強制性規范的差異[13]。荷蘭語、法語和德語版分別以“dwingende bepalingen”和“bepalingen van bijzonder dwingend recht”,“dispositions impératives”和“lois de police”,“zwingende Bestimmungen”和“Eingriffsnormen”來區別命名。 因此,《法律適用法》第4條體現的強制性規范直接適用理論實際上只針對國際強制性規范。
三、國際強制性規范的界定標準
正是基于強制性規范理論中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強制性規范的概念無法從語義學的角度去得到精準詮釋,只能從這類規范的內涵特征出發對其進行界定。薩維尼曾指出,在判斷哪類規范屬于多邊方法的例外時可考慮立法者的意圖,但他并不主張對其所言之絕對的強制規范進行精確界定,因為在他看來,這類特殊規范屬于例外且其重要性必將縮減[2]38。然而,隨著他的論斷被福利國家的出現所粉碎,更多學者指出,有必要對哪些規范能在多邊主義之外通過單邊方法得到適用進行界定,否則,將對傳統的沖突法理論造成沖擊[14]。但不可否認的是,提出一個能夠精確描述這類規范的標準,是十分困難的事[15]。
弗朗西斯卡基斯最初對“警察法”進行界定時,注重該類法律規范在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利益保護中的特殊地位。后來有學者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辨識此類規范的方法,認為國際強制性規范必須具備兩個要素:“其一,法律規范蘊含的政策被認為對社會至關重要;其二,在這些規范涵蓋的范圍內,不適用這些規范對其背后政策的推進將構成障礙。”[5]666這兩個要素分別構成了國際強制性規范界定中的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
(一)國際強制性規范界定的客觀標準
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基本特征是可以排除雙邊沖突規范的指引和當事人的選擇而得到直接適用,這要求屬于該規范調整范圍內的事項只能適用該規范,因而必然對待決事項適用立法國制定的強制性規范,從法院地國角度看,這屬于典型的只指向本國法的單邊沖突規范。單邊沖突規范是國際強制性規范得以強制適用的法律依據,其在國際強制性規范中的存在方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關于明示的方式,例如,“住所在蘇格蘭的人只有在年滿16歲才能結婚”實際上包含了一條實體規范——“年滿16歲才能結婚”和一條單邊沖突規范——“所有住所在英格蘭的人,其結婚年齡適用該規定”。另一種國際強制性規范沒有明確包含空間聯系因素,但也內置了單邊沖突規范,例如,一條強制性規范規定“未經許可從本國出口鐵礦石的合同是無效的”,這其中暗含著“從國內向國外出口鐵礦石的合同需要遵守本國法”這樣一條單邊沖突規范。因此,從客觀上認定強制性規范具有置沖突規范指引的準據法和當事人的法律選擇于不顧而都必須適用的性質,便屬于國際強制性規范。
國際強制性規范和單邊沖突規范在界定法院地法適用范圍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法律選擇程序的功能便是劃定法院地法的適用范圍,而國際強制性規范本身內置的空間適用范圍亦在追求同樣的功能。這兩類規范對空間適用范圍的界定從根本上說都是由國家對本國法律適用的需求決定的。兩者之間的共性及聯系是導致我國有學者將《合同法》第126條第2款我國《合同法》第126條第2款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這一典型的單邊沖突規范誤認作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原因[16]。
在這一背景下,有必要強調單邊沖突規范和國際強制性規范之間的顯著差異。首先,從形式上看,單邊沖突規范的結構與雙邊沖突規范一致,通過給法律范疇設定連結點的方式來指引法院地法雖然我國主流觀點認為單邊沖突規范有時也可以用來規定只適用外國法,但在國際上更為普遍的觀點卻是:單邊沖突規范為特定法律問題指定法院地法,并未包括我國學者所提只指定外國法的情況。(參見:Frank Vischer.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Recueil Des Cours,1992,(232):36.) 的適用,僅解決法律選擇問題卻不管法院地實體法的規定;國際強制性規范則必須包含實體內容,因為它的適用并非像單邊沖突規范那樣由其調整的法律關系導致,而是僅取決于它本身的實體內容[1]156。故前文所舉我國兩則案例中被誤認作國際強制性規范的《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第146條第2款在包含實體內容方面不符合國際強制性規范的要求。其次,從適用對象看,單邊沖突規范指引的準據法被用來調整某類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例如,合同、結婚、時效等法律范疇中包含的一系列問題;國際強制性規范只適用于涉外法律關系中的一個具體問題,例如,涉外擔保合同法律關系中擔保合同的效力問題。最后,從本質上看,沖突規范只進行立法管轄權的選擇,而國際強制性規范不僅只作管轄權的選擇,還包含規則選擇[5]679。這也是強制性規范理論與美國沖突法革命中出現的以規則選擇為根本出發點的各種理論的區別所在,后者片面強調規則選擇而忽略立法管轄權的選擇。
(二)國際強制性規范界定的主觀標準
以單邊沖突規范為標志的空間適用范圍只是國際強制性規范的表征,國際強制性規范之所以成為多邊選法體系的例外,是因為這些規范本身追求的目的和利益。因此,有學者提出:“判斷警察法是否適用于特定案件,顯然是一個法條解釋的過程,這有賴于考慮相互競爭的法律規范中蘊含的目的和政策。”[17]從主觀方面衡量法律規范本身的目的和政策從而辨識法律規范的性質,是國際強制性規范界定中無可爭議的標準。爭論的焦點在于,規定主觀標準時是否把國際強制性規范的目的限制在維護公共利益范圍內,對此,我國學者持肯定觀點,認為關涉重大公益是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必要條件[18]。這種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0條給出的強制性規范的定義中得到了體現。但實際上,對于是否將公共利益作為國際強制性規范界定的必備標準,在國際上并未形成統一意見。德國最高法院和法國最高法院還因為對公益要素的認識不同而產生過截然相反的認定。德國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一個案件中認為,要想適用當時的《民法施行法》第34條該條是將《羅馬公約》第7(2)條轉化為德國國內法的條文,現已被廢除。 ,該規范必須至少是推動了政府利益,因此拒絕認定《消費者信用法》中的條款具有優先適用的強制效力,因為該條款之主要目的在于保護消費者,所涉德國公共利益僅僅只是附帶的。法國最高法院在1999年的一個案件中就已經認定其《消費者信用法》中的某些條款具有優先適用的強制效力,法國最高法院并不反對優先性強制規范為消費者、勞動者等自然人的私人利益提供保護[8]97。
盡管如此,《羅馬條例Ⅰ》第9(1)條在界定優先性強制規范時,還是在主觀標準中引入了公共利益要求:“優先適用的強制性條款是指,被一國認為對維護該國的公共利益,尤其是對維護其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利益至關重要而必須遵守的強制性條款,不論根據本條例適用于合同的是何種法律,它們都必須予以適用。”人們普遍認為,該定義中公益因素的要求來源于歐洲法院Arblade案。Joined Cases C-369/96 and C-376/96, Arblade and Leloup, [1999] ECR I-8453 (ECJ). 在該案中,兩家法國的建筑公司派遣一批員工去比利時工作時,違反了比利時法中的支付最低工資、繳納社會保險和留存記錄的要求,在比利時,這種行為被認為是刑事犯罪。比利時社會法檢查團在于伊(Huy)輕罪法庭指控這兩家公司違反了比利時勞動法的相關規定,雖然這些規定適用于所有在比利時的公司,但確實限制了服務的自由流通,與《歐共體條約》存在沖突。于伊輕罪法庭向歐洲法院請求解釋歐共體法能否否決成員國法中要求派遣員工去其領域內提供服務的另一成員國企業遵守該國國內法中關于記錄和保留員工資料、達到最低工資標準等為了保護勞動者、防止勞動欺詐的規定,歐洲法院在判決中將比利時相關勞動法的適用認定為具有優先效力的公共利益需求,在初步審查意見中指出:“關于根據比利時法將爭議條款定性為公共政策立法的問題,公共政策立法的概念是適用于國內法律規范的,這些規范是指其遵守被認為對保護成員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秩序至關重要,在成員國領域內的所有人和所有法律關系都必須遵守的那些規范。”Joined Cases C-369/96 and C-376/96, Arblade and Leloup, [1999] ECR I-8453 (ECJ), para. 30. 這其中對“公共政策立法”的認定標準為《羅馬條例Ⅰ》借鑒用來界定國際強制性規范的主觀標準。
在界定國際強制性規范的主觀標準中引入公益因素,是為了應對公私法界限模糊給傳統上屬于私法領域的法律適用帶來的挑戰,但也導致一系列問題。第一,在法學領域,公共利益至今仍無明確的、權威的解釋,也鮮有國家在法律中明確其概念[19]。實際上,所有的公共利益都是建立在私人利益之上的,可以對足夠多的個人產生影響的私人利益就可以被認為是公共利益。例如,禁止未經許可的麻醉藥品買賣的法律規范是為了保護個人免受此類藥品濫用導致的身心傷害,但這個規則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為了防范由于麻醉藥品泛濫而導致犯罪率上升和醫療負擔增加。再如,控制租金的法律顯然是為了平衡房東和承租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以保護承租人,然而,此類法律也有提供可承受范圍內的住房和防止社會分化的社會目的。(參見:Michael Hellner.Third Country Overriding Mandatory Rules in the Rome I Regulation: Old Wine in New Bottles[J].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009,5(4):459.) 第二,強制性規范理論和保護性沖突規范之間的關系難以辨識。保護消費者、勞動者等弱者權益的保護性沖突規范主要是為了促進私人利益,如果認為維護公共利益是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必備要件,那么,這些保護性沖突規范指向的法律顯然不能適用強制性規范理論。如此一來,那些尚未設置保護性沖突規范的弱者無法得到強制性規范理論的保護。例如,2005年《羅馬條例Ⅰ》建議草案的第7條COM (2005) 650 final. 曾為代理人設置保護性沖突規范,但在最后文本中被刪除,如果強制性規范理論不適用于私人利益的保護,那么在合同關系中被認為弱勢的代理人之利益將無法得到特別保護[8]96。第三,有些國家的立法已明確規定強制性規范理論適用于私人利益的保護。例如,1987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9條在考慮外國法中強制性規范的適用時,規定“如瑞士法律觀念和一方當事人的重大顯著利益要求考慮外國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就可考慮適用之。綜上所述,在國際強制性規范的主觀認定標準中可以考慮公益要素,但將國際強制性規范限制在僅保護公共利益的范圍內,卻不能自圓其說。因此,在主觀標準中,只考慮對維護立法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等秩序至關重要的因素,已屬足夠。
四、域外立法對國際強制性規范的界定方法
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理論在成文立法中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海牙代理法律適用公約》第16條。其后,1980年《羅馬公約》第7條、1984年《海牙信托法律適用及其承認公約》第16條、1994年《國際合同法律適用的美洲公約》第11條,以及瑞士、亞美尼亞、委內瑞拉、吉爾吉斯共和國、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俄羅斯、立陶宛、摩爾多瓦、烏克蘭、馬其頓、土耳其等國國內國際私法立法中都規定了這一理論。但早期規定強制性規范理論的立法都未定義何為強制性規范,而是將強制性規范的認定留給法院在個案中加以解決。福利國家的出現帶來越來越多半公法性質的法律規范,為了準確適用強制性規范理論,立法者希望通過定義的方法來規范國際強制性規范的認定。
結合上述兩種標準在現有域外立法中的運用,可將國際強制性規范的界定分為兩種立法方法:一種方法僅采客觀標準,認為國際強制性規范即是無論沖突規范指引的準據法為何都必須適用的規范,如《羅馬公約》中的“只要是根據該國的法律,無論合同適用什么法律,這些強制性規則都必須予以適用時,得予以適用”;再如1998年《吉爾吉斯共和國民法典》第1174(2)條:“根據本章規定適用一國法律時,法院可適用與法律關系有密切聯系的另一國的強制性規范,只要依該另一國法律規定,此種強制性規范無需考慮準據法而直接調整該相應法律關系。”另一種方法兼采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最為典型的是前文所提之《羅馬條例Ⅰ》第9(1)條中的定義,這種標準既從主觀上要求強制性規范對維護該國某些利益至關重要,又從客觀上要求其具有不顧沖突規范指引而強制適用的效果。
這兩種定義方法在實踐中都有國家采用,但于立法而言,僅采客觀標準的定義更為簡練、精準。原因如下:第一,在后一種定義方法中,主觀標準的認定也需借助于客觀標準。如何判斷一國法律中的規定達到對該國某些方面利益保護至關重要的要求,還是要看該國的相關規定是否在客觀上具有排除沖突規范直接適用的效果,這樣就在客觀標準之外增加了同樣需要借助客觀標準才能認定的主觀標準,純屬多此一舉。第二,主觀標準的利益要求難以準確概括。這種利益要求無論如何表達,例如,“對維護該國的公共利益至關重要”(《羅馬條例Ⅰ》第9(1)條),還是“對保障民事法律主體的權利和利益特別重要”(2002年《摩爾多瓦共和國民法典》第1582(1)條),都無法涵蓋國際強制性規范所保護的利益范疇。不管主觀標準對國際強制性規范立法利益的要求是公共利益方面的還是私人利益方面的,都顯得片面和狹隘。第三,客觀標準已能夠反映國際強制性規范最重要的特質——含有單邊沖突規范。單邊沖突規范主要用來規定只適用內國法的各種情況,未指明在不屬于該單邊沖突規范規定的情況下應如何選擇法律。國際強制性規范旨在涉外糾紛中保障國內重要政策、利益的實現,如果這種利益可以通過當事人的法律選擇或經由沖突規范的指引加以排除,則不符合該類規范的立法目的,因此,國際強制性規范通過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包含了單邊沖突規范以保障其規定強制適用于相關涉外案件[20]。
五、我國立法對國際強制性規范界定的缺陷及完善
我國《法律適用法》未界定第4條中“強制性規定”的遺憾在201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中得到了彌補,其第10條以兜底列舉的方式規定,《法律適用法》第4條中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公共利益、當事人不能通過約定排除適用、無需通過沖突規范指引而直接適用于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這一界定顯然深受《羅馬條例Ⅰ》第9(1)條的影響,使用了兼采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的定義方法,糾正了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錯誤認識,使強制性規范理論這一亮點能在我國涉外選法體系中落到實處。但綜合前文,我國的定義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使用“強制性規定”的概念不能準確定位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在我國,“強制性規定”不論是在法學理論中還是實在法中都是早已存在的概念,《法律適用法》第4條和《解釋(一)》第10條在國際私法中再度使用這一概念,在界定上易與該概念現有的含義發生混淆,導致國內強制性規范和國際強制性規范之間的區分不明顯。
第二,在客觀標準中忽略了對我國沖突規范指引準據法的排除。實際上,國際強制性規范作為多邊選法體系的例外,不僅被用來排除當事人的選擇,同樣可以被用來排除沖突規范的指引。國內強制性規范和國際強制性規范的區別在于:前者用于對抗當事人意思自治,而后者用于替代準據法,無論準據法是由當事人選擇的,還是經由法院地沖突規范確定的,都需要排除在外[12]1。《解釋(一)》規定的“無需通過沖突規范指引適用”實則等同于“直接適用”,并未將對沖突規范指引準據法的排除包含在客觀標準中。
第三,“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公共利益”作為主觀標準過于寬泛。如前所述,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本非涇渭分明,很難說有一條完全不“涉及”任何社會公共利益的法律規范。即使傳統上屬于純粹私法領域的合同法律規范也可以被認為涉及社會經濟利益、社會誠信體系等公共利益。所以,僅以涉及而不論所涉公益的重要程度作為主觀標準,無法準確體現國際強制性規范在目的和政策等主觀方面的要求。
第四,僅定義我國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無法構建強制性規范理論的完整體系。一個完整的強制性規范理論體系包括法院地國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外國準據法所屬國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和第三國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外國準據法所屬國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原因之一,是多邊沖突規范對外國法的指引,所以對強制性規范理論進行立法時,一般只對法院地國強制性規范的直接適用和第三國強制性規范的授權適用[21]進行規定,且第三國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在國際國內立法中已不鮮見。在此背景下,《解釋(一)》在界定強制性規范時,僅局限于《法律適用法》第4條提及的我國強制性規范,未能從普遍主義立場出發進行定義,從立法技術上講,未給第三國強制性規范在我國的適用留下任何空間。
第五,采用不完全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五種涉及公共利益的情況,其意義不大。其一,從理論上看,國際強制性規范和公共秩序保留原則并列作為多邊選法體系的例外,其在適用上也和公共秩序保留原則一樣,留給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正如立法不會去列舉哪些社會公共利益屬于需要保留的公共秩序一樣,也不應該具體規定國際強制性規范涉及哪些公共利益,而應交由法院在個案中具體認定。其二,從語言表述上看,“社會公共利益”作為一個高度抽象概括的概念,出現在我國現行法律文本中時,通常有抽象表述和具體列舉兩種表達方式,立法采取何種表達方式取決于規范目的。對于作為立法宗旨的公共利益,一般采取抽象表述方式,但對于作為公權力行使依據的公共利益,則采取更為具體化的列舉表達方式[22]。《解釋(一)》第10條使用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與前述兩者不同,其中的“社會公共利益”主要是為了界定權利界限,這個目的定位反而與限制意思自治原則的《合同法》第52條類似。因此,在表述上也應該采用《合同法》第52條的表述方式,在抽象表述的基礎上,交由司法實踐去對社會公共利益加以具體化,而不應采用立法列舉的方式加以具體化。
第六,將“涉及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強制性規定納入其中,使《法律適用法》第4條和第43條之間的適用關系復雜化。假設某外國A國的一勞動者甲來我國境內乙公司工作,雙方在勞動合同中約定適用A國法,后甲遭乙公司無故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并拒付經濟補償,已知A國法中未有經濟補償之規定,在此種情況下,固然應適用我國《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給予補償。但是,我國法律適用的依據應是第43條規定的“勞動合同適用勞動者工作地法律”,還是第4條強制性規范的直接適用理論呢?對于保護性沖突規范和強制性規范理論之間的關系,本已存在四種觀點:其一,德國理論認為,這兩者之間相互獨立,以公共利益為保護對象的強制性規范和以弱者私人利益為保護對象的保護性沖突規范之間沒有交集;其二,以Giuliano-Lagarde報告[23]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強制性規范中也包含弱者保護的強制性法律規范;其三,為弱方當事人提供更高保護標準的條款具有優先效力,只有當國際強制性規范提供的保護水平高于消費者慣常居所地或勞動者工作地的保護標準時,才能被適用;其四,折衷的觀點認為,保護性沖突規范的適用優先于強制性規范[8]96。《解釋(一)》的定義將“涉及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強制性規定明確納入國際私法強制性規范的范疇,使之與第43條之間的適用關系更加復雜化。筆者認為,從我國國際私法的多邊立場考量,在實踐中應該優先適用第43條,因為保護性沖突規范屬于多邊選法規則的一種,而強制性規范作為其例外,只在缺乏相關保護性沖突規范的條件下才應得到適用。
綜上所述,可采取更加準確、簡潔的語言將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界定如下:“國際強制性規范,系指無論沖突規范指引的準據法為何都必須適用的實體法規范。”當前在適用《解釋(一)》中的定義時應注意如下問題:首先,綜合運用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去認定我國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以空間適用范圍中是否含有或暗含單邊沖突規范來判斷強制性規范是否具有排除沖突規范中主客觀連結點指引的效力,從而衡量所涉公共利益的重要程度和受保護需求是否達到了強制性規范直接適用的要求。其次,雖然我國定義采取不完全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五種可能的強制性規范,但在實踐中,不應就某個領域或某部法律籠統地進行國際強制性規范的識別,識別對象只能是個案中待適用的具體法律規定。最后,如果我國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可以根據《法律適用法》第42條(為涉外消費者合同規定的保護性沖突規范)和第43條(為涉外勞動合同規定的保護性沖突規范)而得到適用,便不再適用強制性規范。ML
參考文獻:
[1] Frank Vischer.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Recueil Des Cours,1992,(232):155.
[2]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Ⅷ[M].Berlin:Veit & Comp,1849:32-38.
[3] Michal Wojewoda.Mandatory Ru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2000,7(2):185.
[4] F. A. Mann.Contracts: Effect of Mandatory Rules[G]//K. Lipstein.Harmoniz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EEC.London: Chameleon Press Limited,1978:31-50.
[5] Thomas G. Guedj.The Theory of the Lois de Police, A Functional Trend in Continental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Modern American Theorie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1,39(4):664.
[6] 吳光平.重新檢視即刻適用法——源起、發展,以及從實體法到方法的轉變歷程[J].玄奘法律學報,2004,(2):156-159.
[7] 徐冬根.論“直接適用的法”與沖突規范的關系[J].中國法學,1990,(3):84-92.
[8] Jan-Jaap Kuipers.EU Law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relationship In Contractual Obligations[M].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2:63.
[9] Yvon Loussouarn,Pierre Bourel.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M].Paris:Dalloz,1996:124.
[1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40-42.
[11] Peter Kaye.The New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trac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EEC’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Conven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under the Contracts (Applicable Law) Act 1990[M].Aldershot:Dartmouth, 1993:72-73.
[12] Kerstin Ann-Susann Schfer.Application of Mandatory Rules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tracts[M].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2010:31.
[13] 謝寶朝.論《羅馬條例I》對歐盟合同沖突法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0,12(3):99.
[14] Friedrich K. Juenger.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Recueil des Cours,1983,(193):201-202.
[15] Friedrich K. Juenger.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M].Boston:Martinus Nijhof,1993:81.
[16] 高曉力.國際私法上公共政策的運用[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87.
[17] Bernard Audit.A Continental Lawyer Looks at Contemporary American Choice-of-Law Principle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79,27(4):603.
[18] 肖永平,龍威狄.論中國國際私法中的強制性規范[J].中國社會科學,2012,(10):110.
[19] 王景斌.論公共利益之界定——一個公法學基石性范疇的法理學分析[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1):129-137.
[20] T. C. Hartley.Mandatory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The Common Law Approach[J].Recueil Des Cours,1997,(266):346-348.
[21] Andrew Dickinson.Third-Country Mandatory Rules i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So Long, Farewell, Auf Wiedersehen, Adieu?[J].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007,3(1):53-88.
[22] 唐忠民,溫澤彬.關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J].現代法學,2005,(6):95-102.
[23] Mario Giuliano,Paul Lagarde.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J].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80,C282:1-50.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ndatory Ru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mments on Interpretation I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Act
BU Lu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Article 4 of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Act expressly provid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mandatory rules in Chinese law shall be directly applied. As an exception to multilateral choiceoflaw system, the theory of mandatory rules encounters a core problem on how to identify the international mandatory rules that shall be applied without a choice of law rule indicating its applicability. Either subjective criteria or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riteria can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legislation, and both criteria have been put forward. Article 10 of Interpretation I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Act contains the definition of mandatory rules of Chinese law. It helps the operation of relevant rules, but there are open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andatory rules; objective criteria; subjective criteria; defect of legislation
本文責任編輯:邵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