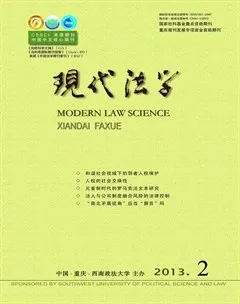刑法司法公信力:從基礎到進退
摘要: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眾認同之間的關系相對應,刑法司法公信力與刑法司法公眾認同也互為表里,且后者構成了前者的基礎。刑法司法公信力與刑法司法公眾認同之間的關系有著心理學基礎和規(guī)范有效性基礎,并蘊藏著有效控制犯罪以達致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最終法治效果。如果想確保并提升刑法司法公信力,則必須致力于刑法司法公眾認同,包括刑法解釋公眾認同、司法定罪公眾認同和司法量刑公眾認同。刑法司法解釋公眾認同、司法定罪公眾認同和司法量刑公眾認同先后構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環(huán)節(jié)性基礎,從而確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環(huán)節(jié)性實現(xiàn)。刑法司法公信力以價值衡量為進,以法治底線為退。
關鍵詞:刑法司法公信力;刑法司法公眾認同;刑法解釋;價值衡量;法治底線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2.14
一、刑法司法公信力問題的提出
有人指出:“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案件審理的結果不僅直接決定了各方當事人的切身利益,還關系到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法治意識的認同,甚至直接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形象。而一個國家制定法律,設立包括審判機關在內(nèi)的各種國家機構,正是為了維護正常的國家運行秩序,促進經(jīng)濟的發(fā)展,維護社會的安全和穩(wěn)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堅持依法辦案的同時,必須綜合考慮各種社會因素,妥善解決矛盾糾紛,努力實現(xiàn)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社會效果在所有的國家都是司法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對所有司法機關來說都是必須高度重視的一個要素。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轉型國家,在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司法的公信力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diào)社會效果。”其實,所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只存在于動態(tài)的司法而非靜態(tài)的立法之中,而所謂司法公信力與動態(tài)的司法所能產(chǎn)生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是直接相關的。但是,我們以往過多關注的是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而輕視了司法公信力問題。司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問題應該通過司法公信力問題予以提升或拔高,因為司法公信力有著更加深遠的法治意義。
在司法公信力問題中,刑法司法公信力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因為刑法畢竟是整個法制體系中的“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刑法司法公信力問題的突出性將體現(xiàn)在刑法公信力的意義上。概言之,刑法司法公信力直接營造著公眾的刑法信仰,據(jù)此刑事法治才能獲得一種心理資源,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才有法治依托。“許霆取款案”、“鄧玉嬌防衛(wèi)案”、“張明寶醉駕案”等典型案件的裁判在社會輿情中大起大落并最終“塵埃落定”,充分說明刑法司法公信力對刑法司法的直接影響,同時也說明刑法司法公信力是刑法司法的一種積極驗證。我們必須關注刑法司法公信力問題。
二、刑法司法公信力的基礎:刑法司法公眾認同
(一)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與刑法司法公信力的關系
社會效果是司法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轉型國家更應該強調(diào)社會效果,而“社會效果是指通過法官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和裁判,獲取的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對其的評價和認可程度。社會效果的實質在于司法的結果要滿足實質正義,滿足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長遠發(fā)展利益,獲得公眾的情感認可和尊重。”司法的社會效果里面包含著司法公眾認同。在所謂“司法公信力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diào)社會效果”,點明了司法公信力與司法公眾認同之間的關系。在筆者看來,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為:司法公信力與司法公眾認同互為表里,即前者為表后者為里。正因如此,司法公眾認同構成了司法公信力的基礎。
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與刑法司法公信力何以能夠形成前述關系?在筆者看來,在認知心理學的層面上,刑法司法公眾認同屬于主觀心理狀態(tài),而刑法司法公信力屬于外在客觀效果。那么,按照主觀反作用于客觀的辯證法原理,則刑法司法公眾認同便構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心理學基礎;而在規(guī)范有效性的層面上,只有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而非刑罰強制才真正賦予刑法立法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規(guī)范有效性,從而真正賦予刑法司法公信力,同時也是刑法本身的公信力。因此,刑法司法公眾認同便構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規(guī)范有效性基礎。
國外有學者說:“如果司法體系判處公眾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有罪或判處公眾認為嚴重侵犯道德而需要定罪的行為無罪,刑法的道德信譽就處于危險之中。”“刑法效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刑法在市民中所贏得的道德可信性的程度……刑法的道德可信性對于有效的犯罪控制是關鍵的,同時其道德可信性也得到了提高。”具言之,“刑法效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刑法在其所規(guī)范的人們心中的道德信譽。這樣,如果現(xiàn)實責任的分配被認為是‘實現(xiàn)正義’,如果分配的責任與刑罰的方式與社會正義直覺相一致,那么刑法的道德信譽對于有效控制犯罪是至關重要的,并且可以得到提升。相反,偏離社會對公正的刑罰的看法,責任的分配就破壞了該制度的道德信譽及其犯罪控制效力。”由此可見,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意義最終在于有效的犯罪控制,從而達致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而刑法司法公信力的前述意義是依賴于社會的正義直覺的。刑法司法公眾認同就是社會對刑法司法的正義直覺的一種標示,若沒有刑法司法公眾認同,難道還有刑法司法公信力可言嗎?若沒有公信力,則刑法司法還能收獲有效地控制犯罪以達致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最終效果嗎?因此,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最終意義是不能脫離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與刑法司法公信力之間的關系的。可以這么說,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與刑法司法公信力之間的關系是一道“門戶”,里面所關著的是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最終意義,而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最終意義又映現(xiàn)著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與刑法司法公信力的關系。
(二)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環(huán)節(jié)性保障
刑法司法是一個環(huán)節(jié)性的過程,刑法司法公信力應通過環(huán)節(jié)性的刑法司法公眾認同而得到保障。
1.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現(xiàn)今,刑法解釋公眾認同問題已經(jīng)日益引起注意和重視。有人指出:“刑法解釋的首要問題,就是當按照不同的解釋理論和解釋方法對同一對象的解釋產(chǎn)生分歧時,我們應當依照什么樣的價值準則來決定取舍、做出選擇。”我們必須接受的是,“在當前我國,這種決定取舍和做出選擇的價值準則就是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更準確地說是刑事司法活動中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問題。”刑法解釋公眾認同有著怎樣的意義呢?“如果說刑法的公眾認同表明社會對刑法的接受程度,那么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則表明社會對司法活動特別是對司法判決的接受和認可程度。而社會公眾對由刑法解釋導出的司法判決的認可和接受,是樹立公眾對法律的信任,培養(yǎng)公眾的司法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升司法公信力,從而強化公眾的法規(guī)范意識和進一步發(fā)揮法律的行為引導功能所必須經(jīng)歷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這一點對處于轉型時期各種復雜而尖銳的社會矛盾頻發(fā)的我國尤為重要,因而公眾認同對于刑法解釋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可見,公眾認同與刑法解釋密切關聯(lián),并在這種關聯(lián)中顯示出公眾認同的重要意義。
那么,刑法解釋如何獲得所謂的公眾認同呢?“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個方面是指刑法解釋的常識化。……其強調(diào)的是刑法解釋的可理解性。第二個方面是指刑法解釋的合理性。……其強調(diào)的是刑法解釋的可接受性。”“所謂刑法的常識化解釋,實際上是指運用一般人具有的常識經(jīng)驗和通俗的生活語言,對刑法規(guī)范的內(nèi)容和應用范圍作出的感性描述和直觀說明,使人們在常識觀念基礎上理解、接受、應用和遵守刑罰法規(guī)的一種法律解釋方法。”其實,刑法解釋不僅應常識化,還應常理化和常情化。刑法的常識、常理、常情解釋等同甚或包含著所謂情理解釋。當常識、常理、常情解釋實質上就是可預測性解釋時,常識、常理、常情解釋便是公眾認同性解釋。
刑法解釋公眾認同是刑法司法公眾認同的極其重要的實現(xiàn)和體現(xiàn),因為它為定罪量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于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刑法解釋公眾認同是以常識、常理、常情為生活基礎或生活根基的。易言之,只有對刑法解釋賦予常識、常理、常情的內(nèi)容,即作出常識、常理、常情化的刑法解釋,刑法解釋才能獲得公眾認同。當刑法解釋具有了常識、常理、常情性,其結論便當然具有公眾的可接受性——公眾認同性,因為常識、常理、常情化的解釋自然符合公眾的預測可能性。那就是說,我們可將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由常識、常理、常情解釋深化為預測可能性解釋。只有可預測性解釋才能賦予刑法解釋以公眾認同,進而產(chǎn)生刑法解釋同時也是刑法司法公信力。
2.司法定罪公眾認同。司法定罪公眾認同包括罪過確定公眾認同和罪名確定公眾認同。
首先是罪過確定公眾認同。較早有人說:“所謂罪過,就是犯罪主體對他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和結果所抱的一種故意或過失的心理態(tài)度。”其后有人說:“犯罪的主觀要件,是指決定和影響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心理態(tài)度。這種心理態(tài)度,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是應該受到譴責的,在刑法理論上通常又把這種心理態(tài)度叫做罪過。”又有人說:“所謂罪過,是刑法所否定的行為人實施行為時對將造成的危害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還有人說:“犯罪的主觀要件,即罪過,是犯罪人在實施犯罪時所持的心理態(tài)度。”以上說法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罪過是犯罪人實施行為時的心理態(tài)度。由于罪過認定是司法者對犯罪人行為時的心理態(tài)度的考察和判斷,故罪過認定是否準確便取決于司法者擇用何種標準。如果司法者擇用行為人標準,則等于沒有標準,因為這將導致有無罪過以及何種形態(tài)的罪過由行為人即犯罪人說了算,于是罪過認定便不復存在;如果司法者擇用司法者自身的標準,則其對罪過的認定以及以之為基礎的判決便容易陷入偏見。那么,司法者惟一的選擇便是采用常識、常理、常情標準,因為司法者畢竟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公眾對行為人的罪過問題作出認定,進而作出責任裁判。既然司法者是代表公眾進行罪過認定并進行裁判,那他或她就必須考慮公眾所擁有的知識即常識、公眾所明曉的事理即常理和公眾所懷有的感情即常情。培根曾說:“人們喜歡帶著極端的偏見在不著邊際的自由中使自己得到滿足,這就是他們的思想本質。”那么,司法者自覺采用常識、常理、常情標準來作出有無罪過以及何種形態(tài)罪過的罪過認定便可避免判決的不著邊際,因為常識、常理、常情排斥著偏見特別是極端的偏見。司法者進行罪過認定擇用何種標準牽涉方法論問題,因為標準的采用意味著一定的立場或角度,故擇用常識、常理、常情標準進行罪過認定應該被肯定為解決罪過問題的正確方法。
故意和過失是罪過的兩種基本形態(tài),而無論是故意,還是過失,都是由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所構成,且故意與過失的相互區(qū)別以及故意與過失各自內(nèi)部的區(qū)別,即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qū)別、過于自信的過失與疏忽大意的過失的區(qū)別,也是先后靠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來說明的。就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關系來說,認識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存在前提,而意志因素則是在認識因素基礎上的發(fā)展。而如果單獨考察意志因素,則意志態(tài)度、意志選擇和意志努力“這幾項意志內(nèi)容的緊密結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意志心理活動過程。”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罪過中的認識因素,還是其意志因素,都離不開常識、常理、常情的說明:就罪過中的認識因素而言,常識本身就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性質和結果的認識的知識憑借,如毒殺犯罪的行為人對殺人行為的性質和結果的認識就是憑借毒藥能致死人命這一常識;就其意志因素而言,常理和常情又往往影響乃至左右著行為人對其所認識到的結果的態(tài)度的善惡與強弱,如“大義滅親”的行為人就是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常理和“為民除害”的常情之下去追求其親屬的死亡結果。那就是說,無論是罪過中的認識因素,還是其意志因素,都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常識、常理、常情正是它們的肥厚土壤,它們都要到常識、常理、常情那里得到說明,只不過常識、常理、常情所作出的說明有時是正面的,有時是反面的。顯然,由于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是罪過認定的本體問題,而常識、常理、常情又直接說明著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故擇用常識、常理、常情標準進行罪過認定又具有本體論根據(jù)。那就是說,擇用常識、常理、常情標準進行罪過認定是融方法論與本體論于一體,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方法寓于本體之中。
有人指出:“要使刑法贏得公民的內(nèi)心認同,繼而形成法律信仰,法律必須體現(xiàn)出對公民的人文關懷,使公民能夠信賴法律。但現(xiàn)行理論僅以心理事實認定罪過,不允許法官根據(jù)社會良心進行價值衡量,將會使刑法的施行過于僵化,缺乏人情倫理。”“信仰”、“信賴”都意味著公信力,罪過確定問題事關刑法司法公信力,而不同的罪過形式對應著不同的刑事責任,故罪過確定公眾認同將在定罪上首先證明刑法司法公信力。
再就是罪名確定公眾認同。這里,我們可先以在高速公路上發(fā)生的“碰瓷案”為例。“碰瓷案”所采用的主要作案方法是:由犯罪嫌疑人駕車在道路上尋找外省市進京的中、高檔小轎車并尾隨其后,當前車正常變更車道時,突然加速撞向前車側后方,造成前車變更車道時未讓所借車道內(nèi)行駛的車輛先行的假象。事故發(fā)生后,其他被告人輪流冒充駕駛人,待到達事故現(xiàn)場的交通民警作出前車負全部責任的認定后,以此要挾甚至采用威脅的方法,向被害人索要錢財。前幾年發(fā)生的在城市主干道及高速公路駕駛機動車“碰瓷”案件,基本上是以敲詐勒索罪或詐騙罪對行為人定罪處罰的,但北京法院開全國之先河,將在城市主干道上駕駛機動車“碰瓷案”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肯定,將“碰瓷案”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加符合當下的公眾認同,因為在“碰瓷案”場合,公眾認為交通安全比一般財物更為重要或更有價值,故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公眾而言具有預測可能性,故能夠獲得公眾認同。以罪名的確定來論述定罪的公眾認同問題,我們還有其他適例。如對劫持火車、電車行為的定罪問題。對此問題,有學者提出不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宜認定為破壞交通工具罪。如果立于預測可能性,則對此行為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符合公眾的預測可能性,至少對犯罪人是這樣的,因為“劫持”與“破壞”在“常識”上是無法進行一種鏈接或“通融”的,故認定為破壞交通工具罪難以獲得公眾認同。罪名是刑事責任的一頂“帽子”,故罪名確定公眾認同同樣將在定罪上說明刑法司法公信力。
3.司法量刑公眾認同。司法量刑公眾認同依賴量刑必定性、量刑及時性和量刑相當性,方可得以實現(xiàn)。
首先是量刑必定性。貝卡里亞曾說:“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因為,即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而“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受到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從刑罰必定性中,我們可以看到預測可能性與量刑的關聯(lián)。刑罰必定性在陳述著一種事實:有犯罪這個因,就必有刑罰這個果。罪刑關系是一種必然的因果關系,而罪刑關系這種因果關系是犯罪和刑罰這對法律現(xiàn)象之間的當然連接。正是由于刑罰必定性對罪刑關系的因果邏輯上的說明,故包括犯罪人在內(nèi)的公民就會在內(nèi)心不斷強化對犯罪結果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其刑法規(guī)范的禁忌意識也得到不斷強化,進而一般預防和個別預防的效果都得以產(chǎn)生。正是在此意義上,司法者在刑罰必定性的約束之下便不可在司法個案中隨意割斷罪刑關系之鏈,除非有法定依據(jù),有罪無刑之裁判當為禁絕。量刑必定性是刑罰必定性的直接實現(xiàn),而預測可能性則是其心理學的支撐與說明。在社會學領域,不可預測的事物,是難以得到認同的。那么,量刑必定性通過預測可能性便可獲得公眾認同。
再就是量刑及時性。刑罰及時性顯然是在刑罰必定性的基礎之上或前提之下,在時間的維度上對犯罪與刑罰之間邏輯關系予以真實反映,并且通過“及時性”盡量使得犯罪與刑罰之間的邏輯關系符合事物的本來面目與矛盾運動,從而使得刑罰必定性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和說明。因此,刑罰及時性可以看成是刑罰必定性的一種延伸。預測可能性與刑罰及時性也有關聯(lián)。具言之,刑罰越及時,則包括犯罪人在內(nèi)的公民對犯罪的后果就越能在內(nèi)心強化一種預測,從而同樣強化著刑法規(guī)范的禁忌意識,進而也在強化著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之效。貝卡里亞曾說:“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隔得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lián)系就越突出、越持續(xù),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罰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而“只有使犯罪和刑罰銜接緊湊,才能指望相關的刑罰概念使那些粗俗的頭腦從誘惑他們的、有利可圖的犯罪圖景中猛醒過來。推遲刑罰盡管也給人以懲罰犯罪的印象,然而,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懲罰,倒像是表演。”可見,刑罰及時性能夠通過縮短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間隔來強化人們對犯罪與刑罰之問的心理連接,從而達到抑制犯罪意念,強化禁忌意識,最終預防犯罪的效果。這就是貝卡里亞所說的“有益”。羅伯斯庇爾說:“拖延審理訴訟案件,等于不處理犯罪;處罰不堅決,就是鼓勵一切犯罪者。”羅伯斯庇爾顯然是從反面強調(diào)刑罰不及時對社會秩序所帶來的害處,因為“不處理犯罪”和“鼓勵一切犯罪者”顯然起著斷絕犯罪與刑罰的因果連接,從而弱化乃至消除人們規(guī)范禁忌意識的反而作用。從貝卡里亞和羅伯斯庇爾的前述論斷中,我們同時可以明顯看出,刑罰及時性通過預測可能性而在人們的心靈中強化著罪刑關系的因果性,而這將在心理學規(guī)律之中實現(xiàn)保障公民人權和預防犯罪的雙重正義,從而使量刑及時性也能夠獲得公眾認同。
刑罰及時性還直接關聯(lián)著刑罰的人道性。貝卡里亞曾說:“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犯人越富有想象力,越感到自己軟弱,就越感受到這種折磨。”因此,“訴訟本身應該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nèi)結束。”顯然,貝卡里亞所主張或強調(diào)的刑罰及時性有著濃烈的人道主義色彩。須知,最能給人帶來心理折磨的不是結果的現(xiàn)實化即結果的確定,而是結果的捉摸不定或不確定。而由此看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拖延的刑罰之所以會帶來犯罪人的痛苦,乃是因為拖延的刑罰不具有預測可能性。那就是說,預測可能性能夠從“內(nèi)里”說明著刑罰及時性的人道性,從而量刑及時性又通過刑罰的人道主義而獲得公眾認同。
最后是量刑相當性。量刑必定性直陳著犯罪與刑罰這對法律現(xiàn)象之間的因果連接,故其有助于培養(yǎng)人們對刑罰即犯罪后果的預測可能性。但是,量刑必定性所直陳的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因果連接未必就是適中的,而可能是罪大刑小或罪小刑大即罪刑不稱或罪刑失衡。顯然,量刑相當性就是要避免罪刑不稱或罪刑失衡,從而使得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因果連接達到適中狀態(tài),進而使得罪刑關系符合事物的應有本性或規(guī)律性。量刑相當性使得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因果關系能夠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中得到確證。正如貝卡里亞曾說:“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邊沁則說:“為預防一個犯罪,抑制動機的力量必須超過誘惑動機。作為一個恐懼物的刑罰必須超過作為誘惑物的罪行。一個不足的刑罰比嚴厲的刑罰更壞。因為一個不足的刑罰是一個應被徹底拋棄的惡,從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結果。對公眾如此,因為這樣的刑罰似乎意味著他們喜歡罪行;對罪犯如此,因為未使其變得更好。”相當?shù)男塘P之所以能夠成為“抑制動機的力量”,預測可能性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原初”的心理力量。可以這么說,量刑相當性是在“大”與“小”即事物規(guī)模上發(fā)揮著對公民預測可能性的“培養(yǎng)”作用。當然,用預測可能性來審視刑罰相當性,我們可以在刑罰必定性和及時性之外提出一個“刑罰充足性”概念。無論是量刑相當性,還是量刑充足性,都將與量刑必定性、量刑及時性一起而在“罪有應得”的預測可能性中獲得公眾認同。那么,值得我們憂慮的是,在我國當今的司法現(xiàn)實中,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犯罪的量刑存在著普遍的背離罪刑均衡原則的輕刑化、緩刑化乃至免于刑罰處罰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既背離了犯罪人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在降低他們的犯罪成本之中折損著特別預防即個別改造的效果,也背離了一般民眾包括潛在的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人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在背離量刑相當性即背離罪刑均衡之中折損著一般預防的效果,以至最終難以獲得公眾認同,這已為老百姓那句“法律袒護當官者”所印證。可見,量刑相當性也通過預測可能性而獲得公眾認同。
司法量刑的公眾認同是定罪的公眾認同的繼續(xù),司法量刑公信力是司法定罪公信力的繼續(xù)。
刑法司法解釋公眾認同、司法定罪公眾認同和司法量刑公眾認同,先后構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環(huán)節(jié)性基礎,確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環(huán)節(jié)性實現(xiàn)。
三、刑法司法公信力之進:價值衡量
(一)價值衡量的切入
價值衡量是針對所謂利益衡量而被提出來的。利益衡量是日本學者加藤一郎在批判概念法學時提出的,也稱法益衡量,主張法律解釋應當更自由和更有彈性,解釋時應考慮實際的利益,強調(diào)實質判斷。學者們盡管對利益衡量所下定義不同,但在其基本含義上則達成了如下一致:當法律所確認的不同利益發(fā)生矛盾,法官對它們進行衡量時應根據(jù)利益的輕重作出取舍。價值衡量與利益衡量相近而不相同,因為不同的利益往往會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念,而不同的價值觀念也往往代表著不同的利益,故兩者有密切的聯(lián)系。但有學者指出,利益衡量和價值衡量在司法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向度并受不同法律概念觀的支配。而有學者則進一步指出兩者的區(qū)別:一是兩者的存在領域不同。利益衡量主要適用于民事領域,而價值衡量在但凡存在裁判的領域都存在;二是兩者衡量的標準不同。利益衡量的標準是法律利益,而價值衡量的標準則是自由、人權等法律價值;三是能動的程度不同。利益衡量的標準具有明顯的客觀性,故法官的能動性總是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圍。而價值衡量的標準則較多帶有主觀性,故法官的能動性顯然大于利益衡量下的法官的能動性。利益衡量與價值衡量的區(qū)別說明著什么?說明著價值衡量在刑事領域有著較為廣闊的運用空間和較為突出的司法意義,而這又說明著價值衡量將帶給刑法司法以較強的能動性。有學者還將價值衡量的能動性予以這樣的突出:一是法律的價值是高度原則化、高度抽象化的規(guī)定,二是不同法律價值的位階關系尚難確定,三是價值衡量有時會突破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的約束。總之,法官的價值衡量充斥其主觀的創(chuàng)造性,使法官可以根據(jù)法律的精神和原理,結合案件的具體事實,作出正當性的判決,使司法能動地解決社會糾紛,維護公平正義。于是,價值衡量所能帶來的司法能動性便有著如下體現(xiàn):一是價值衡量是法官運用法律智慧解決糾紛的信念支撐;二是價值衡量是使司法實現(xiàn)正義的重要方法;三是價值衡量可能成為引導社會價值觀走向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由于價值衡量常常伴隨法官的價值偏見,故價值衡量應受到如下“界限”:一是價值衡量應當被嚴格限制在疑難案件中;二是價值衡量的標準應當是在社會上居于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三是價值衡量的結果不能違背憲法和基本法律原則。就價值衡量的重要性而言,有學者指出:“從價值衡量是SkrXnYXFmr9dYnn+n3wITw==對法律修正和補充的角度看,每一種法律方法其實都可能運用價值衡量的方法。因而,這一方法也被有些法學家稱為黃金方法。”而“事實上,價值衡量不僅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法律方法,而且也是司法能動的顯著表現(xiàn)。”
“黃金方法”形象地說明了價值衡量的重要性。那么,價值衡量是否對當下中國的刑法司法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影響?其影響又是怎樣的呢?對于“鹽城‘2·20’水污染案”,有人指出:“鹽城‘2·20’案除了考慮刑法條文,還考慮了與案件有關的各種因素及判決對未來可能造成的結果和影響,在有數(shù)種解釋結論可供選擇時,它選擇了對社會影響較為有利的那種解釋方法,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一般來說,有數(shù)種解釋結論可供選擇的情況通常出現(xiàn)在新型、復雜或疑難案件中,鹽城‘2·20’案案件的法官恰恰利用了案件在定性時的一些爭議,智慧地選擇今后對環(huán)境保護有利的解釋結論。”“鹽城‘2·20’案通過嚴懲責任人,對環(huán)境污染的社會問題適度能動地干預和調(diào)處,反映了污染所帶來的日益嚴重的壓力——經(jīng)濟發(fā)展不能以嚴重損害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為代價。法官不僅扮演了司法角色,還扮演了促進社會正義和民眾福祗的政治角色。”可以看出,論者就“鹽城‘2·20’水污染案”的司法能動性所進行的如上說理,實質是在集中強調(diào)主流價值問題。環(huán)境問題維系著當今人類社會的一種主流價值。如果本案以重大環(huán)境責任事故罪來定罪量刑,則與環(huán)境價值這種越來越被強烈渴求的主流價值顯得有所脫節(jié)或很大脫節(jié),而按投放危險物質罪來定罪量刑,則迎合或恰到好處地“撫慰”了這一主流價值。也就是說,是環(huán)境這一主流價值使得法院由重大環(huán)境責任事故罪“能動地”走向了投放危險物質罪。這個貌似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案件,在筆者看來,似乎真正地達成了一種具有實質合理性和正義性相融合的裁判結果,而這正是價值衡量所帶來的結果。有人指出;“一個優(yōu)秀的法官,不是埋首法律條文,選擇正確答案的‘法匠’,而應當能正確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預設的價值追求,并將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認識融于法律事實的認定、法律條文的解釋和法律適用的選擇之中,從而作出符合法的價值精神的公正裁判。”其實,漢朝盛行的“春秋決獄”可以被看成是價值衡量方法下的刑法司法的古代“雛形”。沒有價值衡量的刑法司法,將是僵硬的乃至“僵死”的刑法司法。
(二)價值衡量的返回
價值衡量能夠促成刑法司法的能動性,意味著價值衡量能夠祛除刑法司法的呆板性與僵硬性,從而祛除其不合理性與不公正性。刑法司法正是通過運用價值衡量使刑法規(guī)范獲得一種動態(tài)的生命力,從而使其即便是在社會轉型和風險多元化愈加深化的當下,也仍然能夠體現(xiàn)其作為“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的功效。在筆者看來,社會沖突與其說是利益沖突,不如最終說是價值沖突。法律調(diào)整的與其說是利益關系,不如最終說是價值關系。法律必須正視價值關系,而刑法更應該正視價值關系,刑法是“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意味著刑法最終是價值關系的“后盾”,而其所“保障”的最終也是價值關系。社會轉型和風險多元化愈加深化使得對價值關系有“后盾”和“保障”作用的刑法越發(fā)顯得使命重大,方向明確,價值衡量便是刑法特別是中國刑法當下“求生存,謀發(fā)展”之術。刑法特別是我國刑法當下的“求生存,謀發(fā)展”,應更多地體現(xiàn)在刑法司法的價值衡量上。
綜上,刑事司法若體現(xiàn)不出價值衡量,體現(xiàn)不m對主流價值的認可,則是沒有公信力可言的,因為所謂公信力實質上就是價值觀的一種說服力乃至威信力。
四、刑法司法公信力之退:法治底線
刑法司法應注重價值衡量并不意味著刑法司法可以“無所不為”乃至“為所欲為”,而是要堅守底線。堅守底線是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最起碼的保障。
(一)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憲政底線
有學者指出:“憲政語境下的國家刑事法律的邊界是:基本的人權是民主的刑事立法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這里道出了一個問題:刑法實踐包括刑法司法必須接受合憲性審查與裁決。那么,中外的情況怎么樣呢?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刑事法律的司法解釋,可以說是到了司法實踐須臾不可離開的程度。這與我們的司法體制有關,與法官對法律自身解釋的能力的欠缺有關,更與我們太過發(fā)達的司法解釋現(xiàn)狀相關。對司法權的憲政控制,一是司法解釋權不能僭越立法權,將本來屬于立法者的權力占為己有,……二是司法解釋不能違背憲政的基本精神與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用擴大解釋或類推解釋的方式使得諸如罪刑法定等原則徒有虛名或名存實亡,從而危及現(xiàn)代刑事法律的根基。”在刑法司法憲政底線的把握上,以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具體的司法適用的越界。如2000年12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guī)定,認定“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必須有“保護傘”才能構成。而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中有關“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構成并沒有“保護傘”之規(guī)定,即沒有“保護傘”同樣可構成第294條之犯罪,且該立法解釋也沒有時間效力的規(guī)定,這便導致了實踐中有的司法機構對相關案件的審理就對該解釋進行了溯及既往的適用;二是司法解釋的越界,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1年12月7日頒布的《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guī)定》第2條規(guī)定:“對于司法解釋實施前發(fā)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后尚未處理或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辦理。”這一解釋就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實質上,溯及既往的司法解釋也是背離罪刑法定原則的。我國過于頻繁的刑法司法解釋有侵犯人權之虞,從而有實質上的“違憲”之虞。
隨著社會轉型和風險多元化的愈加深化,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這一社會治理理念“激化”下的刑法司法更容易陷入一種侵犯人權的“違憲”之境。求“穩(wěn)定”沒錯,求“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也沒錯,但中國當下的刑法司法應在保障人權和“合憲”之中求“穩(wěn)定”和求“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只有如此,刑法司法的公信力才能得到根本確保。
(二)刑法司法公信力的刑法原則底線
首先,刑法司法不能在實質上背離作為“帝王原則”的罪刑法定原則。聯(lián)系“鹽城‘2·20’水污染案”,重大環(huán)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刑法定因為有了投放危險物質罪的罪刑規(guī)定就不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兼顧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既不是將刑事法治這個根本目標絕對化和僵死化,也不是令刑法司法完全放縱。堅持或貫徹相對的、兼顧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司法公信力在刑法原則方面的首要底線。需要強調(diào)的是,刑法司法堅持或貫徹相對的、兼顧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并不損害刑法的權威性,也并不減損刑法司法的公信力。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不受法條或先例的約束,并不意味著對法律權威性的忽視,而是對法律根本價值或內(nèi)在本質的深入探尋,是法律精神在更高層次上的實現(xiàn),因而也是對法律權威的真正尊重。”但要注意的是,刑法司法所應堅持或貫徹的相對的、兼顧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只意味著刑法司法不受法條的字面的或表面的“絕對約束”,而非完全不要法條。刑法司法背離罪刑法定原則,無疑是對刑法司法公信力的一種嚴重丟棄。
其次,刑法司法不能在實質上背離罪刑均衡原則。元論是“許霆取款案”,還是“鹽城‘2·20’水污染案”,這些案件的量刑在表面上似乎都因獲致輕刑或重刑結果而嚴重違背罪刑均衡原則。但是,從“許霆取款案”的行為人許霆面對著取款機的技術差錯而流露出來的“人性的弱點”及對適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看問題,則其人身危險性的強弱狀況已經(jīng)使得盜竊罪的法定刑在本案中的機械“套用”顯得罪刑失衡,而正是實質的罪刑均衡原則才使得生效判決以“五年有期徒刑”扭轉了一審“無期徒刑”所帶來的罪刑失衡,從而也扭轉了社會效果的欠佳和公信力即公眾認同的“人氣低指數(shù)”。刑法司法背離罪刑均衡原則,也是對刑法司法公信力的一種嚴重丟棄。
最后,刑法司法不能在實質上背離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在筆者看來,刑法司法背離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均衡原則都有一定的“隱蔽性”,因為刑法司法在背離罪刑法定原則時可以借“擴張解釋”之名而行“類推解釋”之實,而在背離罪刑均衡原則時又可以“自由裁量”為托詞,但刑法司法在背離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時則是“外顯的”,容易暴露的。刑法司法背離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均衡原則對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損害是“隱蔽的”,而背離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對刑法司法公信力的損害則是“外顯的”。刑法司法背離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依然是對刑法司法公信力的一種嚴重丟棄,甚至是一種“明目張膽”的丟棄。
謀求刑法司法公信力時對具體刑法原則底線的堅守,可以看成是對“憲政”底線堅守的一種具體落實和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