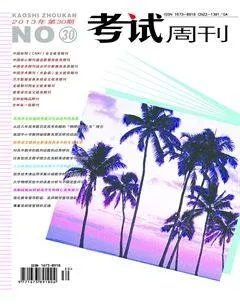多重敘事距離視閾下的外國文學(xué)教學(xué)
摘 要: 外國文學(xué)教學(xué)的關(guān)鍵是理解作品的主題思想,而多重敘事距離是表現(xiàn)主題思想的重要手段。本文通過分析兩部文學(xué)經(jīng)典作品論述多重敘事距離在表達(dá)思想、突出主題方面的作用,指出在進(jìn)行外國文學(xué)教學(xué)時,教師引導(dǎo)學(xué)生掌握多重敘事距離是必要的。
關(guān)鍵詞: 外國文學(xué)教學(xué) 多重敘事距離 《名利場》 《永別了,武器》
在過去的十年里,有關(guān)英美文學(xué)教學(xué)的論文數(shù)量呈現(xiàn)井噴之勢。以“中國知網(wǎng)”的期刊文獻(xiàn)庫為例,鍵入“英美文學(xué)教學(xué)”這一關(guān)鍵詞,2002—2012年相關(guān)論文數(shù)達(dá)到551篇,而在1991年至2001年之間,相關(guān)論文數(shù)總共才20篇。
然而,許多文章都是從教材、課堂活動模式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等角度探討文學(xué)教學(xué),這些文章大都停留在技術(shù)操作的層面,或者停留在教育學(xué)和心理學(xué)的層面,而對文學(xué)本身的關(guān)注不夠。其實,外國文學(xué)教學(xué)的關(guān)鍵是理解作品的主題思想,而多重敘事距離是作者表現(xiàn)作品的主題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教師在教學(xué)活動中對于多重敘事距離的分析對于學(xué)生深入理解作品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就以兩部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為例,闡釋敘事距離加深作品主題思想的技巧。
一、敘述者與人物的距離——以《名利場》為例
在十九世紀(jì)英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家中,薩克雷素以其淋漓盡致的社會批判而著稱。《名利場》的故事取材于英國十九世紀(jì)中上層社會。當(dāng)時英國國家強盛,工商業(yè)發(fā)達(dá),由榨壓殖民地或剝削勞工而發(fā)財?shù)母簧檀筚Z主宰社會,英法兩國爭權(quán)的戰(zhàn)爭也在這時響起了炮聲。中上層社會各式各等人物,都忙著爭權(quán)奪位,爭名求利,所謂“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小說女主人公利蓓加出身于貧窮的畫師家庭,在平克頓女子學(xué)校受盡歧視,后離校成為家庭教師。她不擇手段,諂媚奉承,走小道兒,鉆后門,一門心思攀附權(quán)貴。
在小說前半段,敘述者(領(lǐng)班——一個戲劇化了的男性敘述者、薩克雷的代言人)對于利蓓加的態(tài)度雖然有揶揄諷刺,但是總體上是認(rèn)同她的獨立思想的:
利蓓加打定主意要收服這個肥大的花花公子,請各位太太小姐別怪她。一般說來,嫻靜知禮的小姐少不得把物色丈夫這件工作交給媽媽去做,可是夏潑小姐沒有慈愛的母親替她處理這么細(xì)致煩難的事兒,她自己不動手,誰來代替呢?女孩兒們?yōu)槭裁匆鋈虢浑H場所,還不是因為她們有崇高的志向,愿意出嫁嗎?……忠厚的賽特笠太太是慈愛不過的,心里早已為她的愛米麗亞定了二十來個計劃。咱們親愛的利蓓加,無倚無靠,比她朋友更需要丈夫,自然更應(yīng)該努力了。[4](P23)
在這段敘述中,領(lǐng)班顯然站在了利蓓加一邊,與她的敘述距離非常近。讀者可以把這段敘述者的話看成是對于父權(quán)社會的評判:父權(quán)制滲透了所有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形式,在各個領(lǐng)域無聲地壓迫著女性,而處于從屬地位的女性尚且懵懂不知,只是一味遵從迎合。而勇敢的利蓓加是一個另類,是一群順從羔羊中的叛逆者。她從小缺少父母管束,加之年少時就因為家境貧寒而自謀生路,所以思想獨立解放,性格堅強,沒有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權(quán)思想玷污。在孤立無援的利蓓加獨自面對黑暗強大的父權(quán)社會時,敘述者對她表示了同情與理解。
利蓓加這個人物形象贏得了不少學(xué)者的贊賞,認(rèn)為這是薩克雷塑造的一個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表現(xiàn)了維多利亞時期女性意識覺醒,是對傳統(tǒng)意義上女性角色消極定位的挑戰(zhàn)。
但是如果據(jù)此把這篇小說理解為女性主義小說不免為時過早。敘述者雖然認(rèn)識到了父權(quán)對于女性行為的影響,但是他并非一直如此清醒。在小說的后半段的第64章,領(lǐng)班顯然把自己與利蓓加的敘述距離拉開了:他對她厭惡鄙視,把她比喻為“海上的女妖”,在水面上形容美麗,“跟大家見面的時候,總是十分文雅得體的”,但是如果向透明的水波底下張望,就會看到“海底的吃人的惡鬼”,“那粘糊糊、奇丑不堪的尾巴扭曲旋轉(zhuǎn),一會兒撲打著成堆的骸骨,一會兒在死尸身上盤旋。”[4](P806-807)在故事的結(jié)尾,敘述者甚至暗示利蓓加為了謀取錢財而謀殺了自己溫和的丈夫。薩克雷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越來越遠(yuǎn)離對與父權(quán)制的批判,敘述者與利蓓加之間的距離也是越來越遙遠(yuǎn)。面對作家貌似矛盾的態(tài)度,讀者對于作品的闡釋無法連貫,對其內(nèi)涵難以把握。為什么敘述者的敘述前后矛盾,利蓓加從一個獨立女性搖身一變成了惡魔了呢?
答案就是,薩克雷改變了敘事距離以加深作品主題,因為敘事距離服務(wù)于寫作目的。薩克雷利用利蓓加揭露別人及這個社會的名利,后來通過敘事距離的改變也把利蓓加本人作為揭露名利的例證。利蓓加這個人物的作用是“探討名利在公共領(lǐng)域——社會權(quán)貴和社會地位——里的作用。”[5](P23)如果薩克雷只把利蓓加作為揭示名利的工具,那么他對父權(quán)的批判將始終如一、嚴(yán)厲深刻,但是對于無所不在的名利的揭示效果將被嚴(yán)重削弱。顯然,作家的寫作目的在于揭露無所不在名利而非父權(quán)制的罪惡。那就是小說末尾的一段總結(jié)話語:
唉,浮名浮利,一切虛空!我們這些人里面誰是真正快活的?誰是稱心如意的?就算當(dāng)時遂了心愿,過后還不是照樣不滿意?[4](P874)
為了突出主題,在小說后半段,薩克雷拉開了敘述者和利蓓加之間的距離,剔除了利蓓加良心尚存的一面,而強調(diào)了她工于心計的另一面,于是她從一面女性主義的旗幟墮落成了邪惡的“女妖”。
通過分析敘述者與人物的距離,學(xué)生更加能夠掌握作品主題思想的本質(zhì),明白《名利場》是旨在揭露及批判追逐名利現(xiàn)象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小說而并非女性主義小說,他們曾經(jīng)的闡述不連貫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作者與敘事者的距離——以《永別了,武器》為例
《永別了,武器》中作者與敘事者的距離同樣處于變動之中。鑒于作者海明威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不少經(jīng)歷投射到了男主人公亨利身上,所以教師有必要先帶領(lǐng)學(xué)生了解海明威一生的坎坷經(jīng)歷,以便闡釋《永別了,武器》的內(nèi)涵。海明威本人曾經(jīng)是個熱血軍人——他在第一次大戰(zhàn)爆發(fā)時志愿赴意大利當(dāng)戰(zhàn)地救護車司機。1918年夏在前線被炮彈炸成重傷,回國休養(yǎng)。他反復(fù)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經(jīng)歷,開始著書立說,成為反戰(zhàn)人士。海明威的家庭生活也是歷經(jīng)傷痛:他一生經(jīng)歷了四次婚姻;他父親患高血壓和糖尿病,因為醫(yī)治無效而飲彈自盡。這些遭遇變化,更使他感覺人生變幻無常,好像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毀滅的危機。他的作品對人生、社會都表現(xiàn)出了迷茫和彷徨,他也成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永別了,武器》是海明威根據(j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經(jīng)歷寫成的反戰(zhàn)小說。同故事敘事者亨利曾是一個誠實而好幻想的美國青年,大戰(zhàn)爆發(fā)后,作為支援意大利的美國參戰(zhàn)國的一員,他懷著光榮和神圣的夢想投入到戰(zhàn)爭中。同海明威一樣,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志愿到意大利擔(dān)任救護車駕駛員。在小說中,海明威冷眼旁觀著當(dāng)年少不更事的另一個自我,與敘事者亨利在小說開始就拉開了一段距離。
那年晚夏,我們住在鄉(xiāng)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見隔著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鵝卵石和大圓石頭,在陽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處一泓蔚藍(lán)。部隊打從房子邊走上大路,激起塵土,灑落在樹葉上,連樹干上也積滿了塵埃。那年樹葉早落,我們看著部隊在路上走著,塵土飛揚,樹葉給微風(fēng)吹得往下紛紛掉墜,士兵們開過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蕩蕩,只剩下一片落葉。[3](P5)
開場白中大量短促的平行結(jié)構(gòu)簡潔有力,形成巨大的張力。沒有舒緩的過渡,亨利驟然打開自己的心扉:那靈魂中即孕育了簡單和粗魯,也不乏荒涼和干燥。閉上眼睛,讀者仿佛能夠看見一望無際的平原、高山,紛紛飄落的雜亂樹葉、軍車駛過時混沌空氣中的的蒙蒙塵埃。
頭腦簡單的亨利缺乏獨立思考能力,他相信所有官方的宣傳,對戰(zhàn)爭盲目樂觀。在第一章結(jié)尾時,亨利敘述道:“冬季一開始,雨便下個不停,而霍亂也跟著雨來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結(jié)果部隊里只死了七千人。”[3](P6)這里,亨利的敘述其實是使用了官方的聲明,官方的聲音代替了他自己的聲音。他竟然用了“只”來描述七千條生命的消逝,海明威讓讀者意識到亨利敘述所表達(dá)的價值觀的“嚴(yán)重局限性”。[5](P37)在小說開始階段,讀者已經(jīng)知道亨利熱愛戰(zhàn)爭,頭腦糊涂,是個不可靠的敘述者。
但是亨利的思想隨著戰(zhàn)爭的進(jìn)程逐漸改變了。兩年的參戰(zhàn),使這個熱血青年最初的狂熱降了溫。在目睹了戰(zhàn)場的血腥、好友死亡及交往了溫柔善良的女友凱瑟琳后,他開始反思,懷疑官方的宣傳,質(zhì)疑戰(zhàn)爭的意義,在聽到“神圣、光榮、犧牲”等字眼時,總覺得“局促不安”,這些字眼他們早已聽過,也從“貼在層層舊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讀到過,但是他“沒看到什么神圣的事”。[3](P203)他認(rèn)清了戰(zhàn)爭的真相,所謂的愛國志士不過是好戰(zhàn)者美麗的謊言而已,那些“所謂光榮的事,并沒有什么光榮,而所謂犧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場,只不過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裝進(jìn)罐頭,而是掩埋掉罷了”。而自己也不過是這場戰(zhàn)爭發(fā)動者的幫兇。于是,他期盼逃離戰(zhàn)爭,希望和凱瑟琳共度安穩(wěn)自由、舉案齊眉的生活。這時,作者與敘事者的距離也漸漸縮短,越走越近。
亨利后來終于告別了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在黑暗中奮身躍進(jìn)一條大河,經(jīng)受了死亡的浸禮而重生。逃脫戰(zhàn)爭的他與凱瑟琳再度相會了,處于安逸平靜生活環(huán)境中的他回顧了自己的過去,不僅對戰(zhàn)爭,而且對社會和世界進(jìn)行了深入思考,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世界殺害最善良的人,最溫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3](P271)亨利的這句話常常被評論者引用以說明海明威悲觀迷惘的人生態(tài)度。海明威自己也曾經(jīng)說:“生活是個悲劇,人注定要被冥冥之中不懷好意的宇宙引向毀滅的,這是一個無法改變或緩解的事實。”[1](P69)此時,在亨利的內(nèi)心獨白中,作者與敘事者的距離消失了。作者與敘事者同樣志愿參軍,在戰(zhàn)爭過程中,身心俱損,看清了戰(zhàn)爭的本質(zhì)。他們懷疑一切、厭惡一切,認(rèn)為人生一片黑暗,到處充滿不義和暴力,總之,萬念俱灰,一切都是虛空。亨利的思想和敘述也與海明威交匯,聲音合二為一。海明威為故事安排的悲劇結(jié)局印證了他的悲觀思想:凱瑟琳生下的嬰兒夭折了,而她自己因為難產(chǎn)而死。“亨利拋棄戰(zhàn)爭得到愛情,愛情又遺棄亨利”,[2]在滂沱大雨中,亨利孤獨地走向遠(yuǎn)方。海明威通過調(diào)整敘事距離深刻圓滿地表現(xiàn)了作品的雙重主題——對戰(zhàn)爭的厭惡反對和對愛情的迷惘悲觀。
三、結(jié)語
本文論證了多重敘事距離——敘述者與人物的距離、作者與敘述者的距離,及其變化在解讀文本意義中的所起的作用——作者通過這種距離表達(dá)思想、突出主題、深化讀者對文本的解讀。在外國文學(xué)教學(xué)中,引導(dǎo)學(xué)生注意到這種距離及其變化對于他們理解文本內(nèi)涵非常重要。如果學(xué)生在閱讀文本時能夠?qū)Χ嘀財⑹戮嚯x及其變化了然于胸,更有可能領(lǐng)會文本中深邃且豐饒的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Williams,Writ:The Tragic Art of Earnest Hemingway[M].Baton Rouge:IJ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
[2]丁文.走出逆境 重塑自我[J].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1998(4).
[3]海明威著.林疑今譯.永別了,武器[Z].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4]薩克雷著.楊必譯.名利場[Z].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4.
[5]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作為修辭的敘事[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