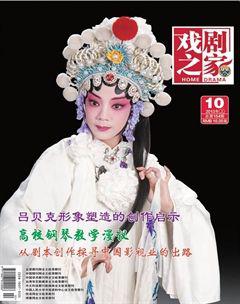楊派演唱藝術淺析
郭軍
楊寶森創立的楊派藝術,是京劇老生行當中頗有影響的一個流派。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它的唱腔藝術上,至今,楊派的傳人和私淑者在京劇界和票界較其它老生流派為多。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楊派唱腔大方工整、純正、通大路,雖然楊寶森本人嗓音天賦條件較差,但是他的發聲比較科學,位置正確,比較自如、松弛。
楊派是在余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楊寶森的嗓音條件與余叔巖不同,余高、中、低音全好,能夠完成各種音區的旋律。而楊寶森的高音較差,中、低音好。他揚長避短,在繼承余派唱腔的基礎上,創造出適應自己嗓音條件的楊派唱腔。他充分發揮“中音”好的優勢,開拓了藝術創造的新天地。避免旋律在高音區做過多的時間停留,以免產生聲嘶力竭的現象。因此,創作唱腔以中音區為軸心,再向兩端適當延伸(高音較少,低音較多)。例如,在《擊鼓罵曹》一戲中,將禰衡的一段西皮唱腔中的[西皮導板]和[西皮原板]在高音區的旋律移至中音區。余派的“讒臣當道”后三個字在高音區的“5”和“6”回旋,“謀漢朝”的“朝”字落在高音的“5”上。而楊寶森則將唱腔移至中音區的“1”、“2”、“3”處進行上下環繞,雖然旋律移低,但是,仍將禰衡的憤恨之情抒發出來了。接下來的“楚漢相爭”也都是運用了降低三、四、五度,旋律在中音區進行。在《武家坡》、《珠簾寨》、《探母》中,都可以看到這種獨特的旋法。
楊寶森唱腔雖然多在中、低音區進行,但是,為了抒發人物高亢激昂的情緒,仍然使用高音區的旋律,如《文昭關》伍子胥的[二黃慢板]中的“一輪明月”的“輪”和“明”兩字,均使用高音“5”,聲音既寬又厚,滿宮滿調,情緒十分飽滿。再如,此劇中[二黃原板]中的“爹”、“雞鳴”、“五更天”的“更天”等字,均在高音區進行,揭示了伍子胥悲憤的情緒,已激化到無法抑制的程度。
楊寶森先生在其堂兄楊寶忠先生精湛琴藝的輔佐下,使楊派藝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唱腔的旋法、結構、節奏、力度和速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使唱腔清剛勁健,由嚴整趨向簡率,由精工趨向放逸,達到氣韻生動的藝術境界。在演唱中,他十分強調唱腔的節奏、力度和速度的重要作用。例如,他在《洪羊洞》一戲,飾演楊延昭時唱的一段[二黃快三眼]唱腔,這段“自那日朝罷歸身染重病”,不同于《二堂舍子》中劉彥昌的“昔日里有一個孤竹君”的[二黃快三眼],它是[二黃慢板]的句式結構和旋法,因此,演唱和演奏都增加了難度。這段單起的[二黃快三眼]過門是由十六分音符組成的,楊寶忠先生的胡琴拉起來字清弓快,十分順暢,疾徐有致,字字珠璣。楊寶森先生演唱得快中見穩,穩而不贅。“自那日朝罷歸”六個字,字頭緊而不僵,松而不懈。加強韻母中韻頭的彈性、力度或音長。“歸”字加強的力度、噴口的彈性適度,使聲音十分純凈。在“夢見了年邁爹尊”演唱時,楊先生保持感情的完整、蘊藉、深透,前五個字一口氣唱下來,做到連感情、連語氣,使聲態流暢、婉轉。“有誰知焦克明他私自后跟”和“千歲爺”等處,在旋律上形成了斷音、重音的頓挫腔,刻畫出人物的心情動態。楊先生在頓挫的地方,巧妙地運用了“歇氣”、“偷氣”、“收氣”。為了避免呆板,小頓后襯一很輕的裝飾音,以見頓挫之意趣。他在《大保國》中楊波的一段[二黃快三眼]的演唱中唱得很有特色,與眾不同。比如四個“只殺得”后面的唱句,若按[三眼]正格習慣,應從“頭眼”起唱,而這里均從板上接唱,顯得十分新穎、動人,一氣呵成,將楊波與李艷妃爭論的戲劇場面推向高潮,使整個唱段干凈利落,產生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
楊寶森在擻音處理上,技巧非常高。擻是在唱劇中字音吐準之后,行腔間產生的大小波動音。就擻音的性質來說,是屬于硬擻或稱干擻。但他的硬擻音比一般的優美動聽。因為他的氣息彈性很強,系比較典型的柔中見剛,貌似連綿而拱來有力。在演唱中使用柔法,就能使一個單純的音,出現圓轉搖曳細膩的小腔,增加了唱腔的韻味色彩。他的用氣方法保留發余的上拔,但不完全一樣,在沉穩方面與馬(連良)近似,但楊又多一種“下壓上升”的辦法。即想把聲音升高時,反而用力把氣往下沉。猶如皮球激水,越往下壓則水激得越高。因此,楊在演唱高音前,似乎上不去,但是在實際演唱中,用氣向上一拱就達到了相應的高度。楊就是使用這種運氣方法,使楊派唱腔不乏高腔旋律。
《文昭關》、《李陵碑》、《調寇》等戲中,都充分發揮楊派唱腔藝術的這一風格,成為楊派唱腔的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