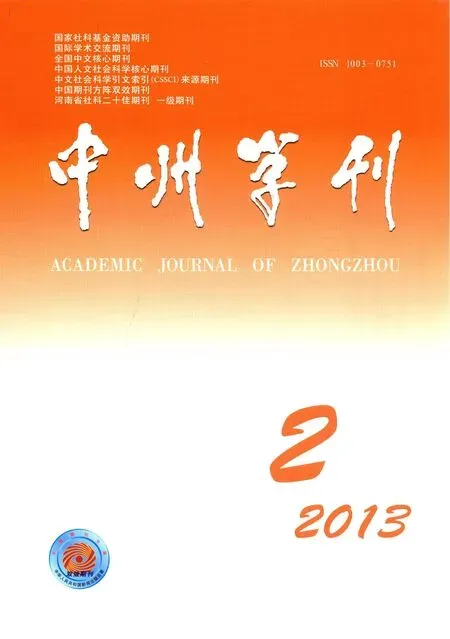新型農村城鎮化的發展類型與發展趨勢*
鄧大才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進新型城鎮化,以城鎮化建設引領經濟發展。很多學者對于城鎮化問題有過很深入的研究,也有豐碩的成果。但是新型城鎮化建設則是一項新課題,“新型”體現在哪些方面?怎樣實施才是“新型”的城鎮化?實踐中很多地方都對此進行過探索,本文通過對三條新型農村城鎮化道路的考察,探討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和趨勢。
一、文獻梳理與問題的提出
關于城鎮化研究,學者們都做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總結出了許多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從城鎮化的落腳或者從城鎮化的載體來說,就有四種不同的模式,如小城鎮化、中等城市化、大城市化及大中小結合之路。費孝通先生主張通過小城鎮實現農村和農民的城鎮化。①李子奈、侯紅婭認為,小城鎮不適應城鎮化。②王臻榮、姚志民等主張走大城鎮化的路子。③李強通過對這些模式的研究提出了“鄉村生活城鎮化”的模式。④
從城鎮化的時間來說,也有四種模式:同步城鎮化模式、過度城鎮化模式、滯后城鎮化模式和逆城鎮化模式。⑤從城鎮化的動力來看,分為政府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墨西哥模式屬于政府主導型城鎮化,而歐美模式則是市場主導型城鎮化。徐勇教授也從動力的角度將農村城鎮化分為企業帶動型城鎮化、政府主導型城鎮化、市場拉動型城鎮化。⑥顧朝林認為,中國不需要拉美式的城鎮化,因為拉美的貧民窟比較多。⑦朱敏還提出了“有城無市”的城鎮化問題,認為“有城無市”的城鎮化是一種偽城鎮化。⑧
這些模式、道路都能夠從不同的視角解釋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城鎮化過程。筆者將另辟蹊徑從農民進城的程度來考察農村城鎮化。從農民進城的程度來看有三種城鎮化模式:身體城鎮化、身份城鎮化、生活城鎮化。
二、身體城鎮化:農民工式的城鎮化
目前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不同類型的戶口將農村和城市分隔成了“兩個世界”。改革開放后,身體解放和勞動力的自由,使農民能夠進城務工經商,但是“二元福利體制”下的戶籍制度,農民身體進入了城市,身份并沒有遷入城市,文化并未融進城市,“心”還在農村。筆者將這種城鎮化稱之為“身體城鎮化”。
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從集體約束、集體勞動中解放出來,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能夠外出務工經商。開始只有少數承包地比較少、難以養家糊口的農民或者能人外出務工經商;90年代以后不管田多田少,不管有沒有能力,很多農民都外出務工。根據有關部門的數據估計,截至到2011年,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數量達到了1.59億人左右。⑨農民工外出務工經商有幾個主要的特點:
一是就業在城鎮,但是身份在農村。農民工已經在城鎮就業,在現代企業工作。按照西方的人口統計標準,農民工已經城鎮化,屬于城鎮居民。但是在中國,農民工不管是管理上,還是統計上都不算城鎮人口。因為農民工的身份還在農村。城市只需要農民工的勞動,但是并不負責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農民工只能拿“裸體工資”,無法平等地享受養老、醫療、失業、住房等社會保障,有時甚至工資都無法保障。雖然農民工可以享受部分城市公共設施,也能夠購買城市住房,但是與身份對應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則難以享受。
二是身體在城鎮,但是歸宿在農村。農民工就業和生活在城市,也就是說身體的輸出活動和身體的輸入活動均在城市,但是農民的歸宿仍在農村。從農民工的心態來說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雖然農民工的身體已經進城,但是大部分農民工的心還在農村,因為自己的承包地、孩子和父母還在農村。從農村工的未來關懷來看,農民工干得再久,也不將自己當成城鎮人,城鎮只是一個暫時寄居地,打工結束還要回歸故里,打工的歸宿還是農村。
三是生活在城鎮,但是文化在農村。農民工已經在城市生活,吃喝拉撒與城鎮人無異,但是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卻沒有城鎮化,仍然堅守農村文化。由于當地政府不接納、城市居民排斥,農民工生活圈子非常狹小。大部分農民的生活圈就是兩點:企業——宿舍,而且居住地和工作地也相對邊緣化,遠離城市中心和城市居民。農民仍然保持著農村的生活習慣,維持著農村的生活方式,保持傳統的鄉村關系網絡,甚至打工農民之間互動也按照農村規矩。因此,農民生活在城市,但是生活方式仍是農村的,仍然堅守農村的傳統文化。
四是工作在城鎮,但是權利在農村。農民工就業與身份分離、生產與生活分離,同時農民的工作與權利也出現了分離。農民工在城市工作,但是其作為公民所擁有的權利則在身份所在地——農村。一是農民的經濟權利,包括就業權、資源分配權在農村;二是農民的社會權利,如新農保、醫保、計生等社會權利由戶口所在地政府提供;三是農民享受政策的權利,如惠農政策、汽車下鄉等權利只能回原籍才能夠享受;四是農民的政治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政治參與權也只能回農村才能夠享受。
總體而言,在城鎮,農民工只有“裸工資”和分享部分城鎮的公共設施及付費的準公共服務,沒有任何福利、社會保障,也無法享受政治權利。可以說農民就業在企業,生活在城鎮,但仍然是農民身份,只能說是一個“半城市人”,即身體進城但是身份與資格沒有進城,文化沒有進城。筆者將這類農民稱之為“身體城鎮化”。
“身體城鎮化”是一種畸形的城鎮化,無論從經濟、政治和社會維度來看都有不少弊端。從經濟層面看,“身體城鎮化”導致了農民工輸出地補貼、支持了輸出地,有加劇區域之間“馬太效應”的趨勢;從社會層面看,加劇了城鄉對立,割裂了家庭生活;從政治層面看,導致了農民工的奉獻與權利的分離,在城鎮農民工只有工作、奉獻的義務,卻沒有分享成果和獲取福利、被服務的權利。“身體城鎮化”雖然避免了所謂的“貧民窟”問題,但是卻扭曲了城鎮化道路,延緩了城鎮化進程,并將身體城鎮化的成本全部轉嫁給農民工及其家庭。
“身體城鎮化”有其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根源。從主觀來看,國家、輸入地政府及城市居民都不愿意讓闖入城市的農民工完全城鎮化。國家政策對于農民進入城市并沒有完全放開,輸入地政府也設置了不少障礙,城鎮居民生產、生活雖然離不開農民工,但只歡迎農民工的勞動,并不歡迎農民工的城鎮化。從客觀來看,農民勞動力自由了,但是農民的身份及與身份相伴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無法自由流動。附著身體的勞動力可以城鎮化,但是身份及其相伴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卻無法城鎮化。雖然企業提供了生產資料,但是企業不提供如國有企業一樣的福利,政府不提供城鎮居民所享受的諸多公共福利和服務。兩個方面共同決定了打工農民只能“身體城鎮化”,而無法實現“身份城鎮化”。身體城鎮化的根本原因是身體的自由與身份的不自由共同規制的,前提條件是經濟比較貧窮。身體城鎮化的解釋模型可以簡化為:身體城鎮化=貧窮的經濟+身體自由+身份規制(強制)
三、身份城鎮化:征地與社區建設式城鎮化
在各地的城鎮化中,還有一種城鎮化類型,即農民本身并不希望城鎮化,但是隨著城鎮擴張、新型社區建設,地方政府強制征地,農民被迫城鎮化、社區化,即農民的身體可能沒有城鎮化,但是被迫獲取了城市居民的資格或半資格,筆者稱這種城鎮化稱為“身份城鎮化”。“身份城鎮化”分為兩類:
第一種類型:征地導致的城鎮化。城鎮化的擴張導致不少城郊農民土地被征用,被征地農民身份被接納進入城鎮。這種接納又可以分為全接納和半接納,即完全變成城鎮居民和部分享受城鎮居民應有的權利。在很多城鎮,被征地農民只能部分享受城鎮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有些農民可能已經進城,也有些農民沒有進城。被征地農民就業基本沒有進城,雖然有些城鎮給被征地農民一塊留用地或者允許其承包物業,但是能夠就業的農民畢竟是少數,總體而言農民就業沒有進城。不管是完全城鎮化還是部分城鎮化,對于大部分農民來說都是非自愿的,與農民進城是自愿的身體城鎮化形成鮮明對比。被征地農民雖然生活城鎮化了,但是文化還是農村文化,包括人際交往、風俗習慣、社會網絡等都沒有改變,依然遵從“熟人社會”的習慣。
第二種類型:新村鎮建設導致的城鎮化。現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在實施新村居和新村鎮建設,許多農民被迫順應“以地換保”、“以宅換房”的政策,也就是“被迫上樓”。“被迫上樓”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只要農民的土地,但是不給農民以城鎮居民的身份,農民的身份沒有改變。另一種情形,要農民的土地,也給農民城鎮居民身份。我們所說的“身份城鎮化”是指第二種情形。客觀地說,“以宅換房”和“以宅換保”有一部分農民是自愿的進城或者“上樓”,但是大部分是“被迫上樓”、被迫進城。按照中國人口統計標準,“被迫上樓”的農民因為有城鎮居民身份,屬于城市居民,但是這部分農民雖然有了城鎮居民身份,但是就業沒有進城。有些農民身體也沒有進城,生活也只是社區化(非城鎮化),享受的保障也只是部分保障,文化基本沒有改變。
在此我們可以將“身份城鎮化”的特點歸納出來:一是身份進城,但是身體尚未完全進城;二是資格進城,但是就業沒有進城;三是歸宿進城,但是文化完全沒有進城。除此之外,對于身份城鎮化的農民而言,身份的改變并沒有改變地緣關系,家庭成員也沒有分離,沒有“候鳥工”的漂移現象;身份城鎮化的農民,不再擁有承包地,大部分的家庭不再擁有宅基地;身份城鎮化的農民,其社會關系整體地移進社區或者移進城鎮,其歸宿感并不明顯,對前途的方向感還不如身體城鎮化的農民。身體城鎮化的農民的目標明確——主要是回鄉村發展和生活。
“身份城鎮化”是一種外部強制的城鎮化,屬于一種強制性的身份改變,沒有任何內生性城鎮化的特點,同時伴隨著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喪失。身份城鎮化對于城市來說是必要,但是對于被迫進城的農民來說則并非必要,“被進城”或“被上樓”的農民也未必準備妥當。雖然身份城鎮化完全或者部分解決了進城農民的城鎮身份和資格問題,但是農民的生產資料和財產喪失了(一般是非等價交換),大部分農民無法在城鎮就業,依然沿襲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網絡。雖然被圈進城、住上了樓房,但是農民仍然認為自己是農民。身份城鎮化的負效應比較大:一是隨著身份的獲取,農民失去農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條件;二是身份城鎮化無法解決農民的就業、工作問題,進城農民既不能種田,也不容易就業;三是農村文化和生產方式被整體移入城市,在農民身份城鎮化的同時,城鎮也農民化了。
身份城鎮化的支配性因素是城市擴張與政府強制。在城鎮化過程中,雖然農民有身體和勞動力的自由,但是身份的認定卻是自己無法決定的。這其中,地理位置對身份城鎮化也有決定性的作用,居住在郊區的農民更有可能被城鎮化。因此,“身份城鎮化”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城市擴張、政府強制和地理位置。其模式可以表示為:身份城鎮化=城市擴張+政府強制+地理位置
四、生活城鎮化:非遷移式的城鎮化
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廣東、浙江等地區,一些村莊既沒有遷移進城,也沒有被城鎮擴張吞沒進城,而是就地對村莊進行改造,不僅硬件方面有城鎮化的設施,更重要的是生活方面有城鎮化的質量,文化方面吸納城市文明改造農村文化。這類村莊的村民,雖然其身份沒有被認定為城市人口,也沒有城市資格,但是其生活則是完全的城市生活,農民都認為他們已經城鎮化,其生活比城市還要好。筆者將這種城鎮化稱之為“生活城鎮化”。生活城鎮化可分為三種類型:
身體未進城,但是生活方式已經城鎮化。廣東、浙江等地有些村莊,村集體經濟勢力比較雄厚,村莊按照城鎮化標準建設:街道、路燈、公園、健身設施等一應俱全,有些村莊還建設污水處理系統或者將污水處理系統與城市污水系統對接,街道定時清掃并集中處理生活垃圾,城鎮生活應有的公共設施,村莊完全提供。另外,更重要的是家庭完全按照城鎮居民一樣生活,自來水、管道煤氣、抽水馬桶、現代化的廚房等應有盡有。村莊公共設施和家庭生活設施完全城鎮化,雖然身體沒有進入城鎮,但是農民的生活方式已經城鎮化,生活方式與城鎮居民無異。
就業未進城,但是社會保障已經城鎮化。村莊除了提供類似城鎮的公共設施外,還幫助農民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生活城鎮化的村莊都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城鎮居民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面向轄區的所有居民,包括農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障、低保、計劃生育補貼都一視同仁。提供者主要有兩個主體:一是政府提供,如計劃生育、低保,農民能夠同等享受;二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提供,有資格限制或需要購買的公共服務,村莊資助農民參加,如城市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可以說,農民就業未進城,其社會保障已經城鎮化。
身體和就業已進城,但是形式化身份還在農村。
在這類村莊也有一些農民已經進城就業,身體進入了城鎮,也在城市就業,甚至也在城鎮吃飯,但下班后要返回農村的家。這類農民身體和就業都已經進城,但是生活還是在農村。但是這里的農村與“身體城鎮化”、“身份城鎮化”的農村有較大差別,村莊內部的設施與城市幾乎沒有區別。這類農民還通過工作的企業加入城市職工養老、醫療保險。這類農民除了身份是農民外,與城鎮居民已經沒有區別。其原因是農民不愿意將戶口遷入城鎮,農民仍然將“形式化身份”留在農村。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生活城鎮化”的特征:生活方式已經城鎮化,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農村文化在村莊和農民共同作用下正在緩慢地改造,這是一種主動的改造和適應,“生活城鎮化”的村莊和農民歸宿感明確。總而言之,“生活城鎮化”的農民執意保留著的形式化農民身份并居住在不亞于城鎮的農村社區。
“生活城鎮化”是一種內生的城鎮化方式,內生于村莊經濟發展和所在地區經濟實力,生活方式、就業方式、身份方式都是農民自愿選擇的結果。身體自由、勞動力自由與生活城鎮化的關聯性不大。地理位置對生活城鎮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影響,只有離城比較近的地方且未被納入城鎮發展的村莊,另外還有成建制的社區,才有機會選擇“生活城鎮化”。所以,“生活城鎮化”受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經濟實力、自由選擇、地理位置。我們可以將此“生活城鎮化”表述為:生活城鎮化=經濟實力+自由選擇+地理位置
五、進一步討論:三種模式的比較
前面對身體、身份和生活城鎮化的特點、分類、形成原因及決定模型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對三種模式進行比較分析,考察三種模式的異同、優劣及發展前景。
(一)城鎮化動力比較
身體城鎮化由勞動力輸出地的經濟發展程度、勞動力自由程度以及城市對身份的控制程度三個因素決定。身份城鎮化由城市擴張與經濟發展、地理位置和政府強制三個變量決定。生活城鎮化由經濟發展、地理位置和自由選擇三個變量決定(見表1)。

表1 城鎮化模式的決定因素
身體城鎮化與生活城鎮化有兩個決定因素相同——經濟因素和身份強制因素,只有變量二不同。身份城鎮化和生活城鎮化也有兩個決定因素相同——經濟因素和地理因素。身體城鎮化和生活城鎮化模型的決定因素只有經濟因素相同,一個因素完全相反,一個因素完全不同。
三類農村城鎮化模式的決定因素歸納起來就是四個變量:身份規制程度、經濟發達程度、地理位置、勞動力自由(包括居住選擇的自由)。其中,經濟發達程度是一個前提條件,地理位置是一個客觀因素,農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地點。真正決定不同類型城鎮化的因素就是自由選擇(包括勞動力自由和居住自由)、身份規制程度或強制程度。
從圖1可以看出,不管是經濟發達地區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身份強制程度大與自由選擇程度低兩個因素作用將會導致“身份城鎮化”;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身份規制力大與勞動力自由選擇度大兩個因素作用導致勞動力流動與“身體城鎮化”;在經濟發達地區,身份規制程度較小和自由選擇度比較高兩個因素作用容易形成“生活城鎮化”。可見三類城鎮化是由不同的外部條件和不同的內因形成的。

圖1
(二)城鎮化程度比較
城鎮化分為形式化城鎮化和實質性城鎮化。前者按照國家統計標準衡量,后者按照城鎮化的實質享受程度來衡量。如果將城鎮化視為一個光譜,則三類城鎮化位于光譜的不同位置,即城鎮化水平有較大的差異。
從形式城鎮化水平來看,城鎮化程度從高到低,依次為身份城鎮化、身體城鎮化和生活城鎮化。身份城鎮化程度最高,因為地方政府已經將征地和新村居建設的農戶全部統計為城市居民,當然公共福利、公共服務是否與城鎮居民完全一致則是另外一回事;其次是身體城鎮化,因為在很多專家眼中,這部分在城鎮務工經商且工作6個月以上的農民應該視為城鎮居民;最后是生活城鎮化,雖然生活城鎮化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生活,但不符合政府統計標準,所以形式城鎮化最低。
從實質城鎮化水平來看,城鎮化程度從高到低,依次為生活城鎮化、身體城鎮化和身份城鎮化。生活城鎮化最高,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面:農民自我認同程度最高,農民享受了城鎮化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文化也趨向于現代城鎮,只是農民不愿意將戶口轉為城鎮居民;身體城鎮化程度最低,主要原因是農民除了身體進入城市、勞動力進入企業外,社會保障、公共福利等都沒有進城,身體雖然進城,但是仍然遵循農村傳統和習慣,農民也不將自己視為城鎮居民。身份城鎮化程度居中主要是其身份已經城鎮化,部分的享受城鎮公共設施、公共服務。

圖2
(三)優劣評價與前景
“身體城鎮化”是落后地區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與現有的城鎮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身體城鎮化”與其說是一種城鎮化,倒不如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一種城鎮寄居方式。這種城鎮化帶來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低工資、留守兒童、空巢家庭等問題。“身體城鎮化”能夠長期存在,主要原因是農民能夠得到在農村無法獲得的貨幣收入,輸入地政府能夠獲得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最優配置,經濟效率比較明顯。也就是說,“身體城鎮化”經濟效率大于社會效率,經濟效率的獲取是以巨大的社會成本為代價。“身體城鎮化“涉及到的群體比較大,即使國家放寬進城條件,城鎮也無法完全吸納,更無法完全接納打工群體的家庭。固然如此,身體城鎮化還是會延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國家也正在逐漸放寬進城條件,接納有穩定職業、穩定收入且已融進城鎮生活的農民工,使身體城鎮化的農民的身份也逐漸城鎮化,從一個”半城市人”變成完整的城市人。
“身份城鎮化”是城市擴張和政府強制的必然結果,其城鎮化程度也要高于“身體城鎮化”,但是身份城鎮化還可做得更好一點:一是可以降低強制程度,給農民以充分的選擇;二是農戶的土地和宅基地征用可以用市場的方式,根據市場價進行等價交換;三是國家對農民的保障完全可以與城市同步,而不應該是“征地農民養老保障”等半城鎮化的服務、“二等公民”的服務;四是被征地農民完全就業有難度,但是將無法就業的農民納入失業保險范圍還是可以的。雖然身份城鎮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持續時間較長的過程,但各級政府可以不僅僅是“身份城鎮化”,還可以將身份與身體、生活一并城鎮化,使被征地農民、新型社區的城鎮化一步到位。
“生活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屬于漸進的內生型城鎮化,對社會、家庭、城市帶來的沖擊比較小。生活城鎮化建設成本比較高,但是社會成本、交易成本比較小,負面作用比較小。它是農村和農民主動的城鎮化,因此阻力比較小。生活城鎮化最終的目標并不是讓人們進入城市,也并不一定都是征地,如果村社區能夠具有城鎮的功能,農民能夠主動向城鎮生活過渡,國家能夠讓這些村莊的農民享受城鎮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生活城鎮化將是農村和農民最好的選擇。雖然生活城鎮化還沒有完全納入國家統計范圍,但它應該是中國農村和農民城鎮化的重要方式。除非必須征地、必須進城,比較遠離城區的農村和農民可以逐漸通過農村社區化而最終走向城鎮化,其路徑是:分散村莊—農村社區—農村城鎮。

表2 三條城鎮化道路的比較
六、結論
三種農村城鎮化模式是城鄉二元福利、戶口制度及地區和家庭經濟發展程度的必然結果。身體城鎮化主要受制于二元的福利、戶口制度、土地承包經營制度以及輸入與輸出地經濟發展差距。只要影響因素不改變,身體城鎮化將會持續。身份城鎮化則是政府的經濟擴張與行政強制的結果,同時也與政府對于身份城鎮化的農民多“取”少“予”有著重大的關系,如果政府能夠在土地進城的同時,按照城鎮居民的標準來為農民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農民的身份與身體將會同步城鎮化。
生活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生活城鎮化不反對農民身體進城,但是更看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城鄉均等,生活方式的城鄉一致。在我國現有國情下,農民全部進城可能不太現實,但讓農民享受到政府的公共服務、享受到城鎮的生活則是當務之急。因此,生活城鎮化可能將是中國未來城鎮化的首選道路,也是震蕩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種城鎮化方式。
注釋
①費孝通:《小城鎮,大問題》,載《費孝通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②李子奈、侯紅婭:《中國農村城鎮化模式的需求分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③王臻榮、姚志民:《關于強化我國小城鎮建設的幾個問題研究》,《城市發展研究》2005年第3期。④李強:《如何看待我國城鎮化現象》,《人民日報》2006年12月8日。⑤葉連松、靳新彬:《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⑥徐勇教授在與博士生討論時提出的觀點。⑦顧朝林:《我們不需要“拉美模式”的城市化》,《人民日報》2010年4月8日。⑧朱敏:《有城無市的城鎮化模式急需改變》,《中國經濟時報》2010年11月25日。⑨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