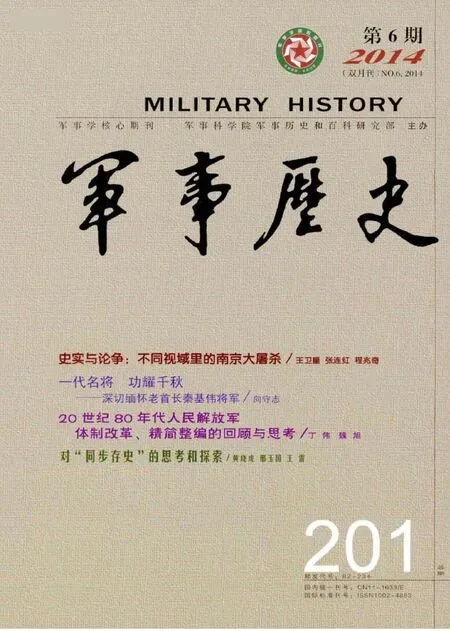《孫子·九變》再審視
——兼論《孫子》研究的方向
□ 王 玨
《孫子·九變》在內容和篇章結構上引起較多爭訟,受到研究者普遍關注。李零先生曾指出《孫子·九變》中存在“章句割裂”問題,最近又見論者發表題為《<孫子·九變>再考察》的文章(以下簡稱《再考察》,詳見《軍事歷史》2013年第5期)與李零先生進行商榷。本文參稽相關文獻,再細加審視,并對《孫子》研究的方向發表一些淺見。
一
《再考察》一文認為,李零先生關于《九變》值得商榷的說法之一是:“他(李零)認為張、劉、趙①指張賁、劉寅、趙本學。等是‘注重書的整體分析’的。愚見以為,張、劉、趙他們恰恰是沒有注重書的整體分析,至少是沒有從整體思想上對《九變》進行把握,眼睛只盯著‘九’這個數字,從而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才找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的錯簡。”
案:《再考察》對元明先輩學人和李零先生的學術觀點理解有偏差。李零先生強調元明學人從結構上整體把握《九變》篇,《再考察》認為元明學人沒有從思想上對《九變》篇進行整體把握,兩者只是理解問題的角度不同,沒有可以商榷之處。
李零先生原文為:“當時著書者每動稱‘錯簡’,改易原書文句,倡為新解,若元代之張賁,明代之劉寅、趙本學,皆一時之著稱者。他們受理學影響,注重書的整體分析,反對‘有一句解一句’”②轉引自李零:《孫子古本研究》,22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李零先生所言分明在強調元代之張賁,明代之劉寅、趙本學注重對《孫子》之書的整體結構進行分析,肯定其研究方法的可取之處,這種評價并無不當。李零先生承認:“張賁、劉寅、趙本學的改動,我不贊同,但他們對舊說的矛盾看得很清楚,對我仍有啟發。”③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318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但《再考察》沒有真正理解李零先生的原意,看不到元明先輩學人因為開始注重從結構上整體分析《孫子·九變》篇而取得的學術成就,仍然說出諸如“張、劉、趙他們恰恰是沒有注重書的整體分析”、“眼睛只盯著‘九’這個數字”、“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之類的話,委實過于苛責古人。
二
在《再考察》看來,李零先生關于《九變》值得商榷的說法之二是:李零根據銀雀山竹簡,批評張賁等人“動稱‘錯簡’,妄改原書”,確是批評在關節之處;但李零自己卻動手對《孫子》版本做出了另外一種改動,這就值得商榷了。李零在最近幾年出版的相關《孫子》類書籍中,《九變》都是被整體搬遷到《九地》之后。雖然他對這樣的改動曾注以說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其實也是一種版本改動。
案:不確。李零先生反對版本改動,也沒有“對《孫子》版本做出了另外一種改動”。《再考察》指認李零先生“在最近幾年出版的相關《孫子》類書籍中,《九變》都是被整體搬遷到《九地》之后。雖然他對這樣的改動曾注以說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其實也是一種版本改動。”根本就是誤判!
首先,李零先生曾態度鮮明地反對版本改動。主張:“我們不能按我們的標準來要求古書,只要我們覺得不通順,就替古人改文章,想刪就刪,想改就改,想移就移,想并就并,一直到我們通順了才滿意,那不叫校勘,而叫新編。”①李零:《唯一的規則:〈孫子〉的斗爭哲學》,254頁,北京,三聯書店,2010。強調:“古書的整理,不管多么粗糙,多么不合理,也不能按今天的道理讀,今天的道理改,最好保持原樣。”②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315頁。有關論證《九變》接近初始狀態,提倡尊重古書原貌的類似說法還有:1、“簡本相當《九變》的一篇,篇題未見,字句殘缺較甚,篇題木牘也沒留下題目,但留下的東西和今本出入不大。我們估計,簡本已經就是現在這個樣子。”2、“《九變》原文本身,混亂擺在那兒,其實更古老。”3、“文章是糊涂文章。但此篇再糊涂,從簡本看,西漢時期就這樣,用不著改動。這類問題,古書多有,我們不必大驚小怪。”③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319~320頁。
其次,李零先生也沒有“對《孫子》版本做出了另外一種改動”。《再考察》所指的第一部書《兵以詐立》的真實名稱為《兵以詐立:我讀<孫子>》,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孫子》課的整理稿。(《再考察》所指的另一部書《唯一的規則》真實書名為《唯一的規則:<孫子>的斗爭哲學》,該書觀點多襲用前書,無足深論。)為了授課方便,李零先生在實際教學中根據內容做了調整。出于旁觀者的良知,這里不妨審視一下李零先生要表達的真實意思:“《九變》篇的位置本來在《軍爭》篇的后面,為了便于講述,我把它的位置挪一下,放在《九地》篇后面講。原因,前面說過,主要是這兩篇,內容相關,沒法分,《九變》篇的內容,不過是《九地》篇的一部分。不講《九地》,《九變》沒法講。我的目的,不是搞新編。”④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314頁。
在此基礎上,李零先生形成的判斷是:“《九地》可能是《孫子》各篇大體編訂后,最后剩下的材料,整理工作有點差,因此結構松散,前后重復。《九變》又是從《九地》分出的一部分。《九變》是一篇糊涂文章,單獨講很麻煩,連題目都成問題。但是,我們把它和《九地》放在一起讀,還是可以理解它的大致含義。”⑤李零:《唯一的規則:〈孫子〉的斗爭哲學》,254~255頁。李零先生唯恐引起有些人誤解,所以,特別反復加以說明,“為了便于講述”,“我的目的,不是搞新編”。已經到了“此心耿耿”的程度,依然被人堅持說成“這其實也是一種版本改動”。仔細想來,李零先生所言并非不易之論,論者也大可不同意李零先生的學術觀點,卻不應將基于誤讀或誤解而形成的不恰當誤判強加于人。
三
在《再考察》看來,李零先生之所以提出“章句割裂說”,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九變》開頭五句,有四句與《九地》重出;二是“絕地無留”一句,在銀雀山簡本中出自《九地》篇。據此李零得出結論:“前人推測‘九變’本來是指‘九地之變’,這點是正確的”,并進一步認為《九變》是一些“編輯很差”、“無法讀通”的下腳料。
案:《九地》、《九變》兩篇存在“句子重出”現象,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時,《再考察》難能可貴地指出李零先生之失,接下來,《再考察》所陳述的觀點卻同樣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
李零先生判斷《九地》、《九變》兩篇之間存在章句割裂的證據有二:一是“《九變》十句話中的前五句,全部與《九地》篇重出。”二是《九變》篇中“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于九變之利,雖知五利,不能得地之利矣”,與《九地》篇“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相合⑥轉引自李零:《孫子古本研究》,232頁。。對照《孫子》原文,“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交合”和“圍地則謀”,四句大抵可歸為“重出”,只有“絕地無留”確乎沒有出現在《九地》篇中,李零先生取《九地》篇中“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的“絕地”,再取銀雀山漢簡本上編《九地》篇“爭地,吾將使不留”中的“不留”改為“無留”,拼接成“絕地無留”,這種牽合彌縫的做法成為招人詬病的主要癥結。
退一步講,即便四句“重出”也僅能為研究者判斷兩篇中是否存在“章句割裂”提供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再考察》以此指出李零先生的不可取之處,彌足合宜。然而在陳明自身觀點時,卻意外地提出另外一種可能性:“至于‘重出’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作者對相關問題更多重視,譬如老師上課,覺得是重點內容,一定要反復叮嚀。”這不能不讓人陡然生疑,究其實,李零先生的“章句割裂”是“句子重出”的可能原因之一,《再考察》提出的“對相關問題的更多重視”同樣也是“句子重出”的可能原因之一。李零先生基于可能性形成判斷的做法固然有失嚴謹,但是,《再考察》沒有拿出有力證據,便直接用自己相信的一種可能性來否定李零先生的另一種可能性,并且,取喻“老師在課堂上叮嚀學生重點內容”,把“重出”的原因說得如此簡單,如此隨意,豈能讓辯者折服。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李零先生“章句割裂”說建立在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展現出深厚的學術功底,其真實意圖在于嘗試解決一個由來已久的學術問題:《九地》、《九變》兩篇是否存在“章句割裂”。李零先生“是從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走上學術研究這條道的”①轉引自李零:《孫子古本研究·自序》。,堪為《孫子》研究領域的淹通之士。他在校讀《孫子》的過程中,發現古書“往往會有篇題不能概括內容,一篇之內層次不相銜接以及篇與篇之間內容重復出入等問題。”“實際上,并不應叫做‘錯簡’,倒不妨叫做‘章句割裂’。”尤其注意到,《孫子》在先秦子書中是屬于形式比較整飭的作品,所謂“其言甚有次序”,但即使是此書中也同樣存在著章句“割裂問題”②轉引自李零:《孫子古本研究》,230頁。。
其實,李零先生的證據遠遠不是《再考察》列舉的這些,行文所限,僅再補充相對重要的兩點:
第一,據《后漢書·文苑列傳》記載:“高彪乃獨作箴曰:‘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李賢注引用《孫子·九變》篇,《北堂書鈔》卷一一五《將帥四》“通九變”條引用《孫子》,皆大段抄引《九地》篇之文當之,并將《九變》、《九地》兩篇文字合抄在一起,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古人早就感到這兩篇在內容上有密切聯系③轉引自李零:《孫子古本研究》,234頁。。
第二,“《九地》篇十二個片段,在內容上十分冗雜凌亂,不但各個片段之間并不銜接,而且后半篇與前半篇也屢有重復,活像同一篇的兩個本子(趙本學及鄧廷羅《兵鏡》均已言之)”④轉引自李零:《孫子古本研究》,234頁。。
李零先生受歷代學人的啟發,在深入研究中發現問題,并試圖做出解答。令人遺憾的是,從“古人早就感到”、“活像”等措辭中可以看出,其結論大多建立在推論基礎之上。然平心而論,這些思考并沒有重大失誤,尤其是“章句割裂”的見解尚有頗多精義。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僅就《孫子》研究而言,歷代研究者浸淫文獻之中,簡直已窮盡智慧,有分量的見解厚厚地積累下來,后來者每推進一小步又何其艱難!李零先生在小心考證基礎之上,洞悉“《九變》《九地》兩篇各自然章句之間的聯系及編次上的矛盾”,提出退而求其次的大膽假設,不失為學術新見,對后學的啟示意義更是難以估量。
進行以上辨析并非單純地進行“商榷”,愚者千慮的真實意圖是要奉獻有關《孫子》研究的一些思考。
歷史研究的真正魅力在于“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⑤[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9~10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若為推動學術進步計,我們更關心學術責任的召喚。因此,“求得真事實,予以新意義,予以新價值,供吾人活動之資鑒”⑥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6~7頁,北京,中華書局,2010。,正是時代賦予《孫子》研究的真正使命,從中也能夠領悟到今后《孫子》研究的三個重要方向:第一,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于增進人類的利益。因此,《孫子》研究最為至關重要的任務即是發掘當代啟示,資鑒當今,指導現實。第二,繼續研究原典,得古人之意。第三,重溫《孫子》研究的歷史,“通過學習,并把自己的經驗與前面各代人的經驗結合起來”⑦[英]E.H.卡爾:《歷史是什么》,21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僅就后兩個方面而言,可能實現的突破之處大致可以確定為:(一)發現新史料,或者重新尋出已經沉沒了的事實;(二)運用新方法得出新解;(三)發現前人之誤并予以糾正。關于這一點需要遵循的原則應該是“不薄今人愛古人”。也就是說,對待學術先輩的成果,要有“與有榮焉”的心態,要給予“理解而不是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