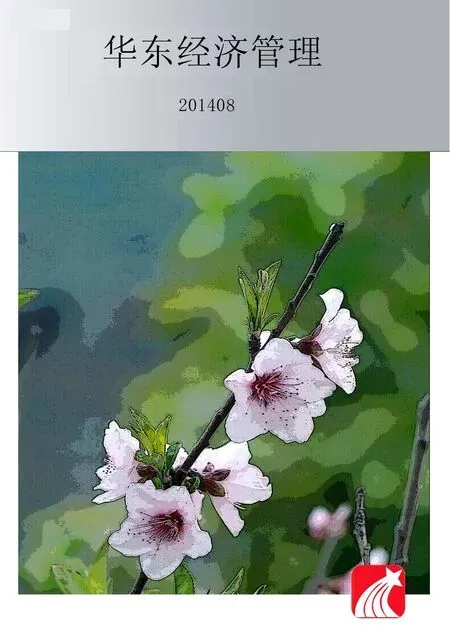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研究:個人—組織多重匹配的分析視角
趙斌,朱朋,李新建
(1.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天津300384;2.南開大學商學院,天津300071)
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研究:個人—組織多重匹配的分析視角
趙斌1,朱朋1,李新建2
(1.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天津300384;2.南開大學商學院,天津300071)
文章基于個人—組織匹配的視角,從微觀層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幸福感進行了研究。理論推演和514份問卷的實證分析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與其工作組織之間的三個匹配維度(價值觀匹配、個人需求與組織供給匹配、工作要求與個人能力的匹配)對工作幸福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感知到的工作意義在此影響關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另外,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現代性,即個體的價值取向,在該影響關系中有正向調節作用,主要體現在價值觀匹配、個人需求與組織供給匹配對工作幸福感的作用關系上。
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個人—組織匹配;工作意義;個人現代性
一、引言
對幸福(well-being)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話題,基于各學科視角對個體幸福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1]。在以往研究中,幸福的定義逐漸從僅偏重物質性擴展到包含豐富的精神因素。20世紀中期研究者提出了“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人們對生活的情感體驗和認知評價”,認為幸福就是主觀感知到的較多的正性情感、較少的負性情感和較高的生活滿意度[2]。員工對工作的情感體驗與認知評價即為工作幸福感[3]。
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具有鮮明特色的新事物,是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中強大的人力資源保障[4]。20世紀90年代后期,農民工結構出現了代際轉變,改革開放之后出生的16~30歲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該群體的61.6%[5],成為該群體的主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高、物質和精神要求高等特征[6],有著更為現代的工作理念和更高的生活期許。但他們同時也有著與父輩相似的工作生活環境和社會地位,這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知產生了重要影響,并集中通過工作幸福感予以體現:工作幾乎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工作幸福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整體幸福感。富士康“連跳”事件反映出主觀追求與現實沖突形成的巨大心理反差對這一群體的深度傷害,并折射出工作幸福感的缺失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后果。
目前對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呈現以下特征:較為集中在社會學領域,關注的是整體幸福感(如生活滿意度);側重對人口統計學變量、人格特質和工作特征等影響因素的探討[7-8];研究對象多為老年人、大學生、青少年和城市居民[9],鮮有對特定職業群體的工作幸福感研究;研究范式多為個體特征、客觀環境等單一性因素對幸福感的靜態影響。然而員工的工作幸福感更是個體與環境的交流、摩擦和協調的產物[10]。隨著互動心理學的興起,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匹配關系及對個體態度和行為影響成為研究熱點[11-12]。該領域的研究發現,個人特質和環境等單一變量難以解釋個體的態度和行為變化,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則可以最大程度解釋這種變異[13]。張興貴等認為,同時強調環境與個體方面影響因素的重要性,將會增強對員工幸福感的預測力[14]。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初創期就“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環境工作,伴隨其身的工作價值觀、文化背景、工作方式、工作技能能否與其工作組織相匹配,可能對其工作幸福感有著重要影響。
二、基礎理論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涉及對兩個核心概念的界定:第一,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是主觀幸福感在工作領域中的反映,是指員工對工作的積極情感和認知評價[3],包含情感和認知取向兩個方面:前者指對工作的感受,后者指工作滿意度[14]。第二,個人—組織匹配。依據互動心理學,個人特征和情境特征的結合,會導致特定個體對既定情境的反應產生聯合影響[15]。目前廣為接受的測量企業員工個人—組織匹配的模型是Cable等人[16]創建的,該模型是在Kristof的二元模型的基礎上延伸出的三元模型,包括一致性匹配(supplementary fit)、個人需求與組織供給匹配(needs-supplies fit,N-S fit)及工作要求與個人能力的匹配(demands-abilities fit,D-A fit)三個維度。它們的含義分別為:員工個人的工作價值觀、工作目標等基本特征是否與其所在的企業相一致,企業提供的資源和機會能否滿足員工的需要,以及員工自身所具備的知識、技能能否滿足其所在的工作崗位要求。
(一)個人—組織匹配與工作幸福感的關系
1.價值觀匹配與工作幸福感的關系
個人與組織一致性匹配的含義為個體的基本特征(人格、價值觀、目標及態度)與組織的基本特征(氛圍、價值觀、目標及范圍)的一致性程度[17],一致性匹配主要反映在價值觀匹配上[18]。由于本研究重點為工作幸福感,因此本文將價值觀匹配聚焦于工作價值觀匹配。個體工作價值觀是個體評價工作價值、指導行為的準則,而組織價值觀是組織所期望的成員行為的規范[19]。新生代農民工是在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的崇拜、盲從權威、參與意識弱等個性特征來說,他們具有受教育程度高、原則性強、強調個體權利,有一定的參與要求,追求公平、民主[20]等特征和更為鮮明的價值取向。在組織和工作中,自我意識強烈、個性豐富,喜歡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理想和意愿行事,思維活躍,有更為積極的主觀認知和自我選擇,并不失反叛精神。因此,當新生代農民工與組織的核心價值觀匹配時,他們會充滿熱情地投入工作,在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中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在此過程中,他們會投入和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感,產生更多的滿足感。相反,當兩者不匹配時,會產生矛盾和摩擦,使個體產生更多的負面情感和不滿意。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a工作價值觀匹配對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情感具有正向作用;
H1b工作價值觀匹配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具有正向作用。
2.個人需求—組織供給匹配(N-S匹配)與工作幸福感的關系
N-S匹配,是指組織的供應系統是否與員工的各種需求相適應[21]。與父輩“謀生、賺錢”的目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到城市工作,更多是抱著尋求發展機會,脫離農民身份轉換為市民的期許[22]。為了能融入城市,在物質、精神消費上向城市人看齊是他們最基本的追求目標,而進入企業是他們融入城市的第一站。因此,組織所能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他們物質與精神消費的重要來源和基本保障,所以他們十分看重組織供給。當N-S匹配時,有助于新生代農民工滿足盡快成為“城市人”的心理需求,他們會將這種滿足歸結于組織的供給,從而在工作過程中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感;同時認為自己的付出得到了組織認同和相應的回報,對工作產生較高的滿意度。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a N-S匹配對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情感起到顯著正向影響;
H2b N-S匹配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起到顯著正向影響。
3.組織要求—個人能力匹配(D-A匹配)與工作幸福感的關系
D-A匹配是指員工是否擁有完成任務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能力,即個體所具備的KSAs與組織的要求是否一致[21]。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和個人擇業意向的轉變,新生代農民工逐步從職業技能要求相對低的城建等傳統行業逐步轉向對技能要求較高的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23],因此個人能力是否能滿足組織要求顯得十分重要。已有研究發現,D-A匹配會減少工作中的緊張、壓力等負性情緒產生,并與工作滿意度有緊密相關性[24]。當新生代農民工擁有專業技能,能夠更好地適應、勝任和完成工作任務時,更可能得到組織的認可、表揚與獎勵,進而促使更多積極情感的產生和更高的工作滿意度。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a D-A匹配與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情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H3b D-A匹配與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二)工作意義在個人—組織匹配與工作幸福感間的中介關系
1.個人—組織匹配與工作意義之間的關系
工作意義是指個體根據自己的價值體系和價值標準,對工作目標的價值認知,是員工關注自己的工作并感覺工作對自己的重要程度[25]。當員工認同工作目標及其產生的價值時,他們就會更加關注和投入工作,并感知到工作對自己的重要性。從工作價值觀匹配維度看,員工會根據工作角色的要求與自身價值觀、信念和行為準則是否一致來評估自己工作的意義[26]。當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匹配時,會較好的融入到組織中,認同自己的工作內容與組織要求,以及工作所產生的價值,從而會更好地理解工作意義。從N-S匹配維度看,已有研究顯示,工作的首要目的是人們通過個人勞動換取物質生活保障,同時注重自我發展、組織認同等精神層次的需求[27]。組織提供的報酬、晉升、發展機會等是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最直接、最明確地肯定方式,當需要的物質及精神需求能被組織供給滿足時,他們可以感知到工作帶來的收益與認可,也會體驗到工作意義。從D-A匹配維度看,Chalofsky[28]指出個體勝任力是構建有意義工作的影響因素,能力匹配是員工能夠較快適應各種工作要求的基礎條件。當新生代農民工具備的能力與工作的要求相匹配時,他們會更好地完成工作,當看到工作所產生的貢獻價值時,則會感受到工作成就感和所從事工作的意義。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a工作價值觀匹配正向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意義感知;
H4b N-S匹配正向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意義感知;
H4c D-A匹配正向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意義感知。
2.工作意義的中介作用
研究證實工作意義對員工工作態度有重要影響[25],工作意義有助于激發出員工工作熱情等積極情感,知覺到工作價值和重要性的個體會有較高水平的工作滿意度[29]。新生代農民工基于對城市生活的向往選擇外出打工[30],當體驗到工作不僅是掙錢的工具,更是個人發展的手段,是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是改變生活狀態和人生道路的途徑時,他們就會認可工作的意義,對工作抱有更大的熱情,也會在工作中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感和對工作的滿足感。
基于上述論證,新生代農民工個體與組織越匹配,其感受到的工作意義越強,從而其感受到的積極情緒越多,工作滿意度越高。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5a工作意義在工作價值觀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H5b工作意義在工作價值觀匹配與工作滿意度之間起中介作用;
H5c工作意義中介了N-S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的關系;
H5d工作意義中介了N-S匹配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系;
H5e工作意義對D-A匹配與積極情感的關系起中介作用;
H5f工作意義對D-A匹配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起中介作用。
(三)個人現代性在個人—組織匹配與工作幸福感之間的調節作用
企業員工在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對其行為具有調節作用。在以往研究中,將具有遵從權威、安分守成、被動接受現實等特征的傳統性價值取向認為是最能描述中國人性格與價值取向的概念之一[31]。但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傳統性觀念形成的基礎逐漸削弱,中國人現代性價值取向越發明顯并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一些研究發現,員工現代性差異成為員工效能與組織行為關系的重要調節變量[32]。現代性主要表現為平等開放、獨立自主、樂觀進取、兩性平等和唯情傾向等[33]。新生代農民工經歷了由鄉村到城市的轉化過程,獲得了豐富的社會閱歷,開拓了眼界,降低了行為的保守性和心理的封閉性,具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更加趨向現代性[34]。但中國地域廣闊,區域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差異極大,來自不同區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現代性也會呈現多元化態勢。個人現代性的差異必然會在工作幸福感的體驗中產生重要作用。
首先,個人現代性強的新生代農民工少有對領導者的盲從和對傳統權威的依賴[35],更注重個人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的契合程度。當兩者匹配時,組織的價值觀與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轉變為自我的價值體現,因而更能投入工作,體驗到更多的工作幸福感。而現代性弱的個體更傾向于遵從權威,即使與組織價值觀不匹配,也會屈從于組織的規范與要求,并對其幸福感的負面體驗也不會大。其次,現代性強的個體更傾向于具有超前的消費觀念,從而更傾向于追求享樂、炫耀性消費等生活方式[36]。對現代性強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N-S匹配時組織的供給更能夠滿足他們“符號化”的消費需求,因而感知到的工作幸福感更強。再次,現代性強的個體更不滿足于將世代相傳的生活經驗和生產技術作為謀生的基本手段,他們更加渴望個人成就,對自身的發展有更高的期待,更加期望自己的能力能夠勝任組織要求。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城市中的人脈資源,只有依靠個人奮斗才能獲得發展機會。因此,對現代性強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個人能力與組織要求越匹配,他們的工作幸福感越強。
綜上所述,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的差異會影響個體對幸福感的感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a個人現代性正向調節工作價值觀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的關系;
H6b個人現代性正向調節工作價值觀匹配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系;
H6c N-S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的關系受到個人現代性的正向調節作用;
H6d N-S匹配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系受到個人現代性的正向調節作用;
H6e個人現代性對D-A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的關系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
H6f個人現代性對D-A匹配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系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
通過以上論述,本研究在個人—組織匹配理論基礎上提出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收集
鑒于新生代農民工目前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制造業[23],本研究選取了13家服務業和8家制造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為調研對象。在天津和石家莊兩個城市共發放700份問卷。這兩個城市對沿海城市和相對內陸的城市具有代表性。回收627份,剔除填寫不完整、具有明顯“Z”字形及測項多為極端值1或7、中間值多為4的無效問卷后,最終獲得有效問卷514份,其中服務業265份、制造業249份,有效回收率為73.43%。調研樣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調查樣本的特征分析
(二)變量的測量
“個人—組織匹配”量表采用Cable&DeRue[16]編制的員工自陳式量表,共包含價值觀匹配、需求匹配和能力匹配三個維度,9個條目;“工作意義”量表采用Sprcitzer編制、李超平[25]修訂的量表,包含3個條目;“個人現代性”使用Farh、Earley與Lin[32]開發的5條目量表;工作幸福感中“積極情感”維度的測量使用Watson等[37]編制的“積極情感消極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其中消極情感采用反向計分;“工作滿意度”維度采用Tsui和Egan[38]開發的6條目量表測量。各量表測量題項均以Likert7級刻度衡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另外,將性別、學歷和任職年限等設置為控制變量。
為了確保被調查者能夠準確理解并順利填寫問卷,在大樣本調研之前,針對問卷題項的表達及問題設置方式等,我們分別選取天津地區的兩家制造業和兩家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了四組深度焦點訪談,并根據訪談結果對相關題項進行修正。
四、數據分析與研究結果
(一)信度和效度檢驗
使用SPSS11.5軟件檢驗調研數據信度,各變量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α均大于0.7;運用LISREL8.7統計軟件對各變量數據做驗證性因子分析(CFA),驗證其結構效度,結果顯示,χ2/df在1~3之間,RMSEA小于0.08,NFI和CFI等指標均大于0.9,GFI接近0.9。具體數值如表2所示。各項指標達到可接受水平,調研數據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2 量表信度、效度分析
(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依據周浩和龍立榮提出的檢驗原則[39],采用加入一個共同方法因子的方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含有共同方法因子的結構方程模型并沒有比不含共同方法因子的結構方程模型顯著變好(Δdf=18,Δχ2=41.09,p>0.0001)。由此可知,共同方法偏差并未顯著影響到本研究的研究結論。

表3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
(三)個人—組織匹配對工作幸福感影響作用的檢驗
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方法檢驗個人—組織匹配對工作幸福感的影響作用,檢驗結果見表4。數據表明個人—組織匹配三個維度對積極情感與工作滿意度均起到顯著正向影響,H1a、H1b、H2a、H2b、H3a、H3b得到支持。

表4 主效應檢驗結果分析
(四)工作意義的中介作用檢驗
采用Baron和Kenny[40]提出的檢驗步驟檢驗工作意義在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與積極情感、工作滿意度之間的中介作用關系。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個人—組織匹配、工作意義和工作幸福感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第一,個人—組織匹配對工作意義具有正向作用,如模型1所示,3個自變量(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與中介變量工作意義顯著相關(β=0.346,p<0.001;β=0.210,p<0.001;β=0.222,p<0.001),因此假設H4a、H4b、H4c得證;第二,工作意義在個人—組織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起到正向中介作用,通過模型2、模型3、模型4可以看出,3個自變量(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與積極情感顯著相關,并且在加入中介變量后,價值觀匹配、N-S匹配對積極情感的回歸系數值的顯著性有所下降(由模型2中的β=0.235,p<0.001、β=0.245,p<0.001降為模型4中的β=0.173,p<0.001、β=0.207,p<0.001),但仍然顯著,表明工作意義在價值觀匹配、N-S匹配與積極情感之間起著部分中介的作用;D-A匹配在加入中介變量后,對積極情感的回歸系數由顯著變為不顯著(由模型2中的β= 0.116,p<0.01降為模型4中的β=0.076,p>0.001),表明工作意義在D-A匹配和積極情感之間起著完全中介的作用。因此假設H5a、H5c、H5e得到驗證;第三,同理,通過模型5、模型6、模型7可以看出,工作意義在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與工作滿意度之間均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設H5b、H5d、H5f得到驗證。
(五)個人現代性的調節效應檢驗
相應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后,運用SPSS11.5驗證個人現代性的調節作用,具體結果見表6。從模型2、模型3可以看出,個人現代性在價值觀匹配(β=0.118,p<0.01)、N-S匹配(β=0.143,p<0.001)對積極情感的影響上有正向調節作用;從模型6、模型7可以看出,個人現代性在價值觀匹配(β=0.085,p<0.05)、N-S匹配(β=0.062,p<0.05)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上有正向調節作用;但模型4、模型8數據顯示個人現代性在D-A匹配對積極情感及工作滿意度的影響上未表現出調節作用。為進一步顯示個人現代性的調節效應,根據Aiken和West[41]推薦的簡單坡度分析程序,繪制圖2、圖3。

表6 個人現代性的調節作用

圖2 個人現代性在價值觀匹配對工作幸福感中的調節效應

圖3 個人現代性在N-S匹配對工作幸福感中的調節效應
五、結果討論、理論貢獻與管理啟示
(一)研究結論
研究結果證實基于個人—組織匹配的視角可以較好地解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理。主要結論如圖4所示:①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是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②工作意義在價值觀匹配對工作幸福感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工作意義在D-A匹配與積極情感關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其他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個人現代性在價值觀匹配、N-S匹配對工作幸福感的影響關系中起到正向調節作用,但在D-A匹配對工作幸福感影響關系中沒有顯示調節作用。

圖4 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的影響機理模型
(二)研究結果討論
(1)當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相匹配時,可以通過引發他們對工作意義的感知,進而促使其工作幸福感的產生。這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個性和價值觀有直接關系。較老一代農民工,他們普遍具有較為鮮明的價值取向和個性彰顯。當個人與組織價值觀相一致時,他們容易在組織中找到歸屬感,進而認同組織,發現工作的意義,并在工作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幸福感;相反,當與組織的價值觀不匹配時,容易與組織發生情感沖突或心理矛盾,則無工作幸福感可言。
(2)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與組織供給匹配時,更容易感知工作幸福感。在此過程中,員工感知到的工作意義起到中介作用。對許多企業員工而言,能否在組織和工作中得到期望的回報可能是他們最為關心的事情。特別是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能否獲得滿足生存和發展需求的“組織供給”,是他們能否在職業生涯初期和初入城市時立足的根本。這一點與城市新生代員工有所區別,后者雖然也有初入職場的困惑,但少有身份轉變的沖擊。表4數據也顯示在影響工作幸福感的個人與組織匹配的三個維度中,N-S匹配影響最為重要(β=0.245,p<0.001;β=0.485,p<0.001)。另外,只有當工作中得到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回報時,他們才能發現工作的意義,體驗到幸福感;同時也可在一定程度彌補遠離家庭和親情缺失引致的失意,感到情感的滿足。
(3)D-A匹配通過工作意義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了被調查者的積極情感及工作滿意度。這與以往國內有關研究認為“D-A匹配更多的是站在組織的角度去強調對員工的要求,所以不被員工考慮,因此D-A匹配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作用不顯著”[11]的結論有所差異。這可能是由以往的研究對象多是城市員工,與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觀、工作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別所致。城市員工把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看作是與生俱來的事情,而新生代農民工則把外出務工當作實現從農民到工人乃至更高層次命運轉變的機遇。城市員工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但農民工想要扎根城市,沒有強大的社會網絡支持,只有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另外,數據顯示工作意義在D-A匹配與積極情感關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這說明當員工技能與組織要求匹配時,不會直接產生積極的情感,只有意識到這種匹配導致的價值時,成就感、愉悅感等積極情感才會油然而生。
(4)研究數據顯示人與組織匹配的三個維度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均大于對情感取向的影響(詳見表4各路徑系數)。說明人與組織匹配程度對被調查者認知取向(滿意度)的影響強度大于潛意識過程結果(情感取向)。這可能是因為情感更容易受到工作中其他因素的“瞬時”影響,而工作滿意度是一個受多因素或較長時間影響的更為復雜的思考過程。
(5)個人現代性對個人—組織匹配與工作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主要表現為個人現代性對價值觀匹配、N-S匹配與工作幸福感之間的調節關系。這說明現代性強的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平等開放、獨立自主和積極進取,價值觀、N-S越匹配,他們越能感知到組織對自己的認可以及在組織中的發展空間,所以越能體會到工作中的幸福;而現代性弱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更具有老一代農民工的某些特征,例如遵從權威、安分守成、聽從組織或習慣接受被外界或他人的角色安排等。因此,即使與組織價值觀及N-S不匹配,也會被動接受,不主動自我調整,而且不會產生過于強烈的負面情感和認知感受。
調查分析顯示個人現代性對D-A匹配與工作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并未起到調節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某些現代性強的新生代農民工過多強調自己能從組織一方的獲得,而不是自己的付出,因此,即使D-A不匹配,但只要能得到更多的回報,他們就可以感到快樂與滿意。因此在統計學上未顯示調節作用。
(三)理論貢獻
以往對幸福感的研究多為個體特征、客觀環境等單一性因素的靜態影響范式,研究對象多為老年人、大學生、青少年和城市居民,鮮有對農民工這一特定職業群體工作幸福感的關注,更未涉及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影響機理的實證研究。本研究基于個人—組織匹配理論,從互動心理學視角揭示了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影響機理和主要特征,理論貢獻與創新主要有以下幾點:①揭示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其工作的組織匹配,是其工作幸福感知的重要影響因素;②已有的個人—組織匹配的研究中,大多從單個維度或整體上來探討匹配對態度及行為的影響,鮮有將三個維度納入同一模型進行比較的分析,本研究同時探究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對工作幸福感的綜合影響作用,研究結果更為精準;③將工作意義引入個人—組織匹配對工作幸福感的作用機理中,實證證明對工作意義的認同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之間有著很重要的聯系;④為體現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和時代特點,引入個人現代性變量,考量了現代性對新一代年輕農民工個人—組織匹配對工作幸福感的調節作用,進一步驗證了近年來研究者較為關注的個體價值觀對個體態度和行為的重要影響這一議題;⑤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的研究,再次驗證了個人—組織匹配理論所具有的普適性及加入情境和主體因素之后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性。
(四)實踐作用
基于新生代農民工“三高一低”的顯著特征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迫切需要,組織可以采取以下管理措施,以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幸福感:①轉變以往對待農民工的觀念和方式,提升新生代農民工與組織在價值觀層面上的契合度;②企業在制定激勵政策時,要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特征,有的放矢地提供相應物質及精神激勵,比如在新生代農民工最關心的工作條件、工資待遇以及亟需改善的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文化娛樂等方面入手,著力滿足其“立足城市”的心理和生理需要;③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的需求,企業在招聘員工和進行組織社會化的過程中,應對員工的技能和能力的適應性給予更多關注,及時給員工提供相應的培訓及學習機會,并使員工能力的提升同員工的個人利益和職業發展相結合;④無論從事什么種類和層次的工作,組織和管理者要引導新生代農民工擺脫“賺錢”的機械目的,讓其了解工作的價值和重要性,因為只有當他們認同了工作的意義,才會把工作作為展示自身價值的舞臺,在工作中也才會體會到更多的滿足和幸福,從而才能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工作中,并產生更大的工作績效。
新生代農民工可通過如下途徑,使工作更加愉快、滿意:①在尋找和選擇工作的過程中,要充分了解企業的相關信息,與自己的期望相比較,從多個方面綜合考慮個人與企業的匹配程度,從而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②在進入企業以后,應通過積極詢問工友、參加入職培訓和各項活動等方式,了解企業核心價值觀;積極參加職業培訓,提升工作技能,適應工作規范,從而盡快融入企業。③另外,在工作過程中應積極挖掘從事崗位的意義及對組織與社會的貢獻,而不僅僅是將其作為謀生的工具,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工作中的樂趣,進而增加工作愉快感和滿意度。
此外,社會應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職業群體的關注,不僅要關注他們的就業和職業發展,更要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特征,構建更加公平的公民社會的微觀基礎。
(五)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數據是在同一時間收集的,這種截面數據分析還不能夠嚴格的表明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未來可考慮通過縱向數據或跟蹤研究,對問題做更進一步的假設檢驗;其次,個人—組織匹配所包含的價值觀匹配、N-S匹配、D-A匹配三個維度的匹配可能不是同步的,另外這種匹配可能是“赤字”也可能是“超支”[14],即會有不同方向上的程度差異。對不同組合及匹配的方向性對員工工作幸福感的影響,可作進一步的深化研究。
[1]彭怡,陳紅.基于整合視角的幸福感內涵研析與重構[J].心理科學進展,2010,18(7):1052-1061.
[2]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34-43.
[3]Wright T A,Cropanzano R.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Job Performance:A Fresh Look at an Age-old Quest[J].Organizational Dynamics,2004,33(4):338-351.
[4]徐細雄,未宇.組織支持契合、心理授權與雇員組織承諾:一個新生代農民工雇傭關系管理的理論框架——基于海底撈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12):131-147.
[5]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EB/OL].(2010-03-24)[2014-02-09].http://www.tjcn.org/jjfx/201003/1042 6.htm.
[6]沈蕾,成志明.基于生活方式的新生代農民工群內細分研究[J].軟科學,2013,27(9):110-116.
[7]陳燦銳,高艷紅,申荷永.主觀幸福感與大三人格特征相關研究的元分析[J].心理科學進展,2012,20(1):19-26.
[8]張興貴,郭揚.企業員工人口學變量、工作特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工作壓力的作用[J].心理科學,2011,34(5):1151-1156.
[9]Phillips D R,Cheng K H C,Yeh A G O,et al.Person-Environ?ment(P-E)Fit Model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Persons in Hong Kong[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9,42:221-242.
[10]莊璦嘉,林惠彥.個人與環境適配對工作態度與行為之影響[J].臺灣管理學刊,2005(5):123-148.
[11]Kristof-Brown A L,Zimmerman R D,Johnson E C.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s’Fit at Work:A Meta-analysis of Per?son-job,Person-organization,Person-group,and Person-su?pervisor Fit[J].Personnel Psychology,2005,58:281-342.
[12]Jung Y,Takeuchi N.Relationships among leader–member exchange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work attitudes in Japa?nese and Korean organization testing a cross-cultural moder?ating effec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4,5(1):23-46.
[13]王忠,張琳.個人—組織匹配、工作滿意度與員工離職意向關系的實證研究[J].管理學報,2010,7(3):379-385.
[14]張興貴,羅中正,嚴標賓.人—環境(組織)匹配視角的員工幸福感[J].心理科學進展,2012,20(6):935-943.
[15]Chatman J A.Match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Public Accounting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36:459-484.
[16]Cabled D M,Derue D S.Th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te Validity of Subjective Fit Perception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87:875-884.
[17]Kristof A L.Person-organization Fit: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Its Conceptualizations,Measurement,and Implications[J].Personnel Psychology,1996,49:1-49.
[18]趙慧娟,龍立榮.個人-組織匹配與工作滿意度——價值觀匹配、需求匹配與能力匹配的比較研究[J].工業工程與管理,2009,14(8):113-131.
[19]趙慧娟,龍立榮.價值觀契合、需求契合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9(10):37-44.
[20]宋陽,閆宏微.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與價值觀變遷研究述評[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4(3):67-72.
[21]Edwards J R,Cable D M.The Value of Value Congruenc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9,94:654–677.
[22]楊春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0(4):80-84.
[23]鄭慧娟.我國新生代農民工轉移、就業的主要特點和趨勢[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1,32(4):409-413.
[24]Jansen K,Kristof-Brown A.Toward a Multi-demensional Theory of Person-environment Fit[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6,28:193-212.
[25]李超平,田寶,時勘.變革型領導與員工工作態度:心理授權的中介作用[J].心理學報,2006,38(2):297-307.
[26]賈佳,陳維政.心理授權對員工角色壓力的影響作用分析[J].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2):69-74.
[27]尚玉釩,馬嬌.“工作意義”的變遷研究[J].管理學家:學術版,2011(3):59-67.
[28]Chalofsky Neal.An Emerging Construct for Meaningful Work[J].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2003,6(1):69-83.
[29]陳浩.工作倦怠的成因與對策[J].前沿,2010(10):103-105.
[30]韓長賦.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是個重大問題——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調查與思考[N].光明日報,2012-03-16(07).
[31]彭正龍,趙紅丹,梁東.中國情境下領導—部屬交換與反生產行為的作用機制研究[J].管理工程學報,2011,25(2):30-36.
[32]Farh J L,Earley P C,Lin S C.Impetus for Action:A cultural Analysis of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3):421-444.
[33]楊國樞.華人心理的本土研究[M].臺灣:桂冠圖書公司,1991.
[34]蔡志海.流動民工現代性的探討[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43(3):65-69.
[35]洪瑜,林少真.個人現代性理論研究述評[J].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2(1):115-120.
[36]呂巍,王麗麗,江麟.個人傳統性/現代性對信用負債的影響研究[J].管理世界,2009(12):106-119.
[37]Watson D,Clark L A,Tellegen A.Development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The PANAS Scal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54(6):1063-1070.
[38]Tsui A S,Egan T D.Being Different:Relational Demography and Organizational Attachment[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2,37(4):549-579.
[39]周浩,龍立榮.共同方法偏差的統計檢驗與控制方法[J].心理科學進展,2004(12):942-950.
[40]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6):1173-1182.
[41]Leona S Aiken,Stephen G West,Raymond Reno.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M].New?bury Park,London:Sage,1991.
[責任編輯:歐世平]
A Research on Job-related Well-being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ZHAO Bin1,ZHU Peng1,LI Xin-ji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2.Business School,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paper makes a study on the job-related well-be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microscopic enterprise lev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The results show that,through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514 questionnaires,three dimensions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fit,individual need-organization supply fit,work requirement-individual ability fit)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occupational well-be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and work significance perceiv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a mediating effect.In addition,the individual modern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namely individual val?ue orientation,positivel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erson-organization fit,mainly reflected by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fit and individual need-organization supply fit playing the role in the job-related well-being.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ob-related well-being;person-organization fit;meaning of work;individ?ual modernity
F272.92
A
1007-5097(2014)08-0124-08
●人力資源
10.3969/j.issn.1007-5097.2014.08.023
2014-01-0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372095);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3YJA630137);天津市科技發展戰略研究計劃項目(13ZLZLZF02800)
趙斌(1972-),男,河北武強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朱朋(1987-),男,河北容城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李新建(1953-),女,河北饒陽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