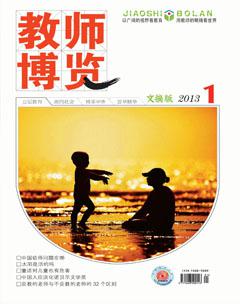我的老師們
王安憶
這半輩子,雖未上過幾日學堂,老師卻很有幾位在腦海中或深或淺地留下印象,不曾忘卻。
入小學一年級,是一位姓徐的老師教導,當時覺得她頗高大,現在想來卻是身材小巧的。對老師的尊重和敬仰似乎是無條件的,或許是上千年來“師道”無形的遺傳,以至有別班的小朋友指出那老師外形上一項不足的時候,我氣得幾乎要昏過去,深覺受了傷害。我們自始至終不知道老師的名字,打聽老師的名字便像是褻瀆,然而那名字又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像是很神圣的秘密。她對我們是至高無上的,即便是平常的一句話,在我們也成了不可違抗的圣旨。在她當著眾人嘲笑我一個習慣性的不良動作時,我的傷心是不可言喻的。長大以后,我深知她一無惡意,可是當時,我對她卻起了一種畏懼的心理,再不敢去親近,不敢愛她了。每天早上,我們都在老師的帶領下,排隊站在街心花園里進行升旗儀式。莊嚴的國歌奏響了,國旗徐徐上升,忽然從人行道上飛跑來一個小女孩,撲在徐老師身上,大叫“媽媽”。徐老師的臉一下子紅起來,要笑又忍住了,別著頭,看也不敢看孩子一眼。以后的日子里,隨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這個情節,老師一次比一次顯得年輕起來,于是,那對我不經意的傷害也逐漸變得可以原諒了。
升上二年級時,換了一位張老師。她的名字一上來就赫赫然地印在我們的作業本上。大概是因為我們長大了一點,老師的名字引不起更多的神秘感。現在回想,她是頗不漂亮的。然而,小學生對老師,就好比孩子對媽媽一樣,從不會想到“漂亮”或“不漂亮”。老師就是老師,至多再有個名字,便完了。她是一個能干的老師,自從她來了我們班,我們班便在衛生、紀律、墻報等等方面躍為先進,得來一些獎狀;她又是那么活潑,永遠令我們感到親切。不久,我們滿九歲了,要建隊了。選舉中隊干部時,我無限委屈地被這位老師武斷地拉了下來,雖然,我得了滿票,卻要讓位給一個只得了零票的女生。至今也不能徹底明白,那位女生為何如此不得人心。只記得她乖巧過人,頗得老師器重,抑或正因為如此而引起的逆反心理吧!當時群情激憤,事情很難收場,張老師只得把所有優秀的學生集中在一間小辦公室里開會。這待遇不是每個人可以企望得到的,參加會議的同學自有一種榮譽感和責任心,認識到應以大局為重,與老師同心同德。事情過去了,可對老師的失望卻永遠不能消除地存在了心里。
在我們那個年紀,對老師的要求近乎是苛刻的,老師永遠不是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出現,而總是真理、公正、正義、覺悟的化身。我們的問題,永遠期待著在老師那里得到解決和回答,如果得不到,便憤怒透頂。然而,事實上卻常常得不到。因此,某一位老師扯了某一位隊員的紅領巾,某一位老師與某一位老師頗不嚴肅的調笑,某一位老師錯怪了某一位學生,某一位老師春游時帶了三個荷包蛋而不是兩個,到了小學開展“文化大革命”時,全成了大字報上要命的內容。文理不甚通順的大字報雪片似的向各位老師撲面而去。
從此,一個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的時代開始了。
事情果真是這么奇怪地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亂哄哄地進了中學以后,第一次見到老師,無冤無仇的,我便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那老師好好地來問我:“叫什么名字?”我不但不回答,還朝他翻眼。至今也說不明白是什么東西在作祟。總之,從那一天起,我與老師間便開始了一場莫名其妙卻又針鋒相對的角斗。
一次開大會,因為沒有呼口號,嚴格地說是沒有揚起胳膊,老師便請來工宣隊當眾呵斥,罵出許多不堪入耳令人生疑的話,罵完之后揚長而去,不負任何責任。老師的表情甚是微妙,并無笑容,卻掩不住得意,他知道自己是不能這樣羞辱學生的,而工宣隊能。我們則明白,是無法向工宣隊要求澄清道歉的,只能找老師。當我們和這位老師面對面地坐下來的時候,才發覺彼此都是那么孤獨無助。
后來,就到了林彪搞一級戰備的日子里。我們正在鄉下參加“三秋”,這會兒就決定不返上海繼續在鄉下堅持戰備。當時,我在學校小分隊里拉手風琴,我是不情愿在小分隊的,因為我在班上有個極要好的同學,假如我們不能在一起生活,農村的日子對我們將是不堪忍受的。負責小分隊的一位江老師居然答應我白天在小分隊活動,晚上派人送我回班級所在的生產隊睡覺。他從不曾爽約,即使實在派不出人,他也要自己親自送我。到了戰備的那一刻,大家想家的情緒便不可抑制地強烈起來,并且伴隨著一種深深的絕望,那家像是再也回不去了,我總是哭了又哭。永遠不會忘記,在這個絕望的時刻,江老師借口修理手風琴,讓我回上海三天,我一個人提著沉重的手風琴,回到了家。家里只有老保姆帶著年僅五歲的弟弟,爸爸、媽媽、姐姐和我的床全揭了起來,露出棕繩綁的床繃,一派凄涼。可是后方尚在,心里畢竟安穩了許多。三天之后,我如期回到鄉下,下了長途汽車,我徑直去了小分隊。
我們和老師一起度過了“戰備疏散”的三個月,他和我們一起步行十幾里買大餅油條解饞,和我們一起用醬油拌粥下飯。有一次,我看見他在對著墻角擤鼻涕,居然也沒覺到太多的失望。有時高興起來,我們就直呼他的名字,他也很自然地答應。而另有一些時候,我們卻極其莊重地喚作“江先生”,盡管“師道”已經徹底粉碎。
三年中學,就這么吵吵嚷嚷、哭哭笑笑地過來了,迎接了“一片紅”的插隊落戶。我的插隊“喜報”,就是這位江老師來貼的,我不在家,當時沒碰上。之后,也沒有機會再碰上過他,心里便越來越覺得他那次是來告別的。
與老師日益增長的接近中,老師越來越向我們顯示出一個普通人的素質,于是便令人有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失望,然而,隨著這失望,“老師”的形象卻也日益真切起來。當我長到也應為人師表的年紀,方才感到,做個老師是極難極難的,而我們對老師的要求也不甚公正。老師亦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對老師的尊重,首先是對人的尊重。或許把“師道”合并于“人道”,事情倒會簡單許多。
一次,參加虹口區三中心毛蓓蕾老師主持的“兒童團”入團式,宣誓的時候,毛老師站在一群年僅六歲的孩子中間,莊嚴地舉起握拳的右手,鮮紅的領巾映著她蒼蒼的白發,我的眼淚涌了上來。這莊嚴的一刻令我銘記終生。我終于明白,老師是一個平凡的人,亦是一個偉大的人。
(江上風清摘自《新民周刊》2012年第26期)
責編: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