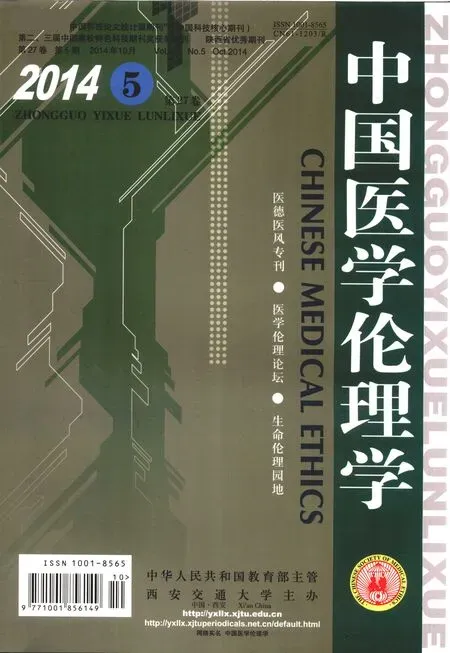從醫護倫理看近代中國醫院與家庭的多重變奏*
張婷婷,李久輝
(上海中醫藥大學社科部,上海 201203,ttzhangsh@163.com)
從醫護倫理看近代中國醫院與家庭的多重變奏*
張婷婷,李久輝**
(上海中醫藥大學社科部,上海 201203,ttzhangsh@163.com)
通過分析西醫對中國家庭在醫學護理中的作用經歷了拒斥質疑-認同移植-主動利用的發展過程,指出了醫療空間的轉變客觀上促使了醫護倫理轉換。認識到西醫制度與中國家庭、地方倫理模式的相互妥協與契合是西方醫療系統進入并內化于中國人生活狀態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近代醫院;醫學倫理;醫療社會史;社會服務;轉變
西醫傳入中國,打破了中醫一統的局面,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藥觀的多元化格局,也引發了從家居到醫院的醫療體驗變化。醫療空間的轉換不僅表征了中西醫醫理的區別,更隱含了醫護倫理的差異。
1 近代中西醫不同的醫療空間和醫護倫理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醫院與近代西方醫院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古代中國,醫事制度完全是圍繞王權的需要而設置。雖有太醫院設立,但以皇室和貴族為服務對象。民間社會的醫療空間主要由私人運作。醫生以個體化形式獨立而分散執業,不管是中醫郎中被請至家中的上門施診,還是醫生坐堂開店或懸牌應診的家居式行醫,醫療空間多與家居環境連為一體。病人在家庭氛圍的親切感中接受診治,醫療單位以“醫家”而非“醫院”的形式出現。因此中國傳統醫療特征是病體的醫治雖依靠外請的醫生,但護理程序的進行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家庭是最基本的醫療單位和護理空間。
中國以家為主導的醫療格局出現,是與傳統“家本位”的倫理思想緊密相連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論形象地解釋了中國人社會關系是按照親疏遠近來確立,即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離中心越近關系越親,越遠關系越疏。[1]因而家庭或家族的人被認為最值得信賴和托付,病人由最親近的家屬來看護有著毋庸置疑的倫理正當性。
近代西方醫院作為一種醫療體制,發端于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盛行年代。醫療空間最初脫胎于宗教空間。早期的醫院是教堂或修道院的外延機構。17世紀以前,醫院主要收留窮人、流浪者、殘疾人、孤兒、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其對病人的宗教關懷(care)遠遠大于對其救治(cure),醫療救助的目的為了讓病人皈依基督。
中國傳統家庭治療模式的顯著特征是家庭控制診斷和決定治療方案,病家在治療過程中居于主動地位。醫生在病人親屬的目光注視下完成診治,并且病家可以自由選擇醫生。為了獲得最佳治療效果,病家常常多次試醫、擇醫,并參與治療方案磋商。家屬(一般來說是家長)握有最終決定權。湘雅醫院創辦者,美國傳教士醫生胡美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有篇名為“家屬控制著醫療”的記述,描述了家屬擁有判斷病情、決定治療方案的生動案例,“他們(家屬)是陪審委員會,我只是被安排在臺上的證人”,其職責就是做出家人認可的診斷結果。[2]與此相對應的,以個體化方式行醫的醫家為自身聲譽和生計考慮則選擇自認為有把握的病人進行醫治。因此“擇醫而治”與“擇病而醫”反映了以家庭為主導的醫療模式中的醫患倫理。
而在西醫委托理念下,醫生被賦予值得信賴的身份,病人需對醫生有絕對信任。在西醫看來,唯有醫生和病家有相互委托的默契,醫生握有治病主體的權力,而且病家對醫生有“信仰”,病家才能要求醫生對病人負責任,責任、權力與信仰,三者相互支持、密不可分。[3]在教會醫院發展過程中,即使后來宗教的委托理念越來越淡,但醫生的主導地位卻進一步強化,一個重要原因是福柯所謂的“規訓”權力的出現。醫院作為重要的規訓場所,通過空間分配、活動編碼、時間安排等微觀技術,以及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和檢查等手段來規范、訓練、控制病人身體。因此,在醫院的醫療空間中,負責任的醫生和有信仰的病人成為西醫致力追求目標,也成為現代醫患倫理導向。
不同醫療空間實踐促成了中西醫各自醫護倫理,二者的倫理邏輯迥然相異。而近代醫院空間能否植入中國社會,不僅取決于醫學本身療效,醫院醫護倫理能否被認同和接收也是十分關鍵之影響因素。對中國家庭在醫護方面的作用,西醫傳教士最初持拒斥、質疑態度,但隨著醫療實踐的展開,情況發生了變化。
2 中國語境下醫院對家庭醫護倫理的妥協
隨著西醫在中國逐步建立起文化權威,他們有意識地教中國人如何扮演“現代病人”角色。而做一個“現代病人”的重要前提乃是接受醫院作為醫療主要場地。而委托理念與中國差序格局倫理的差異,使中國人根本無法接受將病人委托給陌生人予以照顧這種他們認為既無情又不妥的方式。中國人習慣的是在親情氛圍的協調下,疾病在自然的狀態下得到消除,后來被視為“迷信”的傳統習慣和草根倫理不僅不是醫術的敵人,反而可能是醫療本身的有機組成部分。且一旦現代醫療技術無法與鄉民的日常倫理保持一致,無數挖眼剖心的恐怖故事就由此想象出來。[4]中國近代史上層出不窮的教案沖突即是這一矛盾體現。
針對于此,西醫傳教士有意識在醫院中創造出病人療養的家庭式環境,設法保留或者模仿病人原有家庭環境及人際關系,從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的疏離感。當時有傳教士專門寫文章探討如何讓中國病人感覺更適應和舒服些,“我們經常看到婦女入院時忘了帶洗臉盆、梳子、洗臉毛巾、枕頭、衣物等等,這并非因為他們窮,而是因為剛到醫院感到陌生而激動,以至于把這些事置諸腦后。如果為她們準備好這些必需品,我想病人將很快感到醫院與家庭是一樣的,也許思想上會因舒適而有所觸動。”思想上的觸動有利于消除病人對醫院的恐懼感與陌生感。上文提及的胡美醫生在接受第一位住院病人時,在缺乏專業醫護人員的情況下,就讓病人的母親充任了護士角色。英國傳教士德貞在北京建立教會醫院時,有意將病床設計成中國北方家庭常見的炕的形式,“由磚泥砌成的平臺,蓋著席子,病人就睡在上面。冬天,由泥和煤制成的煤球將炕燒得火熱,炕下面埋有煙道以保持炕的溫暖,……根據不同的尺寸,每一個炕可睡上12到14人”。[5]一張病床容納十多位病人,雖從醫護科學來看極其不合理,但病人可能更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醫院中不僅病人家屬被允許陪護,甚至病人的一些迷信活動也得到默許,如在病床下燒紙錢驅魔逐妖,擺放貢品討好鬼邪等。
在中國傳統社會,家庭醫護具有毫無疑問的倫理優先性。但醫院作為陌生空間逐步嵌入中國社會后,為了獲得中國民眾認同與接受,不得不對中國家庭人際倫理關系作一定妥協、移植。如果說西醫傳教士最初是在醫院設施置備和日常管理方面,承認和迎合中國人的倫理觀念,那么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后,則是主動利用中國“家本位”倫理,將家庭及社區轉化為可利用的醫療資源。
3 醫院與家庭、社區的契合:以醫院社會服務部為例
中國傳統個體化行醫的中醫深入家庭,能較好地了解病人的生活環境和情感氛圍。但現代醫院中的標準化、統一化管理,使得醫生面對穿著統一病服的病人。病人的姓名被單調的就診號、病床號所代替,醫生無法獲得與患者病情有關的生活、精神、情感方面信息。20世紀初流行于西醫界的“社會服務”運動的興起是醫院主動尋求與家庭及社區地方倫理契合的表現。“社會服務”運動要旨是使醫院治療與家庭社區的資源相互配置發生作用。
“社會服務”運動與醫院社會工作在歐美興起有關。中國最早將專業社會工作引入醫療實踐領域,當推北京協和醫院。該院專門為困難患者提供了醫療救助服務機構——社會服務部。1921年,從小生活在中國、對中國人生活情感較為熟悉的美國人蒲愛德女士被洛克菲勒基金會選聘來籌建社會服務部。
蒲愛德最初擔心社工活動很難在中國推廣。她曾在一份報告中擔憂地寫道:“中國的家庭是否歡迎家訪,是否有足夠的社會福利機構以便可能對病人進行社會治療。”在工作中她發現,“盡管中國正式的福利機構比西方國家社區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數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說自發組織起來的福利機構比較多。從家庭到遠房的親戚都在分擔著大大小小的責任”。[6]她根據中國社會和文化實際情況加以本土化的工作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社會服務部主要接受醫院門診醫生介紹來的病人。這些病患通常被認為是除生理疾病以外,還需了解社會背景予以輔助治療。社會工作者隨后到患者家中探訪,與患者家庭成員進行談話,了解患者家庭環境、衣食與精神生活狀況、家庭成員的情感關系等,最后研究患病的原因是否與家庭或社會背景有關,并制定治療意見交給主治醫生。醫生據此及時重新評估最初治療方案,對不妥之處做出調整。對于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社會工作者會定期進行回訪,不斷了解患者最新病情與社會生活狀況,并及時反饋給醫生。當時醫院社會服務工作者認識到,對中國病人來說,患者家屬的合作、家庭因素對于疾病治療有重要影響。除北京協和醫院外,上海、南京、山東等各地教會醫院也相繼建立社會服務部。
從以上分析可知,早期醫院被引入中國時,醫院制度對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只是進行了相對被動的妥協。而20世紀初醫院社會工作興起后,醫院開始積極主動地適應并利用中國家庭、社區倫理秩序,將之轉化為可資利用的醫療資源,以拓展醫院工作。這為醫院獲得更多底層民眾的認可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4 總結
近代來華西醫認識到醫療事業不能懸置空中,必須與本土文化相聯系,而依托中國人最信賴的地緣與親緣關系則是進入本土社會較為有效之路徑。西醫對中國家庭在醫護倫理中的作用經歷了拒斥質疑-認同移植-主動利用的發展過程。從近代中國醫院與家庭的多重變奏,我們不難發現西方醫療系統能進入并逐步內化于中國人生活狀態之中,西醫制度與中國家庭、地方倫理的相互妥協與契合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醫院的興起,促使了中國傳統的個體行醫模式開始向集團行醫模式轉變,這種轉變也對醫生的行為規范提出了新的倫理道德要求。在新體制下,醫生的責任心,不僅在于對個體病人的責任心,也包括對社會、對受聘醫院、對整個行業的責任感,也涉及同行之間的合作監督、技術公開等,這直接促進了近代醫學倫理學的發展。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27.
[2][美]愛德華·胡美.道一風同:一位美國醫生在華30年[M].杜麗紅,譯.北京:中華書局,2011:134.
[3]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和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系在民國時期的轉變[A]//李建民.生命與醫療[C].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477.
[4]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23~1985)[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76.
[5]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212.
[6][美]蒲愛德.醫務社會工作者工作與專業訓練[J].唐佳其,譯.醫藥世界,2007,(7):12-17.
〔修回日期2014-06-10〕
〔編 輯 李恩昌〕
The M ultiple Variations Between Chinese Hospital and Fam 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 edical Ethics in M odern History
ZHANG Tingting,LI Jiuhui
(Department of Society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201203,China,E-mail:ttzhangsh@163.com)
About the effect of western medicine in medical care,Chinese family had experienced developing process of from rejection to question identity and then to transplantation active using.From multiple variations between modern hospital and family,we can find that the compromise and accord ofwesternmedical system and local ethics is a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western medical system gradually internalizing into Chinese living.
Modern Hospital;Medical Ethics;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Social Service;Transition
R-052
A
1001-8565(2014)05-0706-03
2014-03-13〕
*項目資助:2012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重點項目(12ZS110);2011年上海市教委預算內課題(2011JW72)
**通訊作者,E-mail:lijiuhuiethique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