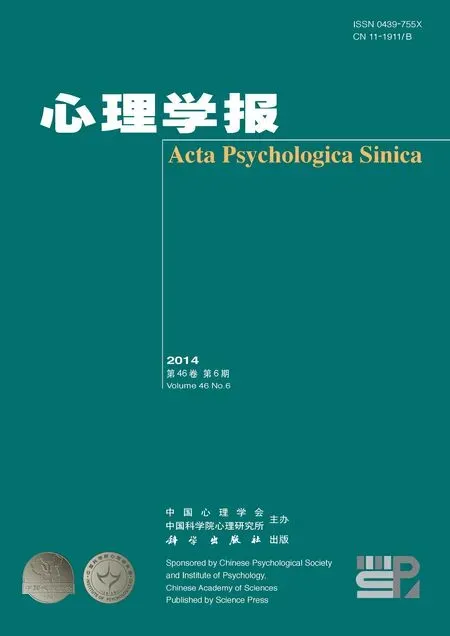不熟練中-日雙語者同形詞和非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王 悅 張積家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 北京 100872) (華南師范大學心理應用研究中心, 廣州 510631)
1 前言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功能。語言在人類的頭腦中如何表征?是心理語言學和認知神經科學關注的焦點。近年來, 隨著雙語者的數量不斷增多, 雙語研究越來越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雙語研究的核心問題是:雙語者的兩種語言在頭腦中如何表征?對于這一問題, 業已出現了大量的研究, 涌現出了許多理論。其中, 概念中介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頗為流行。這一模型認為, 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語義共同表征, 詞匯分離表征(French & Jacquet, 2004;Kroll & De Groot, 2006; Kroll & Stewart, 1994)。
雙語者的兩種語言具有共同語義表征的證據是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Semantic Priming Effect across Language)。以往研究大多采用跨語言語義聯想啟動范式(Associative/Semantic Priming Paradigm across Language) (Frenck & Pynet, 1987; Chen & Ng,1989)和翻譯啟動范式(Translation Priming Paradigm)(Altarriba & Basnight-Brown, 2007; Altarriba & Mathis,1992; Williams, 1994; Kroll & Tokowicz, 2001)。研究發現, 雙語者的兩種語言之間具有跨語言語義聯想啟動效應。當一種語言的啟動詞和另一種語言的目標詞具有語義聯想關系時, 對目標詞的反應會快于啟動詞與目標詞之間無語義關聯時。例如, 當啟動詞為“doctor” (醫生)時, 被試對目標詞“護士”的反應要快于啟動詞為“butter” (奶酪)時(Bonder &Massion, 2003; Duyck, 2005; Perea, Dunabeitia, &Carreiras, 2008)。翻譯啟動效應是指當啟動詞和目標詞分屬于兩種語言的翻譯對等詞時(如“狗”和“dog”), 被試的反應要快于啟動詞和目標詞不是翻譯啟動詞時, 甚至快于啟動詞與目標詞具有語義聯想關系時。翻譯啟動效應是跨語言語義聯想啟動效應的特例。與跨語言語義聯想啟動相比, 在翻譯啟動中,啟動詞與目標詞的語義聯想強度更容易控制。
以往研究大多使用視覺啟動范式, SOA較長。被試都是在清楚地意識到啟動詞的情況下對目標詞反應的, 因而很難避免被試使用策略, 研究的結果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Shelton和Martin(1992)認為, 這些結果反映了一個復雜的過程---有一些人使用了策略, 另一些人沒有。要獲得真正的啟動效應, 就應該排除任何形式的策略加工, 以實現真正的自動化加工。在啟動實驗中, 這就需要縮短SOA的長度。迄今為止, 研究語義啟動效應的最佳技術是隱蔽啟動范式(Masked Priming Paradigm)。在隱蔽啟動范式中, 按照掩蔽刺激和靶刺激的呈現順序, 又分為前掩蔽和后掩蔽。其中,前掩蔽主要用來研究反應準備中的無意識加工過程。該范式一般包括一個前行掩蔽刺激(通常是一串“#”號), 接著呈現小寫的啟動詞(約持續30~60 ms), 再被大寫的目標詞所替代(Forster & Davis,1984; Forster & Forster, 2003; Grainger, 2008)。在這種情況下, 被試不僅不能夠認出啟動詞, 甚至不知道啟動詞的存在。此時, 任何情景記憶的痕跡或策略加工的可能性都被排除, 啟動效應能夠真正地反映出自動加工的結果。在隱蔽翻譯啟動范式中, 一種語言的詞作為啟動刺激出現, 屬于另一種語言的翻譯對等詞或填充詞作為目標刺激出現。由于受到掩蔽的啟動刺激呈現時間短暫, 被試對它們的加工屬于無意識加工, 只能夠通過對隨后的目標刺激的反應中推測出相關因素(如啟動詞和目標詞的關聯程度)是如何對啟動效應進行調節的, 從而影響了對目標刺激的判斷。自從Forster和Davis (1984)提出該范式以來, 隱蔽翻譯啟動范式就被廣泛地運用到跨語言的研究中。Grainger (2008)評論說, 隱蔽啟動范式已經成為詞匯認知研究的主要工具, 它不僅包括對行為的測量, 也包括對大腦活動的測量。行為和神經成像的證據均表明, 加工隱蔽啟動詞和可視啟動詞所引起的大腦激活區域明顯不同(Kouider,Dehaene, Jobert, & Le Bihan, 2007)。
與跨語言啟動效應相關的一種現象就是啟動效應對稱與否。雙語者不僅可以通過兩種語言理解意義, 還可以將信息從第一語言(L1)翻譯到第二語言(L2) (前向翻譯)或從第二語言(L2)翻譯到第一語言(L1) (后向翻譯)。Kroll和Stewart (1994)發現, 雙語者從L2到L1的翻譯速度快于從L1到L2的翻譯速度。隨后,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 在詞匯決定中, 存在著翻譯啟動效應的不對稱性(De Groot &Nas, 1991; Kim & Davis, 2003; Finkbeiner, Forster,Nicol, & Nakamura, 2004; Voga & Grainger, 2007)。然而, Gollan, Tamar, Forster和Frost (1997)采用隱蔽啟動范式, 發現英語-希伯來語雙語者在詞匯決定中出現了顯著的L1→L2方向的啟動效應, 但未發現L2→L1方向的啟動效應; Jiang (1999)使用中-英雙語者, 只在使用高頻詞時發現了L2對 L1的啟動效應; Schoonbaert, Duyck, Brysbaert和Hartsuiker (2009)使用不熟練的荷蘭語-英語雙語者,在兩個方向上都發現了隱蔽翻譯啟動效應;Du?abeitia, Perea和Carreiras (2010)采用熟練的巴斯克語-西班牙語雙語者, Dimitropoulou, Du?abeitia和Carreiras (2011)采用不熟練的希臘語-西班牙語雙語者, 發現前者在詞匯決定中表現出對稱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后者卻表現出不對稱的啟動效應。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現象?修正的層級模型(t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認為, 在L2學習的最初階段, 學習者需要經過L1來通達語義。只有L2高度熟練時, 才會直接通達語義。這種對L1的依賴造成雙語者的不同語言之間的聯系不對稱。L1詞匯同語義系統的聯系強, L2詞匯同語義系統的聯系弱。當L2的熟練程度提高以后, 也能夠獲得同語義系統的直接聯系。但L2和L1的詞匯聯系并未消失, 仍然保留作為可行的聯系。該模型認為, 正是由于雙語者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詞匯聯系不對稱,以及兩種語言的詞匯與語義系統的聯系強度不對稱, 所以才導致啟動效應的不對稱性。
語言在表達意義時具有任意性。同一概念可以由不同的符號系統來表達。然而, 就某些語言而言,它們使用的一些符號具有共同的來源。例如, 許多英語詞和法語詞都源于拉丁語和希臘語。對于特定的兩種語言而言, 同源詞(cognate words)是指由于具有共同的來源而在詞形上或語音上重疊水平較高的翻譯對等詞, 非同源詞(non-cognate words)是指由于不具有共同的來源而在詞形上或語音上重疊水平較低的翻譯對等詞(Voga & Grainge, 2007)。因此, 在不同的語言之間, 存在著相似性大小的差異。語言相似性因而成為影響語義表征和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的重要因素。Markus (1998)指出, 對于L2不熟練的雙語者而言, 無論兩種語言是否相似,L2詞匯都要經過L1詞匯才能夠通達共同語義表征,兩種語言的聯系方式是詞匯聯系模式; 對于熟練的雙語者而言, 如果兩種語言不相似, 詞匯之間就無直接的聯系, 語言聯系方式就是概念中介模式; 如果兩種語言相似, L2詞匯既可以直接與共同語義表征聯系, 也可以經由L1詞匯與共同語義表征聯系,兩種語言之間的聯系模式就是多通道模式。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 在詞匯識別中, 同源詞比非同源詞更容易加工(Dukstra, Grainger, & van Heuven, 1999;Lemh?fer & Dijkstra, 2004; Lemh?fer, Dijkstra, &Michel, 2004); 同源詞被翻譯得更快(De Groot, 1992a,1992b; Sánchez-Casas, Davis, & García-Albea, 1992);同源詞翻譯能夠產生更大的啟動效應(Du?abeitia et al., 2010); 在長時延遲啟動實驗中, 同源詞出現易化加工的趨勢(Cristoffanini, Kirsner, & Milech,1986; Lalor & Kirsner, 2001)。這些研究表明, 語言之間在詞匯拼寫形式上的相似性影響雙語者的語言表征, 影響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
漢語和日語之間具有親緣關系。在古代, 日本民族有口頭語言, 卻沒有書面文字。公元3世紀, 漢字和漢語詞匯陸續傳入了日本。經過四五百年的學習、使用和探索, 日本人創造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漢字利用法, 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1)直接沿用漢字的音、形、義, 如“山河”、“森林”等; (2)利用漢字的形、義表達日語中固有的詞, 如“犬” (いぬ)、“貓” (ねこ)等(楊越, 2006)。因此, 日語中使用的文字有4種:(1)漢字(Kanji); (2)平假名(hirakana); (3)片假名(katakana); (4)英文大寫字母。在近代, 日語和漢語之間又出現了語言倒流的現象。日語中的漢語詞開始對中國的語言文字產生重要的影響。自明治維新以來, 日本在學習歐洲近代文明的過程中,翻譯了大量的政治、經濟、科技、哲學等著作, 利用漢字創造了大量的新詞。在20世紀初, 眾多的中國留學生東渡日本, 又將日譯的西方文化術語及自創的反映日本獨特文化的新詞介紹到中國, 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吸收日語外來詞的運動。這些詞匯借用情況非常復雜:有利用漢字音譯的專業術語, 如“瓦斯”和“米”; 有意譯詞匯, 如“哲學”和“美學”; 有“電話”、“分子”、“公民”等具體詞匯; 也有“市場”、“義務”、“政策”和“民主”等抽象詞匯。目前, 人們所熟悉的漢語詞匯, 許多都是從日本傳來的。光《漢語外來語詞典》就收錄了800多個(李虹, 2004; 萬玲華, 2005)。因此, 漢語詞和日語詞往往具有共同的來源, 許多詞匯的詞形相同或相似。由于就總體而言很難確定漢語詞和日語詞究竟誰來源于誰, 于是, 人們便不辨來源, 將中文和日文詞形相同或相近的詞或字稱為中-日同形詞或中-日同形字(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因此, 中日同形詞是指漢語和日語的翻譯對等詞由于歷史的原因擁有共同的詞根而在詞形上具有高水平的重疊。這些詞包括:(1)書寫結構與漢字相同或者只有很小的差別; (2)屬于未簡化的漢字(如“評論”、“饅頭”); (3)在漢語中沒有, 卻可以引起聯想的詞(如“価格”、“弁當”) (曹珺紅, 2005)。由于平假名與片假名是日本獨創的文字, 至此, 日文才既具有漢字的表意符號, 又具有假名的表音符號, 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二元文字體系(籍二瑞, 杜建萍,2009)。因此,當漢語和日語的翻譯對等詞在詞形上較少重疊, 就被稱為中-日非同形詞(Chinese- Japanese non-homographs)。這些詞的結構與漢字詞之間差別較大, 如“あに” (哥哥)、“パン” (面包)。那么, 中文詞和日文詞的相似性對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有何影響?中-日同形詞和中-日非同形詞的加工與拼音文字中的同源詞和非同源詞的加工有何異同?
綜上所述, 對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表征和加工過程目前還無一致的結論, 對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研究的結果也不盡相同(Schwanenflugel & Rey,1986; Chen & Ng, 1989; Keatley & De Gelder, 1992;Zeelenberg & Pecher, 2003; 莫雷, 李利, 王瑞明,2005)。鑒于已有的隱蔽啟動研究大多基于兩種拼音文字, 或者基于一種拼音文字和一種非拼音文字,還沒有基于兩種非拼音文字的研究。本研究將使用兩種非拼音文字的雙語者, 從字詞拼寫形式(同形和非同形, 即語言相似程度)及語義加工深度(詞匯決定任務的語義卷入程度淺, 語義決定任務的語義卷入程度深)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兩種語言之間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實驗邏輯是:通過操縱啟動詞和目標詞之間的關系(是否是翻譯對等詞, 是否屬于同形詞), 分析被試在不同任務下對目標詞的反應, 進而推測出不熟練中-日雙語者是如何加工和儲存中、日兩種語言的, 以期檢驗當前雙語表征模型的解釋力。目前, 隱蔽翻譯啟動研究大多采用前行掩蔽范式(Forster & Davis, 1984)。沿用前人的做法, SOA為47 ms, 比較中-日雙語者在翻譯對等條件和翻譯無關條件下的反應, 將這兩種條件下的反應時之差作為啟動量。
2 實驗1 詞匯決定任務中中-日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2.1 方法
2.1.1 被試
29名日語系三年級本科生,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已經獲得了日本語能力測試三級證書。日本語能力測試是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和日本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合辦, 專為母語為非日語的學習者舉辦的水平考試。分為4個等級, 一級最高, 相當于大學日語專業本科畢業的水平; 二級可以用于申請到日本的短期大學學習, 也可以用于在日本就業。因此, 被試屬于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
2.1.2 設計與材料
采用2(翻譯方向:中文→日文、日文→中文)×2(啟動類型:翻譯對等條件、翻譯不對等條件)兩因素重復測量設計。材料是60對中-日同形詞,分為3類:(1)閱讀材料; (2)食物; (3)職業。每類有20對詞。24名日語專業的本科生對日語詞的熟悉度做7級評定, 刪去熟悉度小于5的詞, 選取了30對中-日同形詞為材料, 每類10對詞。三類詞的平均熟悉度分別為6.25、6.33和6.38。方差分析表明,各類詞的平均熟悉度差異不顯著,F
(2, 46) = 0.31,p
>0.05。翻譯對等條件是指啟動詞和目標詞是中、日兩種語言的翻譯對等詞, 如“雜志-雑誌”或“雑誌-雜志”; 翻譯無關條件指啟動詞和目標詞不是中日兩種語言的翻譯對等詞, 語義不相關, 如“手表-雑誌”或“時計(手表)-雜志”。用翻譯無關條件的反應時減去翻譯對等條件的反應時來評估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大小。還有30個中文假詞和日文假詞作為填充材料。中文假詞和日文假詞由變換詞語中的一個字組成, 如“雜指”、“雑紙”。控制假詞的字數, 并使假詞的字數和目標詞的字數平衡。2.1.3 儀器
采用E-Prime軟件編程, IBM計算機, 屏幕分辨率為1024×768像素。
2.1.4 程序
被試坐在計算機前, 雙手的食指分別放在F鍵和J鍵上。刺激的呈現和反應的記錄均由計算機控制, 反應時從目標詞呈現到被試做出反應為止。首先, 在屏幕的中央呈現注視點“+”500 ms, 接著呈現一串“#”作為掩蔽刺激, 啟動詞在同樣的位置呈現50 ms, 接著呈現目標詞, 直至被試做出反應。告知被試盡快盡量準確地決定刺激是否為中文或日文的合法詞。如果是真詞, 就按下J鍵; 如果是假詞, 就按下F鍵。半數被試的用手按此規定, 半數被試的用手規定相反。未告知被試有啟動詞存在。實驗后的訪談表明, 被試未發現有啟動詞呈現。為了平衡順序誤差, 半數被試先做中文詞啟動日文詞的試驗, 后做日文詞啟動中文詞的試驗, 半數被試的順序相反。正式實驗共有240次試驗(60次翻譯對等條件的試驗, 60次翻譯無關條件的試驗, 120次填充材料試驗)。
2.2 結果與分析
錯誤反應以及對非詞的反應時不納入統計。反應時分析時刪除M
± 2.5SD
之外的數據, 占全部數據的3.7%。結果見表1。反應時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8) = 1.58,p
>0.05,F
(1, 29) =2.56,p
>0.05。啟動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
(1, 28) =10.14,p
<0.01,F
(1, 29) = 6.78,p
<0.01。翻譯對等條件的反應時(M
= 595 ms)顯著短于翻譯無關條件(M
= 627 ms)。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8) = 0.12,p
>0.05,F
(1, 29) = 0.44,p
>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8) = 0.13,p
<0.05,F
(1, 29) = 1.03,p
>0.05。啟動類型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8) = 0.69,p
>0.05,F
(1, 29) = 1.72,p
>0.05。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8) = 1.03,p
>0.05,F
(1, 29)=0.78,p
>0.05。t
檢驗表明, 在反應時上, 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啟動量(28 ms)與日文→中文條件下的啟動量(35 ms)差異不顯著,t
(28) = 0.35,p
>0.05。在錯誤率上, 啟動量均很小, 不足1%, 故未進行統計分析。因此, 在詞匯決定中, 在中-日同形詞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這一效應在啟動方向上并未表現出顯著的差異。無論是中文詞啟動日文詞, 還是日文詞啟動中文詞, 在翻譯對等條件下的反應時均顯著短于在翻譯無關條件下, 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基本上對稱。

表1 詞匯決定任務中被試對同形詞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3 實驗2 詞匯決定任務中中-日非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3.1 方法
3.1.1 被試
29名日語系三年級本科生,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已經獲得了日語能力測試三級證書。
3.1.2 設計與材料
設計與實驗1相同。材料是60對中-日非同形詞, 分為3類:(1)身體部位; (2)食物; (3)稱呼。每類有20對詞。24名日語系本科生對日語詞的熟悉度做7級評定, 刪去熟悉度小于5的詞, 選取30對中-日非同形詞作為材料。三類詞的平均熟悉度分別5.83、6.04和5.88。方差分析表明, 三類詞的平均熟悉度差異不顯著,F
(2, 46) = 0.42,p
> 0.05。在翻譯對等條件下, 啟動詞和目標詞是翻譯對等詞,如“鼻子-はな”或“はな-鼻子”; 在翻譯無關條件下,啟動詞和目標詞不是翻譯對等詞, 無語義聯系, 如“椅子-はな(鼻子)”或“いす(椅子)-鼻子”。另有60對中文假詞和日文假詞作為填充材料。中文假詞和日文假詞的構成方法與實驗1相同, 如“草眉”、“りチゴ”。3.1.3 儀器和程序
與實驗1相同。
3.1.4 結果與分析
錯誤反應和對非詞的反應時不納入統計。剔除2名不合格的被試后, 刪除在M
± 2.5SD
之外的數據, 占全部數據的5.7%。結果見表2。反應時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顯著,F
(1, 26) = 8.38,p
< 0.01,F
(1, 29) =8.57,p
< 0.01。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反應時(M
=737 ms)顯著長于日文→中文條件下(M
= 654 ms)。啟動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
(1, 26) = 22.32,p
<0.001,F
(1, 29) = 43.75,p
< 0.001。翻譯對等條件的反應時(M
= 669 ms)顯著短于翻譯無關條件(M
=723 ms)。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6) = 3.40,p
> 0.05,F
(1, 29) = 1.71,p
> 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6) = 1.34,p
> 0.05,F
(1, 29) = 1.26,p
> 0.05。啟動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
(1, 26) = 7.50,p
< 0.05,F
(1, 29) = 5.71,p
< 0.05。翻譯對等條件的錯誤率(4.0%)顯著少于翻譯無關條件(6.3%)。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6) = 1.45,p
>0.05,F
(1, 29) = 1.97,p
> 0.05。t
檢驗表明, 在反應時上, 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啟動量(75 ms)顯著大于日文→中文條件下的啟動量(34 ms),t
(26) = 2.05,p
< 0.05。在錯誤率上, 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啟動量(3.1%)與日文→中文條件下的啟動量(1.5%)差異不顯著,t
(26) = 1.15,p
> 0.05。因此, 在詞匯決定中, 中-日非同形詞也存在顯著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即翻譯對等詞條件的反應均快于翻譯無關條件的反應。這一效應在啟動方向上還表現出顯著的差異:中文啟動日文時的啟動效應大于日文啟動中文時的啟動效應。即, 雖然不熟練的漢-日雙語者在兩個方向上都表現出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但該效應在中文啟動日文時更加顯著。
4 實驗3 語義分類任務中中-日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先前關于隱蔽啟動研究的結果往往大相徑庭。原因之一可能是任務不同。Grainger和Frenck-Mestre (1998)在語義分類中對非同源詞發現了L2→L1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在詞匯決定中未發現; Finkbeiner等(2004)在語義分類中發現了隱蔽語義聯想啟動效應, 在詞匯決定中未發現。因此, 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可能具有任務依賴效應(Task-Dependent Effect)。為了證實這一點, 使用語義分類任務繼續進行考察。
4.1 方法
4.1.1 被試
28名日語系三年級本科生,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已經獲得了日語能力測試三級證書。
4.1.2 設計、材料與儀器
設計與材料同實驗1。干擾材料為其他類別的詞, 不屬于閱讀材料、食物、職業、身體部位、稱呼中任何一類, 如“攜帯(手機)”、“扇風機(電風扇)”。

表2 詞匯決定任務中被試對非同源詞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4.1.3 程序
首先在屏幕的中央呈現注視點“+”500 ms, 接著呈現一串“#”作為掩蔽刺激, 啟動詞在同樣位置上呈現50 ms, 接著呈現目標詞, 直到被試做出反應。實驗分為3個區間, 在每個區間之前, 出現一個提示界面, 要求盡可能快而準地決定接下來呈現的詞是否屬于某一類別。如果屬于, 就按下J鍵; 如果不屬于, 就按下F鍵。半數被試的用手按此規定,半數被試的用手規定相反。未告知被試有啟動詞存在。實驗后的訪談表明, 被試未發現啟動詞呈現。
4.2 結果與分析
錯誤反應及對非詞的反應時不納入統計。反應時分析時刪除M
± 2.5SD
之外的數據, 占全部數據的3.4%。結果見表3。反應時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7) = 0.84,p
> 0.05,F
(1, 29) =2.65,p
> 0.05。啟動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
(1, 27) =13.81,p
< 0.01,F
(1, 29) = 9.83,p
< 0.05。翻譯對等條件的反應時(M
= 557 ms)顯著短于翻譯無關條件(M
= 591 ms)。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7) = 0.54,p
> 0.05,F
(1, 29) = 0.63,p
>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7) = 0.46,p
> 0.05,F
(1, 29) = 0.73,p
> 0.05。啟動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
(1, 27) = 8.40,p
>0.05,F
(1, 29) = 6.04,p
< 0.05。翻譯對等條件的錯誤率(4.25%)顯著低于翻譯無關條件(7.25%)。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7) = 0.30,p
> 0.05,F
(1, 29) = 0.18,p
> 0.05。t
檢驗表明, 在反應時上, 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啟動量(37 ms)與日文→中文條件下啟動量(32 ms)差異不顯著,t
(27)= 0.06,p
< 0.05。在錯誤率上, 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啟動量(3.6%)與日文→中文條件下啟動量(1.4%)差異不顯著,t
(27) = 2.04,p
> 0.05。因此, 在語義決定中, 同樣存在著中-日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這種效應不受翻譯方向影響, 表現出對稱的特點。
5 實驗4 語義分類任務中中-日非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5.1 被試
28名日語系三年級本科生,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已經獲得了日語能力測試三級證書。
5.2 設計、材料與程序
設計與材料與實驗2相同, 干擾材料為其他類別的詞, 不屬于閱讀材料、食物、職業、身體部位、稱呼中的任何一類, 如“いす(椅子)”,“うみ(大海)”。實驗程序與實驗3相同。
5.3 結果與分析
錯誤反應以及對非詞的反應時不納入統計。反應時分析時刪除在M
± 2.5SD
之外的數據,占全部數據的3.7%。結果見表4。反應時的兩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方向的主效應不顯著,F
(1, 27) = 1.06,p
> 0.05,F
(1, 29) = 0.73,p
> 0.05。啟動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
(1, 27) = 22.10,p
< 0.001,F
(1, 29) = 16.32,p
<0.001。翻譯對等條件的反應時(M
= 564 ms)顯著短于翻譯無關條件(M
= 608 ms)。啟動方向和啟動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
(1, 27) = 0.17,p
> 0.05,F
(1, 29) = 0.73,p
> 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各種主效應和交互作用均不顯著,p
> 0.05。t
檢驗表明, 在反應時上, 中文→日文條件下的啟動量(45 ms)與日文→中文條件下的啟動量(42 ms)沒有顯著的差異,t
(27) = 0.13,p
> 0.05。在錯誤率上, 啟動量均很小, 不足1%, 故未進行統計分析。
表3 語義分類中被試對同形詞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表4 語義分類中被試對非同源詞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因此, 在語義決定中, 也存在著中-日非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這種啟動效應不受翻譯方向影響:無論是前向翻譯還是后向翻譯, 非熟練中-日雙語者對中-日非同形詞均表現出對稱的啟動效應。
6 討論
6.1 詞匯拼寫形式對隱蔽翻譯啟動效應的影響-拼寫形式依賴效應(Script-Dependent Effect)
4個實驗的結果表明, 詞匯拼寫形式對跨語言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實驗1中,被試對中-日同形詞對表現出對稱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在實驗2中, 對中-日非同形詞對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依然存在, 卻表現出不對稱性:中文詞啟動日文詞時, 啟動量(75 ms)顯著大于日文詞啟動中文詞時(34 ms)。實驗1和實驗2的任務相同, 差異可能是由于下述原因:(1)中-日同形詞對在詞形上重疊。日文中有很多詞匯直接借用了漢字的字形。據統計, 漢字詞在日文中占52%以上。日本(1981)公布的《常用漢字表》中收入漢字1945個, 大部分保持了漢字的字形。因此, 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將中-日同形詞的隱蔽翻譯啟動歸結為隱蔽的語言內重復啟動效應。這就證實了先前研究者的猜測:在隱蔽啟動范式中, 同形翻譯詞對和語言內詞形相似詞對的啟動效應類似(Drews & Zwitserlood,1995; Frost, Forster, & Deutsch, 1997; Grainger,Colé, & Segui, 1991)。(2)任務的影響。詞匯判斷要求加工詞匯的視覺信息, 確定輸入刺激是否為詞。這種作業的特點是, 判斷詞的真假不一定以完全理解詞義為基礎, 語義卷入程度不深。所以, 詞形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實驗1的材料是中-日同形詞對, 它們字形相同或相似, 被試基于詞形就能夠做出判斷。因此, 在L2→L1和L1→L2方向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基本對稱。在實驗2中, 雖然在兩個方向上均出現了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但在L1→L2方向上啟動效應比L2→L1方向上更大。以往使用非同源詞的研究結果也大都如此(Duyck, 2005;Schoonbaert et al., 2009; Weber & Cutler, 2004)。根據修正的層級模型, 由于L1與L2的詞匯聯系較弱,L1與語義系統的聯系較強, 當啟動詞為L1時, 可以預先激活與L2共享的概念結點, 這些概念結點再激活L2的詞匯結點, 因而就能夠產生啟動效應;由于L2與語義系統聯系較弱, 不能夠預先激活與L1共享的概念結點, 因此就未發現啟動效應。
在實驗3和實驗4中, 依然可以觀察到顯著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該效應在啟動方向上對稱。在實驗3中, 詞匯層面和語義層面的雙重原因促使了對稱的啟動效應的產生。首先, 實驗3的材料是中-日同形詞, 詞形的相似度高, 無論哪種語言作為啟動詞, 在翻譯對等條件下都有利于反應。其次, 實驗3采用語義分類任務, 該任務不僅需要理解詞義,還需要在不同類別中做出正確的選擇, 語義卷入程度比詞匯判斷任務深。根據Finkbeiner等(2004)提出的意義模型, 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的大小與目標詞的語義特征集被激活的比例有關。在一般情況下,雙語者的L1是優勢語言, L2是非優勢語言。因此,對翻譯對等詞而言, 被試對L1詞匯的意義掌握得多, 對L2詞匯的意義掌握得少, 表現出概念表征的非對稱性。這種非對稱性會引起翻譯啟動效應的非對稱性。當任務為語義分類時, 被試在反應時可以限制意義激活的數量。即, 為了更好地對目標詞反應, 類別判斷會作為一種限制因素。此時, 被試會關注與目標詞的類別相關的意義, 忽略與類別無關的意義。因此, 分類任務像一個“過濾器”, 屏蔽了詞匯的與反應無關的意義。這樣, 在兩個方向上,目標詞的意義被激活的比例就大致相當, 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因而就對稱。對實驗4而言, 同樣發現了對稱的隱蔽啟動效應。由于采用中-日非同形詞,語義分類任務也使被試更多地關注啟動詞和目標詞的類別語義, 因而意義模型也能夠解釋實驗4的結果。
6.2 加工任務對隱蔽翻譯啟動效應的影響-任務依賴效應(Task-Dependent Effect)
綜合4個實驗的結果可見, 加工任務對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具有重要的影響, 這種影響同字詞的拼寫特征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當啟動詞和目標詞屬于同形詞時, 不管加工任務是詞匯判斷, 還是語義決定, 反應均表現出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這種效應是對稱的。即對于同源詞, 隱蔽翻譯啟動效應并未表現出任務依賴性。但對于非同形詞而言, 情況就不同。雖然依然能夠觀察到顯著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表現卻因任務不同而不同。在詞匯決定中, 中文詞啟動日文詞時表現出更好的易化加工(實驗2);在語義分類中, 無論哪種語言作為啟動詞, 均表現出明顯的易化加工(實驗4)。為什么會如此?
詞匯決定是確認某一視覺刺激是否是某一語言的合法詞的過程。根據相互作用模型(McClelland& Rumelhart,1981), 在視覺詞匯識別中, 包含自下而上的加工和自上而下的加工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字詞的視覺刺激激活了被試頭腦中的詞形表征, 進而通達了詞匯的語音和語義; 另一方面, 被試頭腦中的語義知識激活又反作用于詞形加工, 激活詞形表征。由于中文詞和日文詞不完全同形, 所以, 根據修正的層級模型, 當啟動詞為中文詞時, 由于中文詞同概念系統聯系強, 能夠容易地預先激活與日文詞共享的概念結點, 這些結點再激活相關的日文詞的詞匯結點, 從而有利于對日文詞的識別。日文詞與概念系統聯系弱, 較難預先激活與中文詞共享的概念結點, 對中文詞識別的促進作用就小。另一方面, 被試對中文詞的意義掌握得多, 對日文詞的意義掌握得少, 對中文詞的詞形結構更加熟悉, 對日文詞的詞形較不熟悉。因此, 當中文啟動詞呈現時, 對被試頭腦中意義表征的激活就大, 自上而下的加工就強, 因而表現出較大的啟動效應; 當日文啟動詞呈現時, 對被試頭腦中意義表征的激活就小,自上而下的加工就弱, 因而對中文詞識別的促進作用就小。語義分類是根據意義將某一詞匯劃入某一類別的過程, 該任務的語義卷入程度深。被試需要根據提示界面的信息, 激活要求的特定意義之后即可進行歸類判斷。前已述及, 意義模型將不同的啟動效應歸結為雙語者的語義表征的差異, 認為跨語言語義啟動效應的大小與目標詞的語義特征集被激活的比例有關。因此, 雖然被試對L1詞匯的意義掌握得多, 對L2詞匯的意義掌握得少, 但無論呈現的是中文啟動詞還是日文啟動詞, 被試只需要激活類別意義即可, 兩種方向的意義激活比例大致為1:1。所以, 在分類任務下, 無論是同形詞還是非同形詞, 均表現出對稱的啟動效應。
縱觀4個實驗, 可以發現, 對中文和日文兩種非拼音文字而言, 在雙語者的語言加工中, 同形詞存在著加工優勢, 即同形詞更容易加工, 被翻譯得更快, 能夠產生更大的啟動效應。但這種優勢還要受任務類型的影響:當反應不需激活很多語義結點就可以完成時, 詞形對反應的作用較大, 會出現同形詞的優勢效應; 當反應需要依據特定的語義信息的激活才能夠完成時, 詞形對反應的作用就較小, 同形詞的優勢效應就消失了。據此, 需要對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的語言表征模型進行更加細致的刻畫。
6.3 不熟練中-日雙語者語言表征的性質--- 混合表征模型
目前, 富有吸引力的雙語者的語言表征模型有二:概念中介模型和修正的層級模型, 前者適合于描繪熟練的雙語者的語言表征, 這種雙語者的兩種語言同樣熟練, 如同雙語國家和雙語地區的雙語者那樣; 后者適合于描繪不熟練的雙語者的語言表征,在這種雙語者的語言中, 一種語言非常熟練, 另一種語言相對不熟練。那么, 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的語言表征究竟屬于哪一種類型?
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 與非同源詞相比, 同源詞之間更容易出現隱蔽啟動效應(Gollan et al.,1997), 啟動量更大(Davis et al., 2010)。研究表明,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對中-日同形詞和中-日非同形詞的反應不盡相同。同形詞具有加工優勢, 但這種優勢受任務類型的影響。綜合來看, 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的語言表征既不完全地符合概念中介模型, 也不單純地符合修正的層級模型, 而是屬于一種非常特殊的情形。
對中-日同形詞而言(如圖1a所示), 由于詞形結構相同或者相似, 語義表征共享, 因而發現了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而且, 在中→日和日→中兩個翻譯方向上, 啟動效應對稱, 類似于語言內的啟動效應。因此, 當在詞匯決定任務基于詞形就可以做出反應時(實驗1), 由于詞形相同或詞形之間具有較高水平的重疊, 彼此之間聯系緊密, 可以相互激活,因而出現了對稱的啟動效應; 同時, 當語義決定任務要基于語義信息才可以反應時(實驗3), 由于中、日同形詞各自都可以直接通達到共享的概念系統,所以對稱的啟動效應依然存在。
對中-日非同形詞而言(如圖1b所示), 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的語言表征依據其任務的要求不同(語義卷入的程度不同), 信息激活的路徑也有區別。詞匯決定任務使被試重視詞形的作用, 較少重視語義的作用, 此時就較為符合修正的層級模型。例如, 實驗2發現了典型的不對稱的隱蔽啟動效應:日文詞可以通過詞匯聯系直接激活中文詞的詞匯系統, 中文詞則需要先激活共有的語義系統, 然后再激活日文詞的詞匯系統。語義分類任務使被試重視語義的作用, 較少重視詞形的作用, 此時就較為符合意義模型。例如, 實驗4發現了對稱的隱蔽啟動效應:無論是在中文→日文還是在日文→中文,被試不能僅僅依據詞形就做出反應, 詞形相似與否的作用減弱, 語義能否得到激活就成為關鍵。被試需要在特定的語境下(告知要判斷目標詞是否屬于某種類別)激活目標詞的類別特征, 而此時激活語義結點的比例接近1:1, 所以隱蔽翻譯啟動效應也對稱。總之, 鑒于不同任務的語義卷入程度不同,被試會靈活地采取相應的反應方式。

與以往研究相比, 現有研究不僅采用更為嚴格的實驗范式證實了在雙語者的兩種語言中存在著隱蔽翻譯啟動效應, 還揭示了翻譯方向、字詞拼寫形式和加工任務對隱蔽翻譯啟動效應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發現字詞拼寫形式對隱蔽翻譯啟動效應的影響受加工任務調節, 深化了對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的語言表征和加工過程的復雜性的認識。被試屬于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 因此并未考察語言熟練程度的作用。即使如此, 研究的結果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在理論上, 它證明了跨語言翻譯啟動效應是客觀存在的現象, 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語義共同表征, 而不是由于加工策略的作用; 在實踐上, 它為中國人的日語學習提供了啟示:在教學和學習中,既應該重視中-日同源詞的學習, 充分發揮同源詞在語言學習中正遷移作用, 也應該注意克服同源詞的不良影響, 避免出現“中國式的日語”, 即學生在想用日語表達時首先想到了中文詞, 然后原封不動地轉換成與之對應的日語漢字詞作為日語來使用。應該盡可能地發揮漢字詞對日語學習的有利作用,同時又最大限度地減小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除此之外, 更應該在中-日非同形詞的學習上下大功夫, 加強日文中特有的詞與中文詞、共同語義表征的聯結, 使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能夠盡快成為熟練的中-日雙語者。
7 結論
在不熟練的中-日雙語者的中文和日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隱蔽翻譯啟動效應。隱蔽翻譯啟動效應的大小與是否對稱受中日翻譯對等詞是否同形、啟動方向和任務類型的影響。字詞拼寫形式對隱蔽翻譯啟動效應的影響受加工任務的調節。
Altarriba, J., Basnight-Brown, D. M. (2007).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performing semantic-and translation-priming experiments across languages.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9
,1–18.Altarriba, J., & Mathis, K. M. (1992). Conceptual and lexical develop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6
, 550-568.Bonder, G. E., & Massion, M. E. J. (2003). Beyond spreading activation: An influence of relatedness proportion on masked semantic priming.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10
, 645-652.Cao, J. H. (2005). The range of times, items of comparison and other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homograph.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3
(3), 43–46.[曹珺紅. (2005). 有關中日同形漢字詞匯對比研究中的幾個基本問題.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 13
(3), 43–46.]Chen, H. C., & Ng, M. L. (1989). Semantic facilitation and translation priming effect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Memory and Cognition, 17
, 454-462.Cristoffanini, P., Kirsner, K., & Milech, D. (1986). Bilingual lexical representation: The status of Spanish-English cogn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38A
, 367-393.Davis, C., Sanchez-Casas, R., García-Albea, J. E., Marc, G.,Molero, M., & Feeré, P. (2010). Masked translation priming: Varying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word type with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3
, 137-155.De Groot, A. M. B. (1992a). Bilingual lexical representation:A closer look at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In R. Frost & L.Katz (Eds.),Orthography, phonology, morphology, and meaning
(pp. 389–412). Amsterdam: Elsevier.De Groot, A. M. B. (1992b). Determinants of word transl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Cognition, 18
, 1001-1018.De Groot, A. M. B., & Nas, G. L. J. (1991).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cognates and noncognates in compound bilingual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0
, 90-123.Dimitropoulou, M., Du?abeitia, J. A. & Carreiras, M.(2011).Masked translation priming effects with low proficient bilinguals.Memory and Cognition,
39, 260-275.Drews, E., & Zwitserlood, P. (1995). Morph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similarity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Performance, 21
, 1098-1116.Dukstra, T., Grainger, J., & van Heuven, W. J. B. (1999).Recognition of cognates and interlingual homographs: The neglected role of phonology.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1
, 496-518.Du?abeitia, J. A., Perea, M., & Carreiras, M. (2010). Masked translation priming effects with highly proficient simultaneous bilinguals.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7, 98-107.Duyck, W. (2005). Translation and association priming with cross-lingual pseudohomophones: Evidence for nonselective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bilingual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ning, Memory, &Cognition, 31
, 1340-1359.Finkbeiner, M., Forster, K., Nicol, J., & Nakamura, K. (2004).The role of polysemy in masked semantic and translation primin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1
, 1-22.Forster, K. I., & Davis, C. (1984). Repetition priming and frequency attenuation in lexical acces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10
, 680-698.French, R. M., & Jacquet, M. (2004). Understanding bilingual memory: Models and data.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87-93.Frenck, C., & Pynte, J. (1987).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and surface forms: A look at across language priming in bilinguals.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6
,383-396.Frost, R., Forster, K. I., & Deutsch, A. (1997).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morphology of Hebrew? A masked priming investigation of morphological represent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23
, 829-856.Forster, K. I., & Forster, J. C. (2003). DMDX: A Window display program with millisecond accuracy.Behave Research Methods,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35, 116-124.Gollan, T. H., Forster, K. I., & Frost, R. (1997). Translation priming with different scripts: Masked priming with cognates and noncognates in Hebrew-English bilingual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ning, Memory, &Cognition, 23
, 1122–1239.Grainger, J. (2008). Cracking the orthographic code: An introduction.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3
, 1–35.Grainger, J., Colé, P., & Segui, J. (1991). Masked morphological priming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0
, 370-384.Grainger, J., & Frenck-Mester, C. (1998). Masked priming by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in proficient bilinguals.Language &Cognitive Processes, 13
, 601-623.Ji, E. R., & Du, J. P. (2009). Japan's "take-ism" as view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Kanji.Journal of Liaon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6
, 109-110.[籍二瑞, 杜建萍. (2009). 從日文漢字的發展看日本的“拿來主義”.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26
, 109-110.]Jiang, N. (1999). Testing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for the asymmetry in masked cross-language priming.Bilingualism: Language & Cognition, 2
, 59-75.Keatley, C., & de Gelder, B. (1992). The bilingual primed lexical decision task: Cross-language priming disappears with speeded responses.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4
, 273-292.Kim, J., & Davis, C. (2003). Task effect in masked cross-script translation and phonological primin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9
, 484-499.Kouider, S., Dehaene, S., Jobert, A., & Le Bihan, D. (2007).Cerebral bases of subliminal and supraliminal priming during reading.Cerebral Cortex, 17
, 2019-2029.Kroll, J. F., & De Groot, A. M. B. (2006).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roll, J. F., & Stewart, E. (1994). Category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picture naming: Evidence for asymmetric connections between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3
, 149-174.Kroll, J. F., & Tokowicz, N.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for words in a second language.In J. Nicol (Ed.),One mind, two languages: Bilingual language processing
(pp.49–71).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Lalor, E., & Kirsner, K. (2001). The representation of “false cognates” in the bilingual lexical.Psychonomic Bulletin &Review, 8
, 552-559.Lemh?fer, K., & Dijkstra, T. (2004). Recognizing cognates and interlingual homographs: Effects of code similarity in language-specific and generalized lexical decision.Memory and Cognition, 32
, 533-550.Lemh?fer, K., Dijkstra, T., & Michel, M. C. (2004). Three language, one ECHO: Cognate effect in trilingual word recognition.Language & Cognitive Processes, 19
, 585-611.Li, H. (2004).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ract in the writing systems.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158-161.[李虹. (2004). 論中日漢字在語言文字體系中的相互影響.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4
, 158-161.]Markus, B. (1998). Stroop interference in bilinguals: The rol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 A. F. Healy & L.E. Bourne (Eds.),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McClelland, J. L., & Rumelhart, D. E. (1981). An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of context effects in letter perception: Part 1.An account of basic findings.Psychological Review, 88
,375-407.Mo, L., Li, L., & Wang, R. M. (2005). Evidence for long-term cross-language repetition priming of the highly proficien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1288-1293.[莫雷, 李利, 王瑞明. (2005). 熟練中-英雙語者跨語言長時重復啟動效應.心理科學, 28
, 1288-1293.]Perea, M., Du?abeitia, J. A., & Carreiras, M. (2008). Masked associative/semantic priming effects across languages with highly proficient bilingual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8
, 916-930.Sánchez-Casaa, R. M., Davis, C. W., & García-Albea, J. E.(1992). Bilingual lexical processing: Exploring the cognate/ noncognate distinc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4
, 293-310.Schwanenflugel, P. J., & Rey, M. (1986). Interlingual semantic facilitation: Evidence for a common representational system in the bilingual.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8
, 1191-1210.Schoonbaert, S., Duyck, W., Brysbaert, M., & Hartsuiker, R. J.(2009). Semantic and translation priming from a first language to a second and back: Making sense of the findings.Memory and Cognition, 37
, 569-986.Shelton, J. R., & Martin, R. C. (1992). How semantic is automatic semantic prim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ning, Memory, & Cognition, 18
, 1191-1210.Voga, M., & Grainger, J. (2007). Cognate status and cross-script translation priming.Memory and Cognition, 35
, 938-952.Wan, L. H. (2005). Political terms of Chinese-Japanese cognate words.Journal of Tianjin Manage College,
(2), 65-66.[萬玲華. (2005). 中日同源的政治學術語.天津市經理學院學報,
(2), 65-66.]Weber, A., & Cutler, A. (2004). Lexical competition in non-native spoken-word recognition.Journal of Memory &Language, 50
, 1-25.Williams, J. N. (19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meaning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Evidence for a common, but restricted, semantic code.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6
, 195-220.Yang, Y. (2006). O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ies in Japanese.Journal of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2
,83-86.[楊越. (2006). 試析日語中的漢字和漢語詞匯.浙江旅游職業學院學報, 2
, 83-86.]Zeelenberg, R., & Pecher, D. (2003). Evidence for long-term cross-language repetition priming in conceptual implicit memory task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9
, 8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