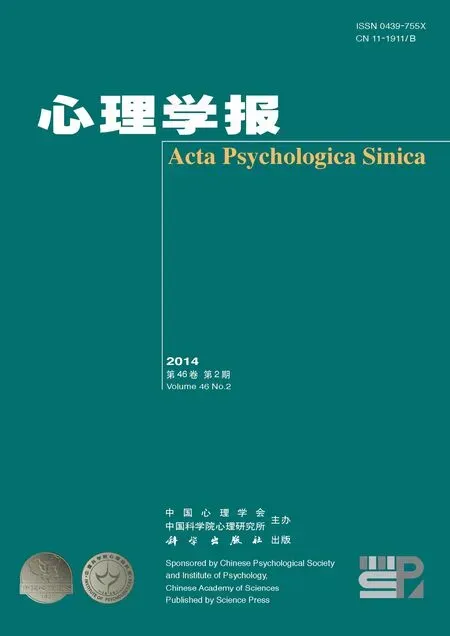道德領導與員工建言:一個調節-中介模型的構建與檢驗*
梁 建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上海 200052)
1 引言
在進入 21世紀后, 員工對于企業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她/他們所擁有的勞動力上, 而且還在于她/他們能夠產生具有創新性的觀點和想法。為了能夠面對稍縱即逝的市場機遇進行有效的決策,管理者經常需要從員工那里獲得決策信息, 以彌補她/他們認識的不足, 從而快速、恰當地回應外界環境的變化, 在問題進一步惡化前修正偏差(Morrison, 2011)。為此, Locke, Alavi和 Wagner(1997:296)曾預測:“在將來, 那些知道的最多、知道的最快, 而且善于利用員工參與的企業更容易因為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功。而且這種趨勢會比以往更加明顯”。
與這一客觀要求相對應的一個事實是, 大多數員工經常感覺到并不能自由地、公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參與企業決策。研究發現, 員工往往出于對個人得失的考慮, 而普遍不情愿指出相關問題和發表個人意見, 不愿參與企業內的合理化建議活動(Dutton, Ashford, O’Neill, Hayes, & Wierba, 1997;Milliken, Morrison, & Hewlin, 2003; 謝章澍, 楊志蓉, 2006)。員工普遍認為建言是有風險的, 就工作議題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會影響企業的和諧和挑戰領導的權威, 不僅不能影響管理層的決策, 反而有可能為自己的職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即使有些員工相信自己可以說出一些有益的建議, 通常她/他們會選擇沉默, 放棄建言。鑒于建言的重要性以及員工在建言時的矛盾心理, 近十年來圍繞建言的研究得以迅速增加。其中, 道德領導(ethical leadership)對員工建言行為的促進作用日漸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Morrison, 2011)。
道德領導是指管理者在與下屬交往過程中展現出符合倫理規范的個人行為, 并通過溝通、決策制定等管理過程在企業內促進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Brown, Trevi?o, & Harrison, 2005)。早在兩千多年前, 孔子就提出治理國家最有用的方式是以身作則, 用道德來引導、作為下屬的榜樣, 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管理。《論語》中曾記載:“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在西方管理思想史中, Barnard(1938)也較早地強調了道德領導的重要性。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一書中, 他認為高尚的道德品德與高超的領導技能(如構建組織架構、有效溝通等)是一名高效管理者必須具備的兩項素質。中西方的研究發現道德領導能夠提升員工積極的工作態度, 促進組織公民行為, 抑制各種反生產行為(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Brown & Trevi?o, 2006; 盧菁,宋繼文, 夏長虹, 2011)。
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討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行為的中介心理機制,并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探討影響這一機制的邊界條件。具體而言, 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三點:首先,在社會交換理論(Blau, 1964)和社會信息加工理論(Salancik & Pfeffer, 1978)的基礎上, 本研究分析了道德領導影響建言行為的效應, 提出了兩個中介變量來闡明其間的作用機制:責任知覺(felt obligations)和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鑒于對道德領導的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對于其中介變量的研究有利于我們理清其作用機理, 加深我們對于道德領導的理解(Brown & Trevi?o, 2006)。其次, 契合近來學者提出檢驗道德領導效應邊界的呼吁(Mayer, Kuenzi, Greenbaum, Bardes, & Salvador,2009), 本研究提出并檢驗了權力距離對道德領導效應的調節效應。我們預期權力距離作為一種測量個人價值觀傾向的特征變量, 會影響到員工對領導道德行為的敏感性, 從而發揮其調節作用。最后,本文整合了本研究中提出的中介和調節變量, 通過檢驗一個調節-中介模型(moderated-mediation model), 系統地分析了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行為的心理機制, 以期能夠促進企業有效地管理建言行為, 并最終提升管理與決策水平。
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的提出
2.1 道德領導和員工建言
員工建言是指員工“針對工作中的相關問題,自由地溝通自己的想法、觀點和疑慮, 以改善組織或單位運作” (Morrison, 2011: 375)。因此, 員工建言一直被研究者視為一種以促進組織變革、提高組織運行效率為目的的親社會行為(Organ, Podsakoff,& MacKenzie, 2006; Van Dyne, Cummings, &McLean Parks, 1995)。Liang, C. I. C. Farh和J. L.Farh (2012)根據建言內容提出了兩維度的行為結構:促進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第一類行為主要指為提高企業效率而提出新觀點和新方法; 第二類行為則是指針對阻礙組織效率的問題(如有害的行為,不恰當的工作程序、規定和規范等)而提出的抑制性觀點和措施。這一概念整合了以往的文獻, 清晰了員工建言的概念內涵。
鑒于員工建言行為往往伴隨著個人風險, 研究者普遍認為領導者對建言的可接納性緩解了員工的退縮認知(withdrawal cognitions), 提升了員工參與的可能性。例如, Saunders, Shepard, Knight和Roth (1992)發現, 在管理者平易近人并且會積極回應員工投入的情況下, 員工建言的可能性會增大。其后的研究發現, 與高層之間的關系質量影響了中層管理者對自己能否成功建言的判斷, 以及建言過程有關的個人風險認知, 并最終影響了建言行為(Ashford, Rothbard, Piderit, & Dutton, 1998; 汪林,儲小平, 黃嘉欣, 陳戈, 2010)。因此, 如果領導者能夠淡化權力差異以促進員工的心理安全感, 則會相應地激發出更多的建言行為(Edmondson, 2003;Detert & Burris, 2007)。此外, 最近的研究還發現當員工在工作中得到上司的支持時, 員工公開建言的程度更高; 而當員工為一名苛責式領導(abusive supervision)工作時, 其公開建言程度則較低(Burris,Detert, & Chiaburu, 2008; 李銳, 凌文輇, 柳士順,2009; 李銳, 凌文輇, 方俐洛, 2010)。
與以往研究關注的領導風格不同, Brown與其同事(2005)提出來的道德領導概念側重于強調一名領導自身需要滿足基本的道德要求(如正直、可靠、公正、誠信、不貪腐等), 能夠成為下屬的道德楷模,同時需要在工作中經常與下屬進行有關道德標準和原則的交流和溝通, 從而在部門內引導和塑造符合道德規范的工作行為。特別針對建言行為而言,研究者認為當領導者的行為符合員工的道德期待時, 會在企業中營造出一種鼓勵員工參與的氛圍,并最終促進員工的建言行為(Walumbwa, Morrison,& Christensen, 2011; Walumbwa & Schaubroeck,2009)。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我們針對道德領導的行為特點, 進一步闡述了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行為的兩種互補的中介心理機制: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其中, 責任知覺解釋了以社會交換觀點來理解的建言行為動機基礎, 而心理安全感則解釋了從社會信息加工角度理解的建言行為機制。
2.2 責任知覺作為中介變量
責任知覺是指員工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應該更加努力地工作, 積極參與各種建設性行為以改善組織運作(Fuller, Marler, & Hester, 2006)。因此,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種主觀的、對工作有激勵作用的個人信念。當員工們意識到自己對組織發展負有責任時, 我們預期他/她們不會僅僅局限于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 而是會積極主動地尋找各種方法和途徑來改善組織運作。而建言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角色外的行為, 屬于自愿性質, 企業無法通過行政手段強迫員工提出高質量的合理化建議(Van Dyne et al., 1995)。因此, 我們認為主動提出建設性意見是一名員工對企業發展持有責任知覺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基于這個觀點, 我們提出責任知覺可以作為理解道德領導與建言行為之間關系的一個中介心理變量。
在領導與成員的交往過程中, 一個具有較高道德水平的領導者會把員工利益始終記在心里, 她/他不會偏袒某一下屬或者以某種借口挑起下屬之間的競爭和爭斗。此外, 在與下屬交流時, 她/他們不虛偽不做作, 以實情相告、遵守諾言、與員工們公正的協商、給予其選擇的自由。在交往過程中, 下屬們會明白自己可以依賴這樣的領導, 在工作中給予領導以極大的信任(Brown & Trevi?o, 2006)。因此, 員工們會有較強地意愿與這樣的領導發展一種長期導向、相互信賴的社會交換關系(Blau, 1964)。
在社會交往過程中, 如果交換成員的一方做了有利于另一方的事, 另一方應該產生回報對方善意的責任感, 以維系、強化這種交換關系。而如果另一方沒有適時地遵守她/他的義務和責任, 那么這種交換關系就開始受到侵蝕, 雙方的關系質量就會下降(Gouldner, 1960)。因此, 領導者的道德水平將會提升其與下屬之間的交換關系質量。為了發展和維持這種高質量的交換關系, 下屬必然會被激發出互惠的意愿, 在工作表現出更高的責任意識, 以回饋其領導的道德行為。一旦員工感覺到了對道德領導者的義務, 互惠行為便成為了一種道德要求。她/他們會為了回報領導者的公正和關心, 而愿意成為組織中“一名負責任的公民”, 為領導排憂解難, 為企業發展積極建言獻策。研究表明責任知覺是員工產生各種主動性行為的一項重要心理驅力(Fuller et al., 2006; Morrison & Phelps, 1999)。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責任知覺在道德領導與建言行為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
2.3 心理安全感作為中介變量
心理安全感是指員工能夠在工作中自由地表達自我, 而不需要擔心受到其他人的指責或報復(Kahn, 1990)。由于員工在建言時往往容易招致誤解, 可能會被其他同事或領導視為抱怨者或批評者,甚至是麻煩制造者。因此當公開提出有關建議時,他/她們通常會擔心是否會得罪相關同事, 導致人際關系的惡化(Dutton et al., 1997; Milliken et al.,2003)。考慮到建言可能引起人際風險, 心理安全感一直被視為員工建言的前提條件之一(Ashford et al., 1998; Detert & Burris, 2007; Liang et al., 2012)。鑒于管理者在工作中有能力去構建一種相互信賴的人際關系, 提高員工的心理安全感, 預期心理安全感可以作為一項心理機制來解釋道德領導對員工建言行為的促進作用。
社會信息加工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認為, 一個人所在的社會環境提供了各種影響其態度、調節其行為的社會信息, 因此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并不僅僅取決于自己的需要和目標,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周圍環境的影響(Salancik & Pfeffer, 1978)。在工作中, 員工們會通過各種人際網絡來判斷在工作中表達自己的觀點是否受到其他人的歡迎或者是否安全。如前所述,一名道德水平較高的領導者不僅會在與員工交往中展現出各種道德品質(如誠實、自律、不貪腐等),而且也會采用各種管理方式在團隊中促進道德行為(如交流、獎勵、懲罰、強化道德標準)。因此, 道德領導能夠利用高尚的價值觀和精神融合團隊, 創造一個良好的人際環境。與這樣領導者一起共事,下屬會了解到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是會帶來回報的, 而不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會帶來懲罰(Brown et al., 2005)。她/他們知道自己不會因為發表建設性意見, 而受到其他人的斥責、邊緣化乃至受到懲罰。如果員工認為自己所處的人際環境是沒有威脅的、支持她/他們發表自己觀點的, 她/他們就不會擔心發表個人看法后可能帶來的個人風險。這種感知讓員工對工作中的人際關系感到放松, 降低她/他們對于提出新觀點后的風險預期, 因此心理安全感會促進員工的建言行為。研究發現, 如果領導者能夠淡化權力差異以促進心理安全感, 則團隊成員會表現出更多的建言行為(Edmondson, 2003)。因此, 道德領導有助于消除其下屬對發表個人意見的負面顧慮, 通過增加員工的安全感而促進其建言行為。基于這些原因, 本研究提出假設2:
假設2:心理安全感在道德領導和建言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2.4 權力距離作為一個調節變量
權力距離是指一個社會在多大程度接受組織或機構中不平等的權力分配(Hofstede, 1980)。盡管這一概念最初定義在國家或社會層面, 研究者發現由于個人社會化經歷不同, 在同一社會不同個體間的權力距離觀念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Kirkman,Lowe, & Gibso, 2006)。在本研究中, 我們把權力距離定義為一項反映個體價值觀差異的心理特征, 而不是描述社會層面差異的文化價值變量。由于組織制度和程序并不能完全限定領導者的行為, 所以領導者在日常的工作中(如任務分配、晉升、考核等)具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性和自主性。而權力距離的不同可能會導致員工對領導者道德行為的敏感程度不同, 因此我們預期這一特點可能導致了權力距離對于道德領導效應的調節作用。
我們預期權力距離可能會影響到下屬對領導者道德行為的敏感度, 從而影響到其心理感知(即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具體而言, 認同高權力距離的下屬傾向于順從行事并避免與領導產生分歧,她/他們通常相信自己的領導是值得尊敬和信賴的。她/他們通常會認為“那些在社會結構頂端的人……,與那些在社會結構底端的人是非常不同的(Triandis,1995: 30)”。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個人信念, 使得她/他們與領導者之間產生了較大的社會距離, 她/他們往往感到自己無力改變領導者的工作方式和行為。所以相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 她/他們更加擔心領導者的不道德行為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后果(Tyler, Lind, & Huo, 2000) 。而這種擔心無疑會提高她/他們在日常工作對于領導者道德行為的敏感性。由于道德水平較高的領導者會嚴格地遵守較高的道德標準, 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下屬, 不會濫用自己的權力來謀取個人的利益, 這種正面的行為信息會受到高權力距離員工的格外關注, 并激發她/他們在工作中產生積極的感知(即較高水平的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
相對而言, 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往往不會認同組織內權力應該不平等地分配。她/他們會認為職位不同只是企業內的分工不同, 而不會將管理者看成是與自己顯著不同。她/他們傾向于相信自己與管理者一樣都是組織內不可或缺的一員, 自己與領導者一樣對企業的發展負有自己的責任。因此, 相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 她/他們對領導者的行為關注相對較少。她/他們的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更多地與工作本身相關, 而不是領導者的行為。與以上推論類似, 周建濤和廖建橋(2012)發現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 他/她們感知到的威權領導與其建言行為之間的關系要顯著高于那些低權力距離者。整合以上的討論, 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a:權力距離調節了道德領導與責任知覺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 這一關系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強, 而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弱。
假設3b:權力距離調節了道德領導與心理安全感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 這一關系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強, 而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弱。
本文在假設1和2分別提出了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對于道德領導和員工建言之間的中介作用,而在假設3中提出因為不同權力距離水平的員工對于道德領導的敏感度不同, 從而造成了道德領導行為對心理中介變量的效應產生了差異。結合以上的中介、調節假設, 本研究最后提出一個整合的假設:道德領導?責任知覺(心理安全感) ?員工建言之間的間接關系(indirect effect)會因為員工權力距離水平的不同而出現不同。
如前所述, 建言行為屬于自愿性質, 企業無法強迫員工提出高質量的合理化建議。但同時它帶有一定的個人風險, 這類行為容易被誤解為發牢騷或對某些人的批評, 甚至有可能被認為是對現行組織規范的破壞和挑戰(Van Dyne et al., 1995; 2003)。因此, 在決定是否進行建言之前, 員工必然會對其人際環境進行評估(Dutton et al., 1997)。她/他們需要通過各種線索來判斷自己的主動建言是否值得、是否會給自己的職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而這種評估的結果會直接地影響到她/他們后續的行為選擇(Lazarus & Launier, 1978)。針對這種行為特點, 權力距離會顯著地影響到個人對這些風險的感知和判斷, 最終表現為對道德領導的效應產生調節效應(假設 3)。
現有的文獻表明, 個人對外界風險的評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是否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資源去應對外界的威脅和和各種挑戰(Quinn, Spreitzer, &Lam, 2012)。具體而言, 高權力距離的人傾向于表現出外部控制源(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特點——即相信自己的決策和生活均被外界所控制, 而自己無力改變這些外界環境因素(Aldag & Jackson,1984)。因此, 她/他們在面對權勢時會普遍感覺到一種無力感(powerfulness, Nicol, 2007)。這種價值導向導致了她/他們在評估建言行為的風險時, 會因為自己的無力感, 而更加關注于外界環境, 特別關注是自己建言的主要對象—— 領導的行為和行事風格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如假設1和2所述, 對于高權力距離的人而言, 領導者的道德行為有望顯著地提升她/他們對建言的責任感和安全感, 從而促進建言行為。
相對而言, 低權力距離的人由于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 從而會低估建言行為帶來的個人風險。這種評估結果使得她/他們更加相信自己的建言可以贏得外界的關注, 而相對忽略周圍人際環境的因素(包括領導者的道德行為)。因此, 道德領導行為產生的激勵效應會相應變弱。與以上假設相類似,Schaubroeck, Lam和Cha (2007)發現高權力距離的員工更加容易接受領導行為的合法性, 受到變革型領導行為的影響, 她/他們會根據領導者的行為而調整自己對團隊的感知; 而相對而言, 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并不太關注領導者的行為, 因此領導者行為對她/他們感知的影響相對較低。綜上所述, 我們提出假設4:
假設4a:權力距離調節了道德領導與員工建言之間通過責任知覺的間接關系。具體而言, 這一間接關系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強, 而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弱。
假設4b:權力距離調節了道德領導與員工建言之間通過心理安全感的間接關系。具體而言, 這一間接關系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強, 而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弱。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樣本和程序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一家本土連鎖超市公司。為了應對零售市場中激烈的競爭, 該公司一直鼓勵員工提出各種改善客戶滿意度、降低經營成本的建設性意見。共有341名來自不同工作崗位的一線員工參與了此次調查。為了保證數據質量, 課題組在兩個時間點發放了兩種不同版本的問卷。在第一份員工問卷中, 參與調查的員工回答了關于道德領導、責任知覺、心理安全感和權力距離的信息。六個星期以后, 我們發放了第二份主管問卷, 直屬主管評價了2或3名員工的建言行為。所有的英文量表都遵循標準的翻譯和回譯(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程序翻譯成了中文。參與者當場完成了問卷并直接交回研究者, 參與調查者都收到了一份小禮物作為回報。
在刪除了不合格的問卷后, 最終成功匹配員工-主管版本的問卷數量為 239份, 問卷回收率為70%。在參與調查的員工中, 73.1%的受訪人介于21到30歲之間, 65.7%為男性, 66.1%的員工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水平的教育培訓。
3.2 測量量表
道德領導
:本研究采用了由Brown等人(2005)開發的十道題目來測量道德領導, 代表性題目如“就道德而言, 我的主管是一個如何正確做事的模范”。在本研究中, 其一致性信度系數為0.81。責任知覺
:本研究修改了Eisenberger, Armeli,Rexwinkel, Lynch和Rhoades (2001)開發的五道題目來測量員工對組織發展的責任感。代表性題目如“我有責任盡最大的努力去為單位獻計獻策, 以實現它的目標”。這五道題目的一致性信度系數為0.77。心理安全感
:根據Brown和Leigh (1996)、May,Gilson和Harter (2004), 本研究開發了六道題目來測量個人的安全感。代表性題目如“在單位中, 我可以表達自己真實的工作感覺”。其一致性信度系數為0.72。建言行為
:本研究采用了 Liang等人(2012)開發的十個題目、兩個維度的員工建言量表。這一量表包括了促進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兩個維度。代表性題目如“主動提出幫助單位達成目標的合理化建議” (促進性建言)和“敢于對單位中影響工作效率的現象發表意見, 不怕使人難堪” (抑制性建言)。這兩個量表的一致性信度系數分別是0.90和0.90。因為建言行為的評價來自直屬主管, 而每位主管需要評價2或3名下屬, 我們進行了組內-組間分析(Within-and-Between Analysis, WAWB, Yammarino &Markham, 1992)以檢驗個體測量的獨立性。結果發現 WAWB分析的 F值并不顯著, 我們因此可以在個體層面對變量的關系進行統計分析。
權力距離
:本研究采用了 Dorfman和 Howell(1988)開發的六道題目來測量權力距離, 代表性的題目如“公司內的主要決策都應由管理者決定, 不需要與下屬商議”。在本研究中, 其一致性信度系數為0.74。控制變量
:因為建言行為很多時候與一個人對公司情況的了解程度有關, 本研究首先控制了兩個變量:教育水平和任職時間。任職時間影響到員工對組織文化和運作的熟悉程度, 而教育水平是一項反應個人知識儲備的變量, 我們用三類來測量:中學或以下、大專和大學。此外, 本研究還控制員工的年齡和性別。年齡用四類進行測量:20歲或以下,21~30歲, 31~40歲, 41~50歲及以上。我們采用啞變量來測量性別:女性計為0, 男性計為1。4 數據分析結果
4.1 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6個主要變量:道德領導、責任知覺、心理安全感、兩類建言行為和權力距離。我們應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技術評估了變量測量之間的區分效度。如表1所示, 觀測數據與假設模型(模型 1)之間的擬合度很好(χ= 787.9,df
= 579;RMSEA = 0.04, NNFI = 0.96, CFI = 0.96, IFI = 0.96),而三種替代模型(模型 2~4)與實際觀測數據之間擬合度則較差, 卡方檢驗和模型擬合指數都顯示假設模型與代替模型之間差異顯著。
4.2 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本研究所涉及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其間的相關系數。道德領導與中介變量、結果變量都呈顯著相關, 符合我們的理論預期。
4.3 假設檢驗
假設1和假設2分別假設了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在道德領導和員工建言之間的中介作用。基于WAWB分析的結果, 本研究采用了結構方程分析程序來完成假設檢驗。結構方程在模型估計過程中控制了測量誤差, 同時可以通過比較替代模型與假設模型之間的優劣來檢驗中介效應, 這是一項適合本研究假設的統計技術。在分析之前, 我們首先針對建言行為加入各種控制變量進行回歸, 保存了建言行為的殘差值, 用于隨后的假設檢驗。

表1 測量模型的比較

表2 均值、標準差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
參照Baron和Kenny (1986)推薦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 在評估假設中介模型的同時, 本研究估計了2個嵌套模型與1個替代模型。表3中報告的模型1是假設的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 我們進一步估計了兩個嵌套的模型—— 模型2和3。在這兩個模型中, 我分別加入了從道德領導到促進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直接路徑, 以檢驗部分中介的可能性。結果如表3所示, 觀測數據與假設模型擬合的很好(χ= 667.12,df
= 399; RMSEA = 0.057, NNFI =0.95, CFI = 0.95, IFI = 0.95)。而兩個嵌套模型在增加了直接效應后, 并沒有顯著地提高模型與數據擬合的程度。因此, 模型1與觀測數據之間的匹配情況更好。我進一步估計了一個替代模型(模型 4)來評估其它關系的可能性。模型4沒有假設中介效應, 而是估計了道德領導、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三者對建言行為的直接效應。這個模型的擬合指數也不錯(χ= 651.59,df
= 396; RMSEA = 0.056, NNFI = 0.95,CFI = 0.95, IFI = 0.94)。然而, 六條連線中僅有一條是顯著的(從責任知覺到促進性建言), 而其它關系則因為變量之間的替代效應而變得不再顯著。因此,假設的中介模型比這個替代模型更為合適、有效地反映了觀測變量之間的數據關系。圖1顯示了假設中介模型的路徑估計結果。為了表述簡潔, 我沒有報告完整的測量模型, 而是僅列出了反映潛變量關系的γ系數。如圖顯示, 從道德領導到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的兩條路徑都是顯著的(分別為γ = 0.40,p
< 0.01和γ = 0.50,p
<0.01)。同時, 從責任知覺到促進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路徑系數都是顯著的(分別是β = 0.26,p
< 0.01和β = 0.18,p
< 0.05)。此外, 從心理安全感到促進性建言的路徑系數同樣顯著(β = 0.16,p
< 0.05), 而其到抑制性建言的路徑系數僅僅是趨于顯著(β =0.15,p
< 0.10)。因此, 假設1得到了支持, 假設2基本上得到了支持。
表3 結構方程模型的比較

圖1 調節-中介模型的模型估計
假設3a和3b提出, 權力距離正向地調節了道德領導與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的關系。根據Ping(1995)的程序, 我首先根據線性模型中各觀察變量的效應, 計算了交互項(即道德領導×權力距離)的路徑系數。然后把交互項加入到假設的中介模型中,并設定了權力距離和責任知覺、心理安全感的直接關系, 以及交互項和責任知覺、心理安全感之間的直接關系。因為這個模型并不嵌套于假設的中介模型, 我通過檢驗這一模型與觀測數據的擬合程度來解釋它與假設模型的優劣。結果發現這一調節模型與數據擬合良好(χ=908.90,df
=617; RMSEA =0.048, NNFI = 0.94, CFI = 0.94, IFI = 0.94)。在加入交互項效應后, 模型產生了更好的數據擬合度(對于 2d.f.
, Δχ= 20.10,p
< 0.01)。與之相應地是, 道德領導與權力距離的交互項對于責任知覺(γ=0.27,p
< 0.01)和心理安全感(γ = 0.29,p
< 0.01)的效應都是正向顯著的。圖2顯示了權力距離對道德領導與責任知覺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對于高權力導向的群體(高于平均值 1個標準差)來說, 道德領導對責任知覺的影響較為明顯(β = 0.46,p
< 0.01), 而對于低權力距離的群體(低于平均值 1個標準差), 這一關系明顯較弱(β = 0.15,p
< 0.05)。圖3顯示的是權力距離對道德領導與心理安全感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在高權力距離組內, 道德領導和心理安全感的關系較為強烈(β = 0.48,p
< 0.01), 而對低權力距離的群體,這一關系也是顯著的正相關, 但是相對較弱(β =0.24,p
< 0.01)。綜上所述, 我們得出假設3得到了觀察數據的支持。假設 4提出道德領導對員工建言的間接效應(通過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在高權力距離組和低權力距離組間存在著顯著差異。我們采用了Edwards和 Lambert (2007)提出的調節中介程序檢驗了這一假設。結果報告在表4中。首先, 我們發現在高權力距離和低權力距離組中, 道德領導與責任知覺(β = 0.30,p
< 0.05)和心理安全感(β = 0.32,p
<0.05 )的關系存在明顯的差異。
圖2 道德領導與權力距離對責任知覺的交互關系

圖3 道德領導與權力距離對心理安全的交互關系
表4中的結果表明:道德領導-責任知覺-促進性建言之間的間接效應在低權力距離組(β = 0.07,p
< 0.05)和高權力距離組(β = 0.18,p
< 0.01)都顯著。其組間差異為0.11, 達到了顯著性水平(p
< 0.05)。而道德領導-心理安全感-促進性建言之間的間接效應在低權力距離組內并不顯著(β = 0.03,n.s.
), 但在高權力距離組內卻達到了顯著性水平(β = 0.19,p
<0.01)。其組間差值為0.16, 也達到顯著性水平(p
<0.05)。而對于道德領導-責任知覺-抑制性建言之間的關系, 結果表明這一間接效應在低權力距離組(β =0.04,n.s.
)和高權力距離組(β = 0.07,n.s.
)內均不顯著, 其間差異也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對于道德領導-心理安全感-抑制性建言之間的間接效應, 我們發現雖然在高權力距離組效應強度達到顯著性水平(β = 0.14,p
< 0.05), 但在低權力距離組效應不顯著(β = 0.03,n.s.
), 其間差值也不顯著。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對于促進性建言而言, 道德領導對員工建言的間接效應受到了權力距離的調節, 而這一調節的中介效應對抑制性建言并不顯著。因此, 假設 4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4 道德領導效應的調節-中介模型分析
5 討論與結論
5.1 研究結果討論
在本研究中, 我們研究了道德領導與員工建言之間的關系。我們的研究結果主要包括:(1)道德領導與員工建言行為存在正向相關關系; (2)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在道德領導與建言行為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3)權力距離正向調節了道德領導與責任知覺、心理安全感之間的關系; (4)道德領導通過中介心理變量對促進性建言的間接效應受到了個人權力距離的正向調節。總體而言,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與實踐啟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 本研究成功地將道德領導和建言行為聯系起來, 揭示了高道德水平的領導者激勵員工超越個人得失、積極為企業發展建言獻策的心理過程。建言行為是一種主動性的自愿行為, 而且是員工努力分析問題、尋求組織改進機會的結果。因此, 研究者將員工建言視為組織創新發展的第一步和重要的組成元素(Rank, Pace, & Frese, 2004)。組織創新始于員工主動地挑戰企業現行的操作步驟和管理實踐, 而產生出的新觀點或新思路。然而, 員工建言同樣可能會被理解為個人抱怨或是帶來人際矛盾。由于涉及到個人風險, 員工在很多時候對是否應該提出自己的建設性建議而感到左右為難(Van Dyne, Ang, & Botero, 2003)。基于建言行為的這一特征, 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 我們把道德領導視作激發建言行為的預測變量, 通過闡述道德領導如何建立適合員工建言的人際環境而構建了兩者之間的聯系。
在本研究中, 我們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和社會信息加工理論提出了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的心理中介變量: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作為權力擁有者, 擁有較高道德水平的領導者并不會濫用職權,而是盡可能地關心下屬的利益。因此, 她/他們能夠與下屬進行高質量的交換互動, 使得員工相信自己的責任并不僅僅限于完成規定的任務, 為企業健康發展提供建設性建議也是她/他們對組織應盡的義務之一。責任知覺作為中介變量與組織公民行為文獻中將建言視為角色外(extra-role)行為的邏輯是一致的(Van Dyne et al., 1995)。另一方面, 道德領導不僅為組織內的人際交往確立了基本道德規范, 而且努力在管理工作中堅持較高的倫理標準。因此, 只要她/他們發表的建議不是受其自身利益驅使, 員工們不用擔心會受到主管或同事的攻擊或疏遠, 能夠輕松地針對各種尖銳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Trevi?o, Brown, & Hartman, 2003)。心理安全感作為中介變量反映了組織沉默文獻一直以來堅持的理論觀點(Morrison & Milliken, 2000)。因此, 我們的研究整合以上兩方面的文獻, 論述了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行為的心理機制。
第二, 本研究提出并檢驗了權力距離對于道德領導?員工建言之間間接效應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權力距離顯著地調節了道德領導與心理中介變量之間的關系:對于認可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 道德領導對于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的影響更加明顯。作為一項描述等級觀念差異的個性特征,權力距離影響了人們對領導者道德行為的敏感程度。那些高權力距離的員工會高度關注領導者的道德行為, 她/他們會因領導者的自律和強調公平的管理政策而深受鼓舞, 并由此影響到她/他們的工作態度和行為。
值得關注的是, 我們從表 4中可以看到, 在道德領導?責任知覺?員工建言之間的間接效應中, 權力距離在第二階段(責任知覺?員工建言)的調節效應呈現出截然相反的效應:責任知覺與員工建言在低權力距離組中的關系比高權力距離組更加緊密(0.58與0.48, 促進性建言; 0.28與0.14, 抑制性建言)。因此, 權力距離可能負向地調節了責任知覺和員工建言之間的關系。結合以往的研究結果(Chen &Aryee, 2007; Farh, Hackett, & Liang, 2007; Sue-Chan& Ong, 2002), 我們認為權力距離可能在變量間因果聯系中扮演不同的調節角色:當我們檢驗道德領導與中介心理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即第一階段的關系), 權力距離影響了員工對領導行為的敏感性,從而正向地調節了兩者之間的關系; 但當我們觀察責任知覺和員工建言之間的關系時(即第二階段的關系), 因為因變量是可觀測的外在行為, 這時變量間的關系反映的不僅僅是心理感知, 更多的是個人社會化學習的結果。高權力距離的員工會認為在社會交往中, 更為重要的是恪守本分和職責, 而不是判斷雙方關系的質量(Farh et al., 2007)。他們/她們認為一名員工不應該對工作職責以外的事情說三道四, 而應該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行為以使之符合主流的社會規范; 而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則認為自己的行為應該源于自己的感知, 而不應該受到社會規范的約束。這一分析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權力距離沒有調節道德領導?中介心理變量?抑制性建言之間的間接關系。因為中國社會一直強調人際和諧,而相對排斥直接挑戰對方的抑制性建言, 所以這種文化傳統可能壓抑了第二階段的抑制性建言, 從而使得權力距離在第一階段產生的激發效應變得不再顯著(魏昕, 張志學, 2010)。由此可見權力距離對員工的影響可能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心理過程, 而不是單一的心理機制。將來的研究應該在現有的基礎之上繼續探索權力距離對員工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最后, 我們的研究表明管理者的道德行為對激勵下屬建言具有重要作用。道德領導為員工建言行為創造了兩個必要條件:因為感激而衍生出的責任知覺和處于良好人際關系中帶來的心理安全感。Kabanoff (1991)曾經指出領導研究存在的兩難情境:一方面領導研究必須強調管理者和一般員工之間的等級差異, 同時又必須研究如何在領導和下屬之間促進認同和合作。我們認為道德領導為解決這種兩難情境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即充分發揮領導者的道德感染力, 利用職位使得管理者成為激發員工學習模仿的榜樣, 而不僅僅是將職位權力作為管理控制的手段。
5.3 研究局限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在本研究中, 我們檢驗了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的兩項心理機制(即責任知覺和心理安全感)。這兩個變量可能并沒有完整地反映道德領導影響建言行為的心理機制。例如 Tangirala和 Ramanujam(2008)發現, 員工在工作中的個人控制感也影響了促進性建言。將來的研究可以從不同的理論角度來探索其它可能的中介機制。其次,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國內的一家零售企業。考慮到本文研究了權力距離的調節作用, 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高權力距離的國家。因此我們得到的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的情境局限。將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我們的結果進行跨層面、跨情境的檢驗, 使得變量間的因果聯系變得更清晰。
5.4 結論
在本研究中, 我們著重分析了道德領導影響員工建言的心理機制, 通過結合員工建言文獻, 推動了道德領導研究的發展。道德領導作為一個新的構念是否能夠持續地受到關注取決于其是否能夠解釋重要的結果變量(Mayer, Aquino, Greenbaum, &Kuenzi, 2012)。本文以道德領導的特點出發, 嚴謹地闡述了其通過兩種心理中介機制來影響員工的建言行為的作用機制, 進一步證實道德領導作為一個獨立變量所發揮的理論價值, 這為推進道德領導的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此外, 考慮到中國社會長期的高權力距離導向, 道德領導對于員工建言的重要性在中國組織情境中顯得尤其重要。管理者們應該在推進企業道德規范建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僅應該身體力行, 樹立道德榜樣, 而且需要在管理過程中強調樹立道德標準, 建立良好的企業道德氛圍。這對于企業長遠的組織創新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Aldag, R. J., & Jackson, D. W., Jr. (1984). Measurement and correlates of social attitud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3
,143–151.Ashford. S. J., Rothbard, N. P., Piderit, S. K., & Dutton, J. E.(1998). Out on a limb: The role of context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selling gender-equity issu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
, 23–57.Barnard, C. (1938).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173–1182.Blau, P. M. (1964).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 New York: John Wiley.Brown, S. P., & Leigh, T. W. (1996). A new look at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job involvement, effort, a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1
, 358–368.Brown, M. E., & Trevi?o, L. K. (2006). Ethical Leadership: 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7
,595–616.Brown, M. E., Trevi?o, L. K., & Harrison, D. A. (2005).Ethical leadership: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7
, 117–134.Burris, E. R., Detert, J. R., & Chiaburu, D. S. (2008). Quitting before leav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and detachment on voi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 912–922.Chen, Z. X., & Aryee, S. (2007). Delegating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diating processes in China.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 226–238.Detert, J. R., & Burris, E. R. (2007).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employee voice: Is the door really ope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 869–884.Dorfman, P. W., & Howell, J. P. (1988).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patterns: Hofstede revisited.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Management, 3
, 127–150.Dutton, J. E., Ashford, S. J., O’Neill, R. M., Hayes, E., &Wierba, E. E. (1997). Reading the wind: How middle managers assess the context for selling issues to top manager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 407–425.Edmondson, A. C. (2003). Speaking up in the operating room:How team leaders promote learning in interdisciplinary action teams.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0
,1419–1452.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Psychological Methods, 12
, 1–22.Eisenberger, R., Armeli, S., Rexwinkel, B., Lynch, P. D., &Rhoades, L. (2001). Reciprocation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
,42–51.Farh, J. L., Hackett, R. D., & Liang, J. (2007). Individual-level cultural values as moderator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employee outcome relationships in China: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distance and traditional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 715–729.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
,39–50.Fuller, J. B., Marler, L. E., & Hester, K. (2006). Promoting felt responsibility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and proactive behavior:Exploring aspects of an elaborated model of work design.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7
, 1089–1120.Gouldner, A. W. (1960).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5
,161–178.Hofstede, G. (1980). Motivatio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abroad?Organizational Dynamics,9
, 42–63.Kabanoff, B. (1991). Equity, equality, power, and conflic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6
, 416–441.Kahn, W. A. (1990).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3
, 692–724.Kirkman, B. L., Lowe, K. B., & Gibson, C. B. (2006). A quarter century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A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corporating Hofstede’s cultural value framework.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37
,285–320.Lazarus, R. S., & Launier, R. (1978). Stress-rela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s and environment. In L. A.,Pervin & M. Lewis (Eds.),Perspectiv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
(pp. 287–327). New York: Wiley.Li, R., Ling, W. Q., & Fang, L. L. (2010). The mechanisms about how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impacts on subordinates’ voice behavior.China Soft Science,
(4),106–115.[李銳, 凌文輇, 方俐洛. (2010). 上司支持感知對下屬建言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中國軟科學,
(4), 106–115.]Li, R., Ling, W. Q., & Liu, S. S. (2009). The mechanisms of how abusive supervision impacts on subordinates’ voice behavior.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
, 1189–1202.[李銳, 凌文輇, 柳士順. (2009). 上司不當督導對下屬建言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心理學報, 41
, 1189–1202.]Liang, J., Farh, C. I. C., & Farh, J. L. (2012).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promotive and prohibitive voice: A two-wave examin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5
, 71–92.Locke, E., Alavi, M., & Wagner III, R. (1997).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perspective.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15
, 293–331.Lu, Q., Song J. W., & Xia C. H. (2011). 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ethical leadership: A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8
,1802–1812.[盧菁, 宋繼文, 夏長虹. (2011). 道德領導的影響過程分析:一個社會交換的視角.管理學報,8
, 1802–1812.]Mayer, D. M., Aquino, K., Greenbaum, R. L., & Kuenzi, M.(2012). Who displays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n examin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thical leadership.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5
,151–171.May, D. R., Gilson, R. L., & Harter, L. M. (2004).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meaningfulness,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and the engagement of the human spirit at work.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77
, 11–37.Mayer, D. M., Kuenzi, M., Greenbaum, R., Bardes, M., &Salvador, R. (2009). How low does ethical leadership flow?Test of a trickle-down model.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08
, 1–13.Milliken, F. J., Morrison, E. W., & Hewlin, P. F. (2003).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mployee silence: Issues that employees don’t communicate upward and why.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0
, 1453–1476.Morrison, E. W. (2011).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Integration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5
, 373–412.Morrison, E. W., & Milliken, F. J. (2000). Organizational silence:A barrier to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pluralistic world.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 706–725.Morrison, E. W., & Phelps, C. C. (1999). Taking charge at work: Extrarole efforts to initiate workplace chang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2
, 403–419.Nicol, A. A. M. (2007).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alienation and spheres of control.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43
, 891–899.Organ, D. W., Podsakoff, P. M., & MacKenzie, S. B. (2006).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ts
nature,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 Thousand Oaks: Sage.Ping, R. A., Jr. (1995). A parsimonious estimating technique for interaction and quadratic latent variables.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2
, 336–347.Quinn, R. W., Spreitzer, G. M., & Lam, C. F. (2012). Building a sustainable model of human energy in organizations:Explor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resources.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6
, 337–396.Rank, J., Pace, V. L., & Frese, M. (2004). Thre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initiative.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3
, 518–528.Salancik, G. R., & Pfeffer, J. (1978).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to job attitudes and task desig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3
, 224–259.Saunders, D. M., Sheppard, B. H., Knight, V., & Roth, J.(1992). Employee voice to supervisors.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5
, 241–259.Schaubroeck, J., Lam, S. S. K., & Cha, S. E. (2007).Embraci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eam values and the impact of leader behavior on team performan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 1020–1030.Sue-Chan, C., & Ong, M. (2002). Goal assignment and performance: 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s of goal commitment and self-efficac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wer distanc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9
, 1140–1161.Tangirala, S., & Ramanujam, R. (2008). Exploring nonlinearity in employee voice: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contro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1
, 1189–1203.Trevi?o, L. K., Brown, M. E., & Hartman, L. P. (2003).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perceived executive ethical leadership: Perception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xecutive suite.Human Relations,56
, 5–38.Triandis, H. C. (1995).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Tyler, T. R., Lind, E. A., & Huo, Y. J. (2000). Cultural values and authority relations: The psycholog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cross cultures.Psychology, Public Police, and Law,6
, 1138–1163.van Dyne, L., Ang, S., & Botero, I. C. (2003). Conceptualizing employee silence and employee voice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0
, 1359–1392.van Dyne, L., Cummings, L. L., & McLean Parks, J. (1995).Extra role behaviors: In pursuit of construct and definitional clarity.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7
, 215–285.Walumbwa, F. O., Morrison, E. W., & Christensen, A. (2011).The effe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group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oup conscientiousness and group voice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Arizona.Walumbwa, F. O., & Schaubroeck, J. (2009). 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Mediating rol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ork group psychological safet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4
, 1275–1286.Wang, L., Chu, X. P., Huang, J. X., & Chen, G. (2010).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Guanxi with the top manager on manager voi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local family business.Management World,
(5), 108–117, 140.[汪林, 儲小平, 黃嘉欣, 陳戈. (2010). 與高層領導的關系對經理人“諫言”的影響機制—— 來自本土家族企業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
(5), 108–117, 140.]Wei, X., & Zhang, Z. X. (2010). The mechanism of reluctance to express prohibitive voices in organizations.Management World,
(10), 99–121.[魏昕, 張志學. (2010). 組織中為什么缺乏抑制性進言?管理世界,
(10), 99–121.]Xie, Z. S., & Yang, Z. R. (2006). Innovative Community: new perspective on the model of all-involvement innovation of firm.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24
, 775–779.[謝章澍, 楊志蓉. (2006). 創新共同體: 企業全員創新模式的新探索.科學學研究,24
, 775–779.]Yammarino, F. J., & Markham, S. E. (1992). On the application of within and between analysis: Are absence and affect really group-based phenomena?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7
, 168–176.Zhou, J.-T., & Liao, J.-Q. (2012). Why Chinese employees like to keep sil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on the employee voice.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11), 71–81.[周建濤, 廖建橋. (2012). 為何中國員工偏好沉默—— 威權領導對員工建言的消極影響.商業經濟與管理,
(11),7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