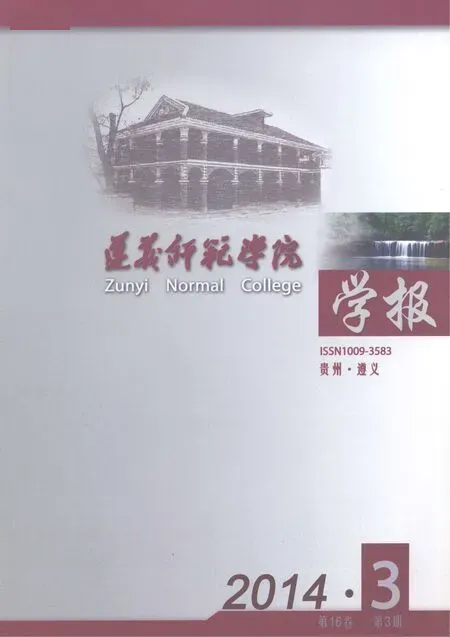“叛逆的靈魂”——論布勒東《娜嘉》的人物塑造
李 徵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400700)
一、《娜嘉》人物塑造的內傾性
《娜嘉》重視挖掘人物的潛意識、幻覺世界,其人物塑造具有內傾性特征。超現實主義文學的內傾性特征在其宣言中早有體現。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1924)中給“超現實主義”下了一個定義,認為“超現實”是一種“建立在相信現實,相信夢幻全能”并踞于二者之上的絕對現實。超現實主義在尊重客觀現實的同時強化了潛意識、夢幻的作用,“超現實”的定義滲入了潛意識、夢幻、幻覺等非理性元素,對現實的理解明顯發生了內傾。而人屬于客觀現實世界,超現實主義對現實定義的內傾不可避免地體現在其作品的人物塑造中,超現實主義作品往往忽視對人物的外貌長相進行細致的描寫,重視對人物的潛意識、幻覺世界進行深度挖掘,使其人物塑造具有內傾性特征。
(一)人物“我”的塑造
人物“我”的塑造體現出《娜嘉》人物塑造的內傾性。作品開頭,作者以第一人稱“我”提出了“我是誰”這個問題并對此作出了思考。“我是誰”不是對現實中“我”的單純指向,它指向內在現實的“我”,具有內傾性和本質性。那么,作者以何種方式追尋這個內在的“我”呢?在作品的第一部分,作者運用自動寫作法完成的“碎片回憶”,拋開了一般的社會關系和事件,把“我”放置在眾多具有偶然性的小片段之中,以此與外在現實中的我區分開來,塑造了一個具有內在現實或者說超現實性質的“我”。所以,“我”對問題“我是誰”的提出和思考很好地體現了《娜嘉》人物塑造的內傾性。
(二)娜嘉的自我定義
娜嘉的自我定義是“我是游蕩的靈魂”,也充分體現出《娜嘉》人物塑造的內傾性。娜嘉是一名年輕的法國女性,作者在一個無所事事、非常單調的下午,于拉法耶特街上偶遇她。娜嘉“穿著寒酸……她走路時頭仰得很高,與其他路人不同。她是那么纖弱,走路時,好像幾乎不觸及地面。她的面上可能浮現著一絲難以察覺的微笑”[1],當我問及娜嘉“你是誰”的時候,娜嘉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游蕩的靈魂”。娜嘉的回答似乎莫名其妙,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作者對娜嘉步姿的描繪,就可看出娜嘉自我定義的妙處。“穿著寒酸”、“走路時頭仰得很高”都給人一種清高、與眾不同之感,字里行間可以感受到娜嘉的不妥協精神。“纖弱”和走路“幾乎不觸及地面”也非常符合“靈魂”的一般特征。她面上的一絲微笑更是帶有些許的神秘,或許是因為這種神秘感,才燃起了作者對娜嘉的求知欲。總的來看,我們根本就無法從作者的這幾句話中看出娜嘉的廬山真面目,這幾句看似普通的步姿描寫并非向讀者告知娜嘉的具體相貌、身份或社會地位,而是娜嘉的整個精神風貌和狀態。它呈現給讀者的是娜嘉的內在精神特質而非外在相貌形體特征,從中我們能感受到娜嘉的與眾不同,這無疑是《娜嘉》人物塑造具有內傾性的一個體現。
(三)對娜嘉潛意識、幻覺世界的挖掘
作者重視挖掘娜嘉的潛意識和幻覺世界,這也體現出《娜嘉》人物塑造的內傾性。作者在人物“娜嘉”的塑造中,重點挖掘其潛意識、夢幻等內在現實:第一,娜嘉常常玩一種類似于自動寫作的游戲。“閉上眼睛,說點什么。隨便什么,一個數字,一個名字。就這樣(她閉上眼睛:)兩個,兩個什么呢?兩個女人。這兩個女人什么穿著?黑衣服。她們在哪里?在一個公園里……我一個人的時候,就喜歡這樣跟自己說話,跟自己講各種各樣的故事”。娜嘉的游戲與超現實主義自動寫作法極為相似,二者都深深觸及了人類的潛意識,娜嘉常靠這種游戲來生活。第二,娜嘉對超現實主義詩歌擁有驚人的感受能力。娜嘉讀到瓦里的一首超現實主義詩歌時,眼前出現了一片森林的幻覺,并從中得出這首詩“死亡”的主題。娜嘉對超現實主義詩歌的解讀言簡意賅、十分到位,娜嘉并非使用正常的理性邏輯解讀詩歌,而是用幻覺來構建詩歌圖景,從而達到解讀目的。第三,娜嘉在閑逛中常常出現幻覺,并企圖借此來探索“我是誰”。一次閑逛中,娜嘉堅持走入一個警察院子,“她飛快往里掃了一眼。‘不是這里……我也進過監獄。我那時是誰?那是好幾個世紀前的事情了。你呢?你當時是誰?’我們繼續沿著柵欄走,有一扇朝向壕溝的低窗,她死死地盯著那里看,目光不再移開。那里,一切都可能發生。她在問自己,她曾是瑪麗王后身邊的什么人”。
二、《娜嘉》人物塑造的非理性
超現實主義這個文藝流派本身具有深刻的非理性特征。在超現實主義還沒宣布正式成立之前,超現實主義元老布勒東、阿拉貢、艾呂雅等人就曾參加過名震一時的“達達主義”運動。達達主義企圖摧毀一切由理性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美學、文學藝術、道德,公然向已經僵化的傳統的社會習慣以及道德責任發出極端挑戰的叛逆行為深深影響了布勒東等人,但超現實主義在繼承達達主義叛逆性的同時摒棄了它的虛無。
在對理性主義叛逆的問題上,超現實主義不可避免觸及到“瘋狂”。布勒東認為瘋子之所以被關起來,僅僅是因為他們做出了某些“違法”舉動,然而這只是理性主義思維下的不忍之舉,因為瘋狂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想象力的犧牲品。
(一)精神病人“索朗日”的塑造
在娜嘉出場之前,作品塑造了一位精神病人形象——“索朗日”。在作品的第一部分,作者詳細講述了一部叫《女精神病人》的戲劇,戲劇因對一位女精神病人“索朗日”的成功塑造而博得作者的極大推崇。戲劇講述了一件在巴黎郊區女子學校的謀殺事件。索朗日是女子學校的學生,她的種種舉動預示著她患有一種周期性發作的瘋狂怪病,索朗日的行為、語言等細節也表現出她就是謀殺兇手。戲中還講述了一些可能誘發索朗日發病的他因,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學校的禁閉和環境的壓抑,戲中還對代表理性世界的園丁和校長暗作嘲諷,嘲笑他們的笨拙和死板。作者對索朗日瘋子形象的喜愛和對園丁、校長的嘲諷體現出《娜嘉》人物塑造的非理性傾向。戲中索朗日的人物塑造也與后文的娜嘉有著一種潛在的精神聯系,這種聯系可以說就是“瘋狂”。
(二)“瘋子”娜嘉的塑造
相對于索朗日而言,主人公娜嘉的“瘋子”形象更能體現《娜嘉》人物塑造的非理性特征。娜嘉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游蕩中出現的種種幻覺、幻聽已經出現瘋狂的征兆。比如,當娜嘉堅持走入警察院子并在此地產生了幻覺之后,“行人的腳步讓她渾身顫抖,我開始擔憂,將她的手一只只扳開,終于迫使她跟我走”。“行人的腳步讓她渾身顫抖”表現出娜嘉莫名的敏感和神經質,從“將她的手一只只扳開”可看出娜嘉此時情緒的極度緊張。一次,作者和娜嘉在經過一座城堡的時候,娜嘉看到自己變成德謝弗勒茲夫人,娜嘉常常在不同的地方,通過幻想把自己確定為某個歷史人物。娜嘉曾給過作者一張簽名為亨利貝克的字條,上面寫了亨利貝克給她的一些建議,而亨利貝克其實是一位歷史人物,他的雕像矗立在維利埃廣場,娜嘉宣稱她得到來自雕像亨利的紙條和建議,也顯示出娜嘉的神經質。娜嘉還出現了幻聽,認為一件原始藝術品老是在對她說“我愛你”。娜嘉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走火入魔般的經歷已經顯示出娜嘉極有可能患有精神病,她的神經質和眼前出現的幻覺就是患病的危險征兆。
其實,娜嘉在和作者相處的那段日子里,幻覺還沒能對娜嘉的身體造成實質性的傷害,在許多情況下娜嘉還能駕馭幻覺并運用幻覺。娜嘉常常在幻覺來臨之后把幻覺畫下來,從而形成了一幅幅具有超現實主義元素的非理性幻覺之作。比如,娜嘉為作者創作了一幅名為“情人之花”的畫,花的花瓣由四只眼睛和兩個心臟組成,并且是從一條蛇的嘴里生長出來的。娜嘉稱構思來自一次鄉間午餐之時的一朵花的幻覺;在娜嘉的畫《一個陰郁的人》中,“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出魔鬼的臉,一位女性的腦袋,一只鳥剛剛啄了她的嘴唇……一顆心,一頭牛或者水牛的腦袋,善惡之樹的枝條以及二十多個其他元素”。畫中的一些元素連娜嘉本人也覺得無法解釋,她只是從幻覺中看到它然后把它畫下,諸如此類。從娜嘉寄給作者的一批批畫作中,可看出畫作的幻覺越來越復雜,最后一批畫作甚至顯示出一種完全不同的畫法,可看出娜嘉在作畫時出現了精神混亂的狀態。終于,在“我”和娜嘉分開的幾個月后,娜嘉瘋了,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三)人物“我”對精神病院的批判
人物“我”對精神病院的批判體現了《娜嘉》人物塑造的非理性特征。娜嘉曾對“我”否認過她得了精神病,或許娜嘉真的沒病,病的是這個缺乏想象力的理性社會,“社會已經成為關押精神自由者的‘精神病院’,它從道德和法律的高度強迫社會成員放棄真正的‘我’,而堅持的必然宿命就是被社會給否定”。所以,當“我”知道娜嘉瘋掉之后,并沒有對娜嘉的瘋狂作出道德方面的判斷,反而對娜嘉被關進精神病院的理性主義式做法表達了強烈的憤慨,對精神病院這種所謂的社會保護機構大加抨擊,宣稱如果“我”也被關進精神病院的話,就會借此機會殺死一兩個醫生。“我”借娜嘉被關進精神病院這個“題”大加發揮、大作評論,具有濃厚的非理性色彩,很好地體現出《娜嘉》人物塑造具有的非理性特征。
三、《娜嘉》人物塑造的象征性
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有其目的和理想。超現實主義不像達達主義那樣,在對理性主義、社會道德進行叛逆的同時把自己引向一條“除了達達還是達達”的虛無之路。超現實主義的目的是通過對潛意識、夢幻等領域的挖掘,擴充人們對現實的定義,解放人們的想象力,使人們達到“思想上的最大自由”,以此“解決生活中的主要問題”。事實上,超現實主義把“自由”等目的滲入到運動之中并積極向法國共產黨靠攏的做法已經明顯看出其用心。所以確切地說,超現實主義是一場精神革命而非是一場單純的先鋒文藝運動。《娜嘉》作為超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作,其人物塑造上除了具有內傾性和非理性,同時還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娜嘉這個人物身上具有的象征意義,充分闡釋了超現實主義的目的和理想。
(一)娜嘉象征“自由”
娜嘉象征著“自由”。布勒東曾熱情地歌頌自由,聲稱“惟獨‘自由’這個詞還能讓我感到興奮不已。我以為這個詞最適當用來長久地維持人類的狂熱,這個詞也許能滿足我那惟一正當的熱望”[2]。在布勒東的眼里娜嘉是自由的化身,“從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都把娜嘉視為一個自由的精靈,就像那些空中飛翔的精靈”。
娜嘉與傳統文學中追求自由的叛逆女性人物形象是有所不同的。傳統文學中的叛逆女性大多追求愛情、婚姻的自由,并把對自由的追求輻射到整個家庭乃至社會,她們多以悲劇收場并從中表現出她們追求自由的深刻性和對其阻力的叛逆性,比較典型的如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安娜。安娜為了追求愛情自由,不顧世俗眼光,拋棄家庭和沃倫斯奇私奔,最后以自殺來表現她對整個庸俗的社會習慣和倫理道德的叛逆。娜嘉與這類女性形象有所不同,娜嘉追求的除了愛情的自由,更多的是思想的自由。
娜嘉愛情失意、販賣過毒品、坐過監獄、幾乎淪為妓女,可以說她在事業和愛情上都是一個失敗者。但是,她卻在巴黎走火入魔般的經歷和種種幻覺中獲得了思想上最大的自由和快樂,她與作者無拘無束地閑逛,與作者分享她的幻覺,利用幻覺作畫,與作者探討超現實主義詩歌和繪畫的內涵等。就算是娜嘉最后被關進精神病院,作者也沒有為其感到惋惜,對于娜嘉來說,在一個精神病院的內部與外部之間沒有絕對的差別。或許是因為娜嘉的這些特殊性,布勒東才至始至終把娜嘉看作一個的自由精靈。
(二)娜嘉象征“希望”
娜嘉不僅象征著“自由”,而且還象征著“希望”。娜嘉的名字極具深意,娜嘉的名字是自己選的,“娜嘉,因為在俄語中,這是‘希望’一詞的開頭幾個字母,也因為這僅僅是開頭”。娜嘉對自己名字的解釋絕非多余,娜嘉自選名字的做法除了個人愛好之外還滲透了她對“希望”一詞的強烈熱望,這也是作者對這位巴黎神奇女子產生好感的原因之一。不僅是娜嘉的名字吸引了作者,從九天的相處中,作者還發現娜嘉身上擁有諸多超現實主義特質,類似自動寫作法的游戲、對城市大街小巷的強烈興趣、對偶然的執著、對幻覺的迷戀、對超現實主義作品的精確解讀等等,無怪乎作者說娜嘉是“超現實主義最自然也是最真實的展現”。娜嘉的身上流著最純正的超現實主義血液,這甚至比布勒東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娜嘉象征著超現實主義的希望。正如布勒東對娜嘉的評價:“我記得出現在她面前,就像一個被擊倒在斯芬克斯怪腳下的人一樣,又黑又冷。我見過她蕨菜般的眼睛在清晨睜開,面對一個巨大的希望振翅的聲音與其他恐怖的聲音幾乎不可區分的世界,而面對這樣一個世界,迄今為止,我見過人們把眼睛閉上。我知道,對娜嘉來說,這一出發,從一個想要到達那里就已經是如此罕見、如此大膽的點的出發,蔑視了一切在非常自愿地遠離最后一張筏而迷路的時候需要祈求的東西,犧牲了一切構成虛假但又幾乎不可能抵御的生活補償的東西”。[3]這個“出發”,不僅是娜嘉的出發,而且還是布勒東的出發、超現實主義的出發(寫作《娜嘉》的時候,《超現實主義宣言》剛發表不久)。“也因為這僅僅是開頭”,我們誰也說不準,現實生活中到底還存在多少像娜嘉一樣具有超現實主義氣質的人?或許十個,也或許一千個、一萬個,關鍵是這樣的人確實存在,存在就代表著希望。
[1][法]安德烈·布勒東.娜嘉[M].董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法]安德烈·布勒東.超現實主義宣言[M].袁俊生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10.
[3]王佳.超現實主義的反叛——論布勒東的娜嘉[J].文學界,201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