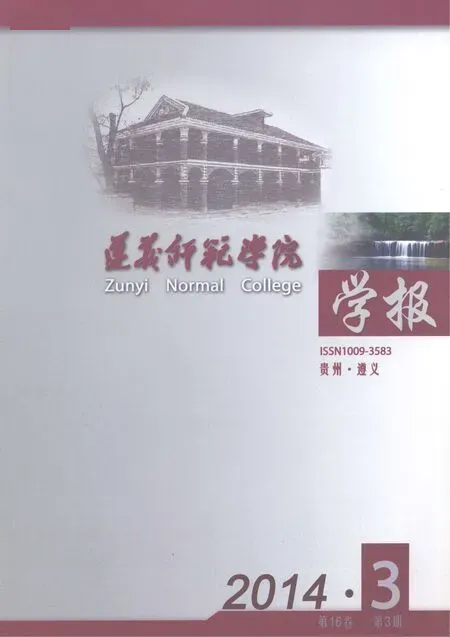黔北風俗的形成及其特征探索
劉麗
(遵義師范學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貴州遵義563002)
黔北風俗的形成及其特征探索
劉麗
(遵義師范學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貴州遵義563002)
黔北風俗的形成與其山川地理、水土物候、歷史發展、民族構成密不可分,在特定的文化時空中,形成了包容忍讓,好客互助;野性大膽,文武兼備;信鬼尚巫,敬畏自然;以農為主,兼營各業;安土重遷,守舊中庸等文化人格,顯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
黔北風俗;形成;特征
一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遵義的風俗文化,與遵義特殊的地域環境密切相關。
遵義市位于貴州省北部,俗稱黔北。位于我國地勢的第二階梯邊緣,東與銅仁市、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毗連,南鄰省會貴陽市,東南面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南與畢節市交界,西及北和四川省、重慶直轄市接壤。大婁山脈橫亙于北、武夷山脈縱橫于東南,烏江和赤水河是其南北兩端的界河。其地貌呈現出兩種景觀:遵義、湄潭、鳳岡、余慶及桐梓、綏陽的大部分地帶,以低山丘陵和寬谷盆地為主,地勢較為平坦開闊,是貴州省的糧食主產區,被譽為“黔北糧倉”;務川、道真、正安、仁懷,赤水、習水等,以中山峽谷為主,間有少量的丘陵和河谷壩地。長期的河流切割,使地勢陡峻雄奇、森林縱橫,曾經是野獸蛇蜥橫行之地,具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虎、豹、豺狼、黃鹿、獐子、野豬、毛狗(狐貍)、水獺、野兔、穿山甲、楠木、桐子、五倍子、生漆、天麻等各種野生動植物,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狩獵、采伐資源,也給生活于茲的人們提供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可能。在長達700多年的土官統治中,楊氏家族列朝列代向朝廷進貢的楠木、馬匹都出自這片土地。狩獵、采集、養殖等不僅是其經濟生活的補充,也是楊氏土司“務農訓兵,以待征調”的政治所需,還是外交的重要手段。而境內豐富的煤、汞、鐵、硫、鋁土、鋅、鉛、銅、大理石等礦產資源,成為人們從事打鐵、煉砂、挖煤等多種職業生活的物質基礎。山地環境決定了經濟生活的多樣性,也制約著民眾的習性發展。在交通要道上的桐梓、仁懷、赤水,因處于川黔交界,為黔北咽喉,是西南與中原聯系的必經之地,結交著南來北往之客,故思想開放,善于應酬。《桐梓舊志》:“原屬播地,鄰綦南,近中國之化。家貧好學,人務耕織。信巫鬼,好詛盟。喪葬用鼓樂。婚姻輕財帛。燕會以禮,崇慕華風。”[1]仁懷由于集聚碼頭,且酒業發達,故民風激越獷悍,樸實重義。“仁懷俗淳土瘠,人性獷悍,類分四種,好戰斗,以劫殺為事。刀耕火種,不善絲蠶。疾鮮用醫,惟事巫祝。婚姻世締,喪祭用樂。”[1]赤水、習水也因靠河而居,既可靠山吃飯,亦可靠水營生,同時還可靠赤水河鹽運經營,故老百姓除了勤儉、刻苦、耐勞外,還善于精打細算。《赤水縣志》:“赤水境內居民,歷來習性善良、淳樸、勤儉、刻苦、耐勞。男性以耕植或手工業、商業、勞動服務等職業為本,女性以紡織、刺繡、家務勞動為榮,有‘男耕女織’和‘窮不丟豬、富不丟書’的習性。農民愛好編織竹具,赤水河沿岸居民熟悉水性,善游泳,多從事水上運輸業。境內不同地域的居民,習性亦有所不同。赤水河流域元厚及以南的土城、淋灘、隆興等地人民習性勤勞、刻苦、強悍、好勝心強。元厚以北的城關、復興、大同、旺隆等地人民的習性較溫和、節儉、勤勞、好客。習水河流域長沙、官渡兩區人民的習性大致與旺隆、復興同”。[2]務川、正安、道真、綏陽等地因較早接受漢文化的影響,淳樸尚義、勤勉好文;同時因務川、正安、道真處遵義和重慶邊緣,受巴蜀巫儺文化的影響,古樸淳厚,尚情好巫。務川在遵義是開發得最早的地區之一,較早接受漢文化影響,同時又是遵義最邊緣的地區之一,古樸與開放并存;《正安舊志》:“正安樸實淳厚,以耕耘為生,大略與漢俗同,土人以元宵為年,禮天神,享歲飯,尚未盡變故習。”[1]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道真縣自然人文調查資料》、《道真縣地方概況調查表》記載,道真民風樸實,勤勞節儉。純用漢文,說漢語,語多川音,一般人民知識程度較低,致多方言。因交通梗塞,內外貨物流通交換困難,人民生活清苦。衣以麻棉絲為主,雖富紳亦罕見“洋貨”。食以玉米、大米、麥子和蔬菜為主,肉食為豬、羊和雞鴨,與海味隔絕。城鄉多為瓦房和草房,縣城始有新式房屋建筑。民多崇奉佛、道、儒三教。婚喪禮俗,多崇漢俗古制。《道真縣志》:“明清兩代,大量漢人遷入,與仡佬、苗、土家等族人民錯居雜處,交往,通婚,相互學習,團結發展,漸次融合為共同的地域習俗,同時又保留著各民族各自的習俗特點。”[3]《陳志》:“綏陽敦龐淳固,崇尚詩禮,士多有守,民敦儉樸,夷俗悉除”[1]。鳳岡、余慶百姓除務農外,幾乎沒有其他產業,故行事務實認真,謙恭禮節。湄潭因曾為黔北的商貿集鎮,其民睿智豁達,謙和善商;遵義市(遵義縣)地處中心區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民多關心政治、經濟,關注社會變化,待人熱情、大方。在自然地理環境和文化教育的影響、制約下,遵義習俗因地域差異而形成區別。地域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主導風俗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有時甚至超越了民族界限,讓相同地域環境中的民眾有著大致相同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二
遵義風俗的各種特點,與遵義原生民族的習俗演變密切相關。
郭子章《黔記》云:“黔,故西南夷。”[4]即指仡佬族、苗族等少數民族。新、舊《唐書》所謂的“南平僚”、“謝家蠻”、“趙家蠻”,就生活在今黔北地區。因而,歷史上黔北的主要居民是夷僚。今境內尚存留有仡佬壩、仡佬寨、仡佬巖、濮老場,夷牢(僚)溪、仡佬洞等地名,即是仡佬族居住的明證。據專家考證,夷僚是魏晉后出現的族稱,由古濮人、越人交融發展形成,為今天仡佬族的祖先,是貴州的原生民族,是開荒辟草的“地盤業主”。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羅繞典《黔南職方紀略》就記載余慶、遵義、仁懷、桐梓、正安均有仡佬族分布。歷史上有關仡佬的記載不多,常璩《華陽國志》、朱輔《溪蠻叢笑》、陸游《老學庵筆記》、田汝成《炎徼紀聞》、田雯《黔書》、李宗昉《黔記》以及各時期的《貴州通志》,對仡佬族的歷史生活信息有部分記錄,成為我們今天了解仡佬民族的鑰匙,讓我們看到“仡佬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死黨,觸之則縻沸,得片肉卮酒即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旁無襞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為花仡佬,紅布者為紅仡佬。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于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為“打牙仡佬”,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為棺,葬之路旁。”[5]
“仡佬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左邊上一齒。以竹圍五寸長,三寸裹錫,穿之兩耳,名銅環。”[5]
“仡佬以鬼禁,所居不著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數尺,以巨木排比,葉覆木者,名曰羊棲。”[6]“仡佬婚,親迎時,無論冬夏,必以冷水淋媒,主夫婦后日和順。新婦至,以小木瓢一柄(曰馬匙)置大門下,必新婦踐之至斷,乃吉。”[7]
這些描寫,雖多為他者的眼光記述,但為了解仡佬族的歷史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史記》記載夜郎是“耕田,有邑聚。”由此可知,仡佬族以農耕為主,“畬山為田”,刨土求食,靠天吃飯,順季種獲,農業生產是最主要的經濟類型,故有歌謠曰“仡佬仡佬,開荒辟草”,在風俗習慣上體現出較強的山地農業特征,曾經享有“貢米”之稱的海龍米就是這一經濟模式的成果。同時,“邊夷則椎髻披氈,以射獵伐山為業,”“以銅器氈刀弩矢為禮,以銅鼓橫笛歌舞為樂。”[1]種植之外,養殖、狩獵、砍伐、煉造也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務川仡佬族的丹砂開采和水銀提煉,就可追溯到春秋時期。人們按仡佬族人從事的不同職業而稱謂并描述其特征:土仡佬“男子披草為衣,專與倮羅雇工,每日用油燒熱搽足,故入山如猿猴”;水仡佬“善捕魚,隆冬猶入深淵不畏冷”;打鐵仡佬“以鐵匠為生,且能鑄犁”[4];蔑仡佬擅長編織……
民族個性深刻于民族靈魂深處,民族信仰尤其代表了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特征。常璩《華陽國志》曰:“有竹王者,興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養之,長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8]據《苗疆風俗考》記載,仡佬族稱“竹子”為“蓋腦”,“蓋腦”即“仡佬”的異寫,是傳說中竹的子孫,其說為學界所認可,并為今天的仡佬族接受。仡佬族崇拜竹,以竹為圖騰,其信仰狀況歷史上雖無文字記載而無法考證,但在現實生活中,還存留有竹崇拜的影像:婦女生育后必須將胎盤深埋于竹叢,小孩才能得到竹神的庇護易長,“老了”才能找得到“回家”的路;春節要用竹筒泡種預測莊稼的好壞;建房的屋柱雕刻為竹形,砍竹時要祭祀竹神,一些家族祠堂及墓碑上刻上拜竹圖等,可見其對竹的特殊情感。這些習俗,也普遍地存在于境內漢族之中,體現出文化的融合與共生。
民族民俗風俗體現于方方面面。遵義有36個少數民族,除仡佬族外,人口較多的還有苗族,土家族、彝族等,其風俗文化與仡佬族又有所不同,因此,遵義風俗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保留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因子,同時又帶有改土歸流后大量移民進入貴州所帶來的五方雜呈。
三
遵義風俗文化的形成,與遵義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
春秋時期,遵義境主要由部落方國所組成。今綏陽、遵義、桐梓諸縣是鄨國,習水四周是鰼國,赤水、仁懷一帶為蜀國東南境。到戰國時期,由濮人建立的夜郎國逐漸擴張,鄨國、鰼國成為夜郎旁小邑。“秦時,命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9]鄨國改置鄨縣。郡縣的設置與五尺道的開通,打開了貴州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通道,務川成套青銅葬器的出土,就表明秦文化已深入黔北地區。西漢元光五年 (前130年),漢武帝開發西南夷,以夜郎地分置牂柯郡和犍為郡。犍為郡郡治在鄨,鄨縣成為黔北政治文化中心。武帝“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9],移民的到來,使漢文化隨之傳入西南,境內漢墓及出土文物的中原文化特色之濃,說明民俗已發生了較大的轉變。由此,乃有東漢尹珍跋涉千山萬水,到中原師從許慎,“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10]
但魏晉的長期戰亂,使南中地區成為權力真空地帶,促使境內漢人為適應環境,紛紛“夷化”,融入當地民族之中。唐初,境內居民依然“俗無文字,刻木為契。散在山洞間,依樹為層巢而居,順流以飲。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謁見貴人,皆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鼓賞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罰之,大事殺之,盜物倍還其贓。婚姻之禮,以牛酒為聘。女歸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慚,逃避經旬方出。宴聚則擊銅鼓,吹大角,歌舞以為樂。好帶刀劍,未嘗舍離。丈夫衣服,有衫襖大口褲,以綿綢及布為之。右肩上斜束皮帶,裝以螺殼、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為外飾。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緋束之,后垂向下。”[11]
唐乾符三年(876年)楊端入播,開始了楊氏土官對播州近八百年的統治。南宋時,楊選重視發展文化,聘賢授教。楊軾留心藝文,楊粲崇尚儒術,“土俗為之大變”,開創了“播州盛世”。儒文化的傳播在境內形成了第一個高峰期,但風俗上仍是漢夷雜陳。宋代《遵義軍圖經》記載:“世轉為華俗漸于禮,男女多樸質,人士悅詩書,宦、儒戶與漢俗同。惟邊夷則椎髻、披氈,以射獵、伐山為業。信巫鬼,好詛盟。婚姻以氈矢為聘粧,燕樂以歌舞為佳會。凡賓客會聚,酋長乃以漢服為貴,出入皆佩刀弩自衛。至與華人交易,略無侵犯”。“敦龐淳固,以耕植為業,鮮相侵犯,天資思順,悉慕華風。”[1]
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戰爭爆發,“播土舊民,僅存十之一二。”改土歸流和“移民就寬鄉”的政策,改變了“夷多漢少”的民族構成,對境內文化、風俗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原生民族為了生存,變服易俗,托身漢戶,風俗表征自覺不自覺地趨同漢人,但內心深處始終保留著自己的民族記憶和個性;而新移漢民則人地生疏,與原居住地生存環境相異,為順應環境,也自覺吸納土著居民的優良傳統。不同風俗的相互交融,整合為具有新質的、民族文化與漢文化共存相融的富有特色的區域文化。正如《遵義府志·風俗》所載:“遵義,巴蜀舊壤,民生其間,至今尚柔弱褊阨,精敏輕疾,與班固、常璩所言大致同。而自改土以來,流移來茲者皆齊、秦,楚、粵諸邦人,土著以長子孫,因各從其方之舊,相雜成俗。”[1]而漢文化漸次成為主流話語,《陳志》說:“自明萬歷庚子后,土辟民聚,俗易風移。蠶桑殊少,專事耕農。士愿而好學,女貞而克勤。及入本朝,士風尤盛,人才間出。士質而有文,民樸而易治,崇尚氣節,不恥貧賤,勤耕織,敦禮讓云”。“冠婚喪祭,不尚奢華。人知向學,深山窮谷,猶聞弦誦聲。雖夜郎舊地,當與中土同稱”[1]。但“郡播而還,人猶近古,民多樸魯,士尚謹醇。曩經奇劫,巴渝族姓避亂茲土,遂家焉,漸染于囂凌之習。”[1]故鄭珍感慨曰:“而遺風未遠,初亦有所染漬,久之遂忘其自來。各省之舊,已多非美俗,更沿土風,益成惡陋。而山川風氣,生人成性,類多徑情任私,不準以前憲,不學子弟泰然安行,無或自稍覺其非者;為賢令守可亦晏然坐觀也乎?”[1]
四
具體而言,黔北民性呈現出以下特征:
(一)包容忍讓,好客互助
遵義是典型的移民社會。移民的勢單力薄,原住民的相對弱勢,形成了遵義人謙讓包容、和諧相處的民性,對人對事多忍讓包容,一般情況下不惹是生非。故民諺有:“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忍氣家不敗,吃虧人常在”;“好話三分軟”;“打架場中莫添拳,吵鬧場中莫添言”等語。
被動式移民喪失家園的沉痛和對新環境的疏離,易于使人與人之間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親近感;峻嶺深壑的自然條件,也迫使人們不得不聚集集體的力量以求生存。由此,在處理各種事務上,大都包容寬厚、沖和恬淡、忍讓認理。對鄰里關系特別注重。一家有事,全村幫忙;一家客來,全村親近。諺語謂“當家不能不儉,待客不能不豐”。對“稀客”(平時少有來往的客人)固然熱忱接待,對常客也從不簡慢。共同遵守的信條是:“相交朋友難上難,得罪朋友一時間”。邊遠地區的農村,有不認識的人求宿、求食,并不過問其來歷,一律承應。而且把最好的床鋪供客人住宿,把平時自己舍不得食用的臘肉煮來款待。甚至進山商販,本為求利而來,主人也會忘記他在討價還價時的斤斤計較,而是以禮相待,故不管是作客還是路過,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直至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機關單位、城鎮住戶,住宅逼窄,如客人住宅不下時,同院、鄰舍都會借出自己的床鋪供其使用,特別是在婚喪等事客人多時,更是如此,表現出樸實的民風。
(二)野性大膽,文武兼備
黔北重山阻隔的交通環境,使信息的傳播深受影響;地處邊鄙,中央王朝的管理相對松散,整體生活在一種“天高皇帝遠”的文化氛圍中。觀念上較少受正統文化的制約,思想上較少羈絆,呈現出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態度。“上海人吃啥有啥,四川人說啥就啥,貴州人要干啥就干啥”的俗語,就是很好的寫照。因而,在思想和行為上保持著一種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于是具有敢闖敢干的精神,獨立思考的創新意識,不為舊框所囿的冒險膽略,不甘落后奮力拼搏的思想,打開山門、迎八方風雨的氣度。如黎庶昌的瀝膽上書,對西方精神文明的激賞,開辦西南地區第一座洋務學堂。鄭珍一方面向程恩澤問漢學,汲取外來文化的營養;另一方面又刻苦鉆研,大膽探索。《說文解字》的研究,乾、嘉時名家輩出,專著二三百部。道、咸學者要想突破可以說難上加難,但鄭珍不囿成見,力圖創新,撰寫了《說文逸字》和《說文新附考》,在清代漢學如日中天,皖、浙名家輩出的環境下,爭得了“西南巨儒”的美稱。這是特定地理環境熏陶下呈現的獨特品格和膽識。
遵義開化較早,儒家文化影響深厚,歷來重視文教。境內書院林立,公學私學,遍布城鄉。“人知向學,深山窮谷,猶聞弦誦聲。雖夜郎故地,當與中土同稱”。特別是清乾隆時,“物力殷賑,戶口繁孨,非大歉,歲無不完之征,非死病,臘無不歸之子;經行雖僻,無一二里無塾童聲;省試舉四十八人,郡獲者常逾四之一。”[12]民國初,各地興起平民補習學校,僅遵義縣就400所。民眾將讀書看成是改變生活及命運的基本途徑,民諺謂“窮不丟豬,富不丟書”。黔北人重文不輕武,冉氏兄弟修造釣魚城,清代武舉97人。特別是咸同農民起義時,不少士子棄文從武,如唐炯、黎氏昆弟等。民國初期的動亂,使人們的觀念發生變化,紛紛投身行伍,形成了統治貴州近十年的“遵桐系”軍閥。
(三)信鬼尚巫,敬畏自然
“信巫鬼,重淫祀”的巫儺文化是黔北民間文化的重要構成。雄奇的自然景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無三日晴”的氣候,造成“其俗信鬼而好神”。原始宗教的“萬物有靈”觀,使黔北人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處處控制著人的精神及其行為的靈異世界,“舉頭三尺有神靈”,“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處理各種問題時,均要考慮與鬼神達成“合同”,并形成了相應的活動儀式。占卜、打卦、驅疫、祈禳、度關、圓夢、祀神、謝土、安靈、咒語、儺技等各種儺儀式,為人們祈福禳災、追求平安提供了心理可能。神靈故事、“端公文化”遍布黔北,儺的精神曾經主宰著黔北人的生活,泛神論深入了黔北人的血液和骨髓。
正因為山山水水充滿靈異,賦予了山、水、草、木等一切自然物以生命,形成了黔北人崇尚自然、順應自然、敬畏自然的觀念。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理念,以種植、養殖、采集、狩獵為主的生活方式,都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地靠人養,人靠地養”“修塘如修倉,積水如積糧”“三山六水一分田,栽樹蓄水富萬年”等諺語,即是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不能竭澤而漁,否則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而“念佛三千,不如救鳥一命”“春來不打山中鳥,兒在家中盼母回”更是將自然視為與人一樣重要的生命,體現了對所有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因此,在黔北大地上,“禁止毒魚”,“禁伐山林”等禁示碑各處皆有。正月或三月的“祭樹”更是成為黔北農村一道亮麗的風景。
(四)以農為主,兼營各業
與貴州其他地區相比,遵義素來被譽為“黔北糧倉”,其糧、油、肉的產量約占貴州省的四分之一。大部分縣市土地肥沃,適宜糧食生產。同時,由于糧食是生活的必需品,大多數的家庭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業經營上,多勤勞肯干,認為“鋤頭落地是莊稼”,“力氣是個怪,今天使了明天在”。強調精耕細作,相信“只要用盡心,瘦土出黃金。”并能充分利用環境,因地制宜,發明了不少利用土地的方法,“山頂松、山腰桐、池塘河邊柳叢叢”。運用聰明才智順應環境,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正落到了實處。所謂“靠山”,即是指山地種植、養殖、打獵、采伐;所謂“靠水”,則主要為水上運輸和打漁。
地理條件的相對優越,也使黔北人口增長迅速,土地承載負荷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較為突出。農民依靠土地常常不能滿足生存所需,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以求生存。于是,養殖、打獵、采伐、經商、工藝活都成為老百姓謀生的手段,不僅不受人歧視,相反被認為是能力所在,故各行各業皆有人參與、學習。境內四處林立的山王廟、土地廟、牛王廟、嫘祖廟及供奉的各行業神即是證明。特別是自乾隆七年(1742年)春,知府陳玉壂“始以山東槲繭蠶于遵義”[13]。至道光年間,遵義已是“紡織之聲相聞,槲林之陰迷道路。鄰叟村媼相遇,惟絮話春絲幾何,秋絲幾何,子弟養織之善否。而土著裨販走都會,十十五五,駢坒而立眙。遵綢之名,竟與吳綾、蜀錦爭價于中州。”[13]由于境民大多貧困,經商本錢無多,因此經商主要是從城市批發一些小商品“趕轉轉場”,出賣勞動力,賺取些微辛苦費用。
(五)安土重遷,守舊中庸
僻處一隅,戰亂較少,社會安定,環境較優越,民風淳厚,生存較易,自然產生了“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金窩銀窩,當不住自己的狗窩”等思想,形成了滿足現狀、安土重遷的觀念。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和移民到此帶來的儒家“虎死必守丘”的理念,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念。封閉的地理環境讓民間文化不趨時、不媚世,而身處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僻壤,面對社會巨變,也易于造成心理上的隔膜和恐懼,儒家文化的保守更是讓人封閉和退縮。由此,堅守節操演變為固執己見;不趨時、不媚世蛻化為對新思想、新思潮的盲目斥拒,形成保守、封閉、排外的文化性格,固守家園,缺乏開拓精神和創新能力。如“老不入廣,少不出川”就是明證。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傳統的安土重遷思想始逐漸淡化。
移民之初,多為親屬相招,因而村寨多是聚族而居,形成相互依存的血緣集團。在以氏族血緣組成的村寨中,家庭是社會的最小細胞,由此,個體的理想和追求都是微不足道的,造成個體獨立創新意識常常泯滅在群體意識的汪洋大海之中。黔北人對超出公共準則的人常用的評價語是“過分”。“公共準則”并非普世價值,而是傳統小農觀念。要求每個人為人處世不偏不倚,不出風頭,不冒尖,“出頭椽子先遭難”是人們生活經驗的總結,“槍打出頭鳥”是父輩對子輩的告誡。怕被別人算計,不愿“露富”,保守做人,踏實生活,妨礙了人們的積極進取。
黔北風俗所顯示出的地域特征,與其山川地理、水土物候、歷史民族密不可分,馬克思曾說“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14]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中形成的風俗,在急劇變化的今天已經有所發展,今后的黔北風俗會增加一些什么樣的新內容,是社會工作者應該加以不斷關注和研究的。
[1]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風俗[Z].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點校本,1986.
[2]赤水縣志編纂委員會.赤水縣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
[3]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4]郭子章.黔記.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M].成都:巴蜀書社,2006.
[5]田雯.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6]宋·朱輔.溪蠻叢笑.符太浩.溪蠻叢笑研究[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7]周恭壽修.趙愷,楊恩元纂.民國續遵義府志·雜記.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M].成都:巴蜀書社,2006.
[8]任乃強注.晉·常璩.校補圖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司馬遷.史記·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10]范曄.后漢書·西南夷傳.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11]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12]平翰.道光遵義府志序[Z].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點校本,1986.
[13]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農桑[Z].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點校本,1986.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責任編輯:徐國紅)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Formation of Qianbei Custom and Its Features
LIU Li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Qianbei Culture,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The formation of Qianbei custom is closely related to Qianbei’s geography,soil,climate,history and nationality.In a special culture space,the custom enjoys the following features:tolerance,compatibility,superstition,etc.,which assume a distinctive regionalism.
Qianbei custom;formation;features
G127
A
1009-3583(2014)-0065-05
2014-01-26
貴州省教育廳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項目“黔北風俗研究”(13GH046)研究成果之一
劉 麗,女,貴州遵義人,遵義師范學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