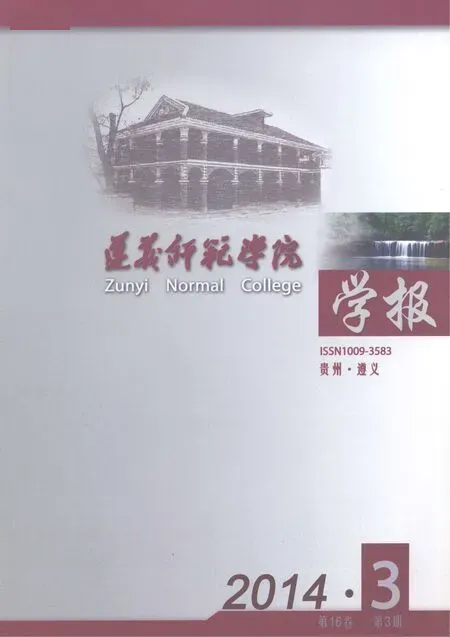中國(guó)年節(jié)文化的族群性呈現(xiàn)——評(píng)吳正彪教授的《苗年》
李國(guó)太
(四川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四川成都610064)
中國(guó)節(jié)日文化豐富多彩,這不僅體現(xiàn)在某個(gè)民族在一年的時(shí)間周期中所呈現(xiàn)出的節(jié)日的豐富性上,而且也體現(xiàn)在五十六個(gè)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節(jié)日文化的多樣性中。在言及中國(guó)的節(jié)日文化時(shí),我們常常首先想到的是春節(jié)。而關(guān)于春節(jié)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看每年春運(yùn)期間全國(guó)涌動(dòng)的人流便可見一斑。實(shí)際上,這個(gè)在傳統(tǒng)上被稱為“過(guò)年”的習(xí)俗雖然是中國(guó)諸多民族所共享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文化體會(huì),但在時(shí)間的選擇和內(nèi)容的呈現(xiàn)上則因各個(gè)族群的文化差異而形成多元的景象。由此可見,中國(guó)的年節(jié)文化并不等同于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春節(jié),它內(nèi)在的豐富性還有待“發(fā)掘”。令人欣喜的是,吳正彪教授的《苗年》正是這樣一部“發(fā)掘”之作。該書將一個(gè)本是天文學(xué)和物候?qū)W的概念置于具體的族群——苗族中進(jìn)行考察,從而在對(duì)苗年的巡禮中體現(xiàn)出苗族文化自身獨(dú)有的知識(shí)體系和文化傳統(tǒng)。這本書至少呈現(xiàn)出以下幾個(gè)特點(diǎn):
一、將苗年置于苗族文化的整體中考察
苗年并非孤立的文化現(xiàn)象,它僅僅是苗人生活節(jié)律中的一個(gè)音符。如果拋開對(duì)苗族文化的整體性考察,便很難理解“年”在苗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對(duì)此,作者在廣泛的田野調(diào)查的基礎(chǔ)上發(fā)現(xiàn)了“苗年”和苗歷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性,從而為這一流動(dòng)而又循環(huán)的節(jié)點(diǎn)尋找到事實(shí)的根據(jù),他指出:“在時(shí)間的差異上,苗年總是與同一年中的其他節(jié)日流程有著明顯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如果把水稻的播種作為一年中一個(gè)與此相關(guān)的節(jié)日如“開秧門”、“祭橋”等的開始,那么“吃新節(jié)”就是這一節(jié)日時(shí)段的一個(gè)前奏,苗年自然是整個(gè)節(jié)日時(shí)段的活動(dòng)高潮期。”[1]p16實(shí)際上,作者對(duì)苗年的這種思考是他長(zhǎng)年行走在苗疆,對(duì)不同地域內(nèi)苗族文化傳統(tǒng)的體認(rèn)和感悟的結(jié)果。他深刻地意識(shí)到,節(jié)日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展演一個(gè)民族的文化表征,更在于“(節(jié)日)如同一個(gè)個(gè)竹節(jié),為人們提供了把握不可把握的時(shí)空的方法,它象征著時(shí)空段落之間有意味的交接點(diǎn),自然成為生活中的高潮部分”[2]。實(shí)際上,苗人對(duì)苗年起源的敘事歌謠便呈現(xiàn)出這一認(rèn)知:
“年從何處起?歲源月亮梢,天宇邊緣來(lái),彩色養(yǎng)人眼。天上爭(zhēng)著要‘年’過(guò),地上爭(zhēng)著要過(guò)‘年’。只因天上手臂長(zhǎng),天上搶得‘年’去過(guò),地下百姓手臂短,空手失望回家轉(zhuǎn),無(wú)奈只好游山去,植物長(zhǎng)勢(shì)作標(biāo)志。莊稼種收把節(jié)過(guò),節(jié)慶舉家品美味,全家老少皆高興。”[1]p32
在這頗具神話色彩的敘述中,蘊(yùn)含著苗人對(duì)“年”之由來(lái)的認(rèn)識(shí)。而“年”的標(biāo)志便在于“植物長(zhǎng)勢(shì)”,而節(jié)日“舉家品美味,全家老少皆高興”的活動(dòng)與世界各民族的豐收節(jié)無(wú)異。苗年、苗歷與農(nóng)耕文化的聯(lián)系由此可見一斑。
農(nóng)耕文化遵循自然的周期性規(guī)律,文化上最直接的體現(xiàn)在對(duì)歷法的重視上,歷法本身便隨著周期性的循環(huán)而在一年中農(nóng)事的不同關(guān)節(jié)點(diǎn)呈現(xiàn)出族群文化的特征,“年”恰好是上一個(gè)循環(huán)系統(tǒng)與下一個(gè)循環(huán)系統(tǒng)的交接點(diǎn),三者的關(guān)系由此體現(xiàn)出來(lái)。對(duì)此,徐新建教授已有精到的評(píng)價(jià):“對(duì)苗年的考察,最突出之處在于將其與特定的農(nóng)事活動(dòng)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展示了苗族及其年節(jié)的農(nóng)耕性和族群性,也就是特定的生態(tài)性和文化性。”[3]但如果將視野放得更廣闊,全方位地考察農(nóng)耕文化中“年”的特征,不僅可以為跨文化比較研究提供一條新的路徑,也能為深入闡釋每一個(gè)族群的“年”文化提供新視角。
二、關(guān)注苗年民族性與區(qū)域性的統(tǒng)一
《苗年》中所呈現(xiàn)的“苗年”是復(fù)數(shù),因?yàn)橥敲缒辏诿缱宓膬?nèi)部卻存在巨大差異。不同方言區(qū)的苗族,不僅對(duì)“苗年”的稱法各異,就連其在時(shí)間的選擇上都具有地域特征。作為一種節(jié)日文化的苗年,在時(shí)間和空間上同一民族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作者認(rèn)為這是由于“苗年節(jié)的形成,不僅體現(xiàn)了各個(gè)不同支系的苗族既有對(duì)自然環(huán)境生物性適應(yīng)的一面,也有對(duì)周邊不同文化族群存在著社會(huì)性適應(yīng)的一面。”[1]p17在“苗年與苗族的傳統(tǒng)歷法的關(guān)系”一節(jié)中,他進(jìn)一步解釋道:“苗歷在各個(gè)苗語(yǔ)方言及土語(yǔ)區(qū),由于居住的自然環(huán)境不同,氣候條件不一樣,農(nóng)作物的成熟期有長(zhǎng)短之分,因而所形成的苗歷體系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由此所導(dǎo)致的苗年在過(guò)節(jié)時(shí)間、節(jié)日規(guī)模、相關(guān)儀式及節(jié)日活動(dòng)等存在著一定的差別”。這種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統(tǒng)一與背離,恰好證明了苗族內(nèi)部的文化多樣性。節(jié)日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意義又何在呢?就在于“有時(shí)某一民族節(jié)日的民族性會(huì)在文化的同化過(guò)程中逐漸被淡化,但節(jié)日的地域性卻依然在時(shí)空建構(gòu)上保留著不同族群相互認(rèn)同和共有的文化烙印。”[1]p22這樣的認(rèn)知,如果沒有常年行走在田野中的經(jīng)歷,是很難體會(huì)到的。
在多元文化主義時(shí)代,多元之“多”的涵義需要再審視,因?yàn)楹斓摹翱缥幕备拍钜坏┻M(jìn)入文化比較的層面,往往便會(huì)忽略文化持有者的多樣構(gòu)成。在跨文化比較研究中已有學(xué)者指出:“對(duì)西方文明開端代表作的文學(xué)人類學(xué)審視,表明原有的以西方地理觀念為標(biāo)準(zhǔn)的東西方劃分及民族國(guó)家劃分,怎樣長(zhǎng)期發(fā)揮著束縛思想和遮蔽真相的副作用。以族群為單位的重新認(rèn)識(shí),將打開一個(gè)我們以前所未知的新世界。”[4]這種反省意義重大。但在此基礎(chǔ)上研究者也不應(yīng)忽視族群內(nèi)在的文化差異性,苗年或許是一個(gè)很好的例證。
三、田野調(diào)查與主位視角
吳正彪教授是出生在黔東南的苗族,又長(zhǎng)期在苗族地區(qū)進(jìn)行關(guān)于苗族語(yǔ)言與文化的人類學(xué)研究,這種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shì)使他能夠從族群本位的視角出發(fā)考察苗年。實(shí)際上早在2006年,作者就已經(jīng)完成了《苗族年歷歌和年節(jié)歌的文化解讀》,《苗年》可謂是那本書的姊妹篇,是作者思考苗族年節(jié)文化的深化。這種持之以恒的對(duì)本民族文化的關(guān)注,體現(xiàn)出作者對(duì)本民族文化的熱愛。《苗年》中引述了一首苗人的歌謠這樣唱道:
“為什么我們要使用自己的語(yǔ)言?為什么我們要配飾自己的裝束?不為什么呵,只因?yàn)槲覀兊拿纸忻缱濉?/p>
為什么我們要閱讀自己的書本?為什么我們要弘揚(yáng)自己的藝術(shù)?不為什么呵,只因?yàn)槲覀兊拿纸忻缱濉?/p>
為什么我們要繼承祖先留下的文化?為什么我們要保留自己的傳統(tǒng)習(xí)俗?不為什么呵,只因?yàn)槲覀兊拿纸忻缱濉!盵5]
或許,這也同樣契合作者寫作本書的心情。《苗年》不僅對(duì)“苗年”文化作了全方位的考察,而且花了大量筆墨就苗年的價(jià)值及其保護(hù)和傳承現(xiàn)狀作了考察,這或許正是源于一個(gè)苗族知識(shí)分子內(nèi)心對(duì)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憂慮感。
但作為一個(gè)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者,作者又十分清楚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任何過(guò)于感情化的論斷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苗年》中,作者總是習(xí)慣于將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呈現(xiàn)給讀者,通過(guò)當(dāng)?shù)厝说闹v述,使讀者在“聽故事”的過(guò)程中直接進(jìn)入苗族人的視角去感受苗年的豐富。
四、結(jié)語(yǔ)
苗年僅僅是一個(gè)展現(xiàn)苗族文化的窗口,而苗族也僅僅是中國(guó)諸多民族和世界諸多族群中的一個(gè),如果以“苗年”為中心延展開來(lái),不僅能看到被單數(shù)化和平面化處理的苗族文化本身的豐富性,也可以看到中國(guó)多民族文化之“多”的現(xiàn)實(shí)性,從而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提供西南個(gè)案,為世界文化多樣性提供中國(guó)的田野案例。因此,《苗年》僅僅是一個(gè)開始,是一個(gè)發(fā)掘中國(guó)多民族文化的良好開端。
[1]吳正彪.苗年[M].貴陽(yáng):貴州民族出版社,2011.
[2]吳正彪.苗族年歷歌和年節(jié)歌的文化解讀[M].北京:中國(guó)文史出版社,2006.61-62.
[3]徐新建.節(jié)日體現(xiàn)的文化選擇[J].三峽論壇,2011,(5).
[4]葉舒憲.“世界文學(xué)”與“文學(xué)人類學(xué)”[J].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2011,(3).
[5]苗青.中國(guó)苗族文學(xué)叢書·西部民間文學(xué)作品選(1)[M].貴陽(yáng):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