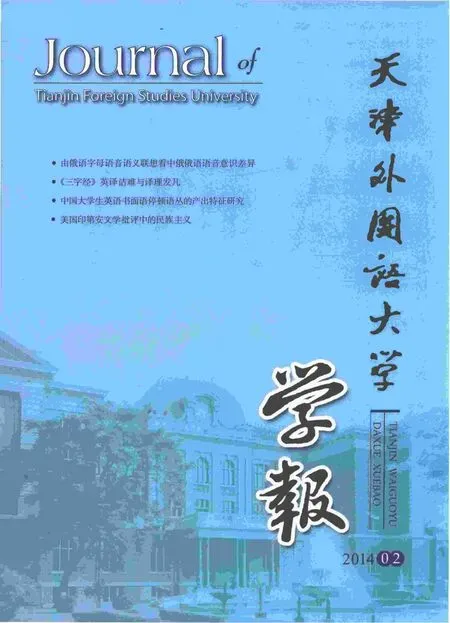亞當·斯密有關語言緣起的學說
賈洪偉
(首都師范大學大學英語部,北京 100048)
一、引言
英國哲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因其提出的經濟學理論而被世人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其著名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對世界經濟學界貢獻頗多,大體可歸納如下:(1)提出“個體為中心”、“追求利潤的正當性”、“經濟自由發展”、“私有財產制度”和“價格機制”;(2)主張“分工”、“價值”、“分配”、“積累”和“賦稅”的經濟學理論;(3)率先運用“系統”(system)、“對比分析”等理論和方法研究經濟問題;(4)開啟現代經濟學研究之門,為現代經濟學研究奠定了理論和方法基礎。通過清末嚴復的翻譯,中國接觸了亞氏的經濟學主張,也因而受到了深厚的影響,這種影響遺存至今。但是,中國學人鮮有所知的是:經濟學并非是亞氏的主要學術活動,而是脫胎于亞氏后期的哲學思想,系用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結合哲學思維探討當時經濟現象的結晶。
縱觀亞當·斯密的學術生涯,他的學術興趣可分為語言研究、邏輯、道德哲學和經濟學,語言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語言緣起”和“修辭與美文”兩方面,發表相關論文兩篇:《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1761)和《論語言緣起與進步》(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1762/1985), 前者為專文,后者為系列學術報告,兩者融于一體,以《修辭與美文演講集》(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1963,1983,1985)為名出版發行;道德哲學研究的成果以《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為代表,經濟學研究則以《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為代表,其中以《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最為著名。截止目前,國內論及亞氏語言學成就的文獻相對匱乏,幾乎只有一篇由郭谷兮譯介蘇聯學者的《亞當·斯密的語言類型學觀念》(1986年)。
有鑒于此,本文擬以亞氏專文《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1761)為史料,輔以相關的論著,系統地挖掘亞氏創作該文的背景、內容及其貢獻,旨在為國內語言學者研究語言緣起學說、普遍語言學思想史和寫作普通語言學史提供史實線索。
二、創作背景
據亞當·斯密于1763年2月7日給喬治·巴德(George Baird)的一封有關威廉·沃德 (William Ward)《語法論》(Essay on Grammar,1765)的摘要中交代,亞氏研究語言的興趣始于Gabriel Girard (1677-1748)的《法語語言原理》(Lesvrais principesde lalangue Fran?oise, 1747),促使他思考語言結構緣起的問題①(Berry,1974:131;Rae,1965:160)。之后,他開始一系列有關語言修辭的探討和演講,但大多言論并未發表,而是在其逝世后經昔日門生之手編輯出版《修辭美文演講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1963), 其 中收 錄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及其縮寫版《論語言緣起與進步》(1762/1985:46-49)二文,方才有了今日讀者得以一見的亞氏語言緣起觀。
據J. c.Bryce (1985:27-30)的相關陳述,《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一文的思想初見于1751年1月16日亞氏就職格拉斯哥大學邏輯修辭學會會長時的演講稿《論思想的緣起》(De Origine Idearum)。亞氏的《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一文先后發表5次,初次發表于1761年由T.Beckett和P. a.Dehondt合編的《語文學雜錄》(Philological Miscellany,1761)第 440至479頁,全稱為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 and the Different Genius of Original and Compounded Languages。之后曾以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單獨發表,屬于上文的縮寫。最終該文被附錄于《道德情操論(第三版)》(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67),使其得以廣泛流傳。
相對而言,亞氏論述語言的著述流傳后世的不多,其原因主要在于他性格怪異,大致可歸納如下:據《時報》有關亞氏的訃告(1790)所言,“博士大人極其珍愛其講稿,視其為財富。一旦看見有人記筆記,他就擔心講稿被轉寫、出版或重復宣講,也憤恨學生草率地筆錄課堂內容 ”②。去世前,亞氏要求銷毀其學術手稿,一批學術手稿在其去世前一周銷毀,其中包括《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一文。亞氏的有關學術思想借其門生之手得以流傳后世,與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遺作情況雖略有類似,但亞氏思想的流傳是違反其遺愿的。
三、語言緣起說
亞氏當年與蘇格蘭學者Kames和Hume等建立“蘇格蘭精英會”(Select Society of Scotland),旨在推動蘇格蘭人講讀英語,構成他講授和探討修辭、美文,以及語言結構形成的客觀要求和主觀動機。在有關語言思想的論述中,亞氏有關語言結構緣起的觀點,主要體現在《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和《論語言緣起和進步》二文之中,其中后者為前者的縮寫,曾一度被疑為學生的課堂筆記構成。因此,本文僅以《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1985:180-196)為依據,探討亞氏該文的內容、主張和性質。
1 內容
從內容看,該文分為三部分:探討名詞、形容詞、介詞、動詞、代詞的緣起問題,探討詞類從推理到現實的歷史:屈折系統與語言結構的斷裂衍化,以分析語與其前身綜合語的衍化評價屈折系統與語言結構斷裂的衍化。
在探討詞類形成問題時,亞氏將形容詞和介詞放在名詞的范疇加以闡述,將代詞放在動詞的范疇加以闡述,這樣劃分的原因在于:名詞屈折系統適于抽象的過程分析,即事物品、性、數與關系的分類,清楚地體現了思維與語言緣起的有機關聯。有關名詞和動詞緣起的問題,他認為:“名詞與動詞形成于同一時期,盡管他相信動詞是最早形成的詞類。”(Smith,1985:188)。
有關名詞范疇的形成問題,他認為,“用特定名稱指稱特定事物,即名物化可能是語言緣起的第一步 ”③(ibid.:180),因為“最熟悉和最常提及的事物產生特定的指稱”,“新事物沒有自身的指稱,但與具有類似指稱的事物彼此相類”,形成舊名指稱新事物的套路,即“個體專名”成為“通名”,構成事物的最初類分,即種屬,以專有品性和特定關系來區分,使人類得以用“最強有力、最鮮活的方式”衍化成長。他把形容詞稱為“名詞性形容詞”,即“表示修飾特定主體品性的詞類”(ibid.:181),用于“區分通稱‘種’下的特定客體”,如“綠色的樹”用于區分于“枯黃的樹”。同理,介詞表示“共處關系客體間的關系”,即介詞前后詞匯間兩客體的存在關系,用于“區分同屬之下特定客體間的關系”。由于品性和關系都不能抽象地存在,表示事物具體存在方式的詞匯必然較早地產生于抽象詞匯,因為抽象詞匯的發明更費力。盡管名詞性形容詞的發明比抽象的實義名詞略為自然,但需要經過“抽象”和“泛化”方可。就形容詞而言,本質上通指而抽象的形容詞預設某一類屬的思想。若要用綠色區分事物,勢必要觀察非綠色的事物,方可用綠色來指稱,這一做法萌生了詞匯衍化的“比較機制”(ibid.:182)。在顏色名稱尚未固定之前,勢必要經過 “排序”、“分類”、“抽象”和“比較”的心理過程。
指稱物質品性的另一種方式既不要“抽象”,也不需要將品性與主體進行區分,比發明名詞性形容詞自然很多,那就是:依據名詞被賦予不同品性而對其給予更異(ibid.:182)。對此,他先以“性”為例做出如下闡述:“‘性’與‘中性’自然地被視為修飾特定客體及其特有品性,通過修飾名詞實體來表達,而不是通過通指和抽象的詞匯來表達。顯然,這種表達方法與其所指稱的物和思想具有更加確切的類比性”(ibid.:183),且“名詞實體在無形容詞修飾時,自身能夠表達上述三個品性,即陰性、陽性和中性”(ibid.:184),“性并非屬于名詞性形容詞的范疇,雖為物質所固有,但不屬于物質品性”;隨后他以“介詞”為例闡述這一方式,即“介詞的形成比名詞性形容詞需要更大程度地抽象和泛化,原因有三:(1)“與品性相比,介詞表示的關系是超自然的,因為品性可感知,關系難以感知;(2)盡管介詞表示共存客體間的關系,但其形成并非不牽扯抽象④;(3)就屬性而言,介詞屬于類屬詞匯,在用法規范化伊始,就被認為可同樣指稱其他類似關系,若在發明之初,無一定程度地比較和泛化,不足以成事”,進而他闡述了表達句法關系的四種例外:(1)運用詞匯屈折手段無須抽象;(2)非介詞類種屬名詞表達關系時無須泛化; (3)非種屬名詞表達句法關系無須比較;(4)用共存賓語屈折變化表示句法關系無須抽象、泛化和比較。他以介詞of為例闡述“現代語言中取代古代語言‘格’的介詞是最普遍、最抽象和最超自然的,因此可能是最后發明的”(ibid.:186-187)主張,即越常用越抽象的詞匯就越難于發明,同時闡明了介詞緣起與人類思維關系的觀點。最后他從自然論的角度闡述表示“數”名詞的衍化,認為“數字是最抽象、最超自然的,是人類思維的產物,并非是人類思想形成之初所固有的”(ibid.:187),“在現代語言中尚有遺留,存在于大部分詞匯之中”,并論證了數字形成與人類思維的關聯。
基于上述,他認為: “最初形成的語言結構,依據實體詞的格和數變化形容詞的詞尾,性的變化亦是如此,如同語音某種規律的形成和類比傾向一般”(ibid.:188);“形容詞表示名詞實體的品性,但其偶爾呈現的關系不會對其品性產生變化”,進而得出結論:“若古代語言形變過于繁復,其配合就更復雜,形變的復雜程度與配合的復雜程度建基于同一原則,即:語言形成初期很難形成抽象的普通術語”(ibid.)。
有關動詞范疇的形成問題,亞氏認為:“動詞一定與語言的緣起嘗試并行,若無動詞的輔助,表達就無法成行”(ibid.),而且“無人稱動詞是第一批動詞緣起的成員,”由獨詞表達一個思想完整的具體事件,進而以“獨詞表達事件”分裂為“多個成分表達事件”為例,闡述“無人稱動詞”向“人稱動詞”的衍化,主張“人稱動詞緣起于古語動詞第三人稱單數”,系“人類不同程度地將幾乎每一事件分為許多超自然的成分,由不同詞類以不同方式排列小句和句子中的成分”,致使“特定事件的表達變得愈加精微而復雜,整個語言系統變得愈加緊湊、結構聯系愈加密切,易于保存和理解”,然后他以第一人稱代詞I為例,闡述“人類語言緣起初期,很自然地避免發明較為抽象的人稱代詞,而是依據第一、第二、第三人稱所肯定的事件變化詞尾,構成古代語言的普遍現象”(ibid.:190),從而得出結論:“鑒于原始語言很難發明數字名稱,將雙數和復數引入名詞實體的形變,在動詞的配合上效仿了類比的行為”(ibid.:191)。
在探討詞類從推理到現實的歷史即屈折系統與語言結構的斷裂衍化問題時,亞氏把語言分為合成型(拉丁語、法語、英語和意大利語等)和非合成語(希臘語),前者形變與配合簡單、結構繁復,后者結構簡單、形變與配合繁復。經過分析,他認為,“語言的基礎和原則衍化的簡單程度與結構變化的繁復程度成反比”(ibid.:194),即語言結構簡單,形變與配合就繁復,反之亦然,其根源在于:“民族混合致使語言發生雜糅,各國語言本可能以此步調發展衍化,即若結構不會變得更復雜,形變和配合也不會變得更簡單”。“從語言基礎和原則看,語言結構有所簡化,引進普遍的形變,不管什么樣的性、數和詞尾,每個字都一樣”。同樣,“反復的配合也幾乎一并消失,幾乎每門語言都存在一個動詞,被稱為實義動詞”(ibid.:192)。
在探討分析語與其前身綜合語的衍化,評價屈折系統與語言結構斷裂的衍化問題時,亞氏“語言結構越簡單就越不完善,越不擅于表達諸多目的,其原因如下:語言簡化后更冗余,幾個詞表達以前獨詞表達的意義”(ibid.:195),這樣的觀念與亞氏所持的修辭和美文信仰有關,屬于美文層面的“表達形式美”;語言原則簡化后更不悅耳,屬于修辭和美文層面的“音美”;簡化后的語言不僅不悅耳,還束縛了發音的方式,屬于修辭和美文層面的“結構美”。可見,亞氏是從審美的層面對屈折系統與語言結構斷裂的衍化問題加以評價的。
2 主張
針對語言的緣起現象,亞氏提出如下主張:語言作為思維概念化的外現,揭示語言的緣起與人類思維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自然語言優越觀;語言結構的衍化猶如語音規范化和相似性一般,越來越傾向于類比化傾向,致使語言衍化傾向于系統化的走向;語言結構的簡化受“個體”發展的影響,換言之,語言結構繁復程度的增加是諸語混合的結果,是不同民族混居造成的;語言結構越簡化就越不完善。
就語言的緣起與人類思維的關聯而言,亞氏主張介詞的形成與人類思想存在一定的關聯,如詞匯of適合表示(上述)所有關系,因為of自身不表示特定關系,而只是普遍性的關系,系思維從介詞聯結二實體詞的本質和位置推理而來(ibid.:186);數詞的形成與人類思維存在關聯,如除去數字化客體的關系,數字是一個最抽象、最超自然的思想,是人類思維的產物,并非是人類思想形成之初野蠻人類所固有的(ibid.:187),等等。就語言結構衍化的系統化走向而言,亞氏并未用systemization這一術語,而是采用analogy⑤,love of analogy⑥,similarity of sound和a certain regularity of sound⑦,說明語言衍化正逐漸走向規范化和系統化。此外,在開篇第一頁,亞氏采用兒童和小丑為例,闡釋“專名”向“通名”的衍化,暗示了人類語言采用“類比”走向“系統化”的傾向。在論述語言體系的衍化時,他認為現代語言對于“特定事件的表達變得愈加精微而復雜,整個語言系統變得愈加緊湊、結構聯系愈加密切,易于保存和理解”⑧(ibid.:190),公開使用system一詞,說明亞氏萌生了語言的系統觀念,這一觀念后來在《國富論》(1776)中得以發展成熟。
就自然語言觀而言,亞氏在闡述“無人稱動詞”向“人稱動詞”衍化時,采用各門語言有關“下雨”的表述,闡明了“自然語言比人為發明的語言表達更為簡明”的主張(ibid.:189)。就語言的衍化發展受到“個體”發展影響而言,亞氏分析了以“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為代表的合成型語言,他發現拉丁語的衍化受到古希臘語和古托斯卡納語(Tuscan)的影響,法語的衍化受到古拉丁語和古弗蘭克語(Frank)的影響,意大利語的衍化受到古拉丁語和隆巴德語(Lombard)的影響,英語的衍化受到法語和薩克遜諸語(Saxon languages)的影響,從而得出結論:民族混合致使語言發生雜糅(ibid.:192),致使語言結構簡化。就語言結構越簡化就越不完善的主張而言,他認為“語言簡化后更冗余,幾個詞表達以前獨詞表達的意義”(ibid.:195);語言原則簡化后更不悅耳;簡化后的語言不僅不悅耳,還束縛了發音的方式。
3 性質
縱觀該文,我們發現亞氏并非如同當時歐洲語言學家那樣從宗教神學角度,探討語言的緣起問題,而是同法國普遍唯理語法那樣從邏輯角度和語言自然觀的視角,探討語言結構的形成問題,該文稱之為“語言緣起”。由于亞氏倡導發起蘇格蘭精英會,力推蘇格蘭人民講讀英語,且自身又反復講授語言修辭與美文課程,“他的興趣大多集中于源自文學和語文學語言結構的本質和演變,但該文并非根植于修辭和美文的原始語境,并未包含源自語文學特有的語言特征,特別體現于該文最后一部分的審美標準,以及西方文學傳統的語言數據缺陷”(Land,1977:678),只局限于希臘語、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等主要的歐洲語言。相對而言,“亞氏較為關注語言結構,形成了語言自然結構、語言結構演變的本質與根源的普遍理論觀點”(ibid.:677),旨在解釋語言結構、相關語言結構間歷史衍化的普遍性問題。
四、學說貢獻與影響
縱觀語言研究的歷史,《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1761/1985)一文的貢獻可歸納如下:(1)18世紀語言理論尚未留意語族問題,仍將語法視為一套公則,即規定性的文法,依然以拉丁文法為綱,以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為據,亞氏該文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考察了詞類(名詞、形容詞、介詞、動詞和代詞)與詞序的衍化問題(Berry,1974 :132);(2)在以洛克認識論(非早期的推理)為主導的18世紀,哲學實證理論為語言研究提供了新途徑,旨在以事實、緣起和目的為基礎,探討語言的心理現實和功能,而非語言現實與邏輯相關聯,亞氏的著述做出了“榜樣”(ibid.:132);(3)18世紀的學者紛紛從宗教神學、有機理論、理性和情感視角,探討語言緣起問題,亞氏則從有機和理性(邏輯)的視角,探討困惑18世紀語言理論家的自然語言結構衍化的問題(ibid.:132-133);(4)亞氏提出了語言符號學的denotation(指稱)和systemization(系統化)的思想,前者見于開篇第一句(用特定名稱指稱特定事物,即名物化,可能是語言緣起的第一步),后者參見本文“主張”部分。
此外,該文還涉及語言相對論的思想。譬如,在論述數字名詞緣起時,他認為,“在社會初始階段,人類所能關注到的數字區分,可能只有‘一’、‘二’和‘許多’”,“我曾了解到,有些原始種族的語言只能表達前三個數字”(ibid.:187-188);在闡述動名詞的屈折變化和關系與品性時,他認為,動、名詞詞根的屈折變化與世界的結構相對應,其相對應的關系和品性與客體不可分割,其行為和施動者與事件不可脫離。
有關亞氏該文的影響,我們以亞氏所受的影響和他對后人的影響兩個部分加以闡述。以《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1761)為起點追溯亞氏的語言學思想,我們發現亞氏在闡述語言緣起時,將語言分為“合成型”和“非合成型”,受到法國語言學家Abbé Girard在《法語語言原理》(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angue fran?oise,1747)中提出的語言三分法:langues analogues(類比語或類似語)、langues transpositives(變位語)和 langues mistes(混合語),前兩種分法曾被法國語言學家Beauzée(1765)所借鑒,與亞氏的二分法頗為相似(Noordegraaf,1977:2),且亞氏在給朋友巴德的信中曾提及Girard對其產生的影響;亞氏使用的“事件”的概念,屬于語言學結構的前句法概念,極可能是經由盧梭(Rousseau)的文本借鑒于孔狄拉克(Condillac)和杜馬爾塞(Du Marsais),因為這個句法概念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德國赫爾德(Herder)和蘇格蘭蒙博杜(Monboddo)的著述中。
以該文為起點跟蹤亞氏語言緣起觀的影響,我們發現,盡管該文篇幅不長,覆蓋面也有限,但完全可以代表亞氏的語言觀點,這些觀點曾一度影響了蘇格蘭的語言學者,如Hugh Blair⑨,Dunbar和 Monboddo等,可見亞氏該文在蘇格蘭本土的影響(Berry,1974:138)。據安得生(Julie Tetel Andresen,1990:25)在《美國語言學評論史:1769-1924》(Linguistics in America 1769-1924:A Critical History,1990)中所述:“在美國語言學的萌芽期(1769-1815),即語言政治概念時期,美國有兩部經常被引用的蘇格蘭語言學著作,一部是 Monboddo(James Burnett)的《論語言的緣起與進步》(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1774-1809),一部是亞氏的語言學著述,特別是《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1761)一文”。可見,亞氏語言緣起說在本土以外的影響,但尚未傳播到遠在東方的中國。
五、結語
任何時代做出的任何成果都不免帶有那個時代所特有的痕跡和特征。就亞氏《有關語言緣起的思考》(1761)一文而言,該文至少具有其時代局限性和作者自身視角的限制。18世紀西方語言學界尚未發現梵文的語法著作,仍局限于歐洲主要語言的探索,尚未形成歷史比較語言學,仍局限于語言結構(主要是詞類)和語言緣起的探討,構成了當時西方語言學的典型特征,亞氏也不免受到這一學術氛圍的影響,是為亞氏該文的時代局限。
亞氏一直從事修辭和美文的教學與研究,導致他傾向于關注文學和語文學主題范圍內的語言材料,旨在用這些材料探討語言結構的本質和演變,不免造成語種材料不全面的問題,只局限于歐洲主要語言(古希臘語、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的探討,忽略了其他主要類型的語言,如德語、俄語、梵語、漢語、日語、西班牙語等。因而,他在基于上述五種語言材料的探討所得出的結論(即語言的基礎構造和原則的簡化程度,與結構繁復的程度成反比,且語言越簡化就越不完善,越不擅于表情達意),能否具有適用于所有語言的普適性,不免令人質疑。
亞氏在以詞類為切入點,探討語言結構形成的過程中,忽視了傳統的語言類分問題,遺漏了詞類劃分中的主要成員“副詞”,卻未做任何說明;對于詞類衍化的主要手段“泛化”(generalization),亞氏未能給出構成詞匯 “泛化”的(家族)相似性標準,致使“泛化”的基礎不夠明確,不免使人質疑“泛化”手段的有效性,進而影響了語言結構衍化三大手段(比較、抽象和泛化)的充分性。亞氏的論述過程及其所得出的結論受其理論假設影響較大,即基于“語言普遍地反映某些邏輯范疇(品性、關系、行為等)”的觀點,從詞類角度探討語言的結構,旨在確定詞類的生成順序,但從詞類角度研究語言結構的衍化,不免使人誤以為“詞類先于語言結構而存在”。此外,就該文題目中language所采用的復數形式,我們斷定亞氏旨在探討世界語言結構形成的普通語言學問題,但他卻只采用了古希臘語、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的語料,忽視了梵語、漢語、日語等諸門語言的考察,影響了該文結論的有效性。
最后,盡管該文存在些許的不足,但就以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為脈絡發展的語言而言,該文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可資借鑒之處。若將該文題目修改成《有關西方語言緣起的思考》,似乎更為可取。
注釋:
① Mr. Ward, when he mentions the definitions which different authors have given of nouns substantive, takes no notice of that of the Abbé Girard, the author of the book called 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angue Fran?oise, which made me think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he had not seen it. It is the book which first set me a thinking upon these subjects, and I have received more instruction from it than from any other I have yet seen upon them. If Mr. Ward has not seen it, I have it at his service. (Rae, 1965: 160)
② The Times Obituary records: “The doctor was in general extremely jealous of the property of his lectures... and, fearful lest they should be transcribed and published, used often to repeat, when he saw any one taking notes, that he hated scribblers.”(1790)
③ 本文所涉及的引文若沒有注明,均為本文作者的翻譯,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④ “在人類尚未把表示關系的詞匯規范化之前,人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能夠從相關客體的角度抽象地考慮這種關系,因為客體的思想無論如何無法進入介詞的所指。”(Smith,1985:184)
⑤ 顯然,這種表達方法與其所指稱的物和思想具有更加確切的類比性(Smith,1985:183)。
⑥ 普遍原則建立于無意識之中,且逐漸地形成了語言傾向于類比和語音相似性衍化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語法規則的基礎(Smith,1985:185-6)。
⑦ 最初形成的語言結構,依據實體詞的格和數變化形容詞的詞尾,性的變化亦是如此,如同語音某種規律的形成和類比傾向一般(Smith,1985:188)。
⑧The expression of every particular event became in this manner more intricate and complex, but the whole system of the language become coherent, more connected, more easily retained and comprehended(Smith,1985 :190).
⑨ 早年為亞氏愛丁堡大學修辭與美文講座的學生,后來曾借用亞氏手稿內容用于自己的修辭學文稿之中(Blair,1838:238)。
[1]Andresen, J. T. Linguistics in America 1767-1924: A Critical History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2]Beauzée, N. Langue [A]. I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é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 [Z]. Par une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Mis en ordreetpublié par M. Diderot, et, quant a partiemathématique, par M. d’ Alembert. Tome neuvième,Paris: Briasson,1765.
[3]Berry, c.J. Adam Smith’ s Considerations on Language[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4, (1).
[4]Blair, H. Lectures on Rhetoric & Belles Lettres[M]. Edinburgh, 1838.
[5]Girard, a.G. 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angue fran?oise[M]. Paris: Librairie Droz,1747.
[6]Land, S. K. Adam Smith’s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7, (4).
[7]Noordegraaf, J. A Few Remarks on Adam Smith’ s Dissertation(1761) [J].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1977, (1).
[8]Rae, J. Life of Adam Smith[M].New York: a.M. Kelley, 1965.
[9]Smith, a.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 and the Different Genius of Original and Compounded Languages[J]. The Philological Miscellany ,1761, (1):440-479.
[10]Smith, a.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M]. London: Nelson, 1963.
[11]Smith, a.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M]. Edited by J. c.Bry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5.
[12]С. Д. Кaцнельсон.亞當·斯密的語言類型學觀念 [J].郭谷兮譯 .國外語言學,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