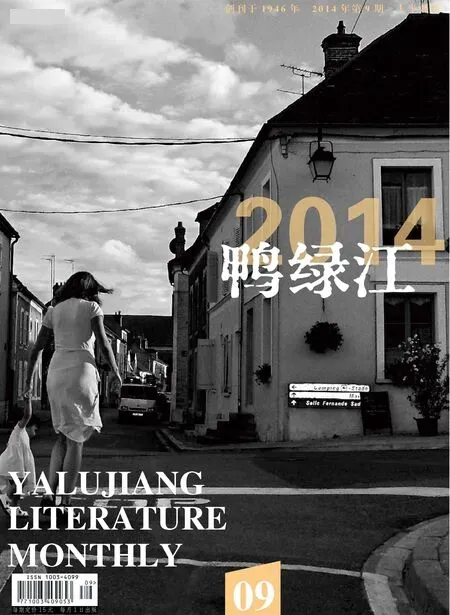不可摧毀的生活與文學
王 蒙
不可摧毀的生活與文學
BUKECUIHUIDE SHENGHUOYUWENXUE
王 蒙

王 蒙,祖籍河北滄州,1934年生于北京。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學者,曾多次獲得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在國內首開意識流等創作先河,倡導作家學者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討論,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現代寫作技巧的開拓者。著有長篇小說代表作《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戀愛的季節》、中短篇小說代表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夜的眼》、《布禮》等百多部(篇),其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他樂觀向上、激情充沛,成為當代文壇上創作最為豐碩、始終保持創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俄、日、泰、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希伯來(以色列)、瑞典、挪威、荷蘭、越南、韓等二十余種文字,在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發行并多次獲得國外重要文學獎項。
我是在不得已與不無困惑的情況下遠赴新疆、另辟蹊徑的。然而,作為個人的人生經驗,我在新疆農村與當地農民特別是維吾爾族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親密無間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文藝工作者的“下生活”。我相當徹底地做到了與各族農民打成一片。生活面的拓寬,沉潛到邊疆大地上的所觀所知所感,性格的錘煉,遭遇的積淀,對于一個寫作人來說,堪稱難能可貴,刻骨銘心。我愛這里的天山、伊犁河、綠洲、人、生活、歌曲與食品。即使在政策偏頗、民生艱難的歲月,生活仍然是強健的、豐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我的體會是,不妥的政策會扭曲生活,而勞動人民的真實與熱烈的生活,卻完全可能消解假大空“左”的荒唐,生活與文學仍然不可摧毀,仍然多彩多姿,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當時光進入70年代,快四十歲了,我開始考慮寫作的事。1971年我離開公社去五七干校,1973年我回到城市擔任自治區文化局創作研究室的維吾爾文翻譯,1974年,在詩人鐵衣甫江的幫助下,我開始了長篇小說《這邊風景》的寫作,得到了創作研究室領導阿不拉尤夫同志的支持。
我無意挑戰“左”的意識形態,但是我必須、本來就是愛生活、愛人民、愛兄弟民族、愛邊疆、愛祖國的。我盡量適應當時難于完全接受的某些宣傳口徑,努力使之圓融于我汲取與消化了的生活細節、生活故事,日常的善惡逆順、喜怒哀樂、愛怨情仇;歷史的風云雷電、滄桑巨變、激蕩沉浮,邊陲的異域風情、民族特色與別有新意之中。而且我選擇了一個以反誹謗為主題的盜竊案件為故事的核心,我也算戴著“左”的鐐銬跳舞,而跳出了那么多的真情,那么多的趣味,那么多的戲劇性與動作性,那么多的對于邊疆、國家、人民的愛。用心亦良苦矣。

2009年,王蒙在伊犁大街上和鄉親們跳起民族舞

1972年夏天王蒙夫婦與他們的三個孩子
說來好笑,1974年正式開始動筆,1976年“四人幫”垮臺,1978年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邀我去北戴河改了三個多月稿子,等到稿子改出來,發現文稿受“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習‘老三篇’”、“人民公社化”等不合時宜或有嚴重偏頗的政治命題的影響,似乎正在變得不合時宜起來。我一面表示將會認真修改,一面拿出少量章節,在《新疆文學》、《東方》等雜志上發表。越改越覺得“它的缺點就像灰塵散布在空氣中,你聞得見,卻抓不住”(此話出自拙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我算是遭到了“報應”。于是七十萬萬字的文稿束之高閣,放到我后來遷入的北京前三門一處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屋的頂柜里,并在那里沉睡了三十五年。
一直到了2012年3月,正是在妻子崔瑞芳去世的天塌地陷的時刻,我的孩子找到了這厚厚的手稿,他們讀了,贊不絕口,與我說起此事。我先是說此稿先天就中了“左”毒,難以挽救,后來自己重讀舊稿,悲從中來,喜從中來,淚從中來,甚至是驕傲從中來。我原來曾經那樣地深入到伊犁的農村之中,我原來做到了對于少數民族的生活與文化的那么深入的理解與把握,我原來寫出了那么多細膩的生活細節,那么撼動人心的歷史故事與生活故事,我原來寫得這樣動情!啊,畢竟這是文學,這是生活,這是土地,這是那個時代的農村故事。我還發現,雖然當時的生活里有時籠罩著極左的霧霾,但這些霧霾畢竟常常只是停留在事件的表層,而霧霾下邊,仍然有生活,有愛心,有奮斗,有青春的活力,有感人的錯綜復雜與恩仇交織,更有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體的創造歷史、改變歷史的中國夢。還有,我寫得最動情的是主人公在政治運動中遭到的誹謗,寫起被誹謗來我不但刻骨銘心,而且痛心疾首。行了,不用多說了,即使是戴著鐐銬的舞蹈,仍然跳出了王蒙的動作,跳出了王蒙的心曲,王蒙的風格。
作為家庭遭遇不幸后的自救,作為我個人的盛年之作的起死回生,作為上世紀60年代的小說寫作空白的彌補,我在2012年對之作了某些有限的卻也是必要的修訂與增補。一是在不動人物與情節框架的前提下,把一些過分夸張與應景的句子刪掉或弱化,如對反修與中蘇矛盾的描寫,關于一個地主婆子的破壞活動的描寫,關于階級斗爭與繼續革命理論學習的描寫等。這些修改與刪節的總字數不超過全文的5‰即一千五百字。另外,為了說明此書是新世紀才出版的,為了對今天的讀者負責,我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學著司馬遷的“太史公”與蒲松齡的“異史氏”的口吻,在每一章后面加上“小說人語”,略加說明或點撥,向讀者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也發發重讀舊稿、重涉舊文的萬千感慨。
那個時候年輕,那個時候深深沉浸在邊疆農村,那個時候老老實實地寫情節、懸念、人物性格、生活細節、風俗畫與風景畫,那個時候說一不二地歌唱著人民、大地、愛情與團結友誼。在這樣一部上下兩冊的大厚書終于在冷凍三四十年之后冰釋、融化、問世之際,我更感動于我們的歷史進程,感動于偉大的祖國土地上的善良人民,感動于歷史的強大,生活的強大,文學的強大。歷史沒有空白,人民永遠可親,生活不可摧毀,文學因為艱難而獨具風格與特別蓬勃的生命。
反響
《光明日報》2013年5月份“光明書榜”第二名
《中國新聞出版報》2013年4月份優秀暢銷書排行榜第三名
南國書香節2013年度“最受讀者關注十大圖書獎”稱號
入選《廣州日報》第五屆“中國圖書勢力榜”年度好書評選活動
入選中央電視臺“2013中國好書”
《這邊風景》是2013年的重要收獲,具有反復地、深入地去進行研討和探討的價值。這幾年來的中國文學和中國小說,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反思歷史。王蒙先生寫于三十九歲的作品,經歷幾十年后,放到2013年來,依然有力地加入了這個話語,加入了我們整個中國文學對于當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反思和認識。他所提供的這樣一部作品,對于我們怎么思考、怎么去表現歷史,怎么去認識歷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性意義的。
這部小說在我們整個新時期文學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本,它寫得豐富性感、非常豐饒。王蒙對于我們的民族歷史,以及民族歷史中的那些活生生的政治保持著一種負責任的書寫態度,小說中對于民俗、對于各族人民生活風景等等的描寫,具備很高的文學價值。其中的政治內容和歷史內容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可以讓我們在歷史的具體性中去理解和認識我們的過去。同時,其諸多價值之中,有一個價值今后對我們GDP的增長也會起促進作用,會有很多博士碩士要來分析這本書的版本問題,探討這本書各個版本之間的異同,這個異同不僅僅是版本上的異同,這個異同由此可以看到豐富的社會歷史魅力,看到一個作家與時代、與社會歷史之間的復雜關系。
這樣一部書是值得反復品讀的,它本身已經經住了將近四十年時光的考驗。我相信,它在未來同樣能夠經得住更長時間的考驗,能經得住更多的讀者去閱讀,也能經得住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和研究者深入的研究。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敬澤

王蒙早年在新疆
王蒙在這本書“小說人語”里寫到“我們有一個夢,它的名字叫做人民”。他進一步表達人民不是簡單的改造我們主觀世界的人,不是簡單的工農兵,不是貼著年代標簽的、已經固化的某一種觀念。由此對人民的侵略、嘲笑、反叛都是歷史的悲哀,聰明的悲哀。我覺得“風景”是有寓意的,《這邊風景》不是平常說的風情、風俗、風貌這樣一些淺層的、外在的東西,而是支撐著這部著作的生活質感。王蒙這部跨越時間的著作,揭示了一個真理:真理永遠在是非正誤中修正,而生活之樹常青。當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斗爭、科學試驗、修正主義等等這樣種種歷史賦予的詞匯都隨著歲月的遷移,隨著時間的變化,當這些輔助于人民之上的種種大詞,在時間的歲月、空間的距離中退出了最初的光澤之時,人民的光澤才開始漸漸地顯露出人民最初的、最樸素的樣子。
《這邊風景》這部長篇的初衷,我想王蒙當時可能并沒有特別自覺意識到要寫人民,以上所說的有關“人民”的認識也是經過歲月的沉淀發酵而來的。但時隔四十年之后我們再閱讀,結合人物和敘事時都會發現在四十年前的文本里,從中凸顯的的的確確是人民。這里的人民不是概念,而是作者十六年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得來的珍寶,是對于最具體的個人的“人民”的還原。而具體的人,人民的人,正是新疆王蒙青銅時代里的黃金。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主任、著名評論家何向陽
這本書的出版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會引起文學研究領域一些重要的話題,也肯定會是今后學生們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文本。王蒙為整個20世紀的歷史提供了一個非常可貴的文本。
今天我想從“內與外跨界寫作”的概念去談這部文本:一,歷史之內與歷史之外。這部作品毫無疑問,它是一部歷史性的寫作,它深深地扎根于某種特定的歷史之中,是承受了一種歷史壓力的寫作,同時,王蒙又能站在歷史之外,在一個歷史臨界點上,給我們提示。第二,民族之內和民族之外。我們的文學95%是在寫漢族的生活,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在有這么一部作品,一個漢族的作家用這樣一種視角去寫少數民族的生活,這在整個中國的當代文學史中是非常罕見的,給當代文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獻。第三點,關于文學之內和文學之外。在文學之內和文學之外,王蒙用他強大的個人風格的創作性,他對生活的知性的一種契入,他對人物性格的把握,他對生活細節那種機智的、賦有才華的表現,他做出了他的一種探索,這是非常可貴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評論家陳曉明
《這邊風景》跟我們今天熟悉的長篇小說完全不一樣的,它是那個呼嘯年代史詩全景式的產物,也是王蒙先生盛年操筆的一部作品。這個作品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漢語文學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這是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非常基礎的問題,我們寫了很多當代文學作品,但是在寫到少數民族的時候往往就寫不下去了,或者請一些少數民族專家來寫,然后硬把它拼湊起來,似乎是完成了一個任務,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有文化隔閡。而王蒙從這個隔閡中走出去了,他真正地進入了維吾爾族人民和新疆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進入了他們的語言文化習俗,也贏得了像姑麗娜爾·吾甫力等其他好幾個來自新疆的作家的認可,他們承認王蒙是他們的知心人,是新疆的知情人,這恐怕是漢語文學一個很大的突破。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評論家郜元寶
《這邊風景》填補了王蒙個人創作史的一個空白,使王蒙橫跨六十年的文學創作鏈條得以完整。在這個鏈條上,《這邊風景》占據了一個承上啟下的位置,就整個中國當代小說來講,我覺得這部作品的出版有重要的意義。
這部小說是一部關于新疆的百科全書,從故事情節來講,有很強的可讀性、傳奇性;從筆調來講,又具有非常強的學術性。同時,《這邊風景》是當代文學一次跨文化的寫作,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與維吾爾族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熟練掌握了維吾爾語,通過閱讀維族人的作品,對維吾爾族的文化,特別是當地的風土人情、心靈世界有了高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走進了維吾爾族人的內心和真正的精神世界。正如維吾爾詩人熱黑木·哈斯木所認為的:“漢族作家反映維吾爾生活,能讓維吾爾讀者稱贊叫絕,說到底,就因為王蒙通曉我們的語言文化,懂我們的心。”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著名評論家溫奉橋
我想說的是關于“小說和公共話語”。我用的是維吾爾語的閱讀方式,可能和大家有不一樣的體會。我覺得王蒙寫下了作為維吾爾人時代的作品,他可能不是刻意要表現維吾爾族的生活,他是寫他自己那一段作為維吾爾人的生活。比如說用維吾爾族方式來討論國家的問題,還有討論“善”的問題,還有討論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和溝通、彼此和解的問題。
第一,這部小說首先是一部隱喻,是對中國各種關系的一種思考和對中國未來的思考,他用小說的方式來解讀他的體會。這部小說本身就是用藝術的方式看待歷史的一種隱喻,用一種善的立場告訴我們在關注自身的同時也要關注那些過著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生活的人。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怎樣用自己的方式演繹國家的故事,以及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對國家的情感,其實這方面在漢語文學中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也是被長期忽視的一個重要命題,那么,在這一點上,這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在當代中國語境顯得尤其重要,而且它裹脅了很多問題的出現,有很多這樣的群體被忽視,他們的話語沒有很好的表達場合。我想王蒙這部作品恰恰切中了民族關系的要害。
第二,小說中的“小說人語”也是一個非常強烈的隱喻,它代表文學在當代社會的一種隱縮,地位的一種隱縮。我覺得它還有一種隱喻是在維吾爾族文學領域中的說書人,說書人從波斯引入到維吾爾族之后,曾經在維吾爾族的古典時代是一個文學主體,它承載著文學的延續,代表社會的希望和力量。這部小說中的“小說人語”,其實代表一種文學在我們當代比較尷尬的地位。而且也非常好地隱喻了維吾爾族文學發展的歷程。
第三,《這邊風景》這部小說帶有比較強的政治參與,它呼喚更加和解的、包容的公共話語的產生。它是打開新疆的鑰匙,它是一個帶有很強的隱喻色彩的、關于中國的故事。
——喀什師范學院科研處處長、人文學院教授姑麗娜爾·吾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