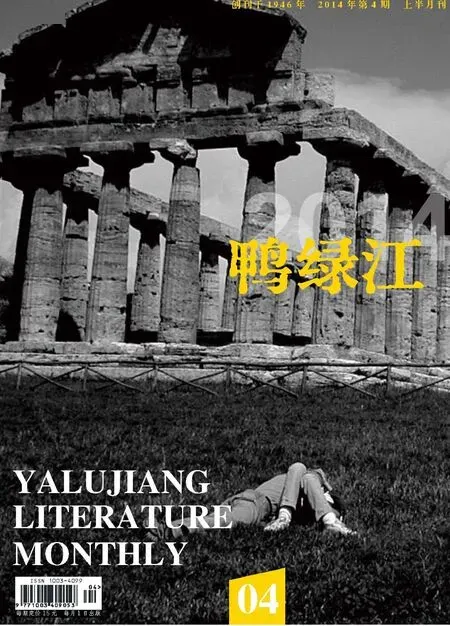悲憫中展現溫暖,精致中蘊含深刻
——淺析安勇的小說
張 英
【理論·本省聚焦】
悲憫中展現溫暖,精致中蘊含深刻——淺析安勇的小說
張 英
安勇是遼寧錦州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近十年代表作品說主要包括《螞蟻戲》《玩一個游戲》《老劉的廁所》《請大黃不要亂叫》《鑰匙》《軟肋》《諾潔斑馬線》《青苔》《鐘點房》《一九八五:性也》等。作為近年來逐漸崛起的新銳作家,安勇的作品雖然多是短篇,卻具有濃厚的悲劇意味,但又讓讀者體悟到了一些溫暖與幽默,留給讀者心靈的震撼與共鳴是持續的、揮之不去的。
一
悲劇意識是人類的一種特有的精神現象,海德格爾曾用“深淵時代”和“世界之夜”來描述悲劇,他認為悲劇是人的精神淪落和毀滅的一種精神狀況,是一種“世界的黑暗化”“精神的閹割、瓦解、荒廢、奴役誤解”。 [1]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于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們的行動,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泄。”[2]“悲劇”一詞對讀者來說,不僅在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而且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也并不陌生。在小說、電影、電視劇等藝術形式的表現中,悲劇比喜劇往往更能造成受眾心靈的震撼,留給受眾回味和共鳴的空間更多一些。正因為悲劇通常以人物悲慘的結局來結尾,所以揭示生活或命運的罪惡的力度更強,在受眾心中激起的悲憤更久。安勇的小說就充滿悲劇的意味。《螞蟻戲》中的小趙老師從一出場就帶給我和幾個小伙伴心靈的震撼,小趙老師是那樣美,那樣優雅,像陽光溫暖著孩子們的心靈和夢想。孩子們是那么喜歡她,以至于發現小趙老師和小常來往頻繁時,孩子們頓生嫉妒之情。可是當小趙老師回城的夢想一點點破滅后,“小常走后,小趙老師的臉上再也看不到那兩個圓圓的酒窩了,她的臉色非常蒼白,和她死時的臉色一樣。我固執地認為,從那時起,小趙老師實際上已經死了。”(《螞蟻戲》)小趙老師的美在小常、二叔的玩弄踐踏之后走向毀滅。小趙老師的后背被二嬸用柳條抽打成一道道紅印子,在二嬸的打罵聲中,小趙老師滿臉淚水,一句話也沒有說,沒有任何反抗,她就像螞蟻戲里被關起來的螞蟻一樣,深陷絕境,無處可逃,任憑怎么掙扎也無濟于事。讀安勇的《螞蟻戲》不禁讓人想起嚴歌苓的《天浴》,《螞蟻戲》中的小趙老師和《天浴》中的女孩文秀都是那樣美麗、善良,那樣富有青春氣息,她們都是知青,她們都夢想有一天能回城。然而對她們來說,回城終究是一場夢,而為了實現這一夢想,她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她們一點點走入歧途,走向毀滅。

張 英,遼寧錦州人。渤海大學國際交流學院講師,遼寧師范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從〈小團圓〉看張愛玲接受熱潮》(《小說評論》2010.6)、《論明星選秀節目》(《新聞愛好者》2008.1)、《張愛玲小說“影視熱”原因探尋》、(《電影文學》2007.12)、《中國當代軍旅小說的受眾接受研究》(《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2009.3)、《網絡娛樂新聞圖片編輯的問題與策略分析》(《編輯之友》2010.10)等多篇論文。
“悲劇用形而上的慰藉來解脫我們,不管情況如何變化,生命仍然都是堅不可摧的、充滿歡樂的。”[3]在世界上,愛是永恒的主題,愛也是最具悲劇性格的。《軟肋》中高傲而聰明的褚艷天一點一點被覃遠志所俘獲,成為覃遠志的奴隸和玩物。她在知道覃遠志已婚的事實后,一怒之下動了殺機,開始失去理智后的瘋狂報復。“有三五秒鐘的時間,褚艷天好像突然變成了一尊石像,保持著僵立的姿勢一動不動。然后,她的喉嚨里傳出一陣野獸般刺耳的尖叫,在叫聲里,她飛快地跳下炕,把掛在北墻上的一把砍刀握在手里,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對準覃遠志的一只手砍了下去。”而瘋狂之后,褚艷天仿佛看見自己成為自由自在暢游的魚,她真的能解脫嗎?
《一九八五:性也》中的我、智行東、薛德松、薛德松的老婆每個人都逃不出時代和個人的悲劇命運。《一九八五:性也》中的智行東,綽號“自行車”,同學和老師都這樣叫他,他坦然地接受這樣的稱呼,反而覺得我叫他的真名奇怪。而當智行東經受一系列打擊后,他不再允許任何人再叫他“自行車”,“自行車咔嚓一聲就從班級里消失了,就像它出現時一樣突然。后來我想,其實智行東是變得越來越接近我們了,但反而讓我們越來越感覺陌生。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說不清道不明的。”智行東的話帶有蒼涼的意蘊,也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你看這些葉子,最初可能長在一棵樹上,但風一吹,就各奔東西,指不定飛到哪兒去了。是不是就像我們,如今在一起,中考后就要天各一方?”《青苔》中的小顧,雖然智力不夠健全,但是不能掩蓋他自身的美和他對愛的渴望。這樣一個善良的小顧在莫麗雅的謀害下淹死了,小顧不會再成為莫麗雅與老秦婚姻道路上的絆腳石,而當莫麗雅的心愿實現了,帶給她的不是喜悅,而是不盡的悲哀。《鑰匙》當中依然流露中很強的悲劇意識,“坐在床頭的椅子上,看著面前躺著的那個人,她驀然感到,人的生命原來是如此的奇怪,那些經過的漫長的歲月,不過是畫出了一個圓弧,從終點回到起點時,人,又回復到了他呱呱墜地時的形態。”
《鐘點房》里的主人公覃曉雅想為自己活一次,想出軌一次,可是出軌的對象綦連安和丈夫的反應都和自己想象的相距甚遠。她感到無比失望。覃曉雅想把青春的時光再抓回來,可是青春早已在生活的打磨中遠去。“她終于意識到,男歡女愛的故事已經離她很遙遠,遠得就像前胸和后背,左耳和右耳,紙牌的正面和反面,雖然近在咫尺,但卻天涯相隔。她已經翻過來了,現在和蘭姨一樣都是反面,有的只是刻板的圖案。她已經不再留意時間,那些時間散落成一顆顆沙粒,而她是一條被扔在沙上的魚,掙扎是死,不掙扎同樣是死。”通過人物形象的心理刻畫,安勇將人物的悲劇命運展露得淋漓盡致。
二
文學創作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創造活動。不管時代如何變換,不管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如何改變,有一種標準恐怕不會因讀者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那就是文學作品總會在某一層面上帶給讀者精神的共鳴和慰藉,帶給讀者心靈的震撼和溫暖。不管是哪種文學體裁——小說、詩歌、散文,也不管文學作品的篇幅長短,優秀的文學作品總能體現出這樣一種特質。安勇的小說就是這樣。雖然安勇的作品中人物都為悲劇命運所籠罩,但是讀安勇的小說會帶給讀者一種莫名的感動和溫暖。這種溫暖來自于安勇對人生和世界的認識,來自于作品中人物形象。作為審美活動,文學創作的核心是尚“善”。 真、善、美即文學創造的價值追求。作為一種精神活動,文學創造的價值取向在不同的題材領域、不同時代的作品中各有自己獨特的表現內容,然而人文關懷則是古往今來一切優秀文學作品的永恒主題,它是“善”的集中體現。安勇的《青苔》《諾潔斑馬線》《鑰匙》等小說中,人物的身上充滿一種善良與溫暖,體現著人性的美好。《青苔》中的傻子小顧用自己的方式去詮釋他對愛的理解,《請大黃不要亂叫》中的父子之間隱晦的感情讓人動容。《諾潔斑馬線》中的人物佳惠和成發雖然是殘疾,但他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當佳惠的女兒車禍去世后,“四馬路小學放晚學的時間到了,佳惠拿起那面小旗穿過馬路站在路邊,抬頭向馬路的對面一看,成發正和她相對站著,手里拿的是自己干活時穿的紅圍裙。兩個人隔著馬路比一個手勢,就無聲地笑了。從這以后,每當中午和晚上放學時,佳惠和成發就會準時出現在路邊,每人手里一面小旗護著學生們過馬路。”他們的行動讓每一個人肅然起敬。雖然生活當中有很多不幸,有很多悲劇,但是安勇讓我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讓讀者看到了溫暖和希望。“按常情,循常理。當我以這樣一個定位重新打量身邊的人和事時,我發現,原來可以寫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諾潔斑馬線》這篇小說,就是在這個思路下寫出的一篇習作。”(安勇創作談《平平常常的生活》)
《鑰匙》中的女主人公對公公的猥瑣齷齪的行為非常憤怒,但是卻沒有跟丈夫發泄的勇氣,在如何解決的問題上不斷掙扎。此時,公公的車禍讓事件發生了轉機,也讓女主人公的心理態度發生了改變,當她面對躺在病床上雙腿截肢的公公,她再也恨不起來了,“這些事做完后,她用力搬起那個人的身體,把那只弄臟的墊子撤了下來。在水房里洗凈了墊子,她打來一盆熱水,又給他擦了第二次。倒掉臟水,打了一盆干凈的熱水,她給那個人擦洗臉和手。她做得很慢,很細致,躲開扎在手上的針頭,把每一寸皮膚都仔細擦凈。她做這些事情時,那個人始終緊閉著眼睛,好像是睡著了,也好像是又一次陷入了昏迷之中。給那個人擦臉時,她發現他的眼角里涌出了兩道淚水。她淡淡地笑了笑,輕輕把眼淚擦掉。但一轉身,眼淚又涌了出來,她再次擦掉,還輕輕在那個人的臉上拍了拍。”這就是人性,此時的女主人公無比坦然放松,安勇刺痛了人性深處最脆弱的那根神經,也撥動了人心靈深處最溫暖的那縷情懷。
《一九八五:性也》中人物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正當少年的孩子們住校以后每頓飯都吃不飽,即使吃了,一會兒也就餓了。“我”向父母求救,當父母知道我的窘境后,火速送來吃的,這就是人間最溫暖的親情。作者用無比形象心酸的語言呈現給讀者這樣一個場景:“爹后來告訴我,媽邊翻餅邊哭,眼淚掉進鍋里,不時發出滋的一聲響。爹也急壞了,向二伯借了自行車,把餅給我送到了學校。爹到時,餅還熱乎著呢!”

當代作家當中,余華的小說也不乏帶有這種溫暖幽默的東西。在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中,在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的日子里,在接連吃了幾十天的稀粥之后,許三觀用口述的方式給兒子們做紅燒肉:“看在我過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給你們每人炒一道菜,你們就用耳朵聽著吃了,你們別用嘴,用嘴連個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豎起來,我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們自己點。一個一個來,先從三樂開始。”“我就給三樂做一個紅燒肉。肉,有肥有瘦,紅燒肉的話,最好肥瘦各一半,而且還要帶上肉皮,我先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有手指那么粗,半個手掌那么大,我給三樂切三片……”[4]面對著饑餓,《一九八五:性也》中我用順口溜兒向親人訴苦:“今有一事相求,不知如何開口。食堂吃得太差,餓得實在難受;肚子咕嚕亂叫,渾身上下發抖。要想兒子活著,快送吃的來救。”半夜里,“黎大白唬突然慘叫一聲,蝎子蜇了似的從炕上跳起來。同學們都被吵醒了,胡立偉拉亮電燈。原來,是黎大白唬另一側的同學,在夢里啃豬蹄,把他的手拉過去咬了一口。大家笑一氣,再躺下時,都加了小心,把手藏進被子里。”就這樣,安勇筆下的人物用幽默化解困苦,他試圖讓讀者看到悲劇背后的一抹亮色。
三
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有深刻的思想意蘊,還有完美的藝術表現,是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結合。安勇的小說篇幅相對短小而完整,精致而含蓄,卻不失韻味。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比起來,長篇小說由于篇幅較長,章節較多,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推動等方面,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是容易出現瑕疵的。作者不可能每一章都寫得很精彩,是可以有張有弛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會忽略一些不出彩的細節。而中短篇小說則缺少這方面的“優勢”。在有限的篇幅內設置完整的故事情節,刻畫鮮明的人物形象,特別是性格豐滿的圓型人物形象是很難的。這對從事中短篇小說創作的作家來說,無疑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和要求。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的魯迅就是這樣一位作家。我們知道,魯迅一生沒有進行長篇小說的創作,他的小說集《吶喊》《彷徨》中的作品,無論是表現農民題材的《阿Q正傳》《故鄉》,還是表現知識分子題材的《孔乙己》《傷逝》《在酒樓上》等,都是短篇小說,都是難以超越的文學精品。安勇也以創作微型小說和短篇小說見長。《螞蟻戲》《玩一個游戲》等都是短篇小說。安勇作品的取材相對狹小,題材具有一貫的連續性,但是在溫婉的書寫中彰顯犀利的筆鋒。安勇筆下的人物,不是帝王將相,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平凡的人物,特別是一些底層的人物。在題材人物的選取上,頗有魯迅的遺風,蘊含“小中見大”的精神特質。《玩一個游戲》《老劉的廁所》《諾潔斑馬線》等小說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底層的人物。作者試圖展示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當代作家余華曾指出:“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變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漸地被更多的讀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時代在變化,還是人在變化,我現在更喜歡活生生的事實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認為文學的偉大之處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憐憫之心,并且將這樣的情感徹底地表達出來。文學不是實驗,應該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探索不是為了形式自身的創新或者其他的標榜之詞,而是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將人的內心表達出來,而不是為了表達內分泌。”[5]在人物和題材的選擇上,安勇在提到創作《諾潔斑馬線》這篇小說時說:“我也終于明白,諾潔大染房這個店名起得恰如其分,因為在這繁華熱鬧的街邊,他們用獨特的方式守護著一個只屬于他們的世界,拒絕了外界的紛擾和喧囂,固守著他們內心的那份純潔和寧靜。而這份純潔和寧靜,不正是每個人都在渴求和期盼的情感嗎?”(安勇創作談《平平常常的生活》)
安勇筆下的這些人物之間的情感有的甚至很卑瑣,難掩一種畸形的情感和心理的糾結。《玩一個游戲》中小慧和丈夫在平淡的生活中失去性愛的激情,在一個游戲中,他們將彼此想象成另外的人,在想象的刺激中兩個人都扮演著他人,這種表演不斷地癡迷入境,惟妙惟肖。直到有一天,當丈夫扮演的大王因為受賄被捕,妻子扮演的余小娥也抓起來了,他們才停止了游戲。《老劉的廁所》中老劉為了在只有二十平米的家里給日漸長大的女兒騰出一張床的地方,想盡各種辦法。最后把廁所挪到了懸空的陽臺上。老劉滿意自己的杰作。而晚上,老劉拉著妻子玉蘭在廁所里完成“天時地利人和”的事兒。《鑰匙》當中的公公竟然鐘情于自己的兒媳婦,《青苔》中的精明美麗的莫麗雅不由自主和傻子小顧發生了關系,《請大黃不要亂叫》里的父親犯的錯誤是偷看別的女人上廁所。《鐘點房》里覃曉雅的夢想是能有一次出軌的機會。這就是安勇獨特的敘述視角和情感切入點,作者沒有直接歌頌或揭露生活和人性,也沒有主觀去評價,而是在這種冷靜的敘述和錯位的愛戀中,滴滴帶血地一一呈現。
四
安勇的小說語言通俗,帶有濃厚的東北地域文化色彩。東北方言是東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北方言簡潔、生動、形象,富有節奏感,特別能體現東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特點。“東北語言是最具有親和力的語言,它從來都是直白和直通人心的,猶如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質樸而純真,不矯揉造作,不留余地。它充滿了張力和情趣,能神奇地把人和人之間的距離縮短,讓你永遠都感到不用設防的親切和真誠。”[6]安勇原來在地質勘探隊工作,這樣的工作經歷使得作家的足跡遍布邊塞江南。多年的野外生活,使安勇獲得了豐富的人生閱歷。安勇小小說的敘述語言生動形象,世俗化的敘事,與生活貼近,親切而自然。通過方言表現人物形象的作品,給人以全新的感覺。東北讀者讀起來會感到格外親切,即使南方的讀者基本也能看得懂,而且閱讀新鮮感十足。《老劉的廁所》中這種東北方言運用得非常鮮明。如“在北方干五六年了,能想出把廁所掛在窗戶外的還一直沒遇著過,不用問,老劉是第一位。瓦工說,這可真應了那句話了,高空中拉屎——有一腚(定)水平啊!”這種歇后語的使用使得小說充滿幽默色彩。再如,“女兒的小床和他們的大床就隔著一道布簾子,放個屁都得一點兒一點兒地往出抻,更別說和王玉蘭有點兒啥舉動了”、“老劉就不敢再嘆氣了,他平時挺聽王玉蘭的話,王玉蘭雖然說話沖點兒,可對他特別好,一點毛病也挑不出來。”、“后來紙盒廠黃了,王玉蘭雖說沒工作,人家一直也沒閑著”、“第二天早晨,老劉燒完開水,就借了老趙頭兒家的倒騎驢,自己騎著上了建材市場。建材市場上隨處都有拉腳的”“接了水管子頂天每月給老孟家一些水費也就行了。”在這里,“啥”“沖點兒”“黃了”、“拉腳”、“頂天”等詞語都是北方常用的生活俗語和方言。《軟肋》中這樣的例子也有很多,大頭對蟈蟈擠眼睛,說:“我看跟咱一斤倒挺合適的,要不我們哥兒幾個幫你拉古拉古?”(“拉古拉古”是聯系、撮合的意思)大頭看雪下得很大,就急了,沖著老龍瞪眼睛,直著脖子吼:“干啥玩意,下這么大雪還能出去干活嗎?”老龍照大頭屁股來一腳,“小兔崽子,你沖老子嚷啥子,自己出門往山上看看。”《一九八五:性也》中:“飯不飽,就鬧個水飽吧,總比餓著強。課上到一半就壞菜了,不知不覺尿來了。”(“壞菜”是糟了的意思)“拉古拉古”“壞菜”等詞語的運用十分符合作品中人物的時代背景和身份角色,無形中增添了作品的真實感和形象性。

“讀者對作品的接受絕非無條件的、被動的接收,像一架收錄機那樣,而是在閱讀之前由其全部的生活經驗和審美經驗構成了對作品的一定的鑒賞趨向和心理定勢,即期待視野。這種期待視野潛在地支配著他對作品的接受方式和程度。”[7]安勇的小說不僅語言通俗,運用大量的方言土語,而且他的小說帶有濃厚的東北地域文化味道。用安勇的話說,這是一種“故鄉的味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會有極強的親切感。安勇的《螞蟻戲》寫的都是童年的記憶,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小村子里,作家給這個村子起名叫八間房。“這個名字起得有些隨意,不太負責任,不太正規,光看這個地名,也不太像能生長出小說的地方。如果瀏覽比例尺足夠大的地圖,很快就會發現,在東北三省的版圖上,叫八間房的地方一抓一大把,再一抓,又會有一大把。它們頂著同一個名字,星羅棋布在廣袤的東北大地上,看似毫無個性,甚至難分彼此,但實際上,每個“八間房”都有屬于自己的故事,每個“八間房”也都會放飛屬于自己的游子,而每一個游子的心中也都有一條永遠無法斬斷的根。”安勇的作品力求清新簡練,他筆下的人物純真質樸,感情隨心而動,那種作品當中的很多細節勾起一代讀者不盡的回憶,“那年冬天,知青們浩浩蕩蕩開進村子里時,我正胯下騎著一根木棍,馳騁在村中的土路上。我左邊跑著的是于大華,右邊跑著的是丁二光。我們用手響亮地拍著自己的屁股,嘴里喊著‘駕,駕’‘嗑達,嗑達’”、“騎驢的游戲很簡單。一個人彎腰成九十度,撅著,另一個人從遠處跑過來,雙手按一下他的后背,從他的身體上掠過去。有點像現在體操比賽中的跳馬。”(《螞蟻戲》)字里行間,娓娓道來,讓讀者不由得跟隨著他們一起回憶童年的生活、兒時的玩伴、家鄉的土路、院子里的雞鴨鵝狗、青春的夢想……
2004年,安勇開始進行文學創作,轉眼已近十年。十年,安勇從放棄工作到正式寫作。十年,從開始的激情寫作到現在的沉下心來,感受生活。安勇的小說讓我們看到了寫作的重量與魅力。十年,安勇的創作從青澀走向成熟,奉獻給讀者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作品。十年,安勇具備了在文學的殿堂崛起并通向巔峰的實力。十年,遼寧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對安勇的創作給予充分的肯定。但這又將作為一個新的起點,我們期待安勇的下一個十年,也相信安勇的下一個十年更精彩。
注釋:
[1]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
[2] 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63頁。
[3] 尼采:《悲劇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版,93頁。
[4] 余華:《余華作品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頁。
[5] 余華:《我的寫作經歷》,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49頁。
[6] 才政、張淑麗:《試析東北語言的親和力》,《新聞傳播》2004年第5期,69頁。
[7] 王衛平:《接受美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第46頁。
責任編輯 陳昌平
安勇作品年表
微型小說:
《仇恨》2005年1期《天池小小說》,入選2005年中國小說學會小小說·微型小說排行榜。
《光頭》2006年21期《微型小說選刊》,入選2006年中國小說學會小小說·微型小說排行榜。
《分析題》2007年15期《微型小說選刊》,入選2007年中國小說學會小小說·微型小說排行榜。
微型小說集《一次失敗的劫持》2008年4月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短篇小說:
《螞蟻戲》2004年9月下《小說選刊》“新浪鏈接”欄目,入選漓江出版社《2004中國年度短篇小說》《跳蚤女孩——好看短篇小說精選》。
《煙囪里的兄弟》2004年11月下《小說選刊》“新浪鏈接”欄目。
《老孟和大孟》2004年6期《短篇小說》雜志。
《王小水是最純凈的水》2004年12期《短篇小說》雜志。
《玩一個游戲》2005年1期《青春》,《小說精選》2005年3期轉載。
《美麗的馬糞》2005年12期《青春》。
《老白在世上的最后三天》2005年9期《都市小說》。
《紅墨水》2005年6月下《青年文學》。
《大柳筐》2006年1期《佛山文藝》。
《老劉的廁所》2006年2期《福建文學》。
《較勁》2006年2期《芒種》。
《紙月亮》2006年8期《佛山文藝》。
《證據》2006年5期《雨花》。
《拯救韓雪》2006年6期《星火》。
論古詩地名使用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以唐詩中的“清湘”與“清淮”為中心……………………………………李德輝(128)
《馬勇敢的午后》2006年7期《短篇小說》。
《雪白的饅頭》2007年5期《雨花》。
《蟑螂》2007年8期《當代小說》。
《搶劫犯胡海山》2007年4期《佛山文藝》。
《衣柜里的男人》2007年6期《佛山文藝》。
《咱們的煙囪》《有鳳來儀》2007年2期《芳草》。
《詛咒》2008年2期《文學界》。
《油錘灌頂》2008年5期《青春》。
《地震》2008年6期《佛山文藝》。
《袁有福之死》2008年7期《黃河文學》。
《殊途同歸》2008年11期《啄木鳥》。
《大白菜多少錢一斤?》2008年9月下《山花》。
《請飛兒帶走那條小路》2009年1期《佛山文藝》。
《這孩子》2009年9期《青春》。
《鑰匙》2010年2期《文學界》。
《單房差》2010年2期《佛山文藝》。
《枕頭》2010年4期《青春》。
《勝男的土地》2010年6期《黃河文學》。
《諾潔斑馬線》2011年3期《天涯》。
《軟肋》2011年6期《山花》。
《重返亞特蘭蒂斯》2012年4期《青春》。
《走眼》2012年5期《雨花》。
《青苔》2012年5期《山花》,《小說選刊》2012年6期轉載,入選漓江出版社《2012中國年度短篇小說》獲得遼寧文學獎短篇小說獎。
《做伴兒》2012年5期《黃河文學》,《小說月報》2012年8期轉載,獲得首屆《黃河文學》雙年獎二等獎。
《野貓》2012年8期《文學界》。
《草貍獺》2012年12期《海燕》。
《鐘點房》2013年10期《山花》。《文學教育》2013年11期轉載,配發評論。
《仙人掌》2013年10月《青春》。
《雅格達》2014年1期《福建文學》。
《603寢室失竊事件》2014年2期《文學港》。
中篇小說:
《孽障》2008年8期《芳草小說月刊》。
《永遠的幸福》2009年7期《廈門文學》。
《殺死楊偉大》2010年5期《芳草小說月刊》。
《一九八五:性也》2013年4期《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