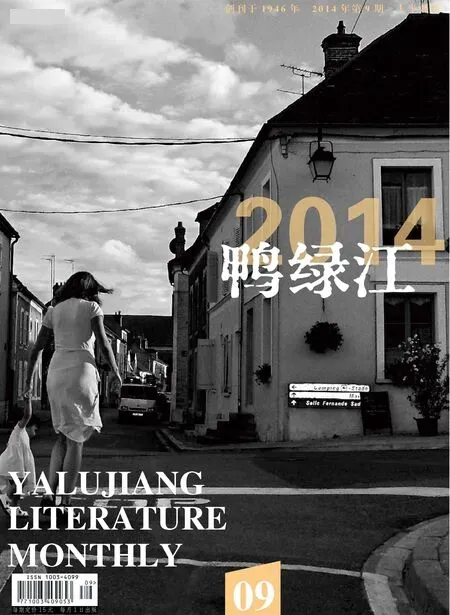主觀書
文盛
散文
主觀書
ZHUGUANSHU
文盛
去寫未知吧
它肯定是存在的,但最后被遺忘了……2002年,當陌生人走近,他們在陽光下跳著肚皮舞,我哪里會想到,又一個本命年也終將如期而至。可是,我曾經把它無限拉伸、縮小,細分為每一年、每一個月、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每一分、每一秒……十二年,我的身體并未蒼老。勞作和苦役,并沒有將未知寫盡,我的同齡人啊,你們已經站立起來,在我的前方,請借我一架高倍望遠鏡,讓我追逐你們的夢境和背影。當然,有人逝去了,我不知道多數人的名姓……相比于你我,他們肯定是存在的……字詞也并非完全虛擬,我一路追蹤,偶爾小憩,路邊野花葳蕤,樹木蒼勁,狼奔豕突。多么龐大而美的人間啊,當我想到有朝一日終將遠離,請賜我那未曾親近的一切陌生,我對地理、海水、愛情、幽暗的角落、敞亮的通途都滿腹鐘情……它肯定是存在的,但最后被遺忘了……在高強度的震蕩和分裂中找到沙礫,在每一個時間的節點上找到永恒和詩意,如果某日,連地球也不在了,請懷念那藍色星空中的流水吧,它們在干枯的夕陽下泛濫著記憶的微光。請注視愛人的面龐和蒼老的山脊,只有在畫幅中才能找到對應物的年代已經迫近,我想在喧囂中隱蔽一個時辰,請許我遠走高飛……去寫未知吧。帶著中年的油彩,少年的爛漫和暮年的容光。去寫那些具體的物,騰空的云霧和外在的矛盾,去寫寫人心的救療,戰爭和破碎,絕望和沉痛中的心儀,去寫寫爬山虎和三國志,去寫寫畢生和一瞬……它肯定是存在的,但最后被遺忘了……這個城市連綿而高聳,如群山中的一脈,去寫寫它最靠近虛無的塔尖,去寫寫爬行的蟻族和他們的苦衷,去寫寫鄰里的咆哮和早晨刺耳的電鉆聲。請你們拿起筆來,簽定最后的合約,請許我暫時告別閱讀和確定的紀年,請在零亂的房間里安裝秘密的監控,請排除詭計和名利之心,請忘記最初的沖動,做一個穩重而踏實的瘋子吧。他每天坐在橋頭,觀察南來北往的人。想想這些年來,那戴面具的日子多么荒謬啊,那狂悖的時間多么荒謬……去寫未知吧。在市場上,隱身衣也出現了,千萬不要故步自封,如果那些被復制的思緒是你的原創,請重視隨時擦拭。做一個絕對的主體,在某一個時期,請忽略建議和悔過書,請鄙視他們的嘲諷。不,不要總是圖謀新奇和好看,請拒絕中庸和別致,請歪曲自己的思想,請拋棄極端,請回歸原點吧。做一個失憶者,對你最熟悉的人保持最大的好奇心,忘掉她的容顏,尾隨她進入那最后的私密的空間……它肯定是存在的,但最后被空洞覆蓋了。請書寫未知吧,請不要起誓和隨意妥協。生真是我們所愿,請讓遐想占滿今后的每一個時空,請直接地談論未知啊,請保持迷茫和最大的本能。
憤怒出詩人
寫作對于抑制憤怒或許是有用的,但遍布于我們生活中的所有得失并不總是存在,它有時成了看不見的物。憤怒對于抑制寫作或許是有用的,有時因為糾結于某一件事,我不得不穿越大半個城市去尋找答案,可是,在幻想中日日路過的街頭,我還是迷路了。經常性地,被過去時日的某個背影所引誘,追隨她的腳步,然后因為言語沖突,而突兀地轉身,自此,我們終于擦肩而過。后來,我體察自己的思想,為解救無法而長期地失眠,在距離她很近的地方,做一個孤單的人而停留于字句。我并非相信寫作更甚于相信知覺,它總是在滑動中流逝,那蒼白的紙面上長滿了蛀蟲和污垢。在搬家的時候,我扔掉了那么一大摞廢紙。它們是我思考無益的見證。更有甚者,我還試圖拉她下水,可是失敗感使我窒息。我從未在周末約她出來。車水馬龍的城市像個迷宮般的咒語,十二年中,我痛失一切所愛。但她說,憤怒僅僅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應該在夢寐中也保持清醒,抓住那唯一的詞,告訴她真理以及尾隨其后的記錄者。可是,夜夜受此折磨,我很快消瘦了。那些年,尚且沒有更好的法子去釋放內心的積弊,直到現在也沒有。可是憤怒,僅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當我對生命保持笑意,我希望它能永恒延續,是啊,距離墓地尚遠,在有生之年,微笑總是迷人的,而贊美更其神秘。我真應該在很早的時候從師,學習他們的偽裝術,做一個左右逢源者多好。可是天性使然,我總是在徘徊中慢慢地落后于人叢,那象征性的幸福也時時送來嘲諷。但是,寫作在可以寫作的時候,總對生活下去是有用的。這么多年,我并非擁有道德的潔癖,它似乎只是少數人的專利,而且在更多的人看來,憤怒既縱容又抑制道德。現在,除了在一天中的固定時刻描畫幾行,剩余的光陰我都是無所事事地度過了,如果憤怒與此有關,我相信這是最大的謊言。但是撒謊有更高的技巧,我不希望片面的理解可以為我的此生命名。我只是一個容易疲憊的人,在蕭索世事中缺乏更多實用的動力。那些蝸居的日子恰好證明了這一定律,相比于理想,我的現實生活真是一團亂麻。但是,我多么憧憬美好和愛啊。是寫作把我的心靈簡化了,當然,盡管我不愿意承認,神經過敏卻是另一個源頭,它豐富、補充、滋長了我的內心。我的周圍同類不多,而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問題,我研究心理學的時候滿懷恐懼。由于憤怒,我的身體肯定被一些不良的寄生物逐步蠶食,我總是能感到內在的物質運行,它們詆毀我不多的理智。可是,我多么善于理解那些不幸的人啊,在無人相助中孤寂地死去,我總是滿腹好奇地想窮盡他們的一生。在所有生者所犯的過錯中,我也一無例外地都擁有過了,像擁有一筆巨大的財富。這多么有趣,似乎我真是個偉大的詩人,而憤怒,是我們共同的淵藪。
彼此

閆文盛,1978年生。B型血,白羊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1996年開始發表詩歌,后轉向散文、小說創作。迄今在《當代》《大家》《天涯》《作家》《散文》《山花》《詩刊》等刊發表作品約二百六十萬字。著有散文集《失蹤者的旅行》(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0年卷)、《你往哪里去》,小說集《在危崖上》,人文專著《天脊上的祖先》等。獲趙樹理文學獎、山西省文藝評論獎一等獎等獎項。他的創作感言是,對我而言,散文就是心靈書。
天底下橫著一個荒村,請相信,這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小小局部。我何曾有勇氣去寫下惡毒的咒,然而這畢竟是惡毒的咒。我相信我現在比以前立場堅定,那廣闊天地的帷幕,曾經是我所有的悲哀和幸運,它偶或抖動,路過我的荒村,那蕭瑟的大木風聲,尚未從我的夢中絕跡。然而,我終將遠離,漸漸分出彼此。那路徑尚在,蕭瑟依舊,可是更改已經發生,可是,再過百年,天底下依然有荒村。那廣闊天幕,飄蕩著沉睡人的靈魂。為什么我總是滿心悵惘,在夕陽的注目中趕路,行色如此匆匆。多少年來,我想象著走出這少年陰影,直至靈與肉重生。父親,請你回去吧,我既已無力逗留,請許我遠走。請容許這彼此間的間距,請許我滿腹惆悵。在你老之將至時,你的力量還大過我些許,你的一生,都比我負重,從肉體的角度,你是頂天立地的巨人。我時時聽到靈魂的噪音。父親,請許我寫詩的權利,我已掌控了這微妙的涂寫術……在世事蹉跎中,我看著你老去,此后便是我的容顏,也被歲月作舊。那些年我已經漸漸淡忘了,他們越來越構不成我此刻生活的重心。在我們彼此之間,一定有一種奇特的力量,使親情本質性的牽連和內在的分崩離析同樣不可阻止。在我們彼此之間,這埋葬前數代人的墳地已經渺無蹤影。我是一個不肖的子孫,父親,請原諒我們彼此的失誤。父親,請原諒祖父,他丟掉了自己的根。我至今尚未回到祖父的生身地。這小小的荒村,是我們祖孫三代人的籠屜,它蒸騰著百年,光陰漫漫,總是在暗夜,自原先的莊稼地里,伸出一只布滿結疤的手,它翻撿我們的骨頭。多少年后,我何曾知道自己棲息何處。這小小的荒村,也變得迷霧重重。在機器的轟鳴聲中,慢慢地滋生時代的病菌,我何曾喜歡它現在的面目。我何曾厭倦荒村。那些早年的沼澤地和魚蝦,那清冽的流水,滋潤我的肺腑,它是我少年時代的神。我何曾厭倦過炎炎夏日,在綠葉枝頭,寄居著一個看不見的荒村。它發出酷似蟬的叫聲,眾蟲仍在,啾啾而鳴。然而我們成為彼此。雨水過后的泥濘延展了道路,我越來越頻繁地出走,直至泥濘不復存在了,我們成為彼此。父親,請你回頭,我何曾不想啊,我們應該居住到一地,朝夕間,我看到你日漸蒼老的雙肩,然而我們成為彼此。在你的注視中,我搭上長途車,這微小的時空,是另外的宇宙。車窗外面,天地仍然灰澀、迷蒙,這父母的城邦,家國啊,荒村,為什么如此灰澀、迷蒙……
暗自飛翔
我們每天都在經歷著死和生。那頑固的宿疾會把你帶入極地。這里沒有陌生人。沒有充足的養分和美景。當你呼吸時所感到的窒息,已經是另一個程序的開始。飛鳥散盡了,它帶走了白云和樹木。每天我都盼望著一場及時的透雨,每天垂暮時,樓下都會響起呼喊聲。我帶著愛和恨下樓,穿過枯萎的草叢,看著西山方向連綿的歲月在慢慢地落入虛無。我不是一個滯留于空洞的幻想家,可是每天都產生積弊,疲憊在勞作后加重,我的羽毛越來越離你遠去。天空啊,離我遠去。我想借重于魯班,學他的神技,每天都可以抖動羽翼,誰知道高處的寒冷,已與昔時不同。請給我取一件保暖衣,請剔除它的重,請告訴生命,飛鳥將盡,天空中鮮有同類。我時常夢到飛行,前此多年,我視此為人生最大的秘密。我時常夢到鳥類,請幫我約會攝影師和鳥類觀察家,我想通過他們的口,與生活溝通。這每一日的孤寂時光,宛如一個象征。我必須使大力,才可以使自己看到輕,截至目前,對于天空,我只有很少的經驗。我不可能成為流云,只有一個垛口,接近它的規則,我請人把它固守。在那高高的極地,只有叢草和浮塵,它們荒萎的面目,是我們的來世或前生。我們每天都經歷著這一片一片的剝落,將身中的污垢去除,請諸神作法,相信神秘和意志力的永恒。那遠年的故事多么讓人崇敬啊,只要乖乖地待在這兒,就會有你所仰慕者,路經你的故地,喊你的乳名。請及時地打開閥門,讓他的船頭抵達你所站立之處。請認準他的面孔,勿用古法,請相信你的辨識力已經足夠。準備行囊,切勿負重。如果可以飛翔,也請勿示于人,那船頭所坐之人,會識破你的伎倆。請保持鎮定和笑容,這里一切的柔暖將與未來混雜,請理智地看待韻律和舊日大風。它們聲如裂帛,已經先自飛行。請勿懷疑萬物,請勿延誤。那溝渠中漂浮著信息瓶,請取來,讀他們的暗語。這是最初的時刻,那救人的人也是生者,他只不過是思想和愛趨同。請暗自飛翔吧,這世上沒有壞人,會目睹你真正受困。請尊重囈語、飄離和無聲的蹉跎。
去寫真實吧
然而真實感并不存在。過去,我經常性地,耽于這樣的冥想。隨著時間流逝,如今的我看起來更為理智些了。我不知道謊言與心虛有無關系,可是只要有慣性的力,就自然會停留于此地、此時。我遍眼皆是暗夜,有時寂靜里有微明,我很少醒來,內心里磅礴的力量阻擋我逸出夢境。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始自何時。已經好幾個月了,我很少在夜里寫詩。假想中的歲月并未發生,天下安然,人仍如螻蟻。那么,還是寫一點真實吧,然而真實感并不存在。我經常把自己駁回。更正的事情經常做。向敵人和親朋致歉,領會他們的傲慢,接受最蠻橫的指責,做一個空心的人,消除苦痛和麻木。去寫寫真實吧,然而真實感并不存在。沒有永久的悲哀,幸福也不是無限的,可是這漫無止境的生活,總是流動得如此之快。很多天,我都沒有空閑去看看人流——我喜歡站在城市的街頭,感覺四季的音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獨自走了很遠的路。冬天了,蕭瑟的北方露出曙光,我迎著朝陽爬一道昔日的陡坡,可是大地已被切割,我站在新翻的泥土前,看遠方的天際線。茫茫旭日東升,我想記錄如此一刻,它使我鄭重、緊張、多疑,我似乎想起了什么,然而或許什么也沒有。茫茫旭日東升,我總是在如此一刻,突出了那種幻象:去寫寫真實吧。然而真實感或者并不存在。我問過一個相愛中的人,然而,愛并不存在。理解了這種真實感的一刻,我備感沮喪地離開了。直到今天,我都無法理解愛,可是,總得去寫寫真實吧。哪怕是最簡短的,它也勝過渺茫。我總是如此渴求而不可得的一刻,長久地籠罩了我以及我所在的生活。如今我也正受著這樣的折磨,可是,除了寫下,我再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了。十年前的午夜零點,我總在“無所事事地忙碌”,那時便植下了這樣的種子,可是我抬起頭,離茫茫旭日還遠著呢。我不知道如何度過了那些年,在黑夜的街頭,我也常常獨自走遠路。那么,去寫寫真實吧,它或許是自傳的一部分,或許便是真實本身……
責任編輯 葉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