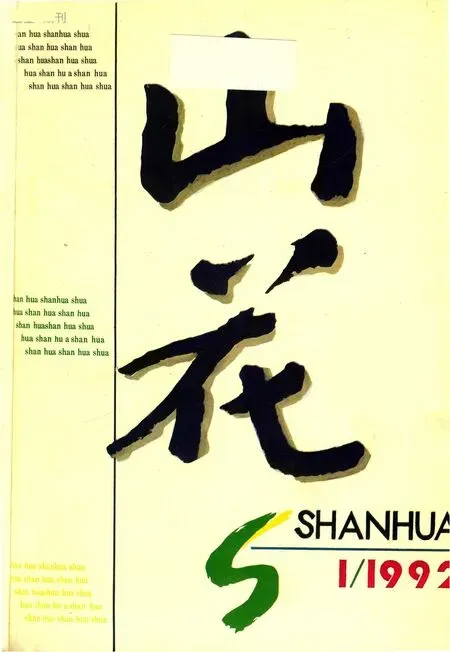論莫言長篇小說《蛙》中的“姑姑”
在長篇小說《蛙》中,莫言塑造了一個經典的小說人物形象“姑姑”,她是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時代的典型代表人物。為了完成黨的工作,“姑姑”既獲得了“活菩薩”的榮譽稱呼,又承受著“活閻王”的恥辱謾罵,“姑姑”的一生因計劃生育政策而充滿了傳奇與悲劇色彩,同時也因為這段不平凡的人生經歷而實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此,本文將深入分析小說《蛙》中的“姑姑”,從“活菩薩”、“活閻王”、悲劇式、自我覺醒者四個方面來探討該小說人物形象。
長篇小說《蛙》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的經典代表作之一,在這部小說中莫言以獨特的人物視角關注了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多年的計劃生育史,其中“姑姑”就是莫言在這部小說中所塑造的核心人物形象。小說中的“姑姑”是一個鄉村醫生,莫言通過敘述“姑姑”極具傳奇色彩且跌宕起伏的人生將我們帶入計劃生育那段特殊的時代環境中,講述特殊革命背景下中國人的命運變遷。小說中“姑姑”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典型代表人物,她的個人榮辱命運始終與黨、革命息息相關,如“活菩薩”是“姑姑”響應國家多生育政策而贏得的榮譽,只因“姑姑”推行的新接生方法為高密東北鄉迎接了一個又一個新生命,于是獲得了群眾的尊敬與愛戴。但是,同樣為了擁護黨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姑姑”又變成了令人唾罵的“活閻王”,死在“姑姑”手中還未出世的嬰兒多達數千。最后,“姑姑”的后半生在懺悔中度過,并最終實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為“姑姑”悲劇性的一生增添了一絲欣慰。
“活菩薩”姑姑
在小說《蛙》的一開始,作者莫言向讀者介紹了“姑姑”的父親的偉大事跡。“姑姑”的父親是一名八路軍醫生,為了革命事業英勇地奉獻了自己的生命,于是“姑姑”自小就以革命烈士遺孤的身份長大成人,“姑姑”的父親對她的人生具有重大影響,這也是“姑姑”選擇從醫的主要原因,“姑姑”希望繼承其父親的職業,為革命、為黨貢獻自己的力量。“姑姑”在十七歲時學成歸來,在高密東北鄉當一名接生員,而在同年期間,當“姑姑”用新的接生方法成功為高密東北鄉接生下一個嬰兒之后,“姑姑”傳奇的一生也由此開始。那時高密東北鄉村莊中大部分的小孩都由“老婆娘”使用古老、不科學的方法接生,因此嬰兒的存活率都不高,當又一個小孩即將命喪“老婆娘”之手時,“姑姑”以她科學的接生方法成功地挽救了處在生死攸關的艾蓮母子。從此,“姑姑”在高密東北鄉更加名聲大振,身兼醫生與革命者身份的“姑姑”為自己的職業感到光榮與自豪。
那段時期對于高密東北鄉來說是迎接新生命到來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姑姑”享譽盛名的時代。新中國成立不久,依據國情需要我國積極鼓勵百姓多生多養,這一時期“姑姑”利用她學習的新接生法為村民婦女們忙前忙后的接生孩子。對于高密東北鄉的村民來說,“姑姑”簡直是“活菩薩”與“送子觀音”的象征,“姑姑”高明的醫術仿佛擁有神奇力量一般,大大提高了村莊嬰兒的存活率,經“姑姑”接生的孩子都能順順利利地出生。作為一名革命醫生,在“姑姑”面前任何一個孩子都是平等的,沒有階級身份的界定,當孩子的生命面臨威脅時她都會竭盡全力挽救這個生命,就如陳鼻,他是“姑姑”接生的第一個孩子,盡管他是一個地主的后代,但生命的價值超越了階級斗爭,“姑姑”還是及時地將他從產道中拖出來,拯救了他的生命。于是,這又增添了“姑姑”在高密東北鄉的神圣性,成為村民們極力擁護、尊敬與愛戴的對象。
事實上,高密東北鄉的村民們對“姑姑”的擁戴,從另一方面也是對革命、對黨的擁戴。因為,“姑姑”是黨與革命絕對的擁護者,不僅是由于“姑姑”自小就出生在一個革命抗日的家庭中,革命烈士遺屬的身份加深了“姑姑”對黨與革命的堅守,而且作為一個革命醫生“姑姑”自小就樹立了一種認同感與優越感。因此,長期深受革命話語熏陶的“姑姑”其言行舉止具有鮮明的革命特色,“姑姑”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革命話語的代言人”,傳遞著強烈、崇高的革命力量。同時,“姑姑”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影響著高密東北鄉村民的思想,那就是對黨、對革命的極大擁護,黨與國家的形象因為“姑姑”對高密東北鄉的奉獻而變得具體、高大起來。
“活閻王”姑姑
然而,當我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時,“姑姑”在高密東北鄉村民心中的形象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受人尊重與愛戴的“活菩薩”形象轉變成受人指責與謾罵的“活閻王”形象。隨著我國人口數量的急劇增長,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姑姑”作為一個黨的忠誠擁護者,她十分認同黨的這一決策,并且以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執行著這一政策。在小說中,“姑姑”操著一腔革命話語嚴肅勸說著想要多生育的村民,要有高度的思想覺悟,堅決擁護黨的決策,配合黨關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號召。同時,她還積極為政府工作人員做思想動員工作,書記要起帶頭作用,號召全黨人員帶動民眾一起落實“一對夫妻一個孩”的鐵打政策,嚴重控制中國的人口增長,努力做好這件頭等大事。
“姑姑”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中一直堅守著“決不讓一個漏網”的原則,嚴格堅守著黨的號召不放過任何一個超生的孩子,關鍵時刻甚至可以做出大義滅親的舉動。如“姑姑”勸說她的黨員侄媳婦小跑說,作為共產黨員的家屬,她應當起帶頭模范作用,于是已經懷孕五個月的小跑被強迫拉上了引流手術臺,結果造成了一尸兩命的悲劇。在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高峰時期,“姑姑”是其中最為活躍的一個,她冷血得讓孕婦流產、讓男人結扎。在面對頑固的村民時,“姑姑”使用扒房揭瓦、連環保甲的野蠻手段來逼迫;還有一個懷孕五個月的孕婦為了躲避“姑姑”的追捕而無奈選擇跳河逃生,結果因體力不支而斃命。諸如此類荒誕、野蠻的計劃生育執行手段還有許多,那時的“姑姑”早已忘卻了她作為醫生應拯救生命的職責,缺失了對生命的憐憫,活脫脫成為一個人見人怕的惡魔,被村民們扣上了“活閻王”的高帽。
此時,“姑姑”的人物形象已經扭曲,她完全被政治化、工具化,成為了一個缺失個人自主意識與人性溫情的執行工具。對此,莫言在“姑姑”外形描述中流露出戲謔的表達,終日忙于計劃生育執行的“姑姑”在外形上開始變得丑陋,潔白的牙齒因無暇刷洗而發黃,身體也開始發胖,她的外形逐漸向“活閻王”的形象靠攏。莫言巧妙地利用牙齒作為寓意對象,發黃的牙齒代表著“姑姑”對黨與革命的迂腐忠誠,她的這種忠誠與擁護是用無數嬰兒生命換來的。然而,身為黨與革命的忠誠擁護者,“姑姑”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絲毫不對,反而因自己成為一個堅定的“無我”革命執行者而光榮。因此,對于“活閻王”的稱號“姑姑”認為這是對她嚴格工作態度的證明,“姑姑”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為了堅決執行黨的計劃生育政策,“姑姑”甘愿做一個令村民們厭惡的“活閻王”。
悲劇式的“姑姑”
事實上,“姑姑”是《蛙》這部小說中一個典型的悲劇式人物,她的一生都在為黨和革命作貢獻,甚至因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成為高密東北鄉中的惡人、“活閻王”,被村民們孤立與誤解。這在小說中母親與“姑姑”的一段對話中有具體的表現,母親懷疑計劃生育的事情是“姑姑”自己琢磨出來的,并不是黨下達的政策,當“姑姑”聽到這話時立刻暴跳如雷,十分憤怒地反駁母親,這是黨的號召、國家頒布的基本國策,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指導,因而不理會母親對她的勸導。強烈的政治使命感讓“姑姑”做出了許多瘋狂而殘忍的行為,對待頑固反抗的村民采用一系列野蠻的手段進行壓制,不給村民們任何逃脫的活路,因此嚴格執行政策的“姑姑”便成為了整個村莊的可怕敵人,成為一個愚忠的執行工具。
在“姑姑”看來,毫不動搖執行黨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正確的、合法的,因此她無論采用怎樣殘酷、野蠻的行為都要堅決執行這一政策,從而間接導致了一個又一個悲劇發生。但那時的“姑姑”并沒有對這一政策進行自主思考,也沒有對自己的荒誕舉動進行審視與反思,只知道一味地做個國策的忠誠執行者,于是她在執行計劃生育的過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近乎瘋狂的舉動。于是,在“姑姑”的手中一個個生命被活活扼殺,不僅是胎兒的還有許多婦女的生命都在“姑姑”的手中結束。因此,到了晚年“姑姑”終日被痛苦折磨著,她夢到以往那些被她戕害的小生命變成了一只只青蛙,在她的夢中發出震耳欲聾的蛙叫聲,好似向她索命,于是現實生活中“姑姑”因為這個“蛙夢”而開始懼怕青蛙。實際上,“姑姑”害怕的并不是青蛙,而是害怕那些被她殘害的孩子,因而她的靈魂才會感到如此不安。
為了黨的事業,“姑姑”奉獻了自己半輩子的時光,但最終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不僅終日被噩夢纏身,沉淪在悔恨的旋渦中,而且她也失去了個人幸福婚姻的生活。正當“姑姑”終日因痛苦備受煎熬的時候,“姑姑”結識了村里的一位泥塑藝人郝大手,這個郝大手雖然性情古怪,但他捏泥人的技藝非常高超,泥人在他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的靈性。“姑姑”的痛苦與人性的回歸在郝大手這里得到了撫慰與接受,于是“姑姑”選擇嫁給了這個能夠給予她靈魂安寧的人。“姑姑”讓郝大手捏了上千個泥娃娃,這些泥娃娃象征著那些死于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姑姑”每天虔誠地供奉這些泥娃娃,希望那些被她戕害的孩子能夠在下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在小說的最后,“姑姑”流露出了自己對以往行為的悔恨,“太聽話、太革命、太忠心、太認真”是“姑姑”對自己前半生的反省,也正是這四點造成了“姑姑”后半生的悲劇性,最終她承受著地獄般的良心折磨。
自我覺醒的姑姑
小說《蛙》中,“姑姑”的一生經歷了許多大起大落,傳奇性的人生經歷也讓“姑姑”最終實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是莫言在小說中賦予“姑姑”這個小說人物的點睛之處。當然,“姑姑”的自省意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曲折的人生經歷才促成了她的自我覺醒,于是莫言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埋下了伏筆,以此來凸顯“姑姑”在最后的自我覺醒。一開始,莫言讓“姑姑”擁有著令人羨慕與崇拜的革命烈士遺孤身份,這一璀璨的出身讓“姑姑”自小就對黨與革命有著天性的認同感與優越感,小說在此也暗示了“姑姑”注定將成為高密東北鄉中一個響當當的重要人物,既享受著黨與革命賦予她的榮譽,成為受村民仰慕的“活菩薩”,同時又承受著黨與革命帶給她的辱,嚴酷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者身份讓她成為了高密東北鄉里的“活閻王”。這種身份的轉變不僅是命運對“姑姑”的考驗,同時也是幫助“姑姑”實現自我意識覺醒的寶貴財富。
通過研讀《蛙》這部小說,我們可以發現莫言在塑造“姑姑”這一小說人物的創作特征。為了凸顯“姑姑”在我國計劃生育時代以及高密東北鄉中的典型性與特殊性,莫言一開始將“姑姑”塑造成一個完美、高大的形象。但隨著小說劇情的不斷深入,“姑姑”的形象開始扭曲,“姑姑”的人生命運也開始走下坡路,通過無常的命運變化來預示“姑姑”悲劇性的人生,從而達到真實與深刻的敘事效果。事實上,“姑姑”人生命運的轉變是從其空軍飛行員男友的叛變開始,曾經“姑姑”與飛行員戀愛的事情讓村莊姑娘羨慕無比,但是其男友為了追逐政權與經濟拋棄了“姑姑”,選擇跟隨國民黨并潛逃到臺灣。后來,在“文革”期間“姑姑”因為這件事成為重點的批判對象,忍受著巨大的肉體痛苦與精神壓力。但這樣的人生經歷并沒有打倒意志堅強的“姑姑”,反而讓“姑姑”堅定了對共產黨、對革命的忠誠擁護信念,可以說這是“姑姑”第一次完成了自我意識的覺醒。
而“姑姑”第二次自我意識的覺醒則是在晚年時期,計劃生育工作讓“姑姑”成為了一個奪人性命的惡魔,無數無辜的小生命在“姑姑”的手中泯滅。盡管“姑姑”也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受害者與犧牲者,但是“姑姑”卻親手將這種生命之痛、人性之痛帶給高密東北鄉的村民們,于是晚年時期“姑姑”雖然生活在安逸、祥和的社會環境中,但她的靈魂卻始終備受煎熬。“姑姑”成為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罪魁禍首,晚年的“姑姑”也通過實際行動表現她的懺悔與反省,以此希望自己能夠獲得靈魂的解脫。而正是“姑姑”的這份懺悔與反省,“姑姑”實現了自我意識的第二次覺醒,同時,“姑姑”也以她的人生命運讓后代的我們關注這段歷史,并從中反思歷史。
總 結
“姑姑”是莫言在《蛙》中的經典人物形象,莫言在她身上蘊含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包括對生命、對歷史的思考。“活菩薩”與“活閻王”的身份界定不僅是高密東北鄉村民們對“姑姑”人生的評價,同時也是經歷了這段苦難時代的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評價,在小說中“姑姑”成為這段歷史中苦難與罪惡的承擔者,承受著生命對她的責難。雖然“姑姑”的人生因為堅定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充滿了悲劇色彩,但“姑姑”對黨、對革命的堅守與擁護并沒有動搖,反而在救贖中實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透過“姑姑”那傳奇與悲劇性的人生,莫言讓更多的人正視這段歷史,讓更多人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從而幫助迷茫于這個物欲橫流社會中的人們實現對生命存在狀態的追思。
[1]陳威.延續與突破——對莫言小說《蛙》的解讀[J].群文天地,2011,(23).
[2]晏羽.因沖突而存在,因存在而真實——試析莫言《蛙》在沖突中的反思[J].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2):80-82.
[3]李曉亮.遠未終了的悲劇——論莫言《蛙》[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1,30(4):56-58.
[4]胡海梅.關于民間敘事困境的思考——以莫言小說《蛙》為例[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2):92-9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