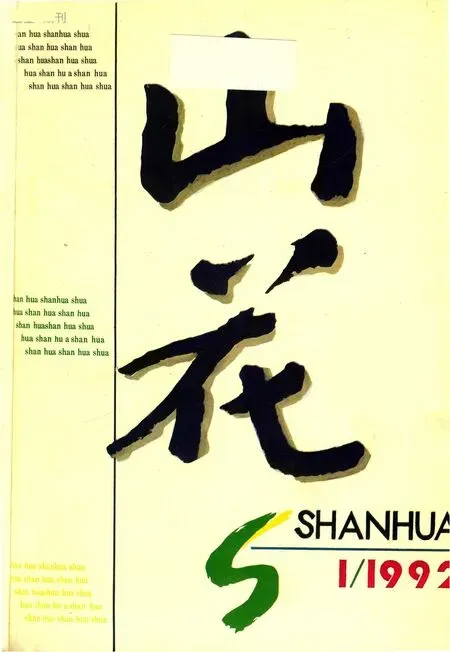詩意生活的可能性,及不可能性
李云雷


文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一位以“創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畢業論文便是她早期小說的代表作《第八日》。以我對文珍的理解,她的性格中充滿了不安定的因素,也充滿了幻想的色彩,以及對遠方的憧憬。但在現實生活中,她并不是一個適應社會的人,她對小動物充滿愛心,也長于廚藝,但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卻常常是羞澀、內斂甚或是緊張的。在生活以及她的小說世界中,她常常是游離于現實之外,而更耽于個人小世界的,或許在她的內心與社會生活之間,有一種緊張,也有一段距離,她在個人小世界之中尋找一種詩意棲居的方式,同時也在隔著那段距離,以審美的眼光打量周圍的世界,我想這是文珍的人生態度,這也決定了她小說中的敘述姿態。
文珍的小說都在探討一種“詩意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面對一個復雜的時代與世界,一個內心豐富微妙的青年(尤其是女性),能否尋找到一種詩意的生活?或者說可以找到一種什么樣的詩意生活?文珍的小說中那些內心惶惑、焦灼的主人公,都在這個意義上探尋著自己的出路,在他們與世界的關系中,他們并不試圖融入或介入具體現實的糾葛,而寧愿超越其上,帶著現實所給予他們的傷痕與惆悵,回到高于現實世界的“小世界”,以審美性的眼光返觀這個世界。文珍的小說大多描述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細膩,豐富,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復雜多變的世界,這個世界既是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關系,也是個人幽暗而深邃的內心世界,她的小說在內外之間互相交織,為我們打開了一條通向內心與世界的道路,我們從中看到的不僅是主人公糾纏的關系與糾結的內心,也可以從中看到這個時代城市生活的流動性、偶然性,以及置身其中的“個人”的孤單、寂寞以及交流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文珍的小說是現代城市生活的產物,這樣的生活方式將每個人孤立為“原子”,不僅缺乏公共生活以及參與的熱情,也缺乏與他人交流的經驗與習慣,每個人都被封閉為“自身”,但是另一方面,渴望交流的愿望卻埋在心底,只能在適當的時候以“愛情”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樣的情形下,“愛情”所承擔的便超越了男女之間的情感,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對小說中的主人公來說,這是他們與世界交往的一個途徑,相戀或者分手,便是與一個世界的交流或者交錯。
在文珍早期的小說中,所抒寫的大多是單身青年的孤寂與交流的渴望,在《果子醬》、《色拉醬》、《關于日記的簡短故事》之中,我們看到的主人公都處在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他們沉浸在幻想與回憶中,與自己喃喃自語,敏感地注視著身邊發生的事情,但又置身事外,他們處于這個世界之中,但又仿佛置身于這個世界之外,他們有著一個孤單、敏感而又豐富的內心世界,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憂郁與詩意,這些小說的故事大多糾纏于內心,但是在敘述上顯示了文珍的特色,那就是在故事之外,她的小說可以給人以一種獨特的美感,一種詩意的哀愁繚繞其中,在她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詩的特質。
在《北京愛情故事》、《中關村》、《氣味之城》、《我們夜里在美術館談戀愛》、《畫圖記;或動物園的故事。》等小說中,文珍所處理的是較為復雜的題材,如果說以前的小說是“單純的詩”,那么這些作品可以說是“復雜的詩”,它們并不只是抒情,而是直面當代都市青年的復雜情感狀態,在這些故事中發現“詩意”,在這些主人公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中,文珍把握住了其中曖昧難言的部分,以細膩的筆觸將之呈現了出來,讓我們看到了生活的真實,以及蘊含在這些真實之中的詩意,只是這種“詩意”不是單純的美感,而是一種五味雜陳的復雜感受,是現代城市生活的“詩意”。
《第八日》是文珍頗為成熟的一篇小說,在小說中,她描述了白領女青年顧采采的生活,讓我們看到了在她平靜外表下所隱藏的孤寂與焦灼,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她無法找到心靈寄托與情感慰藉,只能沉浸在幻想中自我安慰,只能在難以忍受的失眠中煎熬,小說寫出了當代城市青年的生活狀態,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自身的影子。在這篇小說中,文珍以自己的筆觸去貼近主人公的心靈,顯示出了她關注與理解他人的努力,這是她通向外部世界的一個窗口。《第八日》的姊妹篇《錄音筆記》,講述的是一個都市中孤獨的女孩曾小月的故事,她是一家禮品公司的接線員,除了一副好嗓子,她別無長處,既少有男性青睞,在公司的地位也很邊緣。對于聲音的敏感,讓她總能聽到同事之間勾心對角的對話,也時常淹沒在電話鈴聲和顧客的扯皮中。偶然之間,她發明了一個自己玩的小游戲——用錄音筆將自己的聲音錄下來,再放給自己聽,這讓她與周圍嘈雜的聲音隔離開來,沉浸于自我的世界中。在她與自己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了她在這個城市卑微的處境,錯過的愛情,疏遠的友人,以及無聊的工作,構成了她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中她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安慰,只能自己與自己交流。在這篇小說中,文珍寫出了當代都市白領的生活與內心困境,讓我們看到了她們孤獨、壓抑乃至于自閉的心靈。在寫法上,《錄音筆記》的敘述既緊貼著小說的主人公,而又隔著一段距離,仿佛在稍高處觀察著曾小月的生活,這有限的距離使讀者可以接近曾小月的世界,又使小說繚繞著一種詩意,這是一種喃喃自語的詩意,也是一個孤獨靈魂的詩意,在這個龐大的城市中她無處訴說,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安慰自己。文珍的小說擅長描述喧囂都市中的孤獨者,這兩篇小說細膩真切,以絮語式的筆調呈現出了小說主人公的生命困境,小說在寫實中飽含著豐富的寓言性:在當代都市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她們的困境,又何嘗不是我們的處境?
在《安翔路情事》中,文珍關注的是兩個底層青年男女的愛情,他們在城市里生活但又不屬于城市,他們生活卑微,但是他們也有愛情,小說寫出了他們愛情的曲折與艱難,他們無法掙脫城市生活喚起的渴望,但又難以融入城市,他們之間也為此互相糾結著,愛是不可能的,不愛也是不可能的,到最后,他們只能隔著一條街遙遙相望……,在這篇小說中,文珍寫作的范圍進一步拓展,她關注的是另外的人與另外的世界,這也顯示了她不斷突破自我的努力,預示著她更為寬廣的寫作道路。
我們可以看到,文珍在她的寫作中經歷了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從關注自我到關注他人,從“單純的詩”到“復雜的詩”,文珍在她的寫作中探索著,仿佛一個少女逐漸睜開了眼睛,以她的眼光在打量這個世界。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文珍的小說中仍存在著不變的因素,那就是對詩意生活的探尋,在《第八日》、《錄音筆記》中,我們可以讀到都市白領女青年孤寂靈魂的詩意,而在《安翔路情事》中,我們在底層生活的艱辛生活中也可以發現詩意。這樣的詩意超越現實生活之上,但又與現實生活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是由生活中生發出來的情緒、情感以及將之對象化的一種美學把握,文珍就是帶著這樣“詩意”的眼光在觀察這個世界,或者說在她的內心深處隱藏著對這個世界難以言說的情愫,這是她小說的底色,這也讓她的小說更接近詩歌或音樂,更接近純粹的藝術。
在《衣柜里來的人》和《我們究竟誰對不起誰》這兩篇新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文珍小說中的“變”與“不變”。《衣柜里來的人》更接近文珍早期小說的特色,小說的主人公都市女青年小枚在北京有一個相戀的男友C,但在結婚前夕,她出于對未來的恐懼逃離北京,獨自重游西藏,和在拉薩的“拉漂”阿七、達叔、二彬子、小丸子、葉恬、劉單等在一起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但她心中仍存在著巨大的情感困惑,她是否應該將自己的命運與C聯系在一起,而拉薩的朋友對她與阿七的誤解則讓她處于尷尬、曖昧的情感邊緣。小說中她與阿七騎自行車去納木錯湖的一段頗富美感,也讓她逐漸清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會忘記的。總有一天,所有愛過的,不愛的,都會忘記。就像這沙粒。他握起一把,然后看著沙粒從指縫簌簌下落。小枚,即使這一分鐘我喜歡你喜歡得要死,可是如果你不和我在一起了,我又繼續活下去了,我也仍然會忘記你的,小枚。就好像你男朋友一樣。就好象我以前的女朋友一樣。我相信他非常非常地愛你,可是你要是真的呆在拉薩好幾年都不回來,他一定會忘記你,盡量抹去關于你的痕跡,重新去過自己的生活的。這就是最讓人絕望的一點:愛情他媽的真是太不可靠了。可連愛情都不可靠,到底什么可靠呢?人活著又到底為了什么呢?就是為了讓一個人慢慢忘記另一個人在他生命里留下的痕跡嗎?”——小說中的逃離在此一刻達到高潮,充滿了對愛情與人生的省思、無奈與感慨,而小說的結尾,小枚穿透人情之網,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她的逃離以回歸而終結。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小枚所逃離的不僅是情感,而且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都市中那種庸常而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婚姻生活),她所向往的是拉薩及“拉漂”所象征的動蕩不羈的生活,但當她真正抵達時,卻發現這也并非她所真正尋求的,而她真正向往的或許只是“在路上”,只是“生活在別處”,只是一種詩意飛翔的空間,這是她抵抗日常生活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中所描述的情感困惑其實更具深意,它讓我們看到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異化”,而逃離則是抵抗這種異化的一種方式。而小說的結尾也讓我們深思:當逃離終將歸來的時刻,我們是否還有可能抵抗異化,是否還有可能重建一種詩意的生活方式?
《我們究竟誰對不起誰》寫的是四個都市白領女青年的情感故事,“我們一定要幸福”既是一個奮斗目標,也是一種自我安慰或自我暗示,小說中的小顧是她們這個“腐女四人組”中最早結婚的,在一次聚會之后她竟然割腕自殺了,這揭開了她幸福生活的假面,也刺傷了三位姐妹的心,小說中的“我”、小朵和張帆探尋小顧自殺的原因,也在這一陰影下追尋著各自的幸福。在這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與文珍以往小說中的不同因素,小說關注的重點不是情感問題,而是婚姻問題,“我們一定要幸福”的前提便是婚姻,但同時婚姻也并非簡單日常生活的延續,而呈現出了諸多罅隙與謎團,在寫法上,小說不再以某一人為主人公,而以四位姐妹為主人公,打破了以往封閉的個人世界,同時在寫作上也并不強調詩意,而更加自然,更加貼近生活,或許這意味著文珍寫作上的新變化。
文珍很少被納入80后作家中討論,但她的寫作也呈現出了這一代作家的特性,那就是以唯美的語言講述青年男女的故事,但文珍與其他80后作家不同的是,她在作品中始終營造著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她的藝術世界并不是華麗而空洞的,而是來自于現實生活及她個人的生命體驗,正是將這種生命體驗對象化使她的作品充滿了血肉與疼痛感,在她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她的內在自我和她獨特的氣息,也可以看到她對時代脈動的觀察與思考,她對“詩意生活”的探尋則顯示了她對庸常乏味的日常生活的抵抗,而永遠保持著一顆自由不羈的心靈。
在文學史的脈絡上,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觀察文珍的創作,一個是從《紅樓夢》到張愛玲的敘述傳統,在小說的語言、色澤與敘述姿態上,文珍從這一脈文學傳統中汲取了不少營養,她對漢語的細膩把握及詩意氛圍的營造,都可以說得其真髓,但另一方面,相對于《紅樓夢》或張愛玲來說,文珍卻少了“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一面,她更關注孤獨個體的生活與精神苦悶,或許這是文珍在美學趣味上的選擇,但也有可能是她涉世未深,尚未真正“世事洞明”之故。另一條脈絡則是五四以來“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寫作傳統,在文珍小說主人公的身上,我們可以辨識出莎菲女士、林道靜等人的身影,她們內心豐富、眼界甚高,對世界滿懷幻想,但在現實中又處于苦悶的狀態,她們在歷史風云中追逐著自己的夢想,尋找著自己屬意的詩意生活。但在文珍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主人公同樣苦悶,同樣在追尋著詩意的生活方式,但她們的小世界已經不再與“大歷史”聯系在一起了,她們每個人都限于苦悶的孤島上,難以與他人溝通,也難于融入社會中成為其中有機的一分子,或許文珍寫出了我們這個時代“小資產階級女性”的處境。這也讓文珍的小說更接近村上春樹筆下的世界,那種不知從何而來的憂郁與絕望籠罩一切,在這里,最想訴說的卻被層層隱藏起來,主人公陷在時空的絕境中最終難以突圍,或許這是后現代社會普遍彌漫的情緒,是混雜著憂郁、苦悶、焦慮、絕望的一種詩意。或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意。在我們這個時代,詩意的生活是否可能?或者,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生發出怎樣的詩意?在文珍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詩意生活的可能性及不可能性,正是在不可能性中追求可能的詩意,讓文珍的小說別具一格,她的小說也為我們形塑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意”,這是一種復雜的“詩意”,一種百感交集、無可言說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