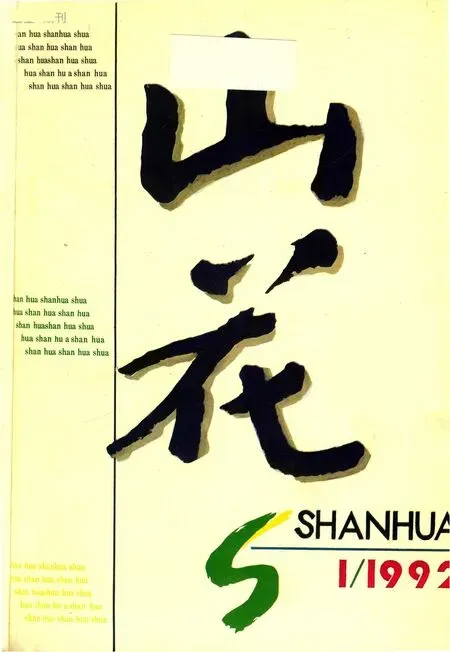水下
走走

離開貢院西街后,她坐上了一輛出租車。早上去的時候,她坐的是公共汽車,那會兒她心里想著,那份半個世紀前的愛該有多浪漫。她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這種東西了。要是她知道,這次出行將改變她的整個生活,她也許會立即跳下車的。
可那時,她根本就沒想到該回家,她凝視著那些搖搖晃晃掠過的店鋪,想著自己身上那種相信真愛的純真也許將再次萌生,臉上就隱隱約約有了笑意。
現在,她只想快點到家,把窗簾都拉上,睡一覺。但那張臉,毫無笑意的臉,總是出現在她眼前,揮之不去。
她一進家門,就在傍晚的暗淡光線下看見了那幅全家福巨像。客廳中的兩扇門打開,就是全家福。照片上那個唯一的男孩,此刻正在寬敞的屋子里來回踱步。他穿了件舊毛衣,腳踩在拖鞋里,手指間夾著根快燒完了的香煙。他一見到她,就像是見到面熟陌生的朋友似的,向前走了一步,卻又遲遲疑疑地站住不動了。
在從窗戶映進來的余暉下,他不斷打量著她,她卻看著巨像上那張毫無笑意的臉。
“那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他退到椅子邊坐下,“所有老朋友都離開你,連見面能說個‘你好的朋友都找不著。你可能要去最偏遠、最貧窮、最落后的小地方。那時候,你心里慢慢開始有了點怨氣,很快你就知道,那是唯一的辦法,根本就不允許有其他的辦法,你知道你內心的黑暗開始造反了。你只是想抓住屬于你的生活。真的,很多妻子帶著孩子離開,所有人相互出賣,都只是為了這個。”
“那真的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他繼續說下去,“混蛋們得勢,而我們失寵。一切都從你手上奪走,你一下子掉進最黏最稠的那個泥潭。在那兒你是沒法抗爭的,你越用力,就會在那泥潭里陷得越深。”
但她記得的,只是他在八十年代寫過的那些回憶性散文,那些文章讓他們全家重新名聲大振。他出版第一本散文專輯時她才二十三歲,正是黃金年代。雖然從全家福上,那個戴著眼鏡的中年男人身上,她一點也沒感覺到天生的著名作家氣質,但她想,她一定會在眾人之中脫穎而出的。她和他的血液里,都有來自一個著名作家的天分和勤奮啊。每次演出著名作家寫的那些話劇時,她都是坐在第一排的觀眾。每次演出結束時,聽著人們熱烈的鼓掌聲,她就會驕傲地抬起頭,含著熱淚望向舞臺,那在黑暗中緩緩合攏的幕布。
三十多年來,他頻頻出現在電視或報紙上,最近則是網絡上,回憶那位著名作家。他回憶他們曾經一起度過的幸福生活,他公布了很多照片,他努力寫文章,調入作家協會,他談論自己的日常生活,對各種話題提出觀點,想證明自己配得上做那個著名作家唯一的兒子。拍照時他拿著作家的文集某卷本,擺出各種姿勢。他參加各種展覽的開幕式,不太重要的文藝會議。只要有記者提問,他都愿意侃侃而談,就作家的教育觀、閱讀觀、寫作觀、愛國主義觀等問題發表見解。
“就算那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你也很快走出來了。”她低聲咕噥了一句。
“那年你才三歲,我先是被停了職,整天無所事事地在單位里坐著,后來開始寫檢討,寫到麻木,寫得胳膊和手,連動一動的念頭都沒有。每天早上起來,一點都不想把自己好好收拾干凈。從上到下,一粒粒扣上那些扣子時,要用上全身的力氣。大部分時候,我一天都不說一句話。”
“今天是他的檔案向社會開放的第一天。我告訴過你我要去看看,你為什么不阻止我?在那里,看到那些材料,我驚呆了。我經歷過的那些失敗、背叛,在他的遭遇面前,顯得多么不值一提。”
他低下頭,不再看她。過了很久,他站起來,從桌上拿起煙,披上他掛在椅背上的夾克衫,“我們去那里轉轉吧。”
他們坐上出租車。車開了很久,才開到一個廠區前。她看著他靠近門衛,給門衛遞了支煙,低聲說了幾句后轉身向她招手。
廠區的南側是地鐵車輛段,北側是剛剛修復的轉河。空蕩蕩的廠區里,似乎只有他倆在走動。
“這里從前是片湖水,再往前,是一眼望不到頭的蘆葦蕩。據說這片水域源自元朝,是什剎海在城墻外的一部分。五八年春天對這片蘆葦蕩進行改造時,我還在列寧格勒讀書呢。唯一見過這片湖水的那一次,就是那年夏天的那個早上。要是沒發生那事兒,這湖水,還真是美麗。”
“美麗的東西,不是應該帶給人一種生活的樂趣、愛的愿望嗎?”
他沒有接她的話,他只是說,“你閉上眼睛,想象一下。”
她真的閉上了眼,于是,呈∞字形的湖水在她眼前蕩漾了起來。湖的東邊是苗圃、花壇、游人長椅、碼頭。湖的西邊是荷塘、稻田、灌木林。湖上架著一座三十米長的木拱橋。湖心是一座孤島,島上種著柳樹。
“那年初夏,湖里先是出現了許多大紅、墨黑的金魚,然后是字畫、瓷器、三槍牌自行車,再往后,就漂上來了一些死人。又過了兩年,為了修建戰備工程,這湖成了渣土填埋場。一車車土石滾進湖里,水泥構件朝天空豎著。再后來,湖被徹底填平,建成了地鐵修理總廠。”
她睜開眼。遠處,地鐵車輛正從黑暗的地下駛出地面。
“他穿得干干凈凈,獨自來到這里。這里是他覺得,這個城市最美的地方。他在湖邊坐了整整一天,在樹下,聽著鳥雀鳴叫,幾乎沒動過。看到天開始擦黑,他會不會有些傷感?黃昏,總是會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憂傷。最后,夜深了,除了黑鴉鴉的柳樹外,什么都看不清了,湖邊什么人都沒有了,他步入湖水自盡。作為一個著名作家,他死得體體面面,卻沒給你們留下任何字,你覺得是為什么?”
他搖搖頭,抽出一支煙來點上,“我知道今天你看到的那些材料讓你很悲傷,我那時候還年輕,我相信那樣做,是為了未來,要是我知道……從那時開始,我的整個世界就塌了。”
“我是坐在一個角落里翻閱那些東西的,我好像本能地就看到了那些。”她沒法告訴他,那些秀麗的書法字,對她有多大的觸動。她也說不清楚,她一共讀到過多少遍,那個簽名。
“那份材料,一筆一劃,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拿起筆來,就像個第一次做作業的小學生似的。我是在單位里寫的,還沒寫完的時候,我感覺有人坐到了我面前,我抬起頭,愣住了。他平靜地看著我,臉上沒有流露出任何痛苦。那一瞬間,我的內心充滿了犯罪感。‘爸爸,我輕輕喊道,‘我這就撕掉。但他突然在我眼前消失了,我不安地轉頭,門好好鎖著,屋子里空無一人。過了很久,我才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上交了那份和他劃清界限的材料以后,我雙手捂住臉,哭了一會兒。但我是如此害怕,既沒有哭出聲來,也沒有流下眼淚。”
他說完,看到她沉默不語,就盯著她的眼睛說道,“如果當年的那一切在今天重現,我真的希望,你也像我那么做。”
“爸爸,”她側了側身子,他的目光讓她很不舒服,“我看到的,不是你說的那些。”
兩人之間靜了許久,就在這段沉寂里,她想到了那張沉靜安詳的臉,“和我說說奶奶和爺爺的故事吧,”見他一臉的詫異,她解釋道,“我記得小時候,奶奶總是會長時間地看著爺爺的照片發呆。他們相愛嗎?”最后那五個字,她像是在說悄悄話似的,把聲音壓得低低的。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很好的母親。一次我生病,她一邊看著我掉淚,一邊撫摸著我的頭發。她愛父親,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不長,但是,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很幸福。”說到這兒,他頓了頓,帶著種安慰她的語氣補充道,“她應該愛他的,他是個很有魅力的人。他愛花,在你小時候住過的小院里種過一百多種花花草草,他走后,她一直把它們照顧得很好。她以前和我說過,她最喜歡那座小院了,對她來說,他在院子里澆花,小院的煙囪里往外冒著煙,那就是幸福。”
她聽著,一些已經遺忘的圖景浮現在腦海里。一個夏天的早晨,父親似乎打算和奶奶一起出門去一個什么地方,最終父親一個人走了,她還在他的身后跟了幾步路。她長大了一點,一次一連吃了好幾個柿子,之后肚子疼了好幾天,因為她不知道不該喝涼白開。那座小院里有兩棵柿子樹,每年秋天,樹上墜滿沉甸甸的柿子,發出橙色的光,很是溫馨。她的眼前滿是那橙色的光,她甚至感受到了它散發出來的溫暖,但光越來越強烈了,讓她焦躁不安起來。這和她眼下面臨的另一種痛苦的煎熬很相似。她想起來,從她確定戀愛關系的那一天起,她就很害怕這段感情,就是因為害怕失去時的這種痛苦。她已經害怕了二十年。今年,他們的兒子考上了大學,兒子離家后,一天早晨,丈夫提出了離婚。
那時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她進了臥室,先是躺到了床上,不過很快她又爬了起來,因為聽到了丈夫鎖門的聲音。她起床的速度太快,導致了體位性低血壓,眼前一片漆黑。她跌坐回床上等了一會兒,感覺到血液重新正常流動了,才走到窗邊,開始向下張望起來。一輛黑色的奧迪A6駛來,停下,她看見丈夫上了車,車子并沒有馬上發動,也許丈夫也在隔著玻璃望著她吧。車終于動了,離開了她的視線。她的胃開始灼痛起來,痛一直擴散到了整個胸腔,讓她難以呼吸。
此后的每一天晚上,她聽著樓道里的聲響歸于寂靜,想象著丈夫正在干什么。到后來,她痛得連想象的力氣都沒有了。有時她站在窗后,把目光投向外面黑幽幽的車道,看看有沒有什么奧迪A6停下。他不會回來了。她拉上窗簾,從窗戶那兒一直退到床邊,仰面倒了下去。她想自己這一生真是失敗,她將作為一個不幸的女人,在孤獨中死去。
有天晚上,她隨手打開電視,竟然看見了丈夫被采訪的鏡頭。身為大學校長,丈夫正侃侃而談對創意文化產業人才的培養。采訪結束,她換一個臺,主持人正在講解一部俄羅斯電影全片開頭的那個長鏡頭,“導演拍攝了一棵沒有一片葉子的樹,從清晨一直到太陽升起,預示著什么也不做苦苦等待,是沒有春天的……”
她一度認為,這是上天給自己的一個暗示。但在最終寄出那些匿名信之前,她猶豫了。
她決定去一次東城區市檔案館。這一年,距她的爺爺,那位著名作家去世,四十六年;離她的奶奶去世,十一年。是個陰天,還刮著大風。她想這城市怎么像自己內心一樣,那么陰,那么暗。她記得自己睜大眼睛,聽著奶奶講述她長長的逃難尋夫過程。那一年,她一個人雇了幾個車夫,帶了十件大行李,三個孩子,乘著夜色悄悄離開北平,先是坐火車到了安徽,又離開火車向西進入河南,夾在災民隊伍里一路向西,穿越整個河南省,走了五十多天,一直走到重慶,和丈夫團聚。每次聽,她都會像是第一次聽到這些似的對奶奶說道:“您太了不起了!”于是,老人的眼眶禁不住濕潤起來,走到那幅全家福前,用手撫摸一下,那張毫無笑意的臉。
她想親眼看看,那些家人口中,證明患難情緣的情書。既然它們能在幾十年前,讓一對男女彼此感動得熱淚盈眶,也許那些文字也會讓自己重新充滿愛的能量。
她一到那里,就貪婪地翻閱起來。她甚至看到了著名作家中學時代的習作,但她沒找到她真正想看到的東西,她急了,她可是為了它們才來這里的。就在這時,她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字體。
如果這是一個長鏡頭,那么,鏡頭先是從很遠的地方照出一條胡同,然后慢慢拉近,再往后就出現了一個三進小院,一進門是一座灰色磚影壁,接下來看到的就是第二道門了,一座五彩木影壁,鏡頭再近一些,是一個秀麗的“福”字。繞過木影壁,院子豁然眼前。(她在這兒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兩棵大柿子樹,從俯拍的這個角度看,它們尤其枝繁葉茂。院子里掛著剛洗完的衣服,屋檐,墻壁,慢慢看到了一間窗戶。鏡頭從窗外慢慢拍到里面那些家具、擺設、書、畫,以及坐在床前正寫著什么的女人。鏡頭推到筆尖,她看清了女人筆下的字……
“我好像就站在那兒,站在她的身后。我看著她正在寫字的手,就像是在看著我自己的手一樣。”
那些類似日記一樣的揭發信,完全可以充當著名作家的工作日志,比如今天寫了多少字,寫的是什么,給哪里寫的,寫給誰,見了多少客人,都有誰,說了些什么,等等等等。一日之內諸多事情,一、二、三、四、五,分頭敘述,總到十以上。也有為其開脫辯解的,細心的人一定可以猜得出來,寫下這些的女人,是個感情豐富而細膩的人。
當她看到這些時,她哆嗦了起來。
“原來我的身體里有這樣的基因,”她說道,“在她寫下那些的時候,他在這里,一個人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天。”
“傷害了他,毀滅了他的,并不是我們,而是不幸本身。……那年頭,我們大家都太害怕了。”
“在那個小院里,大家都選擇忽視,他的孤獨。”
“你以為她沒有注意到嗎?她早就知道,但她應該怎么做?她要是愿意,就不會把他們拆開了。在她辛苦持家,照顧他病重的母親時,他卻和另一個女人一起在另一個城市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惜的是,有五年時間,她一點兒也不知情。她還一直期待著他能來找她呢。后來告訴她的,是他的朋友,當然是出于好心。于是她帶著我們上了路,但他還是不肯來見我們,他說自己病了,需要住在醫院里,因為另一個女人也病了,他們就在醫院里躲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另一個女人主動離開為止。此后,有一段時間,他們仍然保持著聯系,他還猶豫過,要不要兩人一起離開……他對很多朋友說起過,說人的一生只會有一個愛人……”
她聽著聽著,抱緊了自己的肩膀,頭有點暈,但也許只是因為站立得太久了。她真想躺下來,蜷成一團。
一個男人,要是老想著另一個女人,在他寫作時,看書時,坐在樹下等待夜晚來臨時,甚至在他和這一個女人說話時,那另一個,總是忽地出現在他眼前,會是怎樣的感覺呢。而這一個,為了忘記這一切,每天準備著家里人要吃的飯菜,心不在焉地聽著大家談論文學,感嘆世事……
現在,她能感覺到,身體里,那個不幸女人的存在。她避開他的目光,扭過頭朝廠區出口望去,路燈已經亮了,但那些細細的彎著的桿子在她看來,像是一個個格外憂郁因此格外沉默的女人。
“我們都是可憐的人……”
“人是為了自己以為想要的東西而生活的,”他又點起一根煙,他長時間地輕輕按著她的肩膀,夜幕像罩子一樣落下,兩人衣角的輪廓也開始模糊起來。
“但是,相信我,父親優秀的血脈每天都在我們身體里流動不息,”他用一種神秘的語氣驕傲地對她說道,“別放在心上了。來,讓我們回家,閉上眼睛,睡一覺,一切都會好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