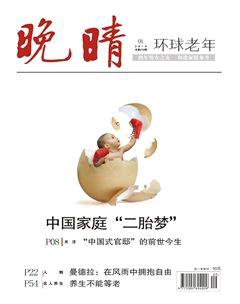請讓我們安然逝去
張麗+張杰+孫秀萍
“帶著光彩與幸福,父親平靜地走了”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鮮花、氣球、蛋糕、親友的陪伴,這一切讓浙江省紹興市人民醫院放療科病房變得溫馨起來。滿頭白發,身形消瘦,皮膚發黑,整潔的藍色襯衫外是一件黑色西裝外套,臉上洋溢著幸福,2013年5月的一天,沈水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吹熄了為自己點燃的生日蠟燭。3天后,他平靜地離去了。
62歲的沈水濤,發病前獨自在新疆工作了25年,只有春節假期才回紹興跟家人團聚。直到2013年5月,他被確診為胰腺癌末期,住進了諸海燕護士長所在的放療科病房。確診后,生命留給他的時間只有不到半年。住院后,雖然兩個女兒精心照料,積極配合治療,可對于癌末病人來說,任何醫療手段都是無力的。“25年來,父親默默付出,我們從沒為他做什么,一直覺得很虧欠。”女兒沈明琴說。
“我們了解到,病人住院期間恰逢生日,”諸海燕便和家屬精心策劃了一場生日會。在醫護人員和親友等四十多人的陪伴下,病情已非常嚴重的沈水濤,臉上卻散發出了少有的光彩。“他走得非常平靜,沒有什么痛苦。”這讓諸海燕和他的同事們備感欣慰,也讓他們和病人家屬成了朋友。諸海燕說:“我一直有個心愿,就是讓更多人知道,除了醫療手段以外,我們還有很多可以為癌末病人做的。”
“安寧療護”開啟照護新模式
諸海燕所說的心愿,就是積極傳播“安寧療護”。安寧療護,又稱臨終關懷、姑息療法等,由英國人桑德斯于上個世紀60年代開創,他的目的是“盡一切努力,讓患者安然逝去,也會盡一切努力,讓患者好好活到最后一刻”。但在我國大陸,這一理念剛剛萌芽。
一本叫做《死亡如此多情》的書里,記錄了百位臨床醫生口述的臨終事件:“他的表情非常痛苦,臉色灰黃,佝僂著身軀,張著大口竭力呼吸,但仍然感覺力不從心……”“他常跟我說,你能不能給我打一針讓我過去就算了,太痛苦了。”在這本書中,臨死前的人早已失去了尊嚴,很多都是渾身上下插滿管子,在疼痛哀號中結束一生。
其實,全世界的醫務工作者在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過程中,都無法忽略一個事實:面對絕癥患者和家屬,基本宣告無效的醫療手段,絕不是他們在最后的生命過程中唯一需要的。尊嚴、體面、幸福、安寧,在患者身上都可以實現。諸海燕強調,“安寧療護”不是“安樂死”,是給予臨終患者積極而整體的照顧。
“四全照顧”讓病人死得有尊嚴
“安寧療護”在國外并不是新鮮事了,比如在英國,目前,已有一百多家安寧療護機構,每年都會有十多個國家前往學習觀摩。在日本,更是將這種人性照護發揮到了極致。
日本靜岡縣的癌癥中心有一棟特殊病房——“姑息治療”病房,是專為不能治愈的癌末患者準備的。病房寬敞舒適,如同賓館,窗外是綠樹成蔭的庭院。為讓患者在臨終前享受更多的家庭溫暖,醫院盡量創造條件,讓親人們經常陪伴患者,同時還為家屬提供心理咨詢,幫助他們減緩親人即將逝去的痛苦。
在中國臺灣,每年有3.5萬多人死于癌癥,其中40%的癌末患者接受了安寧療護。他們有“四全照顧”的特色,即全人照顧(身、心、靈),全家照顧(病患、家人),全程照顧(臨終、家屬悲傷期),全隊照顧(醫生、護士、心理師、社工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宗教人員等),讓很多癌末病人免受了痛苦的煎熬。
“我們的臨終關懷做得太少”
目前,我國每年新發癌癥患者160萬人,因癌癥死亡130萬人,但自1988年成立首家安寧療護機構以來,目前能提供安寧療護的醫院仍然極少。國人對“死”的忌諱,使“放棄搶救”的安寧療護推廣起來異常艱難。
北大醫學部醫學人文系教授王一方對生命看得也很理性,他說:“人重要的不是光活著,而是有尊嚴、有品質地活著,減少人生最后一個無謂的傷害。”
“人握著拳頭來到世上,經歷一生,應該放開手、輕松地、平靜地離去。”可事實上,多數癌末病人仍攥著拳頭離開。郭航遠指出,對多數癌末病人的搶救,基本都是創傷性和徒勞的。醫療手段可能讓病人延續幾天生命,但也會造成極大損傷。比如,心臟按壓會讓病人的肋骨斷掉,除顫可能燒焦皮膚,全身插滿管子,肚子鼓起來,整個人都會變形。面對無休止的搶救,病人會陷入極度恐懼,全身痙攣。其實,醫護人員在搶救過程中也很痛苦。“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是一步步升華的從醫境界,也是目前醫學界應該思考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