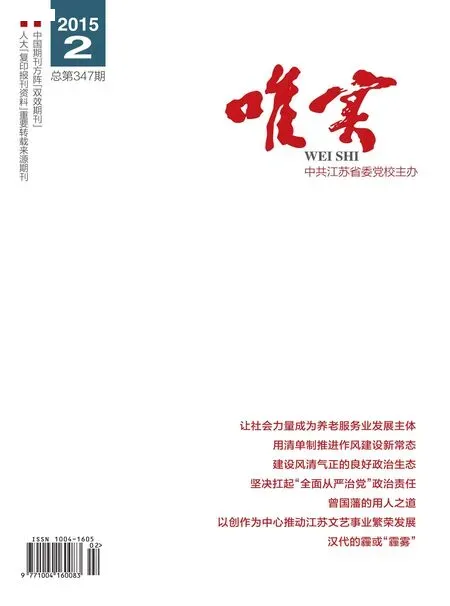美國戰略調整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
張政文
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奧巴馬政府積極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大力度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和圍堵。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則積極推動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筆者以為,只有把握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質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積極加以應對,才能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一、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質及重要舉措
“重返亞洲”及其后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其最終目的就是保持和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改變地區安全形勢,推廣美國價值觀。這一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其關注點及著力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政治上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是全球霸權。冷戰期間,美蘇爭霸,保持美國在歐洲的強大存在和跨大西洋聯盟體系,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的地緣政治格局迅速變化。面對亞太地區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迅速崛起,美國必須將更多的戰略關注轉向亞太地區,只有首先保持其對亞太地區事務的主導權,才談得上對世界的領導地位。美國總統奧巴馬高調宣稱,自己將成為“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而這正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關鍵所在。
經濟上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奧巴馬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美國經濟的舉措,與此同時,面對亞太地區一系列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和區域經濟合作的加強,美國竭力主導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為此,美國全力打造TPP,即“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其主要目的,一是想借此強化美國在日益繁榮的亞太經濟圈中的經濟主導地位,增加美國出口,提升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二是想借此排斥中國,削弱中國經濟在亞太經濟圈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為此,美國為加入TPP談判設置了兩個高門檻:一是享有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二是實行完全的市場準入,即成員國之間實行零關稅,試圖借此把中國擋在TPP的門外。
外交上維系美國的盟主地位。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基礎和前提之一,就是要加強與亞太地區主要盟友的關系,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和存在,同時在中國周邊一再挑起事端,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為此,美國一是繼續加強在亞太地區已有的雙邊及多邊同盟關系,二是發展與一般性友好國家的關系,三是積極拓展新的外交和戰略空間,改善與曾經視為敵人和對手國家的關系。“重返緬甸”,就是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外交上的一個大手筆。美國對緬甸策略上的調整,有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及能源戰略考量,是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和圍堵的重要步驟,客觀上也對中緬關系產生了沖擊和影響,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和挑戰。
軍事上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保持一支超級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美國維護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戰略支撐。盡管由于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和影響,美國不得不在今后十年內總共要削減大約50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并且相應地減少在世界一些地區的軍事存在和軍事干預行動。但與此同時,作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舉措,美國卻一再強調將繼續保持和加強其在亞太地區主要軍事存在或軍事關系。2012年6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大會(又稱“香格里拉對話”)上明確表示,美國將繼續增加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在2020前,美國海軍軍艦部署會從現在的太平洋地區和大西洋地區各分布50%,逐漸轉變為太平洋60%,大西洋40%。在2013年6月1日舉行的“香格里拉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再次強調,美國將繼續亞太“再平衡”戰略,并將采取更多“看得見的”行動實現戰略重心的轉移。
二、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和挑戰
冷戰結束后,“遏制”和“圍堵”始終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主軸。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其實質就是進一步強化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和圍堵,也因此導致近年來中美關系頻起波瀾,在雙邊關系領域及中國周邊地區展開激烈的博弈和對抗。
挑戰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首先表現為在雙邊關系領域一再挑戰中國國家核心利益,如媒體所稱的“三T”問題,由此導致近年來中美兩國關系中風波不斷。一是貿易問題(TRADE)。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發展勢頭迅猛。2012年,兩國貿易額已超過了5000億美元,中美兩國互為對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但隨著兩國貿易額的增加,兩國間的貿易摩擦和貿易糾紛也愈加頻繁,特別是美方頻頻舉起貿易制裁的大棒,對中美正常貿易造成了嚴重干擾。美國一方面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借口,竭力阻撓中國企業進軍美國市場,另一方面繼續禁止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國市場。而與此同時,美國卻又把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責任歸咎于中國,無端指責所謂的中國政府出口補貼政策,甚至打著貿易“再平衡”的旗號,強逼人民幣升值,企圖使中國重蹈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嚴重衰退的覆轍。二是西藏問題(TIBET)。眾所周知,“涉藏”、“涉疆”問題,都是中國國家核心利益所在。近一個時期以來,“三股”勢力活動猖獗,嚴重影響了中國西部地區的社會安定和民族宗教團結,西部地區維穩、反恐、安邊的斗爭形勢十分嚴峻。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持續在“涉藏”、“涉疆”問題上大做文章,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挑戰中國家核心利益。三是臺灣問題(TAIWAN)。臺灣問題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國家核心利益所在。當前兩岸關系繼續向緩和方向發展,但影響臺海局勢穩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奧巴馬上臺以來,美國政府一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連續兩次對臺軍售,軍售總額達到131億美元,嚴重損害中美關系。
影響亞太地緣戰略格局及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周邊狀況頻出,海上安全環境更趨復雜,對國家安全戰略全局的影響更加突出。美國積極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一再挑起事端,加強從外部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其重點之一,就是加強在“第一島鏈”的軍事存在。一是加強在東北亞的前沿軍事存在。其一,加強美韓軍事同盟關系。2012年12月以來,由于朝鮮連續進行“光明星3號”衛星發射及第三次核試爆,半島局勢驟然緊張,朝核問題再次發酵,朝美博弈及朝韓對抗進一步加劇。在韓國總統樸槿惠訪美期間,雙方發表了《韓美同盟60周年聯合宣言》。奧巴馬對韓國作出了三個承諾:為韓國提供絕對的核保護傘;堅決阻止朝鮮發動對韓國的大規模地面進攻;如果有必要,美國將直接摧毀朝鮮的核設施。奧巴馬強調,美國保留對朝鮮發動核打擊的選項。美國還借機將大量高新武器裝備部署在半島周邊。與此同時,美韓兩國頻繁展開“關鍵決心”、“禿鷲”等各類聯合軍演,對朝鮮進行武力威懾。由此,美韓聯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其二,加強美日軍事同盟關系。在過去幾年日本民主黨執政期間,美日同盟關系一度受到沖擊和影響。但自2012年4月中日島爭再次發酵以來,特別是自民黨的安倍政權上臺后,美日軍事同盟關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日本積極充當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抓手,挑戰中國,同時借釣魚島問題拉美國下水,讓美國替它背書;美國則一再縱容日本突破禁區,在復活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與此同時,美日頻繁舉行包括“離島奪占”科目在內的大規模聯合軍演。由此,美日軍事同盟關系得到加強。在此基礎上,美國積極撮合日韓放棄嫌隙,尤其是在“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上的尖銳對立,推動建立美、日、韓聯盟。美國此舉名為應對朝鮮的核威脅和導彈威脅,實則進一步強化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二是鞏固與臺灣的實質性軍事聯系。其一,加大對臺軍售力度及規模。2010年1月,美方宣布向臺灣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3”反導系統、“魚鷹”級掃雷艇、“魚叉”導彈等總額近64億美元的武器裝備。2011年9月,美國再次宣布有關對臺軍售計劃,包括為臺“改裝”其現有F-16A/B型戰斗機,售臺軍用飛機零配件并提供有關訓練項目,軍售總價值約為58.52億美元。其二,進一步密切與臺灣軍方的Link-16數據鏈聯系,實現美軍與臺軍之間信息情報的互通互享。其三,實質性地參與臺軍的年度軍演,包括兵棋推演以及實兵對抗演練。這不僅是展示一種政治上的姿態,而且臺海一旦有事,此舉也極具實戰價值。endprint
三是重返東南亞,實現在南海的直接軍事存在。其一,加大在南海方向實施抵近海空軍事偵察活動的力度,緊盯海南島及南海方向戰略設施以及軍事部署。其二,頻繁地與南海周邊國家舉行一系列的雙邊及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其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國,離間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關系,一旦中美在南海有事,將逼迫這些國家選邊站。其三,尋求在南海周邊如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新加坡的樟宜基地,特別越南金蘭灣基地的使用權。由于金蘭灣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港口條件,一旦美國重新得手,整個南海區域,北至臺灣海峽,西南到馬六甲海峽,都將完全置于美國的直接軍事控制范圍內。這意味著在南海方向,中國將直面美國的軍事存在。
三、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如何確保中美關系健康、成熟、穩定發展,不僅事關中美兩國人民的福祉,而且關系到亞太地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因此需要準確把握中美關系的戰略定位及發展方向,通過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走出一條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之路。
準確把握中美關系的戰略定位。今天的中美關系,已經取代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成為當今世界上一對最重要的大國關系。但今天的中美關系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一是過去的美蘇關系是大國爭霸的關系,而今天的中國一再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中國并不試圖挑戰美國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也不試圖單方面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關系體系。二是美蘇之間是單純的競爭和對抗關系,進行所謂的“零和游戲”,利益直接沖突,幾乎不存在共同利益,而中國則強調互利、合作、共贏,把利益的蛋糕做大。中美之間客觀上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空間和聯系,如中美互為對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還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這種共同利益以及緊密的經濟貿易聯系,客觀上已經使得中美兩國成為一個巨大的利益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一個時期以來,西方曾經流行過“中美共治”與“G2”(即中美兩國集團)等說法,但都未得到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的接受和認可。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對于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遠沒有達到美國的水平,不能像美國那樣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只能是盡責而已;二是中國政府堅持獨立自主及不干涉內政原則,主張自己的事自己作主,國際上的事則大家商量著辦,反對像美國那樣四處插手,干涉別國內政。而對于“中美共治”背后所隱含的美國做老大,中國甘心做老二,配合美國的戰略意圖,中國更是不能接受。因此,如何把握中美關系,給兩國關系一個準確的戰略定位,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意義重大。1997年至1998年,在中美兩國元首的互訪中,雙方同意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但由于1999年發生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兩國關系嚴重惡化。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把中美關系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關系”。直到2002年,中美雙方再次把兩國關系定位為“建設性合作關系”。2009年,兩國確立了面向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2011年,兩國再次強調共同努力推動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在此基礎上,中美兩國建立制度性的戰略對話機制以及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合作對話機制已多達190多個,特別是2009年,中美兩國元首決定,將原有的中美戰略對話以及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合并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至今已展開了五輪對話,并且取得了豐碩成果。2009年至2012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共進行了12次正式會面,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奧巴馬總統在5年中也進行了9次電話交談、書信往來及正式會面。由此可見,中美關系的戰略定位以及相互之間的對話溝通機制是成熟和完善的。
推動建立中美關系的新架構。我們不僅要明確中美關系的戰略定位,更需要把握中美關系的戰略走向。從歷史發展長河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而一個新興大國與一個守成大國之間如何避免對抗和沖突,則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回顧歷史,近代以來世界范圍的權力轉移,既有英國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和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從而建立起日不落帝國,也有美國以暴力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始,而后卻有英美之間的權力和平過渡;既有歐洲的德國和亞洲的日本企圖挑戰既定國際秩序、建立新的霸權卻以失敗而告終,更有二戰后蘇聯與美國爭霸卻最終導致國家的解體。由此可見,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和權力轉移,往往都是伴隨著血雨腥風,暴力、沖突,甚至戰爭不斷。我們要用實踐證明,我們能夠走出一條和平崛起的新路,規避近代以來由于大國崛起所引發的歷史悲劇。在此情況下,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美關系應該向何處去?應該如何確立中美關系的新架構?歷史需要答案,而現實更需要一個正確的答案。這個答案就是中美兩國應該共同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種新型大國關系,要求中美之間要超越你得我失、你贏我輸、你興我衰的零和思維,進一步增強戰略互信,要尊重對方而不是挑戰對方,關照彼此核心關切而不是逾越戰略底線。它意味著對傳統大國關系模式的摒棄,是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也是中美兩國的必然選擇。
(作者系解放軍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黃 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