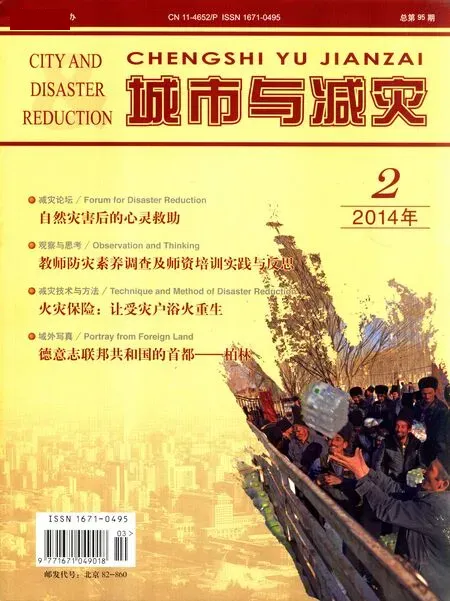自然災害后的心靈救助
中國佛教協會 學誠
自然災害后的心靈救助
Soul relief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中國佛教協會 學誠
【編者按】科學、宗教、藝術并非鴻溝難越,防災減災事業需要多學科積極參與、社會各種力量為之貢獻力量。為此,本刊特節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于“第十六次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所作基調發言內容,期望以全新視角,帶來些許思考。

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威脅
自從人類出現之日起,自然災害就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人類前進的腳步。漢字的“災”是火焚屋的形狀,意味著外在的自然力量對人類文明成果的破壞。當這種破壞嚴重損害了人類利益,“災”便稱之為“害”。
佛教認為世界由“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構成,因而自然災害可分為四種類型:地大不調——地震、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火大不調——火山噴發、山林大火;風大不調——臺風、颶風、龍卷風等氣象災害;水大不調——洪水、海嘯等水文災害。現代文明日新月異,而自然災害依舊頻繁爆發,其造成的經濟財產損失也隨著人口密度日益增加、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日益擴大、經濟生產日益集中而直線上升,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仍然受到嚴重威脅。
我們看到:諸多大型設施潛藏安全隱患,一旦發生重大天災,極容易引發連鎖災難,如海嘯引起核電站泄露、地震造成大壩決口、極端氣象災害導致電網崩潰等等,令人猝不及防。
我們看到:自然災害背后的人為因素越發突現,大規模的經濟開發能直接改變一個地區的地貌、水文條件,為日后爆發威力更為巨大的自然災害埋下伏筆。
我們看到:自然災害對人類社會造成整體性沖擊。跟突發性災害相比,漸發性災害的長期性威脅更不容樂觀,氣候模式的深刻變化引發諸如全球變暖、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等現象,可能在不遠的未來給人類社會帶來致命的威脅。
災后心理創傷與心靈救助
相對于物質財產的損失,個人心靈蒙受的創痛更需要關注。一場不期而至的災難,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也破碎了人們的心靈家園。生活的廢墟很容易在幾年后重建,心靈的廢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
墟有時用一生也難以復原。在搶險救災的重要關頭,遭受災害直接打擊的幸存者,身處災區緊張工作的救援者,后方關注救災進展的社會公眾,都有需要接受側重面不同的心靈幫助。
(1)恐懼感。當災難降臨之時,恐懼感是人類最直接的心理感受。相當多的遇難者是在絕望和痛苦的掙扎中逐漸死去,幸存者也大多經歷了種種磨難、九死一生,尤其是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在災難到來時更容易受到驚嚇,甚至產生嚴重的心理應激障礙。
恐懼的主要原因是生命缺少堅固的依靠。人生中能依靠的事物很多,父母親人、老師同學、領導朋友以及金錢、地位、權勢、名氣都能給人依靠的感覺。然而一旦災難瞬間而至,生死一線間,那些看似堅固的依靠,卻轉眼間如紙牌屋一般土崩瓦解。真正堅固的依靠并不在身外,而是內心的光明。光明令人問心無愧、心安理得。人生終究會有一場生死的大考,即便不是眼前,早晚都會來臨。如何生活才能無愧此生、死而無憾?這就需要增長生命的智慧,懂得人生的真諦。
(2)幻滅感。從死亡線上僥幸逃生的幸存者,常常會有一種生不如死的心理,感到自己失去了生命中的至愛至親,喪失了繼續生活的意義。相依為命的親人、畢生積累的財富、白手開創的事業、健康完整的體魄,曾經是人生幸福的最大來源,是人生價值的最終體現,如今一切都沒有了。很多人從此再也無力面對現實,迷失于對過去生活的深切眷戀。
在佛法看來,所有的不忍放手、不忍分離都是一種執著。只要人繼續活著,人生的價值就不會消失。人生如同一顆不斷燃燒的蠟燭,只要存在一天,就可以釋放一份光熱,給世界送去一份希望,給人間增添一份溫暖。人生最大的價值就在當下,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把握。
(3)愧疚感。沒有比眼睜睜地目睹他人生命消逝而無力搭救更令人心痛的事情了。盡管救援者奮盡全力,但是面對復雜的環境和有限的人力,能在短短72小時內搶救出的受難者畢竟有限。很多時候,幸存者與救援者都會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懊悔所煎熬。有的幸存者會將親友的亡故歸咎為自己的過錯,無法原諒自己茍且偷生。有的救援者會不顧疲憊一再加班,卻仍舊為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備受打擊。
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別人的不幸也未必都是自己造成的。在為別人遭受苦難而心生悲憫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分擔他們的痛苦。盡管他們可能無法感知我們的付出,然而功不唐捐,我們的付出將伴隨他們的無限生命。
(4)憤世感。當社會公眾透過新聞媒體,看到災區群眾飽受饑寒的時候,除了喚起很多人的惻隱之情,往往也會招致某些人的義憤填膺,從偏激的角度批評社會問題,以挑剔的態度指責他人行為。
通常這些指責都是一些想當然的看法,是對復雜事態膚淺而簡單化的理解。我們應該看到更多人是在真心為他人付出,為災民奉獻自己的愛心。個別的“假惡丑”不能掩蓋社會整體上的“真善美”。正是要靠社會上足夠多的善良和愛心,才能最終感化丑惡和冷酷。

近年來,我國連續遭受重大自然災害侵襲。中國佛教協會號召全國佛教徒積極參與救災救難,除了給予災區必要的物質幫助,更深入實地開展了各項心靈救助行動,取得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良好的社會反響。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北京市仁愛慈善基金會聯合各方佛教慈善組織緊急趕赴災區,迅速制定了“物資賑災、校園重建、心靈重建”三階
段的救援計劃;在震后第一周,就開辦了災區第一個恢復上課的臨時教學點,及時穩定災區兒童的情緒,盡早排除負面的情緒影響;在震后兩周內,共開辦了4間學堂、7所學村,保障了上千名學童在學校未建好之前的過渡性學習,并組織心理專家進行心理干預;又進一步啟動“心在行動”教育援助計劃,為災區300多位教師解決災后心理問題,傳授心理輔導技能;聯合有關社會機構與政府部門成立“北川心理援助聯盟”,針對當地百姓提供長期心理援助。2010年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發生后,仁愛基金會繼續組織佛教信眾,開展了援建板房校舍、編寫心理輔導教材《生命讀本》、建立仁愛社區與兒童活動中心、開展教師心理輔導培訓等援助活動,為災區群眾心理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



結合幾年來的經驗,我們認為災后的心靈救助,既要充分發揮宗教信仰的傳統優勢,也應有效結合現代心理學的豐富資源,廣泛聯合社會各方面力量,重點關注易受創傷的弱勢群體,開展有計劃、分階段的心理援助。心理救助一般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無畏施——解決生存問題,為災民提供急需物資,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緩解應激性障礙;第二階段:財施——解決生活問題,幫助災民重建信心,排遣心理焦慮;第三階段:法施——解決生命問題,開展生命教育,引導人生方向。
人類集體意識
在彌合心靈創傷的同時,我們還應關注自然災害與人類集體心理的深刻關系。人類集體心理是人類共通的心理模式和共有的心理狀態,直接決定人類如何思考問題、行動決策。佛教認為,有思故有業,業是能夠產生現實作用的一種力量。個人的、單獨的思想活動所產生的是“別業”,只會決定個人的苦樂境遇。集體的、共通的思想活動所產生的是“共業”,則會決定人類的前途命運。正如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指出:“我們個人的心理狀態只是一薄薄的表層,只是集體心理之海的一個波浪。那改變了我們整個生活、改變了已知世界的外表的強大因素、那構成了歷史的強大因素,就是集體心理。”
一個心理狀況不良的社會,注定是脆弱短命的。孔子在《論語》中提出“足食、足兵、民信”是社會的三大支柱,并將“民信”放在首位,看得比“足食”、“足兵”都更為重要。我們可以用“食”比喻物資儲備,用“兵”比喻科技能力,用“信”比喻心理健康,三者是人類抵御災害的三件法寶,心理健康也應位居首位。就像一個人如有嚴重的心理問題,就可能做出瘋狂的舉動,如果人類陷入不良的心理狀態,也會產生種種非理性的集體行為,甚至危害自身的生存。
人類集體心理跟個人心理一樣,也可分為意識和無意識(或潛意識)兩個層面。集體意識表現為社會上的各種學說、思想、信仰;集體無意識則是集體意識背后的原動力,是歷史沉淀下來的精神內核。“原型是巨大的、決定性的力量,他們促發真實的事件,而不是我們個人的理性或實際的知識。”
在人類集體意識的歷史上,人類對待自然災害的態度經過了三個階段:
(1)神話階段。在早先人類的眼中,各種自然現象是具有意志和生命的人格,風、雨、雷、電等氣候變化皆是神靈的身影,自然災害是神靈偉力的展現。人們必須向神靈獻祭,才能避免災害的降臨。
(2)宗教階段。人類進入軸心時代以后,有神宗教相繼創立。在西方宗教信徒的眼中,自然是上帝的創造,自然災變是神圣旨意的體現,是對人間邪惡的懲罰。在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產生了“天人感應”思想,也同樣把社會運行跟自然變化建立起聯系,認為自然災害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人間統治者的倒行逆施觸怒天意所致。
(3)科學階段。近代科學的興起使西方文明率先跳脫神學思想的禁錮,對有神論的災害觀提出了大膽質疑。尤其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悲劇,引發了伏爾泰、盧梭、康德等思想家的集體反思。人們開始相信,自然災害是與人類社會全然無關的自然現象,必須著手科學調查與觀測來解釋災害、預防災害,而非沉溺在妄自臆想之中。
時至今日,科技的飛速發展顯著提升了人類抵御災害的物質能力,不過在巨大天災面前仍然顯得不堪一擊,災害來臨前人們也來不及在短暫的預警時間內妥善避險。而且當預報自然災害具有不確定性的時候,人們往往不甘犧牲短期經濟利益以提前采取充分的防護措施或是遷離潛在的受災地區。因而科技進步還是無法完全避免自然災害可能造成的慘重破壞。
更嚴重的是,一味崇拜科學技術與物質力量的思想傾向,令人類一葉障目,非但不從災害中反省,反而加劇對自然的對抗情結和控制欲望,表現為:僅僅看到自然災害損害了自身欲望,無法看到自身欲望違背了自然界的本性;僅僅看到理所應當向自然索取,無法看到更應有責任為自然付出;僅僅看到自然應該順應人類,無法看到人類理應順應自然。這些都讓人類無法真正的理解自然、適應自然,只會加深人與自然之間的隔閡,加重人類唯我獨尊的偏執。
人類對自然災害的態度是一個重大問題,它既有可能引導人類社會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也可能誘使人類墮入永無寧日的死亡循環。如果人類繼續執迷不悟,那么自然災害造成的長期痛苦將無法避免。
人類集體無意識
從集體無意識的角度看,人類對自然災害的對抗情結,并非發展科學技術的直接后果,真正的根源乃是內心深處對自然的恐懼。正是由于恐懼,人類才會仰仗科學技術來保護自己,才會遠遠地逃離自然,藏身于鋼筋水泥的叢林,隔絕于自然之外。人類為自己筑起了高墻,也就慢慢喪失了對自然的感受能力。自然成了一種遙遠而陌生的存在,成了供人把玩的盆景。
以往人類通過神話或宗教的方式,將恐懼升華為對大自然的敬畏,取得了內心的和諧與平衡。然而現代人壓抑了內心矛盾,粉飾了自我偏執,選擇了一條用科技武裝自身、征服自然的道路。科學知識固然祛除了一些虛妄想法,但卻無法真正緩解原生的恐懼。自然還是自然,只能被接受,不能被馴服。直到有一天,自然以猙獰的面目擊碎了人類的炫耀,人類才會如夢初醒。可是一次次,人類不是重拾對自然的敬畏,反而喚起更強的不平與忿恨,造成更深的對立與排斥。
只要存在對立與排斥,就會永遠伴隨不安和恐懼。自然如同人類的父親,既令人生畏,也值得尊敬。自然是人類成長的故鄉,也是文明萌芽的起點。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亞里士多德的名言是:“技藝摹仿自然”。西塞羅說:“我追隨‘自然’這個最好的向導,對她敬若神明,遵從她的命令。”達·芬奇說:“繪畫為自然的孫兒。”夸美紐斯認為,“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給一切人們的教學藝術的主導原則,這是應當、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為借鑒的。”大自然本是文明進步的良師,亦是創新靈感的源泉,當今諸如循環經濟、生態文明等前沿概念不正是通過效法自然而獲得的啟示嗎?
自然其實是人類內心本來面目的呈現,人與自然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對立。面對自然,就是面對自心。
我們相信,未來的世界必將是心之世界,非物之世界,非我之世界。人類應當共同攜手建立一個匯聚眾人之善心、愛心、慈心、良心的嶄新世界。在新的世界里,我們擁有新的意識,開創新的文明。那將是:
經濟的增長,社會的運行,不是劃分人與人之間的鴻溝,而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包容!
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不是加劇人與自然的對立,而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
文化的繁榮,藝術的復興,不是制造人與自我的分裂,而是達成人與自我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