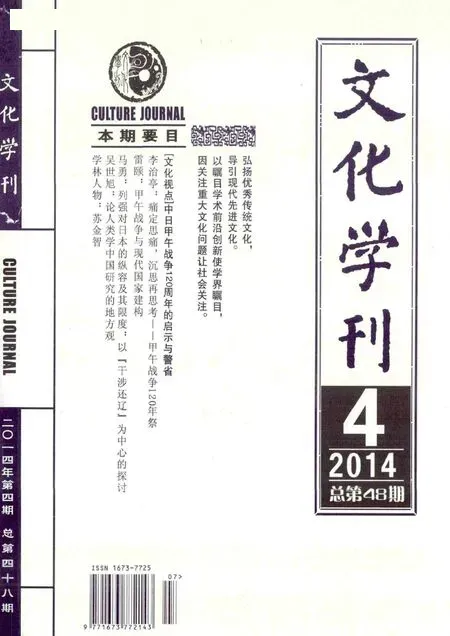讀《滿蒙古跡考》
紀曉晨
(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某些有關中國的民族調查和考古發掘由外國學者開創先河,他們創造的學術財富為日后人類學的中國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素材。回溯人類學的東北研究,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的貢獻不可磨滅。鳥居龍藏被認為是日本研究東亞民族土俗及歷史文化的先驅人物,他在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方面均有建樹。《滿蒙古跡考》乃是他1927年第八次探查滿蒙地區的概要,此書偏重于歷史考古學,尤其側重對渤海、遼、金三國的歷史和遺物的研究。鳥居龍藏具有開創性的研究不僅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翔實的學術資料,更重要的是樹立了一種研究的典范。
一、簡述鳥居龍藏的學術生涯
相較于書齋中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學術源泉多來自于密集的海外調查。鳥居龍藏調查地域之廣、領域之多、時間之久在當時的學者中無出其右。他田野研究的地域“包括千島群島與庫頁島 (今俄羅斯)、朝鮮、滿蒙 (中國東北、熱河)、日本列島、沖繩群島、臺灣及中國西南,可以說縱橫環東亞地帶,囊括中國文化圈自東北而西南的邊緣地區。”[1]1895年到1900年,他多次來到臺灣調查當地原住民的情況,并將研究所得撰寫成民族志,這比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出版民族志還提前了十幾年。1902年到1903年,他考察了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這也是他對臺灣原住民研究的補充。“調查地區為湖南、貴州、云南、四川等地,調查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瑤族等。他考察了諸民族的分布與自然地理條件之間的關系、各族體質、服飾、居住、習俗、語言、文化等,事后編寫了《苗族調查報告》和《中國西南部人類學問題》等著作。”[2]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本土學者對西南少數民族做過真正的田野調查。1905年后鳥居龍藏的研究重點轉向中國東北地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的日本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民族學的主要理論是進化論和傳播論等,而日本殖民主義的擴張也是日本民族學發展的背景和條件。鳥居龍藏前往遼東半島時中日甲午戰爭已經結束,這個時期還處于軍事上的緊張狀態,他的田野調查是在日軍的協助下進行的,考察地點主要選擇在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他熱衷于滿蒙及朝鮮等地的研究還在于“這兩個地區近年來狀況改變得非常顯著。因為這種理由,從過去繼承到的傳統文化正在迅速流失,這也就意味著,鳥居龍藏在這兩個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是過去被繼承的傳統文化的最后時期,資料的價值可以說是非常高的。”[3]從 1895年首次踏入遼東半島到1935年,鳥居龍藏先后在中國東北調查了九次,在蒙古調查了五次,在朝鮮調查了六次,這也是他學術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
二、鳥居龍藏與《滿蒙古跡考》
鳥居龍藏撰寫的考察報告和著作極多,《滿蒙古跡考》充分地反映了他的研究風格,在實地考察中融入了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學科的思考。《滿蒙古跡考》一書共三十三章,由于章節偏多且每章篇幅長短不一,暫將內容歸納為四個部分:(一)回溯對于滿蒙文化的研究軌跡;(二)滿洲歷史與現狀;(三)記錄沿途的考古發現,尤以渤海、遼、金三國的文化和遺物為重;(四)漢族在滿洲的遺跡。此次調查鳥居龍藏從大連出發,考察地包括奉天、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析木城、普蘭店等,其記錄之周全、涉獵之廣泛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滿蒙古跡考》序言中寫道“余之研究滿蒙(或朝鮮),殆費半生心血矣”。[4]這位學者以其行為證明了此言不虛。
回顧鳥居龍藏的滿蒙考察史要追溯到1895年,由于當時南滿鐵路沒有建成,因此他通過步行加上車馬的方式從柳樹屯開始先后途徑金州、旅順、熊岳城、析木城、安東等地。這次關于高句麗和遼金等時代的調查令他收獲頗豐,例如他在析木城發現了遼代的石棚和磚塔的遺跡,在熊岳城發現了石矛頭,在貔子窩發現了石斧,在普蘭店發現了漢磚,在金州見識到了古佛像雕刻等,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啟發了他對于東北地區石器時代的研究。1905年鳥居龍藏關于普蘭店鍋底山的調查對滿洲石器時代史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價值,隨后他又至奉天調查清宮殿寶物和薩滿祭具,沿途測定滿洲人的身體。他在楫安(今吉林集安)考察高句麗時代的陵墓和古碑,還在遼陽考察了磚塔和漢代磚墓,借此聯系到漢代的遼東郡治。1905年至1907年,他開始了對東蒙古的探查,他學習蒙古語言文字,測定蒙古人的身體,過赤峰至錦州觀遼代磚塔。1910年,鳥居龍藏在旅順老鐵山附近發現漢墓、磚墓、貝塚、土器、石短劍等遺跡,又在遼陽發現了石棺、磚棺、石槨,為滿洲漢代的考古學研究建立了基礎,隨后在撫順發現了金代的陶器。1911年鳥居龍藏調查了朝鮮咸鏡道、滿洲的延吉,在圖們江發現了石穴,在龍井研究高句麗古墳群,在局子街觀銅佛寺古碑考察石器時代遺址,在琿春調查古城和滿洲人的土俗。1912年至1913年,鳥居龍藏在鐵嶺帽子山研究堡塞遺跡,又考察了在開原附近的石棚、遼金時代的石人,在柳河森林發現了女真文石碑。1919年,鳥居龍藏調查了東西伯利亞和北滿洲。除了上述七次他又由朝鮮入滿洲三四次,調查涉及朝鮮、東西伯利亞及滿蒙的基本情況。
回溯滿洲的歷史,就不得不提到通古斯民族。鳥居龍藏在《滿蒙古跡考》中指出在漢族來到滿洲之前這片土地的主人是通古斯民族,歷史上的肅慎、扶馀、高句麗、靺鞨、渤海、女真等均屬于通古斯民族。當通古斯民族居于滿洲時,燕國人最先侵入此地并在遼東建立殖民地,以遼陽為中心,東擴至鴨綠江,鳥居龍藏也在當地發現了燕國人所使用的通貨。在燕國鞏固勢力的同時,齊國侵入滿洲南端,建立齊國的殖民地。燕國后為秦所滅,再待秦滅亡,漢代在此地設立遼東郡,觸角又深入朝鮮西北部,在今黃海等地設樂浪郡。當時漢人也與日本人接觸,日本自此開始引入漢族文化。漢在遼東和朝鮮得勢之際,北方的高句麗崛起。高句麗是通古斯民族中扶馀的一支,后征服漢在滿洲的殖民地。自此,高句麗久踞于朝鮮北部和滿洲,其歷史遺跡多現于此二地。高句麗后為唐與新羅國夾擊所滅,其亡命者多逃于日本。此時,北部滿洲同為通古斯民族的渤海王國興起。渤海國與唐朝交往頗深并吸取了唐的文化,極力模仿唐的制度和文物,上流社會更是彌漫著唐朝文人喜好作詩的文人雅趣,因而渤海國重和平,少戰爭。除了引入漢族文化,它在日本奈良平安時期就與日本溝通交流,還與土耳其民族的突厥人有往來,文化程度較高。當渤海國統治滿洲時,蒙古的契丹興起,后滅渤海國建立遼國,控制滿洲與東蒙一帶。契丹人欣賞渤海文化,抓捕大量渤海人從事鍛造、冶煉、造車等工作。遼之文化多受突厥、漢族、朝鮮的影響,軍事與文化優勢遠強于渤海國。遼最終為女真征服,后者建立金國,滿洲多見金之遺跡。
歷史上滿洲人最終滅明朝,進駐北京。由于中國地域遼闊難以統治,因此清廷便任命同族人加以治理,唯恐人數不足又遠及松花江和黑龍江等地招致滿人進入內地。如此一來滿洲人深入內陸,他們原先的居住地遂成為無人勞作之地,而滿洲人以此片土地為祖先之地不可侵犯為由禁止漢族人移居于此。山東由于當地人口眾多,耕地有限等,因此早已秘密潛入此處采參、狩獵、伐木、造房,開墾者日益增多,待到滿洲人發現大勢已無可挽回時,不得已解除禁令。此后,越來越來的山東人和山西人移民此地,滿洲也逐漸變為漢族的居住地。如鳥居龍藏所言,居住滿洲者并非是以前居住在此的民族,而是近代由山東移民至此的漢族人,他探訪的滿洲實為漢族的滿洲。
鳥居龍藏在書中尤為側重對于渤海、遼、金三國的考古,他通過考察三國之上京來塑造對歷史的想象。渤海之上京在寧安的南牡丹江畔,都城選址和形貌與唐的都城頗為相似。渤海古城坐落于巨大的玄武巖石之上,城墻先用土筑再以玄武巖石打造表面,由外部觀看宛如石城,然而當時石塊多被運往市街,早已看不到滿墻的石磚。在城內北門附近的五層樓故址發現不少古瓦、古磚、鐵盔等,鳥居龍藏發現此處的瓦片和西伯利亞某古城的瓦片相類似,頗為關注。古城的中心地在北門,南門處有寺院的遺跡,鳥居龍藏對王宮舊址的石礎和寺院舊址的石塔最為看重。他借助城內石礎、池沼、瓦片、寺院、佛像等遺跡來推測渤海國當時的情況。遼上京位于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城壁由土磚砌成,規模大,城門多。城內多建有宮殿和寺院,可見散落的瓦片、石臼等,城外建有磚塔。錦州、遼陽和鐵嶺等地的磚塔多為遼代寺院的遺址,可見遼上京昔日的盛大。鳥居龍藏又由上京發現的大日如來像得知遼在當時推行密教信仰。契丹人歷來視薩滿教為固定信仰,但由于與中國、朝鮮、渤海等國的接觸輸入了佛教,尤以密教最為重視。鳥居龍藏在遼陽與鐵嶺等地所見的磚塔皆為遼之遺物,可見當時佛教之盛行、藝術之發達。金上京則分為南北二城,北為古城,南為新城。金上京的城墻砌以土磚,待鳥居龍藏進城發現城內已不見皇宮、石塔、寺院等遺跡,古城內遺物多被運往他處。由發現的一對造車用的簞瓢型石可知當時盛行造車,此城出產的瓦片與渤海古城的瓦片完全不同,這也引起了鳥居龍藏的注意。金上京的城內常發掘出薩滿教的銅人、瓦片、陶器破片、古錢等,此地出土甚多的古鏡為薩滿教巫師祭祀時所使用的腰鏡,因此可知薩滿教在當時的盛行。另外,此處又發現金屬十字架,暗示了基督教傳播的痕跡。
以鳥居龍藏看來,金不僅模仿漢族的文化還受到遼文化的影響,沿襲了遼在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傳統。相較于遼上京的盛大,金上京相形見絀,二者的文化高度可見一斑。鳥居龍藏在遼金時代的古城內探查瓦磚、陶器、古錢等物,對兩代出產的鬼瓦最感興趣。鬼瓦分為新舊兩種,據此可知它的年代。舊瓦產于遼代具有遼代的特征且樣式更佳,新瓦產于金代,但工藝卻遠不及遼代。此外,他發現遼代多磚塔,遼上京等多處建有大型磚塔,金上京則沒有磚塔,此即遼文化更為繁盛的佐證之一。
滿洲的歷史脫離不開對漢族的書寫,漢族在這片土地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鳥居龍藏記錄的漢族在南滿洲的遺跡大致可分為墓所和住所兩類。墓所中留有形狀功能各異的石棺、石槨、磚棺、貝殼棺等,由住所中發掘出的器物、錢幣等遺物則可窺見當時的生活狀態。古墓中的遺物更為豐富,如多種形態的獸镮、壺瓶、器皿、缽、椀、盆、鼎、登、爐、模造品、瓦當等土器和陶器,銅器類則有銅缽、銅鏡、金具裝飾物、首飾、腕環指環、插垂頭、武器等。此外還記有玉制和玻璃制的裝飾品、鐵器、骨制玩具、朱及紙、古錢、人骨等遺物。鳥居龍藏通過對比不同地區的發掘物發現當時土器和瓦器的使用多于銅器,這是出于經濟上的考量,銅器為上流社會和宗教儀式所使用,普通百姓則使用木器土器等。他還認為“滿洲之遺跡遺物絕非遼東所獨有者,實當時廣行于漢族間之一般風俗也。又可知此種遺跡遺物,不僅以上諸地有之,中國各省必皆有之。”[5]進而確定滿洲的某些遺跡是漢族留下的。除了《滿蒙古跡考》中所記載的考古成果,鳥居龍藏還陸續研究了遼代畫像石、林西遼慶陵、醫巫閭山東丹王陵等遺跡。
鳥居龍藏在《滿蒙古跡考》中對研究對象進行了詳細的記錄,他結合史料分析與實地調查的研究方式,借助人類學、考古學、地理學等學科間的融合,多角度綜合性地考察研究對象。書中對考古描繪的成分居多,內容扎實,注重細節,行文簡潔流暢,相較于學術著作而言,本書田野游記的風格更盛。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當時的工作規模較小而且研究主要側重遺物的尋找和描述,作者并沒有將研究內容上升到理論的層面,他更多的是如實地描述而沒有透過對象論述其背后的一套社會組織與關系,其中的民族關系和宗教變遷等內容存在很深的挖掘空間。相較于史祿國注重田野調查和理論建構以及凌純聲側重歷史分析的治學方式,鳥居龍藏在理論提煉中略有欠缺,但本書的學術價值仍是不容忽視的。鳥居龍藏作為中國東北地區近代考古活動和民族志調查的拓荒者,反駁了當時世人皆以為滿蒙之地無歷史文化的論斷。他通過長時間、多地域的實地調查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資料,他的研究具有著實證主義的風格,這對當時推崇書齋研究的學術傳統產生了極大的開創性和示范性,鼓勵了更多學者轉向田野。他的人類學研究滲入了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民俗學等內容,雖然理論性較弱,但在彼時實屬可貴,樹立了獨特的研究風格。
三、后記
由鳥居龍藏的考察可知人類學的東北研究開啟時間并不遲于西南和東南,卻鮮為后人關注,遠沒有達到后兩者所獲得的公認性的成果。相較于宗族之于東南、斗雞之于巴厘島等充滿地方色彩的記錄,東北似乎缺少能代表本地社會與文化的典型性描述。與已形成研究范式的地域相比,東北也具有特殊的歷史內涵和地方性知識,同樣具有研究潛力。東北這個詞語本身就經歷了多種變遷,最早傳說在遠古時代,舜帝冊封天下十二座名山,位于醫巫閭山以北的地方都稱作東北,而這只是模糊的地理方向的概念。后遠古中國被分為九州,東北劃歸到幽州境內,肅慎古國是東北地區最早的起源。在遼統一北方后,東北被看作為一個區域,從遼史中可以知曉在遼代東北已被引用為軍政建制名稱并廣為使用。在金代,東北地區則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用東北取代清發祥地“滿洲”,現今的東北則指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和內蒙古東部。東北的概念就是在歷史中被不斷改寫,在這個書寫的過程中社會的變遷得以體現,東北的地域獨特性也越發彰顯。人類學的東北研究離不開對東北歷史脈絡的梳理,尤其應重視鳥居龍藏、史祿國和凌純聲等中外學者的資料。研究民族志材料的對象需要聯系其背后的歷史條件,理清它與周遭對象的關系進而明確它在當下又被塑造成怎樣的現實。
東北雖處于“邊緣”卻不是獨立隔絕的,歷史的沿襲、自身的因素與外界的接觸共同塑造了東北的獨特性和一般性,這個變動的過程也將持續存在。人類學的東北研究目前還未形式研究范式,而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需要借鑒中外不同的研究方法與民族志材料,從中尋找到適合于本地區的研究取向。鳥居龍藏注重田野調查和歷史考古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種方向,例如他通過儀式器具來推測當時東北地區的宗教情況,從當時的交通狀況聯系到中日民間的交往等等。以《滿蒙古跡考》中展現的東北為例,對比它與其他地域不難發現東北自身的歷史軌跡與文化特性,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東北與外界的聯系并明確它在整體中處于何等位置。鳥居龍藏作為“他者”具有跨文化的觀察視角,為本土學者更深入地認識東北提供了新的角度。人類學的東北研究根植于學術史的回顧,對于民族志的運用須置于歷史的脈絡中,在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中尋找研究地方性知識的靈感。

泥模藝術——陳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