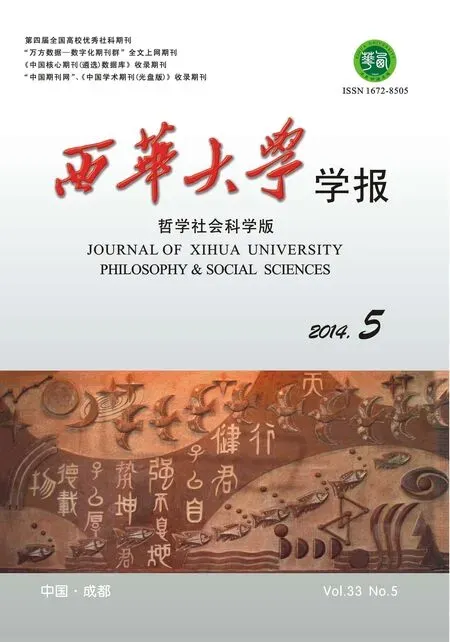關(guān)于實現(xiàn)翻譯教學中“學”與“術(shù)”有機統(tǒng)一的思考
龔小萍 陳 達
(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 四川成都 610039)
翻譯教學中的“學”、“術(shù)”問題是指翻譯教學中理論與實踐的關(guān)系問題,重點是翻譯教學是否需要理論的問題。翻譯教學從重“術(shù)”輕“學”的傳統(tǒng)轉(zhuǎn)向重“學”輕“術(shù)”的學術(shù)型翻譯研究生培養(yǎng),如今又從重“學”輕“術(shù)”的傳統(tǒng)回歸重“術(shù)”輕“學”的應(yīng)用型翻譯碩士培養(yǎng)。在顧此失彼的“學”“術(shù)”選擇中,翻譯教學始終未能找到“學”與“術(shù)”間的平衡點。學者們普遍認為,重“學”輕“術(shù)”的翻譯教學模式不太成功,培養(yǎng)出的學生雖腳跨中西、學貫古今譯論,卻難以擔當翻譯市場重任。如今,重“術(shù)”輕“學”的翻譯碩士培養(yǎng)模式就一定能在天賦的支撐下,在勤學苦練中,培養(yǎng)出適應(yīng)市場的高級翻譯人才?這個問題不能留待后人評說,它迫在眉睫,急需回答。
一、翻譯教學應(yīng)注重“學”與“術(shù)”的有機統(tǒng)一
翻譯教學有兩個目標,培養(yǎng)翻譯理論人才和翻譯實踐人才。這兩類人才的培養(yǎng)都離不開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
1.翻譯課堂教學環(huán)節(jié)應(yīng)注重“學”、“術(shù)”的有機統(tǒng)一
撇開翻譯實踐,翻譯教學難以培養(yǎng)出真正關(guān)心和切實解決中國當下翻譯實踐問題的翻譯理論人才。純翻譯理論教學可以讓學生知曉英美德法等西方以及中國傳統(tǒng)譯論,卻無法讓學生看清這些翻譯理論與其自身翻譯實踐以及中國當下翻譯實踐的關(guān)系。這樣的翻譯理論教學可以培養(yǎng)出大批的譯論“學舌”者,卻培養(yǎng)不出中國譯論研究的創(chuàng)新人才,醫(yī)治不了中國譯論的“失語癥”,實現(xiàn)不了與西方譯論接軌、對話的愿望。只有在譯論教學中加入翻譯實踐基礎(chǔ),學生才知道譯論從何而來,解決了什么樣的翻譯問題,對當下中國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有什么啟發(fā)。
撇開翻譯理論,翻譯教學也難以培養(yǎng)出應(yīng)用型翻譯碩士,盡管翻譯碩士的培養(yǎng)目標就是“市場所需的應(yīng)用型高級翻譯人才”。在人們(翻譯教師和學生)的經(jīng)驗常識中,翻譯是神而明之的天賦,是反復(fù)訓練即可獲取的技巧,與翻譯理論似乎無關(guān)。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大家林紓則成為翻譯理論無用論者最厲害的武器。林紓不僅不懂翻譯理論而且不懂外語,但他卻是翻譯名家。事實上,林紓及類似的成功譯者不僅否認了翻譯理論的作用,甚至否認了翻譯教學的作用,似乎翻譯教學沒有存在的必要。但,翻譯教學確實存在,而且規(guī)模越來越大。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都面臨一個選擇:“要么翻譯,要么覆滅”(TRANSLATE OR DIE)[1]2。少數(shù)幾個林紓似的翻譯天才已無法滿足各行各業(yè)對翻譯職業(yè)化的需求,小范圍直接的經(jīng)驗分享也不能滿足社會的翻譯需求。傳統(tǒng)師徒制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由課堂培養(yǎng)模式所取代。經(jīng)驗感悟式的翻譯教學必將走上有理論指導的翻譯教學。
學生對“老師覺得”、“老師認為”的權(quán)威教學方式已不太滿意,他們希望知道為什么如此選擇。在翻譯碩士第一堂“翻譯基礎(chǔ)”課上,筆者給學生一些翻譯材料進行翻譯,翻譯完后,由學生們自己對譯文進行評價。他們的觀點在某些譯文上高度一致,在某些譯文上又分歧頗大。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就會追問:你們欣賞和不欣賞某種譯文的標準是什么?學生往往給出“我覺得”、“我認為”的回答。有少數(shù)學生會用“信、達、雅”的標準來評判。這時,筆者就故意選擇一篇較差的譯文,對其大加贊揚,也給出“老師覺得”、“老師認為”的解釋。學生對此面面相覷,卻又無可奈何。于是,對譯文的評判就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眾說紛紜中。筆者想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學生,沒有翻譯理論指導的翻譯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沒有理論指導的譯評是亂評,是評論者的主觀印象。翻譯教師唯有“以理服人”地評判學生譯文,才能讓學生在吸取成功翻譯經(jīng)驗和規(guī)避失敗翻譯教訓中不斷地進行自覺選擇,以提高翻譯水平。
另外,只要一提起翻譯標準,大多數(shù)學生總會認定嚴復(fù)先生的“信、達、雅”標準。待學了中西翻譯理論之后,他們又興致勃勃地認定翻譯的多元標準。當問及翻譯的多元標準與翻譯的無標準有何差異時,他們又不甚了了。翻譯標準給老師和學生造成的理論混亂必定會走向?qū)嵺`的混亂。筆者曾讓學生將下面中文句子譯成英文,并且事先告訴他們,這句話是某大學校長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的發(fā)言稿標題,目的是要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該校合作、交流。
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的使者(原文)
Universities:Messengers for Sino-US Cross-Cultural Exchange(學生譯文)
Universities:Platforms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教師譯文)
學生不約而同地按照“信、達、雅”標準做出了相似的翻譯,準確地再現(xiàn)了原文信息和語言形式。可他們的譯文并沒受到筆者的認可,相反,筆者告訴他們,這樣的譯文不僅得不到市場認可,而且可能賠錢。學生驚愕!于是,筆者拋出自己的譯文并且分析說,從原文和譯文的對比效果來看,你們的譯文明顯更忠實,但為何你們的譯文會是糟糕的譯文呢?這是因為原文本身有瑕疵,“信”于原文的譯文當然就是瑕疵譯文了。翻譯消費者如果使用該譯文沒有達到預(yù)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譯者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事實來講,大學并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人文交流的使者,這種說法太過崇美;從表達來看,大學并不穿梭在兩國之間,難稱“使者”;從使用效果來看,該校長剛說完題目,德國、日本、加拿大的專家、學者有可能紛紛離場,因為大學只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使者,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在這個場合的出現(xiàn)仿佛是多余的。在這種情況下,譯者不僅要翻譯而且要糾錯。現(xiàn)實生活中的翻譯不僅有經(jīng)典文本也有瑕疵文本,“信、達、雅”標準顯然不適合現(xiàn)實生活中的瑕疵文本翻譯。聽了筆者的分析,學生恍然大悟。瑕疵文本是難以達到使用目的的不完善文本,是翻譯從業(yè)者在真實的翻譯生活中要遇到的情況,忠實原文還是改譯成為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如果沒有文化翻譯理論的指導,教師和學生勢必根據(jù)嚴復(fù)的“信、達、雅”來翻譯,不敢越雷池半步,這表明忠實也會給譯者帶來麻煩。
離開了翻譯實踐,翻譯理論教師能培養(yǎng)出有譯論知識的學生卻培養(yǎng)不出有理論素養(yǎng)的翻譯研究人才。離開了翻譯理論,或者對翻譯理論一知半解,翻譯實踐教師無法解釋翻譯過程中的諸多選擇,無法令學生信服,給學生以真正意義上的啟發(fā)。翻譯教師的作用就是讓學生由自發(fā)盲目的選擇變成自覺理性的選擇。翻譯不是一種高精尖的活動,稍微有兩種語言知識的人都能翻譯,但翻譯選擇有高有低,教師是要幫助學生做出更好的選擇。林紓不是譯論家,但他以天生的直覺和悟性做出了較好的翻譯選擇。而我們不能因為有像他那樣的翻譯天才就否認翻譯理論的重要性,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
2.考試測評環(huán)節(jié)應(yīng)注重“學”、“術(shù)”的有機統(tǒng)一
翻譯理論考試的目的是要檢查學生對譯論的掌握程度。對譯論的掌握不僅僅是指對譯論內(nèi)容的熟悉,還包括如何用譯論來解釋和解決翻譯實踐的問題。翻譯考試的目的是要考查學生的翻譯能力。大多數(shù)時候,更好的翻譯選擇都靠天賦、直覺和頓悟。一旦翻譯難題出現(xiàn),翻譯理論的作用就得到凸顯,良好的理論素養(yǎng)就能保證更好的翻譯選擇。
現(xiàn)在,翻譯考試的內(nèi)容應(yīng)該從文學文本延伸至政治、經(jīng)濟、商貿(mào)、法律、醫(yī)藥、日常交流等文本,從目的明確、邏輯縝密、字斟句酌的經(jīng)典文本擴展至思維紊亂、語病百出但使用目的十分明確的非經(jīng)典文本。顯然,僅僅局限于經(jīng)典文學文本的翻譯考試已經(jīng)不能滿足翻譯市場對翻譯人才培養(yǎng)的需求,盡管其依然十分重要。學生在課堂、考試中只知有經(jīng)典文學文本翻譯,難以應(yīng)用“信、達、雅”標準應(yīng)對千變?nèi)f化的原語文本。
再有,對于同一原語文本,譯者可能有不同的翻譯方式,這是古今中外各種譯論向譯界展示的一幅圖景。無論是翻譯教師還是學生都知道有“信、達、雅”翻譯、有“等值”與“等效”翻譯、有“目的論”翻譯、有“后殖民主義”翻譯、有“女性主義”翻譯等等。如果翻譯教師沒有在答題要求中明確限定某種翻譯標準的話,學生有理由選擇任何一種他認為恰當?shù)姆g方法,而翻譯教師不能只用“信、達、雅”標準來評判。現(xiàn)實情況是,翻譯答題要求中沒有限定標準,翻譯教師閱卷時卻默認“信、達、雅”標準。通常情況下,這種做法不會出現(xiàn)什么問題,考試題目都是經(jīng)典文本,學生和老師都默認“信、達、雅”標準。問題在于,翻譯考試不能一直把非經(jīng)典文本擋在試卷外,畢竟,非經(jīng)典文本的翻譯日益重要。況且,即使如《圣經(jīng)》般經(jīng)典文本的翻譯,不同時代的譯者也有不同的翻譯選擇。根茨勒(Gentzler)就指出,奈達發(fā)展翻譯科學的動因,就在于他不喜歡19世紀翻譯方法中的古典復(fù)興,即強調(diào)技術(shù)精確、注重語言形式和專注直譯意義的《圣經(jīng)》翻譯方法。看來,還沒有一種翻譯方法可以囊括任何時代的《圣經(jīng)》經(jīng)典文本翻譯,漢外翻譯教師又豈能用“信達雅”來框定一切經(jīng)典文本翻譯,甚至非經(jīng)典文本翻譯?
理論與實踐互動在翻譯考試測評階段的重要性體現(xiàn)在:學生應(yīng)用譯論來解釋、解決翻譯問題或在譯論指導下進行更好的翻譯選擇;教師要根據(jù)具體翻譯材料在答題要求中厘定翻譯標準,讓學生按照所給標準翻譯,然后按照該標準閱卷。
3.學位論文環(huán)節(jié)應(yīng)注重“學”、“術(shù)”的有機統(tǒng)一
論文的生命在于創(chuàng)新,沒有創(chuàng)新就沒有論文,它要么充實、發(fā)展了理論,要么解決了實踐中的問題。如果論文不能帶來理論或?qū)嵺`知識增量,它的價值就微乎其微。學術(shù)型翻譯研究生要在發(fā)現(xiàn)、解決翻譯實踐問題中去充實、發(fā)展譯論;應(yīng)用型翻譯研究生要論述如何在理論指導下才能進行更好的翻譯選擇。理論與實踐在這兩類學位論文中彼此依存、相互促進。
盡管翻譯碩士培養(yǎng)與職業(yè)化、應(yīng)用型、專業(yè)化目標緊密相聯(lián),但它未曾須臾離開翻譯理論。依據(jù)國務(wù)院學位辦下發(fā)的“全國翻譯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性培養(yǎng)方案”,MTI學位論文有項目、實驗報告、研究論文三種方案。學生完成項目的過程中要進行諸多選擇,沒有理論指導的選擇是盲目的,即使準確的選擇也不過是“瞎貓碰見死耗子”,其成功經(jīng)驗不可以復(fù)制,這樣形成的研究報告對其他譯者或理論研究者啟發(fā)意義甚微。學生對口、筆譯某個環(huán)節(jié)展開實驗,發(fā)現(xiàn)沒有理論指導的實驗報告不過是一堆無用的材料而已。翻譯理論在第三種方案中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穆雷教授認為現(xiàn)有的翻譯碩士論文仍沿用傳統(tǒng)學術(shù)型學位論文模式,不僅與翻譯行業(yè)的實際操作脫節(jié),而且違背了MTI教育設(shè)置的初衷,她將原來的三種方案調(diào)整為重要崗位的實習報告、翻譯實踐報告、翻譯實驗報告和翻譯調(diào)研報告四種方案[2]。她的MTI學位論文四種方案更有利于引導學生走向職業(yè)化、應(yīng)用型、專業(yè)化,更符合翻譯碩士學位設(shè)置的初衷。不過,學生要做好這四種方案的學位論文,離開了翻譯理論也是不行的。項目經(jīng)理實習報告若沒有翻譯“外圍”研究的理論知識,其成本、周期等的預(yù)算就難以準確,其質(zhì)量的評判難以客觀,其報告也難稱科學、系統(tǒng)。沒有理論支撐的項目翻譯實習報告不過是一堆支離破碎的主觀材料。每次正確選擇沒有理由,每次錯誤選擇沒有原因。沒有理論依據(jù)的審校實習報告不過是個人價值判斷而已,質(zhì)量好壞的把關(guān)沒有統(tǒng)一標準,錯誤糾正難以令人信服。沒有理論指導的翻譯調(diào)研報告的結(jié)論可能是偏頗的,建議可能是經(jīng)驗性的感悟。另外,作為譯者或參與翻譯實踐的學生不僅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需要為中國翻譯理論構(gòu)建提出實踐中的新問題,提供最直接的動力。即使是偉大的翻譯家,若沒有理論指導,也不能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地培養(yǎng)各行各業(yè)需要的翻譯人才,他只能轉(zhuǎn)向傳統(tǒng)的手工作坊式的培養(yǎng)模式,在小范圍內(nèi)為學生傳金送寶。這顯然已無法滿足當今翻譯市場對翻譯人才的需求。
看來,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構(gòu)成了翻譯教學的完整圖景。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在課堂教學、作業(yè)批改(其與考試測評對翻譯理論的需求類似,因而本文未加論述)、考試測評以及學位論文等各教學環(huán)節(jié)相互促進。可以說,翻譯實踐能力和翻譯理論素養(yǎng)是翻譯教師教學能力的兩個指針。對于任何一次翻譯選擇,學生可以憑直覺和感悟來判斷,而翻譯教師卻需要在理論指導下進行。對于教師的翻譯選擇,學生可能會因信奉權(quán)威而停止追問“為什么如此選擇”,但教師得為這種追問做準備,甚至主動告訴學生選擇的理由。唯有這樣,才能達到翻譯教學的目的,否則,學生的翻譯選擇永遠停留在“我覺得”、“我認為”的主觀判斷和個人好惡中。這樣的教和學與不教不學沒有任何區(qū)別。
二、在現(xiàn)實的翻譯教學中存在“學”與“術(shù)”分離的情況
在翻譯教學中,“學”與“術(shù)”的關(guān)系問題始終是個難題。勞隴先生就曾提到,1985年王佐良先生召集首都各高等院校翻譯課教師開會,有同志在會上宣稱:翻譯教學只需要實踐不需要理論,教理論是外行話[3]647。翻譯教學中這種重“術(shù)”輕“學”的做法頗為流行。盧思源教授批評說,有些人認為“翻譯無理論”,有些翻譯教師“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招牌,卻行著只談實踐不談理論之實[4]122。他還分析說,由于我國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存在劃一性、片面性和非國際性思想弊端,“致使我國的翻譯教學與研究一直未能很好地引導學生和翻譯從業(yè)者樹立正確的翻譯觀”[4]116-119。楊自儉教授認為,中國學科意識很淡漠,分類先有“道術(shù)”,后有“學術(shù)”,重術(shù)輕學[5]。
重“術(shù)”輕“學”的翻譯教學不利于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曹明倫教授認為,合格譯者要自覺接受理論的指導,否則就是盲目跟風,沒有恰當理論指導難以成為合格譯者[6]前言。楊自儉教授語重心長地說:“我勸從事各類翻譯的同志,抽出部分精力對你的實際工作從理論上進行總結(jié)和探索,這不僅能提高你的理論思維能力,而且會使你的實際工作更有成效。恐怕這也是培養(yǎng)理論人才最可靠最有效的途徑”[7]4。
在學術(shù)型翻譯研究生培養(yǎng)中,又形成了重“學”輕“術(shù)”的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難以培養(yǎng)出市場所需的應(yīng)用型高級翻譯人才[8]序。
在翻譯需求不斷攀升的同時,作為主要培養(yǎng)翻譯人員的高校,卻日益暴露出其在翻譯教學與實踐之間的脫節(jié)問題。畢業(yè)生翻譯技能不扎實,知識面狹窄,往往難以勝任不同專業(yè)領(lǐng)域所需的高層次翻譯工作,致使翻譯領(lǐng)域特別是高級翻譯領(lǐng)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能滿足目前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需要。
為了解決翻譯人才的這種供需矛盾,適應(yīng)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事業(yè)的需求,培養(yǎng)高層次、應(yīng)用型高級翻譯專門人才,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于2007年1月23日第23次會議審議通過設(shè)置翻譯碩士專業(yè)學位(MTI)。此后,“學術(shù)型”和“應(yīng)用型”成為翻譯人才培養(yǎng)的兩種模式,前者以培養(yǎng)學生學術(shù)研究能力為目標,而后者以培養(yǎng)學生翻譯實踐能力為目標。在翻譯實踐領(lǐng)域,理論無用論再次高漲,翻譯理論在翻譯碩士的培養(yǎng)中再次被邊緣化。筆者在“2012中國翻譯職業(yè)交流大會”上頻頻聽到理論無用論的聲音。翻譯的“學”、“術(shù)”問題今天還嚴重困擾著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有學者指出[9]73:關(guān)于如何真正實現(xiàn)MTI與傳統(tǒng)學術(shù)型碩士差異性培養(yǎng)的問題。大家普遍認為,目前少數(shù)院校的MTI課程設(shè)置和人才培養(yǎng)理念仍然不能與傳統(tǒng)的學術(shù)型碩士的課程設(shè)置和培養(yǎng)理念做到清晰明確的區(qū)分,這造成兩種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近似化,在就業(yè)或進一步深造時,給用人單位和學生本人帶來困惑與困難。
當前,翻譯教學通常體現(xiàn)出“學”、“術(shù)”并行的趨勢,如,無論是本科還是研究生課程設(shè)置中都有“翻譯理論與實踐”這門課,且翻譯教材的編寫也涵蓋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兩個方面。不過,教材全面介紹了中西各種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但理論篇與實踐篇互不相涉。教師向?qū)W生傳授中西翻譯理論與翻譯技巧兩個方面的知識,卻較少引導學生運用翻譯理論解決實際翻譯問題。因此,學生學習了“翻譯理論與實踐”這門課后,能夠?qū)χ形鞣g理論如數(shù)家珍,能夠?qū)Ψg技巧熟能生巧,但對如何在翻譯理論指導下進行翻譯技巧的選擇始終茫然,以致于懷疑翻譯理論學習的意義。既然不學翻譯理論也能學好翻譯技巧,學了翻譯理論又不能提高翻譯技巧,翻譯理論學習有什么意義?這是善于思考的學生關(guān)于“翻譯理論與實踐”這門課程向翻譯教師提出的一個難題。
翻譯教學中的“學”與“術(shù)”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翻譯“學術(shù)”。在翻譯教師的思想認識中,有重“學”輕“術(shù)”和重“術(shù)”輕“學”的現(xiàn)象。在翻譯師生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中,在教材的編寫中,翻譯的“學”與“術(shù)”也處于一種貌合神離的狀態(tài),有二者的相關(guān)知識卻鮮有二者的結(jié)合應(yīng)用。
三、在翻譯教學中實現(xiàn)“學”與“術(shù)”有機統(tǒng)一的基本思路
翻譯理論與實踐在翻譯教學各環(huán)節(jié)的共生性毋庸置疑,而翻譯教學中“學”、“術(shù)”分離的現(xiàn)狀又顯而易見。翻譯教學離不開翻譯理論,中國翻譯學不乏翻譯理論,其囊括古今中外翻譯理論。翻譯教學緣何拒斥這些寸步難離且又唾手可得的翻譯理論?
翻譯教學不是沒有譯論指導,而是在眾多譯論中不知接受何家何派的指導。與其說翻譯教學無理論指導,不愿意接受翻譯理論指導,不如說翻譯教學在理論眾說紛紜中無所適從。通常,無所適從的翻譯教學對待翻譯理論有兩種態(tài)度:盲目跟隨譯論和譯論無用論。前者總是在翻譯教學中追隨最新最時髦的譯論。當學界言必稱嚴復(fù),“信達雅”則是翻譯教學的金科玉律;當學界言必稱奈達,“等值”、“等效”、“功能對等”即成為翻譯教學的不變定律;當學界言必稱“后現(xiàn)代”、“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各種操縱、改寫又成為翻譯教學的不變公理。當這些矛盾沖突的譯論并置,譯論多元研究蔚然成風,翻譯教學不得不暫停追隨的腳步,茫然四顧。譯論研究可以跨學科、可以多元,但翻譯教學必須在多元中選擇,教會學生選擇。如果翻譯教學沒有教會學生運用翻譯理論指導實踐,他們就會隨心所欲地選擇。隨意對待譯論的結(jié)果便是,譯者可能會生產(chǎn)出“胡譯皆可”、“唯利是圖”和“喪心病狂”的譯文,這些譯文都是受不同譯論指導的結(jié)果,忠實有忠實的好,叛逆有叛逆的妙。翻譯理論沒有讓翻譯教學更理性,反而更盲目,以致于譯論無用論甚囂塵上。
因此,翻譯教學不是不需要翻譯理論,不是不愿意使用翻譯理論,更不是無翻譯理論可用,而是不知道如何使用翻譯理論。面對翻譯教學“學”、“術(shù)”分離的現(xiàn)狀,理論研究者不能一味指責教學雙方理論意識淡薄,而應(yīng)更多探索正確使用譯論的方法。沿此思路,翻譯教學雙方需從以下兩個相反的方向努力:
一方面,翻譯教學應(yīng)由“學”指導“術(shù)”。如前所述,翻譯教學不是不愿意使用譯論,而是不知如何使用譯論,尤其是多元沖突的譯論。翻譯被認為是宇宙間最復(fù)雜的事物,它涉及作者、譯者、讀者、原文、譯文、原語文化、譯入語文化,甚至包括權(quán)力、性別、翻譯委托人、翻譯使用者諸因素。事實上,這些因素存在于一切翻譯活動中,但它們不會同時等量地出現(xiàn)在翻譯思想家和譯論家的研究視野中。不同時代的主流翻譯問題會凸顯其中的某個或某些因素。時而,作者在翻譯諸因素中脫穎而出,作者中心論流行;時而,譯者在翻譯諸因素中鶴立雞群,譯者中心論勢強;時而,讀者在翻譯諸因素中與眾不同,讀者中心論來襲;時而,文本外因素在翻譯諸因素中后來居上,翻譯外圍研究遇熱等等。筆者在此無法一一贅述這些翻譯研究中心論,也無法預(yù)測新的翻譯研究中心論。于是,這些共時性存在的翻譯諸因素就跟隨不同譯論凸顯不同因素在國人面前歷時性展開,出現(xiàn)一個“中心論”取代另一個“中心論”的假象,仿佛新論實現(xiàn)了對舊論的終結(jié)。
多元譯論僅僅是凸顯了不同翻譯因素的譯論并置,而不是后來譯論對先前譯論的超越或終結(jié)。如,西方語言學翻譯理論敲響了嚴復(fù)“信、達、雅”的喪鐘或西方文化翻譯理論將語言學翻譯理論趕入了死胡同。翻譯中某些因素的前景化必然意味著其它因素的背景化,處于背景中的翻譯因素雖不夠醒目但并未消失。這種認識會讓翻譯教學主動關(guān)注某個譯論如何通過前景化某些翻譯因素和背景化某些翻譯因素去應(yīng)對當時的翻譯問題,也會讓翻譯教學關(guān)注到某個時代處于背景化的翻譯因素會在別的時代凸顯出來,更會讓翻譯教學關(guān)注到目前這個時代需要前景化翻譯中的何種因素來服務(wù)于該時代的主流翻譯問題,處理好該時代的非主流翻譯問題。另外,多元譯論不可能同時前景化,不同時代的不同主流翻譯問題決定何種譯論被前景化,與前景化相對的是那些處于背景化中的譯論主張。翻譯教師要關(guān)注被當下時代前景化的譯論,主動接受該譯論的指導,分析其前景化和背景化的翻譯因素,將其用于教學中,實現(xiàn)“譯者忠實對象的多元互動”[10],培養(yǎng)出符合當下時代需要的翻譯人才。
另一方面,翻譯教學應(yīng)由“術(shù)”帶動“學”。翻譯教學不僅要培養(yǎng)翻譯實踐人才,還要培養(yǎng)翻譯理論人才,推動學術(shù)創(chuàng)新。翻譯碩士論文形式雖有變化,但其寫作目的也是要給他人的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有所啟發(fā),否則論文要求就沒有意義。創(chuàng)新翻譯理論,治愈中國譯論“失語癥”,是學界的共同心聲。譯論創(chuàng)新不是對傳統(tǒng)譯論和西方譯論的重新拼接組合,而是在解決當下時代翻譯實踐新問題中產(chǎn)生。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翻譯新問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實踐有與中國救亡圖存時代以及其它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翻譯實踐不同的新問題。“術(shù)”的探討會將這個獨特的翻譯新問題帶進翻譯課堂,在解決這個翻譯新問題時,某個翻譯理論成為我們關(guān)注的對象。因為“唯有當下的一切才能使以往的歷史重新復(fù)活,才能使過去史變成當代史。因為盡管過去的歷史中有無數(shù)的史實,但只有我們心中的問題能使我們真正地關(guān)注某一段歷史或某一種思想,換句話說,是當下的生活使得我們的過去得以再生”[11]61。這個譯論在幫助解決當下翻譯問題中的現(xiàn)代化或本土化,得到修正和發(fā)展,實現(xiàn)譯論的創(chuàng)新。
翻譯教學接受譯論的指導并在解決當下翻譯問題中帶動譯論創(chuàng)新,這就是“學”、“術(shù)”互動的翻譯教學,即翻譯教學中的“學術(shù)”。許淵沖教授的實踐經(jīng)驗詮釋了這種“學”、“術(shù)”互動式翻譯教學的有效性,他“以自己的文學翻譯理論指導自己的翻譯實踐,又借大量的翻譯實踐來充實、豐富自己的翻譯理論,終于結(jié)晶出‘美化之藝術(shù),創(chuàng)優(yōu)似競賽’的‘許氏譯論’”[12]。
四、結(jié)語
翻譯教學實際上是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在課堂環(huán)境中的結(jié)合。有“學”無“術(shù)”的翻譯教學可以給學生的頭腦中塞滿古今中外各種譯論,讓他們鸚鵡學舌般言說這些譯論,但無法進行譯論創(chuàng)新,難以完成譯論構(gòu)建的當代使命,因為這樣的翻譯教學隔離了催生新譯論的翻譯新問題。有“術(shù)”無“學”的翻譯教學可以給學生的頭腦中塞滿各種各樣的翻譯技巧,讓他們在反復(fù)練習中熟悉翻譯選擇。這可以在有限的領(lǐng)域培養(yǎng)出翻譯“匠”,卻難以培養(yǎng)出目標明確、選擇理性的優(yōu)秀譯者或翻譯家。因為學習翻譯理論就是在學習譯者如何運用翻譯選擇去應(yīng)對翻譯的時代課題,為譯者解決自己當前的翻譯問題提供參照。因此,翻譯教學應(yīng)主張“學”、“術(shù)”互動。
“學”、“術(shù)”互動的翻譯教學并非沒有偏重,結(jié)合學術(shù)型和應(yīng)用型翻譯研究生的培養(yǎng)目標,在“學”、“術(shù)”互動的前提下重提重“學”輕“術(shù)”或重“術(shù)”輕“學”比較恰切。這里的“重”或“輕”不是過分注重或過分輕視的意思,而是有所側(cè)重。
[1] Engle,Paul,Hualing Nieh Engle Writing from the World II[M].Iowa City:InternationalBooksand the University ofIowa Press,1985.
[2] 穆雷.翻譯碩士專業(yè)學位論文模式探討[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1(1).
[3] 勞隴.翻譯教學的出路[C]//楊自儉,劉學云.翻譯新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4] 盧思源,吳啟金.展望21世紀的翻譯教學與研究[C]//嚴辰松.中國翻譯研究論文精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5] 楊自儉.學術(shù)研究應(yīng)是目的,還是該為手段?[J].宜春學院學報,2008(1).
[6] 曹明倫.英漢翻譯實踐與評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7] 楊自儉.論我國近期的翻譯理論研究[C]//楊自儉,劉學云.翻譯新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8] 王宏印.中國文化典籍英譯[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9] 錢多秀,楊英姿.北京地區(qū)翻譯碩士專業(yè)學位(MTI)教育:經(jīng)驗、反思與建議[J].中國翻譯,2013(2).
[10] 龔小萍.譯者忠實對象的多元互動[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
[11] 李雪濤.孔子的世界性意義— —衛(wèi)禮賢對孔子的闡釋及其對我們今天的啟示[J].讀書,2012(8).
[12] 張智中.許淵沖的小說翻譯[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