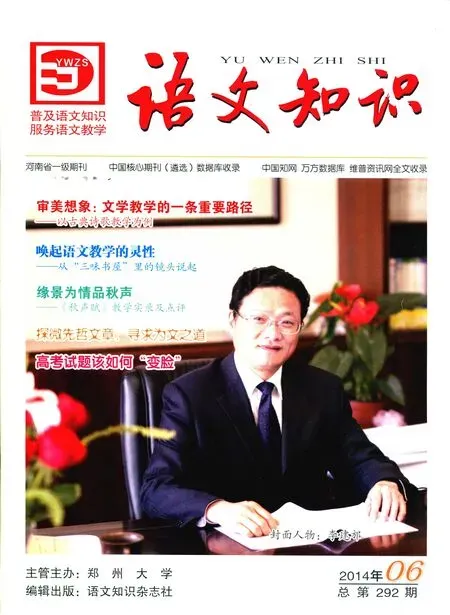論老舍文學語言的“方言化”
◆ 鄭州大學文學院 陳 晨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老舍的成就不僅在于他作品中文化思想的豐富與深刻,還在于他在語言運用方面的非凡成就。他被譽為“語言藝術大師”,代表了“五四”以來現代白話小說在語言藝術上的高峰。這也是老舍的經典作品成為中、小學語文教材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論及老舍的文學語言,“方言化”是其突出的特點之一。正如冰心所說:“他的傳神生動的語言,充分地表現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風光;充分地傳達了北京勞動人民的悲涼和辛酸,向往和希望……這一點,在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中,是獨樹一幟的。”[1]老舍運用方言寫作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他所使用的北京話是“普通話”的基礎。盡管如此,相對于普通話而言,北京話也還是一種方言。老舍正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形成了自己既通俗又淺白、既樸素又活潑的文學語言風格。此外,方言不僅是一種地域文化最外在的語言標記,同時又蘊涵著最底層的文化。因此,“方言化”不僅是老舍文學語言突出的特點,更是我們進入老舍文學世界的特殊路徑。
一、平民精神與對方言表達的自覺追求
老舍出生于北京最底層的平民家庭,“童年習凍餓,壯歲飽酸辛”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他從小就對貧苦市民的不幸境遇有深刻了解。這使得老舍與平民之間具有一種深刻的內在的精神紐帶。他熟悉他們,同情他們,他從來不是高高在上俯瞰窮人的生活,而是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將他們視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并不強調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而是自稱“寫家”,將寫作看作是極為平常的一種勞動,打拳的、賣唱的、洋車夫這些苦人們都成了他的朋友。這種生命情感的融入正是老舍選擇用北京方言來進行寫作的最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我能描寫大雜院,因為我住過大雜院。我能描寫洋車夫,因為我有許多朋友是以拉車為生的,我知道他們怎么活著,所以會寫出他們的語言。”“從生活中找語言,語言就有了根,從字面上找語言,語言就成了點綴,不能一針見血地說到根上。話跟生活是分不開的。”[2]長期浸淫在民間文化氛圍中,又使老舍形成了平民的審美心理,他明確將文學語言的“俗”作為自己的自覺追求,他說:“說我的文字缺乏書生氣,太俗,太貧,近于車夫走卒的俗鄙,我一點也不以此為恥!”[3]在此基礎上,他強調“言文一致”,提倡一種方言化、口語化的寫作:“我愿在紙上寫的和從口中說的差不多”“而不是去找些漂亮文雅的字來漆飾”。[4]
如果從語言文化學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為老舍對“方言”的自覺追求找到更為有力的闡釋。現代語言學把人的存在本質歸結為語言自身,人的認識、思維都不能脫離語言而獨立存在,因此,“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每種語言都包含著屬于某個人類群體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體系”。[5]在這樣的理論觀照下,方言與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得以呈現:“它深刻地體現了某一地域群體的成員體察世界、表達情緒感受以及群體間進行交流的方式,沉淀著這一群體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也敏感地折射著群體成員現時的社會心態、文化觀點和生活方式的變化。”[6]對此,研究者早有過精辟的論述。趙園指出:北京方言不僅是“北京文化中最易于感知的那一部分”,更“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構成材料”,而“‘說’的藝術,其條件,其心理內容,其美感效應,應該比之別的更有利于說明北京人‘審美的人生態度’。”[7]正因如此,方言不僅是老舍對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展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是老舍自己生命的源頭,它比任何方式都更為強烈地顯示著老舍自己身上的文化印記。
二、“方言化”的具體表現
老舍的文學語言具有鮮明的“方言化”特色,首先體現在大量方言詞語的使用上。據統計,他在《龍須溝》里一共用了136個北京方言詞,“諸如晌午、沒轍、泡蘑菇、累贅、大脖拐、耽待、老梆子、緊自、得煙兒抽、多咱、擠兌、這不結啦、至不濟、大八板兒、王大膽、歸掇、圣明、左不是、抱腳兒、耍骨頭、納悶兒、橫是、抖漏、趕碌等等。”[8]就拿我們中、小學語文課本中常收錄的《駱駝祥子》等作品來說,里面的方言詞也俯拾皆是,例如:
“這就是咱的榜樣!到頭發慘白了的時候,誰也有一個跟頭摔死的行市!”(《駱駝祥子》)
“只要是自己的車,一天好歹也能拉個六七毛錢,可以夠嚼谷。”(《駱駝祥子》)
其中的“行市”“嚼谷”都是來自北京市民口中的土語方言,它們質樸自然、活潑生動,具有獨特的魅力。“兒話韻”是北京話里的一個重要語音特征,它在老舍作品中的出現頻率非常高,也充分反映出老舍文學語言的口語化、方言化特色。例如《駱駝祥子》中出現的“眼兒熱”“傻大個兒”“今兒個”“大子兒”“拉晚兒”等等,它們帶著輕松隨意的語氣,透出活生生的北京口語氣息,使人讀來倍感親切。而“著”“了”等助詞、“呦”“嘿”“吧”“嘔”等感嘆詞的使用,更呈現出了人物說話時多種多樣的語氣和口吻,流露出北京話輕松俏皮的獨特韻味。
其次是在成語、諺語、慣用語、歇后語等熟語的使用上。熟語是民間生活經驗的總結和大眾智慧的結晶,它不僅簡潔活潑、通俗易懂,更富含哲理,增添了語言的形象感。例如:
“修溝不是三錢兒油,倆錢兒醋的事,那得畫圖,預備材料,請工程師,一大堆事那!”(《龍須溝》)
“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別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沒你的好兒,告訴你!”(《駱駝祥子》)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藝兒,別看傻大黑粗的,韃子拔煙袋,不傻假充傻!”(《駱駝祥子》)
最后是在句式的使用上,老舍將大量的具有北京地域特點的方言句式帶入作品之中。這方面已有學者進行過專門研究。方言句式在老舍小說的人物對話中體現得最為充分,但在他的散文中,我們依然可以尋找到明顯的例證。我們就以老舍的名篇《濟南的冬天》為例,看看老舍如何將方言的句式融入寫作之中。
“那點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點粉色。”
北京口語中常見的一個語法現象就是“在雙音節的復合詞或成語中插入一個或幾個詞,使之成為一個短語。”[9]在雙音節復合詞中間插入“了”,表示動作或變化已經完成。如“害了怕”“及了格”等等。“害了羞”就是典型的北京口語的用法。
插入語也是北京口語中經常使用的語法現象,例如“您瞧”“我說”等等,它們的使用不僅使句子在語義的轉接上自然得當,也會給讀者帶來平易親和的感受。在《濟南的冬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如:
“真的,濟南的人們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
“看吧,山上的矮松越發的青黑,樹尖上頂著一髻兒白花,好像日本看護婦。”
老舍格外注重語言的“聲音形象”,這也是“方言化”特色的體現。北京方言是依賴于“腔調”的語言,尤其是旗人講究說話的藝術,在“嘣響溜脆”“甜亮脆生”的語音腔調中傳遞出“不纏綿粘膩,不柔靡”[7]的北京文化氣質。老舍在談到自己的創作經驗時,始終把“能讀”作為一個重要的標準。他說:“我們寫的白話文,往往不能瑯瑯上口,這是個缺點。”他主張挖掘語言的“聲音”潛力,讓它既有意思,又有響聲,還有光彩,這不能不說是從北京方言中汲取的養分。
以上這幾個方面,充分地體現出老舍在文學語言“方言化”上的大膽追求與探索,這使他的作品語言充滿了生命力,在新鮮活潑中透著樸實醇厚,為讀者展現出一個具有北京情韻的語言藝術世界。
三、語言觀念變化中的方言選擇
老舍重視文學語言的口語化、方言化,但與此同時,他又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不斷對“方言化”進行反思。正是這種理論的自覺性,使他的文學語言逐步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在老舍文學創作的最初階段,就已經在語言上顯露出明顯的“京腔”,如《老張的哲學》《趙子曰》等作品。但卻在信手拈來中少了節制與篩選,不可避免地落入油腔滑調。到了《小坡的生日》,老舍逐漸形成了自己“淺明簡確”的白話語言觀,《離婚》《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等一系列作品都顯示出他對方言土語的從容調動。他努力往“細”里寫,在方言的使用上精雕細琢,并非完全趨附與投合大眾的審美趣味;他強調語言的淺近明白,極少使用那些難懂的方言和拗口的俚語。老舍說:“白話本身并不都是金子,作家應該在大白話中找出金子來,把白話精選提煉成金子,作家的任務不是作白話的記錄員,而是精打細算地寫出白話文藝。”[10]他的方言寫作,正是在對“俗”與“白”的追求中,呈現出語言的審美性和藝術性,這正是老舍小說雅俗共賞的原因所在。
上世紀50年代,在全國推廣普通話、強調漢語規范化的大潮下,老舍的語言觀念也發生了調整,他對《龍須溝》中因大量方言土語的運用而造成的演出限制進行了反思:“我們應該讓語言規范化,少用方言土語。只有這句土語的確是普通話里沒有的,又有表現力的,可以用一些,不一定完全不用。”[11]作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深刻意識到推廣普通話的時代任務,并自覺將其化為行動,他說:“我以后寫東西必定盡量用普通話,不亂用土語方言,以我的作品配合這個重大的政治任務”。[12]而這其中,無疑也顯示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語言共同體的“普通話”對于方言土語的規范。《龍須溝》之后的《西望長安》《青年突擊隊》等劇作,雖然緊貼時代,在語言上“盡力避免用土話,幾乎都是普通話”,[11]但卻不再是老舍最為熟悉的關于老北京的城與人的生活,最具老舍特色的那種語言風格也無處可覓。直至《茶館》《正紅旗下》,我們才在老舍式的主題中又重新感受到京腔京韻的巨大魅力。
從晚清的白話文運動開始,以“言文一致”為目標的書寫語言的通俗化就成為現代漢語變革的重要訴求之一。“五四”白話文運動徹底打破了文言的束縛,開辟了白話文學的新紀元,方言土語作為民間語言資源也被納入到白話語言體系中,但此時的白話文學剛剛起步,歐化調突出、學生腔泛濫。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興起使得“大眾化”成為文學語言的明確要求,但是卻停留于形式的探討,并沒有有力的文學實踐。老舍的白話語言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形成的,其文學語言“方言化”的獨特意義和價值也從中凸顯。老舍是真正實現了文學語言“大眾化”的作家,他筆下的方言浸潤著文化的底蘊,與個人生命體驗緊緊相連,他堅持對“方言”的藝術創造,用心“燒”出了白話的“原味兒”,也展現出現代漢語書寫的藝術魅力。老舍對于文學語言中方言的吸納、使用和思考,永遠是現代文學發展中值得珍視的寶藏。
[1]冰心.懷念老舍先生[J].人民畫報,1978,(10).
[2]老舍.我怎樣學習語言[A].老舍全集(第 16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3]老舍.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A].老舍全集(第 16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4]老舍.我的“話”[A].老舍全集(第 6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5]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汪東如.漢語方言修辭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7]趙園.北京:城與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舒乙.老舍小說語言發展的六個階段[J].語文建設,1994,(5).
[9]馬爾華.《離婚》中北京口語的運用[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2,(12).
[10]老舍.怎樣寫通俗文藝[A].老舍論創作[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11]老舍.記者的語言修養[A].寫與讀[C].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2]老舍.擁護文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N].北京日報,195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