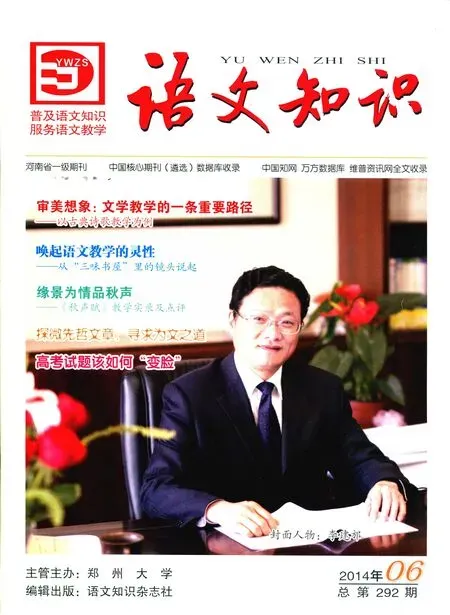魯迅小說教學內容的確定——以《再讀〈祝福〉 走近“我”》為例
◆西安交通大學蘇州附屬中學 陳興才
魯迅的小說在中學教材各版本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內容,與過去相比,數量上有了一些調整,但其經典選文的地位并未改變。文本未變,教學上卻不可能不變,無論是作品解讀,還是課程觀引領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都應發生變化。所以跟所有經典一樣,魯迅的小說必定面臨一個再讀和新教的問題。以《祝福》為例,它是一篇經典選文,各類教材多年來都不可或缺。老課新教,表面上看好像是教法上的出新,其實,“新教”首先應該是教學內容的選擇和確定,然后才是課堂教學的實施。那么,怎樣看待和把握其教學內容呢?試以李倩老師把切入點定為“再讀《祝福》走近‘我’”這樣的設計里包含的教學內容的選擇與確定為例,從三個方面評價。
一、接受美學為教學內容的重新確定提供必然性
從接受美學角度出發,文本、作品、經典作品是三個不同概念。三者雖然都是以文字為符號,但卻有著不同的符號意義。作品,比如一部小說問世了,它是由文本作為形式的,它的文本可以固化,但接受美學認為文本不等于作品,作家完成的文本是一個多層面的未完成的圖式結構,有著不確定性。文學作品的意義并不是在作者完成文本時就已產生,而是在閱讀過程中由讀者完成的,讀者通過自己的審美經驗和想象去填充和改造文本,進行新的創造,這是文本與作品的區別。再升一個層次,經典作品又不同于普通作品,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因為它是一個更加開放的系統,它的價值不是由作家、文本自己決定的,讀者的閱讀理解以及多時代多種群體對它的闡釋、研究都會進入經典的語義場,經典的內涵和外延都會不斷地豐富與擴大,而這后加進去的東西就成為經典的有機組成部分,就像《紅樓夢》,后人的三百年研究解讀,不管正確與否、褒貶如何、觀點如何,這些東西本身都成了《紅樓夢》作為經典的有機組成部分。同理,經典作品的教學同樣具有這個屬性,它是以師生間、生生間、人與文本間、新舊觀點間在課堂共生的方式,來進行接受美學上所說的解讀賞析。它也是一個開放系統,這個系統比前面所說的經典作品系統的開放性還要大,它要基于學情。學情與其他動態因素相比,它更活躍和豐富。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經典作品的教學不能說它是老作品,就再也沒有什么可新教的了。事實上,它的經典屬性恰恰為我們提供了再讀、再教的可能性。這是討論李倩老師這一節課的前提,我想這也是她設計這一節課的前提。所以我們看到了她的教學設想基于再讀和再教,看到了她的這一節是與過去所看到的切入點完全不同的閱讀指導課。在課上,李老師與學生探討出來的對于魯四的“假人”定性而不是過去習慣上說的“劊子手”“衛道士”形象,對于“我”的“真人”稱呼也不是簡單的“新一代知識分子” 的說法,以及沒有把魯四作為剝削階級代表與其他人如柳媽、長工等分開對待,而是作為群體無意識中的一員,都體現了師生在課堂上對經典的一種生成性解讀,相信這也會使經典作品、經典作品教學的開放系統更加豐富。
二、魯迅研究的價值取向變化促使教學內容的調整
長期以來,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與精神性格,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需求,一直進行著微妙調整和企圖權威化解釋。魯迅的創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核心文化資源之一,他對傳統文化的顛覆、對社會事件的尖銳批判,形成了一種新語義力場。魯迅以非凡的語言才能所構建的文學作品令人難忘,成為新派知識青年追求的精神食糧,而魯迅本人也變成不滿于時代的青年們的精神導師。他的尖銳思想和犀利語言,本是切開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那層臃腫脂肪的鋒利手術刀,但他的作品卻被作出了最適合某種需要的解讀,如《狂人日記》譴責舊社會是“吃人的”;《祝福》控訴“萬惡舊社會”對普通勞動群眾的壓迫;《阿Q正傳》《墳》等揭露中國文化的冷漠的“國民性”及“看客”文化;《傷逝》描寫普通知識分子的精神頹唐和肉體的衰敗。這些,都被定位成了革命文學的典型樣式。而《在酒樓上》《孤獨者》這樣的深刻反思性作品中,通過“呂緯甫”“魏連殳”的塑造,魯迅表達出了對社會革命、對革命者、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懷疑,這些作品則不被提及。魯迅的《故事新編》是現代文學中的杰作,但因為作品充滿懷疑精神和游戲精神,充滿對既定社會秩序的消解力,而無法在閱讀理解上加以有效引導和管理,而被語文教材指導者和編寫者有意地排斥。失去了懷疑精神的魯迅、失去了對現實決不妥協精神的魯迅,成了一幅定型的偉人畫像。而教學中,特別是從階級斗爭意識出發,把批判與揭露封建制度與封建禮教、反動黑暗勢力迫害人民作為最重大的主題,像一個大蓋子,一度影響了對經典作品閱讀教學的動態生成。很多時候,師生只是在課堂上去印證這一個先行的主題,它一旦成為一個結論和固定模式時,教學所應具有的一些要義就受到了破壞。在這點上,我們還可以考察教材中魯迅作品的數量變化,曾經在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文學史作家座次表上,政治道德考量是第一位的,文學性考量退居二、三線,并且有個森嚴的等級,比如魯、郭、茅、巴、老、曹,如魯迅可以占三章,老舍占一章,沈從文、蕭紅等可只占一節兩節,張愛玲等根本就不能存在。與之相應的是,當這樣的等級出現時,作品的解讀也就有了一個最重要的基點,服從于政治道德,魯迅的形象也成為一種“樣板”。所以過去中學課本出現魯迅的作品時,從選文到教學,反封建迫害基本占據了最大的解讀話語場。顯然,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問題時,選擇性失明或戴帽子式解讀,都阻礙了經典作品不斷豐富的過程。
魯迅的精神其實有兩大方面:一是批判、斗爭;二是反思、懷疑。前者一直作為魯迅作品的解讀主話語呈現,后者則極少或是不痛不癢地作為副產品出現。李倩老師的課著落點在“我”上,這一個“我”是當時的新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他是新人,是真人,完全不同于魯四,但他又軟弱、逃避,又會自責反思,這正體現魯迅作為寶貴資源文化的核心要義——懷疑與反思。從這點看,李倩老師的課的選點具有學術性、深刻性和研究性,這是一個優秀語文教師應該具備的品質。以后魯迅作品若進入中學課本,不妨把批判揭露斗爭的價值取向朝“反思、懷疑、自責的知識分子的性格呈現和擔當”的方向作一微調,將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三、帶著課程開發的意識確定教學內容
魯迅的作品該選哪些文章,該怎么教讀,是課程意識的體現。同時,也需要教師具備獨特的眼光和能力。如《祝福》作為一個課程資源,我們開發它有三個基點:一是作品本身。《祝福》中的“我”,絕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線索人物,這個“我”與《孔乙己》中的“我”、《一件小事》中的“我”在角色的重要性上不可同日而語。《孔乙己》中的“我”主要出于線索和見證者存在,只是作為“有同情心的年輕人”這個不大的價值存在;《一件小事》中的“我”是作為反襯勞動者并自我批評的知識分子存在,只是初步顯示了反思的品格;而《祝福》中的“我”,則是一個深刻的懷疑者、反思者,懷疑作為新文化倡導者在劇烈的社會轉型期的軟弱、渺小、怯懦,這是魯迅作品中最重要的一個“我”。李倩老師這節課,以重讀作為鋪墊和臺階,把對“我”的分析作為《祝福》教學的重點,體現的正是她的課程開發意識和資源整合能力。二是學生。說小點,是為學情;說大點,是為教育目標以及培養什么樣的現代人,從這點上來說,把呈現知識分子的自責、反思、弱點與責任感作為對學生的一種浸潤,其價值一點也不小于給學生灌輸萬惡的舊社會吃人本質這個題旨。這體現了教學內容對教育本質的關照。李老師課上還提到《在酒樓上》《傷逝》《孤獨者》這幾部作品,表明了李老師對這個價值點的自覺關注和有意識關懷。三是“文本互涉”。“文本互涉”也稱“互文性”,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間的結構、故事等相互模仿、主題的相互關聯或暗合等情況。當然也包括一個文本對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這種現象,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間,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是因為:作家不可能在一部作品、甚至所有的作品中完美地塑造他心中的藝術形象,也很難完整地表現他全部的思想觀念,他必然會在潛意識里多次修補他的作品,或者說在不同的作品中多次涉及同類的人物形象,并互相補充,從而導致他的作品“文本互涉”的現象產生。因而,我們在解讀一個作家的藝術文本時,面對作者的不同文本,應保持一種整體的、比較的眼光,要在互涉文本的對照中去領悟他的作品的深刻內涵,并在相關性的尋繹中去理解其作品的整體思想。魯迅小說,作為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學系統,我們應將其視為一個共同的文本世界。基于此,在李老師的課上,我們可以看到她為學生提供了多種文本資料,如魯迅不同小說中的“我”、魯迅的詩、自傳散文作品、研究者的評論等。《祝福》作為魯迅的“共同文本中的一個”的屬性得到了體現和證明,我們讀《祝福》,不僅是在讀《祝福》,而且是在讀魯迅,這是一種教學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