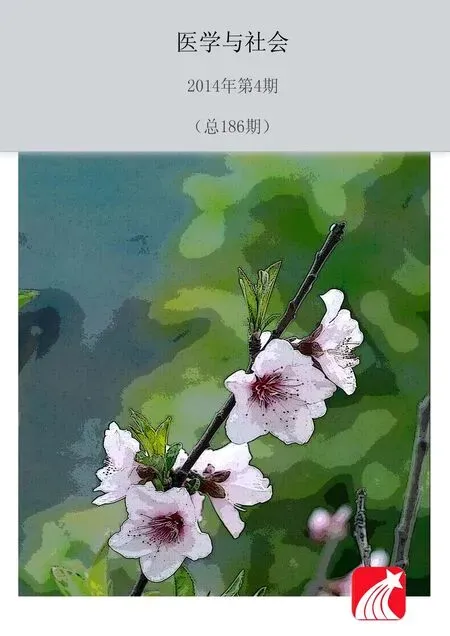廣西壯族自治區商販流動人口艾滋病風險的階層分化及其實現機制
王文卿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100081
國外研究顯示,人口流動會促進艾滋病的傳播。鑒于我國流動人口較多,其行為動力很可能成為影響我國艾滋病疫情發展的關鍵因素。由于經非法采供血傳播HIV的途徑已被有效控制[1],同時流動人口使用非法毒品的比例很低[2],因此流動人口的艾滋病風險主要與風險性行為有關。艾滋病風險性行為(HIV Sexual Risk Behaviors)指的是商業性行為和非商業性的多伴侶性行為,尤其是指在上述性行為過程中沒有使用安全套的無保護性行為。研究顯示,相對于非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從事風險性行為的可能性更高[3]。為了降低流動人口的艾滋病風險,遏制艾滋病傳播,需要深入了解推動流動人口從事風險性行為的動力機制。
有研究注意到流動人口內部的分層或分化現象[4],由于艾滋病風險與社會地位等級或階層密切相關[5],研究者不應再泛泛談論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的艾滋病風險,而應關注流動人口內部的階層分化與艾滋病風險等級之間的關系。本文將以從事經商的流動人口為例,探討階層與艾滋病風險之間是否存在關聯,以及這種關聯是如何實現的。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地點和對象
研究地點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數據顯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率在全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排在前幾位。截至2010年9月,廣西壯族自治區累計報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達6萬人,其中柳州市累計報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超過1萬人,在區內位列首位。
1.2 資料搜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來搜集資料,訪談在相對封閉的空間內進行。在訪談的開始階段,研究者特別強調保密原則,消除被訪者的顧慮,并在此基礎上征求他們的知情同意。在被訪者許可的情況下,研究者對訪談進行了錄音。如果被訪者不同意錄音,研究者則進行筆記,并在訪談結束后盡快地進行補充。由于話題的敏感性,大部分訪談采用了筆記方式。問題涉及商販的流動經歷、社會經濟背景、家庭生活、社會交往、休閑娛樂、商業性行為和非商業性的多伴侶性行為、艾滋病風險認知以及安全套使用情況等。在資料分析中,本文借鑒了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思路,通過反復細致的閱讀所有轉錄的資料來識別關鍵的編碼類別和主題。
2 結果
2.1 風險性行為的階層差異
在60名男性商販中,49人在30歲以上;42人為中等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5人為高等教育水平(大專或本科);52人已婚,在接受訪談時與妻子共同居住的有46人;超過一半的商販(32人)來自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其他地方,其他人分別來自浙江省、湖南省和湖北省;57人為農村戶籍,3人來自柳州之外的其他城市。
商販內部存在明顯的階層分化,30名商販在市場中通過擺攤的方式銷售蔬菜、水果、肉類或其他食品,可稱其為攤販。另外30人在市場中通過開店的方式銷售服裝(13人)、小商品(9人)和建材(8人),可稱其為店販。兩類商販在收入上存在明顯差別,攤販每日的凈利潤一般不超過100元,店販每日的凈利潤不低于300元。兩類群體在閑暇時間長短及閑暇生活方式上也存在明顯區別。
15名商販承認曾從事過風險性行為,其中10人曾與女性性工作者發生過商業性行為,4人曾有過臨時性伴侶(即僅發生一次或性關系持續時間很短的性伴侶),7人曾有非婚、非商業性的長期性伴侶。15名商販均為店販(由于一些商販有過多種類型的風險性行為,所以分類匯總后的人數不等于15)。這表明,商販的階層地位與其艾滋病風險密切關聯。但是,這種關聯不能完全歸結為經濟實力的差異,因為并非所有店販都從事風險性行為,所以還需要提供其他解釋。
應酬在階層與風險性行為的關聯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方面,應酬在特定情境下會卷入商業性行為或者為發展情人關系提供機會。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需要,一些店販更多地參與應酬,因而擁有更多參與風險性行為的機會。
2.2 應酬與風險性行為的關聯
應酬是旨在建立或維持特定的社會關系的活動,在我國應酬體現為宴請或送禮。研究顯示,與商業性行為相關的應酬主要圍繞宴請而展開,就商販而言這類應酬又包括兩種類型:生意伙伴之間的應酬和朋友之間的應酬。其中,朋友應酬不僅與商業性行為有關,也與非商業性行為有關。
2.1.1 生意應酬與商業性行為。柳州市經濟比較發達,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重要工業城市和商品集散地,周邊地區的商販是在柳州市區的市場上批發商品,然后以更高的價格進行零售或批發,從中賺取差價。因此,柳州市區的店販有兩類客戶群體:①為自身消費而進行零星購買的消費者;②為自己的經營活動而進行批量購買的商販。盡管店販只靠零售業務也能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如果他們想獲得更多的利潤,就必須擴大批發業務所占的比重。為了做到這一點,部分店販試圖通過應酬來強化與經營類客戶的關系。他們把這些客戶分成兩類。①對于進貨量較少的客戶,他們只須設宴招待。②對于進貨量較大的客戶,店販除了宴請他們之外,還會邀請他們參加休閑娛樂活動,這其中包括性服務。一名56歲的服裝店商販表示,做生意的商人去娛樂場所不可避免,唱歌或桑拿后叫個小姐的情況很普遍。
2.2.2 朋友應酬與商業性行為。店販和朋友之間的應酬在某些情況下也與商業性行為有關,店販一般從早上9、10點鐘開始營業,下午5、6點鐘關門,因此有較多的閑暇時間進行社會交往。關系要好的老鄉、朋友之間會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行聚會。在只有男性參與的應酬中,商業性行為有時構成了娛樂活動的內容之一。一名50歲的小商品商販表示,偶爾會約朋友打牌,大家把贏來的錢湊一起,吃飯喝酒之后就會去桑拿,花幾千元錢,美女一大排任人挑選。
上個世紀60至80年代產生后現代女權主義,它的產生應該和兩個因素相關。其中一個因素是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將男女對立起來的女權思想,后現代女權主義導致了不可計數的家庭破裂,還有出現更多的單身母親、問題兒童,以及愛滋病盛行,然后社會的人們在思考:社會是否值得去為“性”的解放和女權主義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另一個因素是80年代后,女性在政府、企業、學校和媒體的領導地位的人數不斷加速上升,于是,后現代女權主義應運而生。
對于經常一起參與應酬的朋友來說,尋求性服務似乎成了慣例,相互間心照不宣。但是,剛剛進入一個朋友圈子的新成員,由于不熟悉圈中的應酬文化,在面對他人的提議時會表現出遲疑,而這則會激活其他成員的合理化辯護。由此而形成的群體壓力促使一些新成員就范。一名28歲的服裝店商販表示,有時吃過飯后朋友會去消遣一下,我會猶豫,但經不起朋友的忽悠還是會去。
2.2.3 朋友應酬與非商業性行為。應酬不僅與商業性行為有關,也與非商業性行為有關,這是此前的研究所沒有注意到的。在一些應酬中,參加者除了店販及其男性老鄉、好友外,還有一些女性。這些女性不是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也不是性工作者,而是參與應酬的一些柳州市當地男性的同學、同事或其他女性朋友。這說明,外來商販的社會網絡已經越出老鄉的圈子,通過當地男性店販結識了當地女性。某些店販會利用這些機會來發展潛在的(非婚、非商業性的)性伴侶。
綜上所述,4名店販有過臨時性伴侶,7名店販有過情人(非婚、非商業性的長期性伴侶)。他們均是在吃飯喝酒的情況下結識這些女性的。盡管其中某些人對網絡很熟悉,也會使用網絡聊天工具,但并不試圖通過網絡來尋找性伴侶。在他們看來,通過上網接觸的都是陌生人沒法信賴;而在飯桌上認識的則是朋友的朋友比較令人放心。在個別情況下,店販在應酬當晚便與剛結識的女性發生了性行為。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雙方需要后續的聯系和互動才能建立必要的信任。
2.3 應酬機會的階層差異
相對于店販,攤販參與應酬的機會非常少,兩個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他們的參與。
首先是經濟實力和閑暇時間。對攤販來說,應酬既浪費時間又浪費金錢。攤販一般早上五、六點鐘起床,趕到批發市場進貨,然后迎接早市;晚上八、九點鐘結束營業,然后回家吃晚飯,看一會兒電視,10點鐘左右睡覺。如果攤販參與應酬,他們的生意會受影響。尤其是應酬活動安排在晚飯時間下午六、七點鐘,對于經營食品生意為主的攤販來說,這個時段恰好是生意的晚高峰,是人們購買食品準備晚飯的時段。因此,即使是之前朋友很多、喜歡交往的男性,在做了攤販之后也傾向于避免應酬活動。
其次是經營模式。店販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批發業務,而一些店販為了拓展批發業務,努力通過應酬來拉攏客戶。與之不同,攤販基本上都是零售商。他們從柳州市的批發市場上批量購買各類食品,然后零售給個體消費者。盡管有些攤販(如賣魚或賣肉的攤販)有時也會為餐館小批量供貨,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因為餐館為了降低成本也是從批發市場集中采購,只是在一些應急的情況下才在零售攤販那里購買原料。因此,攤販沒有穩定的批量購買者,他們不會像店販那樣為了加強與客戶的關系而進行應酬。對他們來說,那種做法是得不償失的。
3 討論
3.1 健康風險的階層分化
社會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關聯是社會醫學、公共衛生和醫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從二戰時期到現在所積累的大量研究文獻表明,在社會階層和健康之間始終存在正相關關系,人們的社會階層地位越高,其健康狀況越好。換言之,人們的社會階層地位越高,其面臨的健康風險越低。盡管具體的經驗研究表明,社會階層與健康風險之間的關聯還存在很多復雜狀況,但作為一個總體性的結論,社會階層與健康風險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仍是被廣為接受的。
有學者在全面回顧艾滋病研究的相關文獻后得出結論:社會階層與健康風險的一般關聯模式同樣適用于艾滋病領域,即人們的社會階層地位越高,其艾滋病風險越低;艾滋病風險較高的群體主要來自貧困的階層或地區[5]。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種概括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無疑忽視了一些復雜的具體狀況。
例如,本研究表明在流動人口這個亞群體中,就艾滋病的性傳播風險而言,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店販群體因為其更多地參與商業性行為或非商業性的多伴侶性行為而面臨更高的風險。該發現有悖于上面陳述的一般模式,但卻并非特例或偶然因素使然。一個基于中國普通人口的隨機抽樣調查發現,收入更高的男性更可能從事無保護的商業性行為,而與收入更高的男性存在性關系的女性也更容易感染性傳播疾病[6]。這表明,至少就艾滋病的性傳播風險而言,社會經濟地位越高,面臨的風險越高;并且,這種模式并不局限于特定人群(如流動人口)。由于商業性行為和非商業性的多伴侶性行為要求當事人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所以在艾滋病越來越多地通過性途徑傳播的背景下,艾滋病越來越趨近一種富貴病。
當然,由于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具有更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因此在收入較高的男性群體中,性病和艾滋病風險較高的男性更可能是經濟上比較成功但教育水平和自我保護意識較低的男性。本文所考察的店販恰好符合這一特征,將來更可能遭遇艾滋病的人群也應該主要是具備類似社會特征的人群。
3.2 應酬在健康風險階層分化中的作用
應酬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維持社會關系,并借助這些關系提高自身的收益。在中國,應酬主要圍繞吃喝和娛樂這兩類活動而展開,這兩類活動分別與不同的健康風險相連。
男性應酬中的娛樂活動常常圍繞女性提供的服務而展開,包括性服務。事實上,商業性行為經常甚至主要發生在應酬的背景下,本研究中的店販就是這種情況。另一項研究考察了四川省曾有過商業性行為的562名男性,發現67.8%的男性經常是在應酬的背景下與朋友一起尋求性服務[7]。應酬與商業性行為的關聯使得其與艾滋病風險聯系起來。同時,由于參與應酬的機會與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相關,這進而使得應酬在艾滋病風險的階層分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其他健康風險的階層分化中,應酬同樣可能扮演重要角色。應酬中常常涉及飲酒和吸煙,應酬的氛圍能制造很大的規范壓力,常常使得拒絕飲酒難以實現。拒絕吸煙面臨的壓力相對小一些,但是在一個煙霧繚繞的環境中,即使個人不吸煙,也難免二手煙的危害。另外,應酬背景下的飲食結構也不甚合理。因此,經常參與應酬的人罹患各種慢性疾病的風險便會顯著增加[8]。同樣,由于應酬要求人們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所以與應酬相關的各種慢性病風險也是階層化的,并且與階層地位成正相關關系。
3.3 對健康教育工作的啟示
通常人們傾向于把艾滋病風險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聯系在一起,從而忽視了那些擁有較高社會地位但卻面臨更大風險的人群[9]。今后的艾滋病工作應該克服這種局限,在重點人群的選擇上,由于應酬與風險性行為具有密切關聯,將來的艾滋病預防干預工作應該對經常參與應酬活動的男性給予特別關注。
同時,由于應酬能夠增加人們罹患慢性病的風險,將來的相關健康教育工作也應該關注那些經常參與應酬的人群,并思考如何削弱甚至切斷應酬與慢性病風險的關聯。
不過,由于導致艾滋病或慢性病風險增加的活動嵌入在應酬實踐中,而應酬實踐則深深植根于中國人建構和維持社會關系的文化傳統之中,有效地健康教育工作不能僅僅針對具體行為(如飲酒、吸煙、商業性行為等),而必須回應和改造將這些行為裹挾在一起的整體性的文化實踐。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而需要持久和富有創造性的努力。
[1]汪寧.艾滋病在中國和全球的流行現狀及面臨的挑戰[J].科技導報,2005,23(7):4-8.
[2]Wong F,He N, Huang Z, et al.Migration and Illicit Drug Use Among Two Types of Male Migrants in Shanghai China[J].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2010,42 (1):1-9.
[3]Wang W, Wei C, Buchholz M E,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s fo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a National Sample of Migrants versus Non-Migrant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D & AIDS,2010(21):410-415.
[4]唐燦,馮小雙.“河南村”流動農民的分化[J].社會學研究,2000(4):72-85.
[5]景軍.泰坦尼克定律[J].社會學研究,2006(6):123-150.
[6]Parish WL, Laumann EO, Cohen MS, et al. Population-based studyof chlamydial infection in China[J].JAMA, 2003,289(10):1265-1273.
[7]Yang C, Latkin C, Luan R, et al., Peer norms and consistent condom use with female sex workers among male cli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0,71(4):832-839.
[8]Uretsky E. The risk of success: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chronicdisease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urban Chinesemen[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011,26(2):212-219.
[9]Uretsky E,'Mobile men with money': the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o-economic context of 'high-risk' behaviour among wealthy businessme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urban China[J].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2008,10(8):80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