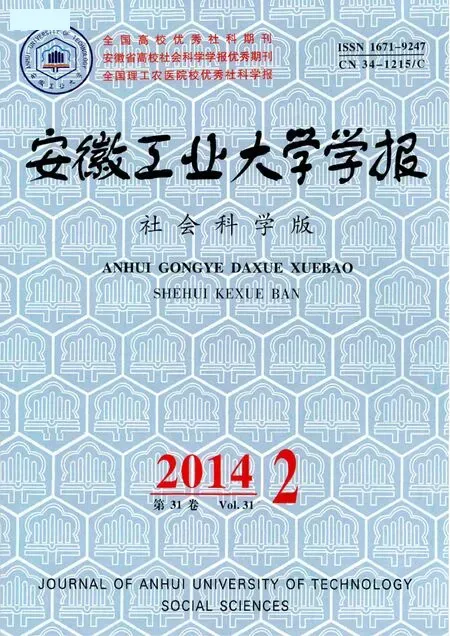農民工臨時社區的提出與創建
蔡 弘,王云飛,溫書劍
(安徽大學 社會與政治學院,安徽 合肥2306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鄉關系由原先相互分割、相互隔絕的剛性二元結構逐漸轉變成為允許城鄉間部分流動的剛性、彈性兼有的二元結構。在這樣的城鄉結構下,城市因具有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收入水平、較好的社會服務、較優的教育資源等拉力因素,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隨著城鄉發展速度漸漸拉開,城鄉之間的“剪刀差”越來越明顯,農村社區居民向城市轉移的意愿也愈加強烈,流動速率開始逐漸加快,出現了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特有的民工潮現象,而農民工的稱謂伴隨民工潮也開始被廣泛接受。結合時代背景,現在普遍認為農民工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從農民工的數量變化來看,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 261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1]從農民工內部發展來看,他們已由第一代農民工、第二代農民工向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更替,但無論是哪代農民工,他們的城市融入狀況都不容樂觀。如何探索出新的農民工城市融入之路,始終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一、臨時社區的提出
“Community”首次提出是在1887年出版的CommunityandSociety中,20世紀30年代初以費孝通為代表的燕京大學的學生將滕尼斯首創的“Community”譯為“社區”,由此,社區的概念開始廣泛傳播并發展。據社會學家楊慶堃在1981年的統計,社區的定義已經多達140余種,但從中很難找到一個為大多數社會學家所認同的概念。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帕克將社區的三個基本要素鮮明指出——有一群按地域組織起來的人群;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們所生息的那塊土地上;社區的每個人的生活都在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之中。也就是說,人口、地域和互動成為社區成立的核心因素。
(一)農民工城市社區的三種類型
目前,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居住的社區類型可以分為三種——工棚、專門聚居地和散居所在城市的小區,若從與城市社區的距離視角出發,與三種社區相對應的是沒有進入社區類型、“準社區”類型和進入城市社區類型。[2]第一類居住于工棚,主要是進入城市從事基建工程的農民工。這一類農民工廣泛存在于我國大多數城市,他們的城市融入除了地理意義上的靠近,在心理和文化認同上始終是一群陌生人。第二類居住于以業緣和地緣為基礎形成的農民工聚居地,典型模式就是浙江村、河南村以及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工聚集地。這種“準社區”的存在會吸引新來的農民工前來安家,也往往成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起點。但是,“準社區”也成為城市中社會治安問題的多發地,如“浙江村”中治安不良、幫派橫行等問題出現頻次相當高。第三類散居于城市社區,包括在城市居住了一定年限、有穩定住所、有穩定工作和收益的農民工。由于他們相對單獨的工作以及居住,“外來戶”的形象尤為明顯,即使他們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但城市歸屬感依舊不強,社會認同并未改變,社會資本也沒有展開。
(二)農民工的臨時社區
工棚雖然屬于未進入社區類型,但較之其他農民工聚居類型有諸多特殊之處,也因此將其視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典型。從刻板印象來看,社會對農民工的最初印象就來自基建工地;從工棚與其他農民工聚居地比較來看,數量最為龐大,形式最為簡單,環境最為惡劣;從社會互動來看,生活在工棚內的農民工除了簡單的聊天和休息時間的打牌娛樂,并未涉及深層次的互動;從農民工利益保障來看,這部分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最難伸張,權益保障也常被忽視,討薪事件的主角往往都是在工地工作的農民工。臨時社區的概念就來自于工棚,在借鑒現實中工棚存在的狀態下,這里認為臨時社區是以業緣關系為紐帶而在一塊相對穩定的地域空間內進行自我娛樂、自我提升、自我管理的農民工的集合,在社區內擁有統一規范、基本服務和維權組織。
人口、地域和互動是傳統社區構成的三大要件,臨時社區也包含這些要素。從人口維度考察,臨時社區表現出人口數量少,構成同質性強及人口密度大的特質。臨時社區的人口數量是由工程規模所決定的,但與傳統的成熟社區相比,臨時社區中農民工數量還相當少。傳統社區的居民異質性強,不同職業、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可能都居住于一個小區,社會分層中處于不同層級的人能夠在一個小區中充分體現。而臨時社區中的居民都是為了追求勞動報酬而聚集在一起的農民工,從橫向來看都是基建工人,只有工種的區別,在縱向上更沒有地位高低之分。人口密度是指單位面積上人口的數量,雖然臨時社區的居民數量不及傳統社區,但是因為地域面積小,人口數與地域面積的比值就大,因此表現出人口數少但是密度大的分布特征。從地域維度來看,臨時社區表現出臨時性和流動性特征。傳統社區存在于特定的空間,雖然依照所選擇的研究群體不同,社區的空間范圍就不同,但是傳統意義上的社區以社區圍墻為界,還是擁有明確的地域范圍的。而臨時社區以工地上一塊空地為地域,在劃定的地域內搭建臨時房,這就決定了存在時間與存在地域上具有不確定性:在存在時間上,工程時間長短決定臨時社區的壽命;在存在地域上,它是隨著建筑工地的流動而流動。從社會互動來看,因為臨時社區的制度結構簡單,社區內部聯系單純,其互動深度自然不如傳統社區。一個成熟的傳統社區,包含物業、商業街、黨群、家庭等組織,在日常生活中社區內的居民會直接或者接觸這些組織,從而加深了社區內的互動。但是臨時社區中只包含了簡單的便民服務和基本社區規范,連家庭這一基本要素有時也難以達到,社區內的互動自然不如傳統社區。同時,在傳統社區中,由于個人長時間生活于相對穩定的親屬、鄰里及社區組織當中,容易對社區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而臨時社區僅由農民工構成,社區成員流動性強,缺少穩定的人際聯系,因此不會形成與傳統社區一樣強烈的社區歸屬感。
二、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約性因素
農民工城市融入艱難并非單一因素的作用,是農民工自身主觀意愿與城市客觀要件是否允許之間的博弈,不同的理論模型和解釋視角都對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進行了解讀,但是歸根結底是由制度因素與非制度因素中經濟、社會和文化在起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戶籍制度做了優化,農民工向城市居民轉型又邁進了一步,享受了越來越多和城市居民一樣的保障與福利,制度因素的限制作用開始松動,而非制度因素依舊是能否成功融入的門檻。
(一)關于農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理論梳理
有學者把當前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討論總結為三種解釋范式,即現代化理論、社會網絡分析、制度主義的解釋范式。在現代化理論的解釋范式下,農民工自身素質的缺陷與自身現代化的不足被認為是導致農民工低度城市融入的主要作用機制;社會網絡分析的解釋范式傾向于從中觀上對農民工所擁有或卷入的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網絡方面進行闡述,認為農民工邊緣性的社會地位與其社會資本占有量較小有密切的關系;制度主義的解釋范式則試圖在更為宏觀的制度或結構的角度探討農民工城市融入難題的解釋機制。[3]也有學者從現代性、社會化和社會排斥角度對農民工城市融入做一番分類和梳理。現代性視角注重農民工從傳統向現代、從農村向城市、從封閉向開放轉變的過程研究,從這一視角做過嘗試的學者主要有周曉紅、李培林、江立華等。社會化視角關注農民工在經濟、社會、文化與心理四個層面的城市適應或融入,并視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種再社會化的過程,研究學者有田凱、朱力、王春光等。社會排斥與互動的視角則認為農民工融入障礙在于城市的社會排斥,以及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缺少社會互動而產生的社會隔離,學者李強、郭興華等有過相關研究。[4]之后,隨著“公民權”和“市民權”的興起,為農民工城市融入帶來了新突破。王小章借公民權的社會學研究,從承認與排斥的關系來理解公民權的實質,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和思考了農民工這個群體及其獲取公民權的進程。[5]陳映芳從“市民權”概念入手,探討城鄉遷移人員成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構機制,認為對既有戶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戶籍制度及農民工制度長期被維持的基本背景。[6]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促進城鄉發展提出的以“創新人口管理”為核心的戶籍改革新思路正是沿著“公民權”與“市民權”的理論路線。
(二)多因素共同作用加劇了融入難問題
通過梳理可以看到,因為農民工自身素質不夠,社會資本存量不足等原因,在融入過程中受到了城市社會的排斥,并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互動出現障礙,進而使他們城市融入的再社會化過程出現了偏差。除了這些,農民工在城市融入的過程中還存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三個層面的突出問題,且它們互聯、層遞——經濟層面的問題不解決就會直接導致社會層面的問題,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又會影響到文化層面。[7]
在經濟上表現為“建設吸納,社會拒入”的尷尬局面。目前我國農民工與城市的關系往往僅限于城市提供簡單的體力勞動,農民工付出勞動然后獲得相應報酬的“建設吸納”階段,但從城市社會的其他方面來看,農民工實際上還是被拒于門外,以學校準入機制為例,農民子女在城市學校中始終被視為“外地人”并要繳納借讀費,這就造成了“社會拒入”的局面。在社會生活上表現為相對剝離。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居住、生活,實際上已經承擔工人的角色;但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他們并沒有改變農民的身份,這便出現角色扮演和實際身份的相對剝離。由于差序格局的影響,農民工在生活圈選擇上會不自覺地選擇與其擁有相似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習慣的其他城市農民工,這又促成了一個亞文化群,隨著亞文化群的鞏固,更加疏遠了他們與城市的距離。文化層面上的“過客”思維表現明顯。由于農民工在進城前已經擁有相當長的農村生活經歷,農民意識和農民氣質已根深蒂固,而老家的責任田更讓農民工在心理上有一種經濟安全感,一旦在城市難以生存就回家務農的想法會被作為退路而不斷強化,進而“過客”心理就被誘發和放大,久而久之就與城市社會產生疏遠感。[8]無疑,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農民工城市融入并非是個一帆風順的局面。
(三)隨意性與規范性的矛盾不容忽視
實際上,社會環境的改變對農民工城市融入也造成了阻礙。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相比更具傳統性,農業文明的部分特征還殘存保留,農業文明中包含的隨意性和片斷性在農村社區表現明顯。反之,城市社區因為發展速度快,更加能夠體現出工業文明所包含的特征——規范性和連續性。在城市社區中,擁有更加健全的規章制度,個體生活在城市社區中為了盡量使自己看起來像一個“城里人”而需要約束自己的行為,去遵循社會的秩序。對于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而言,各種行為約束已經習以為常,并且也不覺得是一種外在制度或者規則的制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但是,對于農民工而言并不盡然。從小的農村生活讓他們已經適應了農村那種沒有具體行為規則的生活方式,也不會有人因為一些不文明的行為而指責他們,甚至懲罰他們。因此,當農村居民突然進入城市打工時,他們很難在短時間去適應城市中各種規范,他們“反規則”言行的不斷出現就會招致城市居民的排斥與反感,進而加深兩者之間的矛盾——城市居民視農民工為“外地人”,不包容和接納他們,農民工視城市為賺錢的場所,難以產生歸屬感與存在感。臨時社區的創建就是基于這種缺乏規范性的理論假設,在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選擇一個農民工最常聚居的場所,進行規范化建設,讓農民工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逐步褪去農村生活的隨意性,漸漸適應城市生活的規范性。
三、臨時社區創建模式探討
在臨時社區初步創建的過程中,要盡量使農民工臨時社區體現出一定規范性,這就需要從制度化管理、基礎設施建設、業主委員會設立和社工機構介入四個方面入手。
制度化管理是臨時社區建設的基礎。工棚建設準入門檻低,缺乏基本制度規范,僅是一個提供“鋪位”的地區,日常生活也顯得“雜亂無章”。臨時社區的建設要改善工棚的“混亂”狀態,在“政府牽頭,企業執行”的原則下設置一套完整、科學的社區管理條例。這個社區管理條例具備通用性,即無論全國哪個基建工程開工前建設農民工生活區的時候都需要遵循這個管理條例。
基礎設施建設應是臨時社區運行的基本保障。在臨時社區與傳統社區對比中可以看到,完備的基礎設施能夠增強社區群體的歸屬感。臨時社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應當摒棄工棚基礎設施建設的隨意性,但也不能追求與傳統社區相同的完備性,基本住房條件、個人衛生設施、食堂衛生環境、簡易休閑設施在臨時社區中將成為標準配置。住房是核心,臨時社區中的住房要滿足“人人有床鋪、戶戶不透風、間間有窗戶”的基本要求;個人衛生設施包括廁所、男女浴室和理發店,這是直接關系個人衛生也人人都需要的最基本的設施;食堂衛生是臨時社區中農民工的飲食保證,干凈、廉價、足量是其基本要求;休閑娛樂設施是工作外放松的需要,因為臨時社區以工棚為藍本,男性農民工占據大多數是事實,但也應該照顧到女性農民工及其部分農民工子女,因此常用健身設施是現實要求。
業主委員會的建設應確保臨時社區內農民工利益訴求的滿足。面對農民工,尤其是工地農民工的合理利益無法滿足,大部分農民工也不知道如何去訴求的現狀,臨時社區建設中應當成立以農民工自身為主體,以企業代表為補充,以解決農民工合理利益訴求為目標導向的業主委員會。不同于傳統社區居委會的日常性性質,業主委員會是非常設機構,代表人員選出后只有當遇到問題或做某項決策時才聚集一起商討具體事宜。業主委員會的建立將通暢農民工合理利益向企業反饋的渠道,二者的利益訴求能夠有條件得到協商,緩解目前農民工缺失“話語權”的局面,而這樣的“合作模式”是工棚完全不具備的。
社會工作者的介入可加強臨時社區內農民工的存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農民工不能有效融入城市,從自身原因出發可以發現很多農民工對自身身份的理解和認同實際上比較模糊,即使已經生活在城市仍然認為自己是農村人,社會工作者的介入能夠有效改善這種局面。在此過程中,可以通過與高等院校或者與專業社工機構合作,建立起一只臨時社區社會工作者隊伍,對不能適應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和對自身身份認知偏差的農民工進行小組工作或個案輔導,亦可以將整個臨時社區視為對象,定時、分階段進行社區工作,從而加強農民工的自身認同與城市歸屬感。
四、結語
臨時社區的創建試圖為農民工城市融入尋找一個新的突破口。臨時社區的創建中,規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是臨時社區創建的根本,而業主委員會可以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以及政治權益,加強其話語權,一定程度上改善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從而實現加速融入的目的。與此同時,這個融入不再是單純意義上地理位置的改變,而是在政府、企業、社工機構合力下,讓農民工切身參與到城市建設、社區創建、身份認同、文化建構之中,加速農民工向“城市建設者”身份的轉型。如今,二元制度已經松動,這無疑為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減少了制度成本,優化了整體環境,相信農民工城市融入會愈加順利。
[1]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EB/OL].[2013-05-27].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30527_402899251.htm.
[2]張利軍.農民工的社區融入和社區支持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06(6):71-75.
[3]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來農民工的市民化——對已有研究的綜述[J].人口與發展,2010(4):73-91.
[4]符平,江立華.農民工城市適應研究:局限于突破[J].調研世界,2007(6):14-17.
[5]王小章.從生存到承認:公民權視野下的農民工問題[J].社會學研究,2009(1):121-245.
[6]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J].社會學研究,2005(3):119-244.
[7]馬廣海.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J].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3):67-69.
[8]徐鶯.農民工融入城市之難的思考[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275-279.